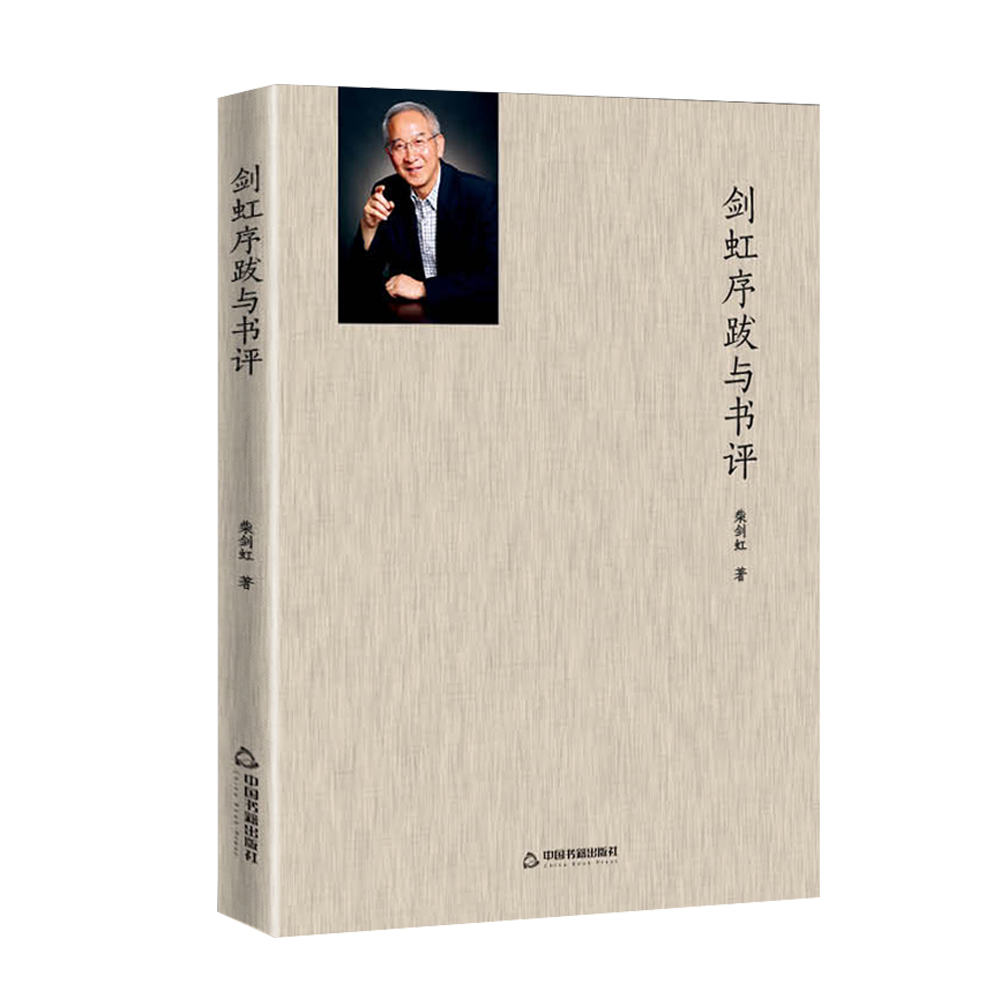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书籍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3.50
折扣购买: 剑虹序跋与书评
ISBN: 9787506890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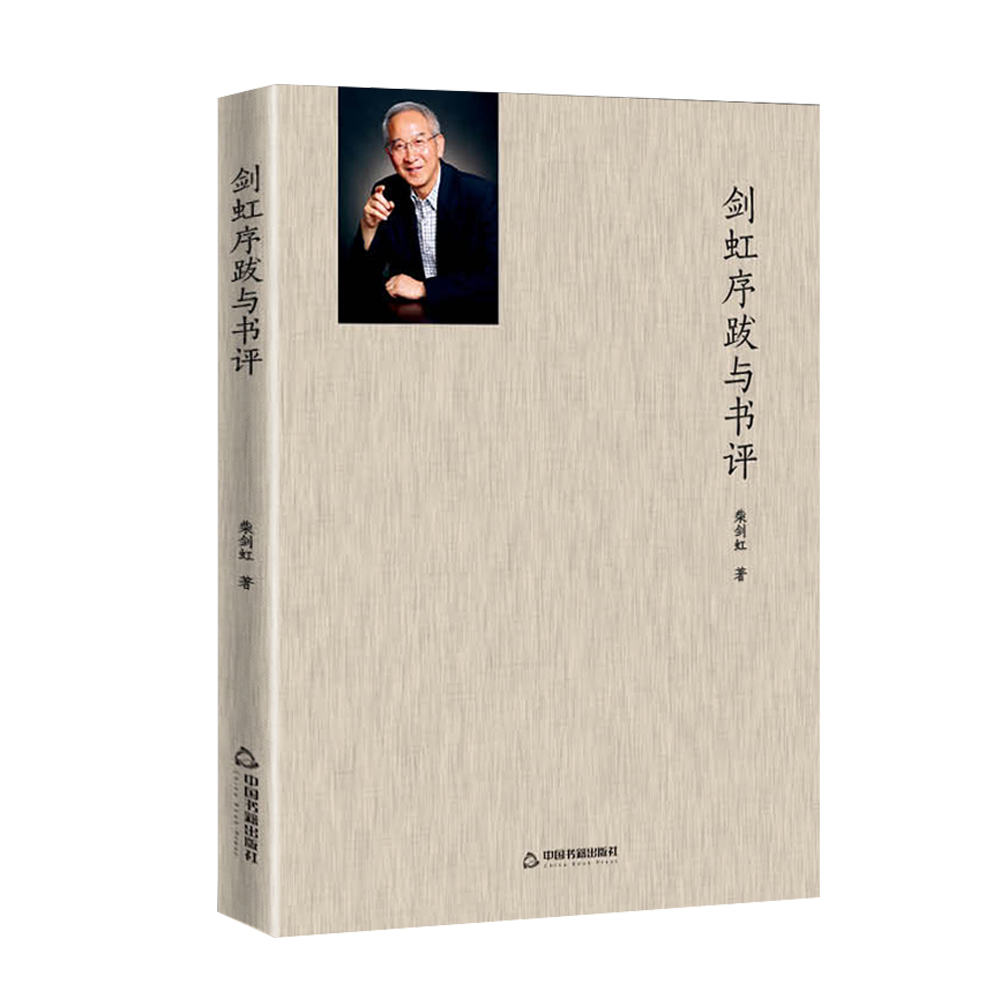
柴剑虹(1944— ) ,浙江杭州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志愿赴新疆任教十年。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华书局任编辑,1989年起先后任副编审、编审。曾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敦煌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等几十所高校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炎黄艺术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等文化机构做学术演讲,多次应邀赴法、德、俄、英、日、韩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出版有《西域文史论稿》《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敦煌学与敦煌文化》《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品书录》《高山仰止论启功》《敦煌学人和书丛谈》《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等十余种著作。担任《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研究》《汉学研究》等学术刊物编委。主编“中国历史宝库”“走近敦煌”“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等丛书。自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0世纪初,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现天日,大批珍贵写本遭劫流散海内外,“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兴起,“敦煌文学”便成了王国维、罗振玉、刘师培等几位中国学界的“预流”者为关注、用力勤、成果丰硕的领域;而后,又是在向达、王重民、孙楷第、潘重规、任二北、周绍良、饶宗颐等前辈学者和他们的后继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学者始终保持了领先地位的领域。 对“敦煌文学”做历时性研究,是颜廷亮先生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敦煌文学千年史》,即是该项目的结项成果。我个人觉得,提出这个课题,撰写一部填写研究空白的敦煌文学专史,廷亮先生是合适的一位人选。因为作为原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负责人,他早在1 9 8 2年就成功筹办了全国性的“敦煌文学座谈会”,催响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声春雷。之后,他又组织以中青年为主体的敦煌文学研究者,在周绍良先生的带领下,主编出版了《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促进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的建立,参与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起到了为敦煌文学研究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由于廷亮先生的学术专长和工作背景,他早关注“敦煌文学”的理论建构问题,几次提出“敦煌文学”的概念界定,在2 0世纪9 0年代初为《敦煌学大辞典》撰写“敦煌文学”专条时,又吸取笔者建议,将“敦煌文学”定义为:“指保存或仅存于敦煌莫高窟的,以唐、五代、宋初写卷为主的文学作品及与此相关的文学现象与理论。” 这十几年来, 他持之以恒, 仍继续不断地探究这方面的问题,整理思路,将自己的思考反映在《关于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专文与《敦煌文化》等著作中,为撰写《敦煌文学千年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虽忝列于“敦煌文学”研究队伍有年,除撰写若干敦煌文学写卷的整理研究文章之外,也考虑过如“敦煌文学”定义、某类写本文体特点,以及如何将敦煌文学作品真正置于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考察等问题,但终究还没有深入进去,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现在拜读了《敦煌文学千年史》,再一次受到启益。诚如作者在“前言”与“结束语”中所概括陈述的,此书对许多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创新之见颇多。其中给我印象深的,有以下几点: , 明确提出了对“ 敦煌文学” 应做历时千年的研究,即起自东晋十六国时期,止于元代末年,与作者对“敦煌文化”的分析同步。书中认为:“敦煌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其存在的历史和敦煌文化一样确实也长达千年。”这就将研究的视野拓宽到研究敦煌文学者通常不注意的沙州回鹘、西夏、蒙元时期的敦煌文学作品,也厘清了在敦煌地区文学创作与流传由兴盛到衰亡的脉络。书后的附录《敦煌地区本地文学作品编年简编》,既是作者下功夫首编的敦煌部分文学作品年表,也是他立论的基础与根据。尽管对“敦煌文学史”是否能框定或仅框定于“千年”,研究者肯定还会见仁见智,而有了此框定,毕竟可将过去对敦煌文学作家、作品做散兵游勇般或零篇断简式的研究引导到历时性的文学史的轨道上来,将该地区的“文学创作与传播”与“文化发展”的进程紧密结合起来探究,当然是很有见识的。 第二, 明确提出“ 敦煌文学”“ 其内部构成的主体乃是中原传统的文学”,强调“敦煌文学是以中原传统的文学为主体的一种多元性文学现象”,认为“这正是敦煌文学所以能够称得上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文学作品的“ 构成主体” 与“ 相对独立” 的关系, 涉及文学理论问题,我对此并无研究;但落实我国中古时期一个相对偏远地区常达千年的文学现象与中原文学传统的关系,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关键问题。我觉得, 作者的这个结论, 是建立在对敦煌地区大量文学作品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也符合敦煌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当然,作者又认为“从曹氏归义军晚期开始,特别是从沙州回鹘统治时期开始的几百年间,敦煌地区文学的内部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原传统的文献失去了在敦煌地区文学中的主体地位,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主体文学”,得出此结论的依据,应该也是那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少数民族用他们本民族文字撰写的。我对这些作品可以说是相当陌生,它们是否变成了那个时期敦煌文学的“构成主体”,确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新问题。在本书中,作者进而将“敦煌文学”的概念界定为:“所谓敦煌文学,指的是主要保存并主要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由以唐、五代、宋初为主要创作时代的、以敦煌地区为主要创作地区的文学作品构成的文学现象,其内部构成的主体乃是中原传统的文学。”可见这个“内部构成的主体”与作者多年来一直试图阐述的“敦煌文学”理论框架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