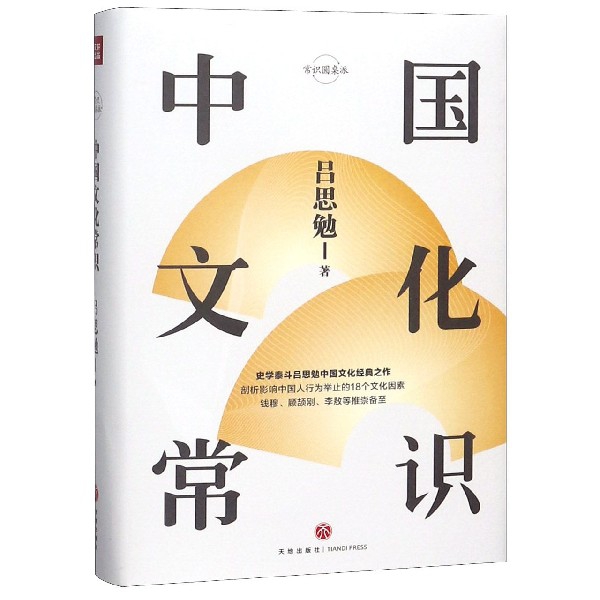
出版社: 天地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4.30
折扣购买: 中国文化常识(精)/常识圆桌派
ISBN: 9787545543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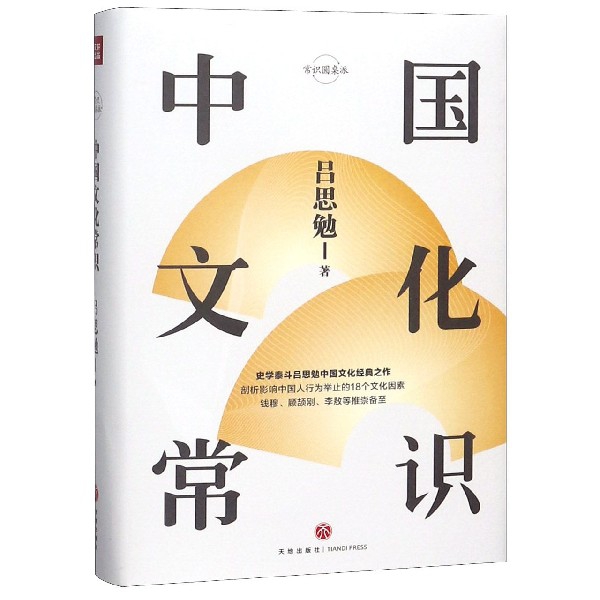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家贫,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研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我国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其史学专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中国近代史》等,均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 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 :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作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 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 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 ,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 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 。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们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目 前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吗?而 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 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 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 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 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 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 ,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 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 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 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 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 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 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 ,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 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 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 着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 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 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须知我们要知道一 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 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 ,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 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 “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 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 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 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 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 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负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 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 原因安在?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 是偏重于政治。 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 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态所 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