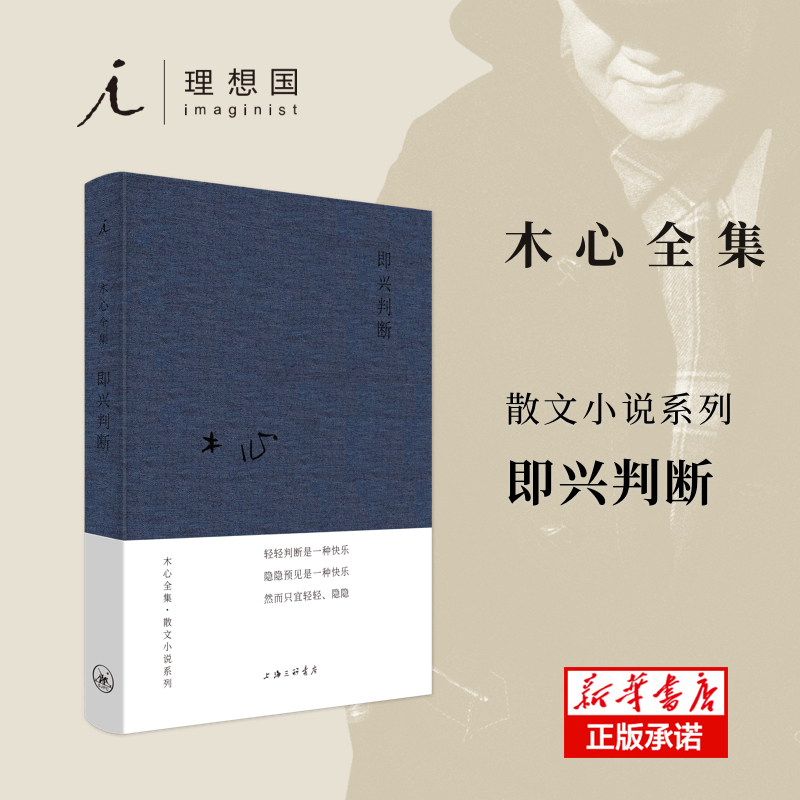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三联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6.00
折扣购买: 即兴判断(布面精装)
ISBN: 9787542668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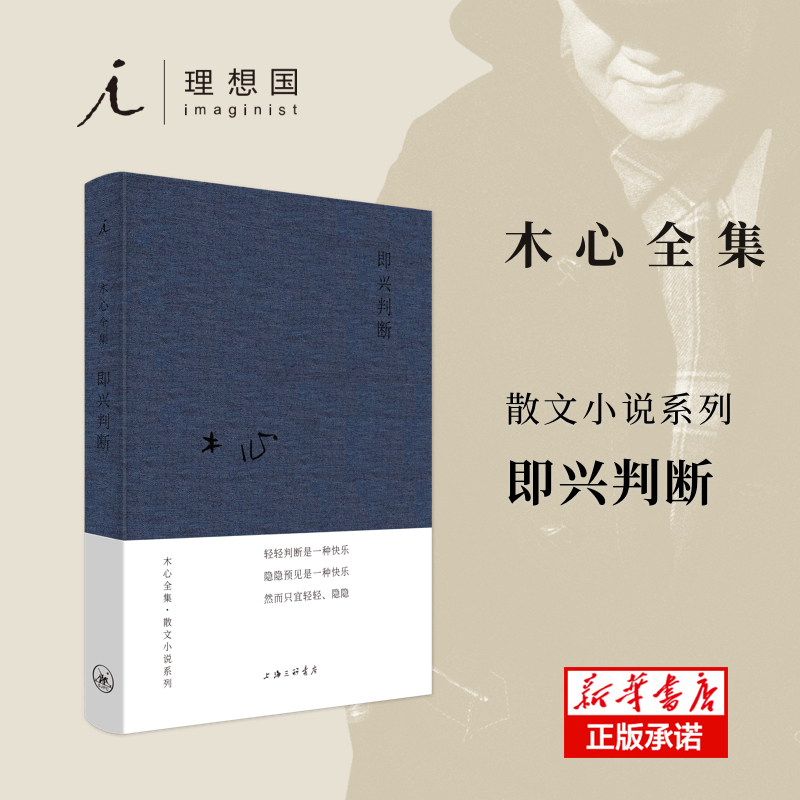
木心(1927—2011),本名孙璞,原籍浙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82年定居纽约,晚年归根故里乌镇,被海内外华人视为深解东西方艺术传统的精英和传奇人物。 生前定稿出版有文集13种著作,即散文小说系列6种《哥伦比亚的倒影》《琼美卡随想录》《温莎墓园日记》《即兴判断》《素履之往》《爱默生家的恶客》,诗歌系列6种《西班牙三棵树》《我纷纷的情欲》《诗经演》《巴珑》《伪所罗门书》《云雀叫了一整天》(引发刷屏的小诗《从前慢》即来自《云雀》),包括答问录1种《鱼丽之宴》。逝世后,另有“世界文学史讲座”整理成书《文学回忆录》(即听课学生陈丹青笔记),及作为《文学回忆录》补遗的《木心谈木心》。陈丹青说,《文学回忆录》布满木心始终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数家珍的文学圣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样持久地影响了这个人。 不止文学。英国BBC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世界文明》(20世纪以来的公众艺术教育电视片经典),中国部分,拟拍摄宋元以降的山水画。这部影片将探讨逾千年的中国山水画之路,摄制组为此来到乌镇的木心美术馆,拟将画家木心作为BBC千年历程纪录片的“一个开场的故事”,以诠释艺术的力量。
木心《眸子青青》选摘 慢慢地,其实也不慢,也很快,总是前后十年光景。 古典音乐,即所谓喜欢、或所谓爱好、或所谓着迷地那样听古典音乐…… 不再听,不想听,不要听,不必听。看到别人在听,觉得可怜,可鄙——还听这种东西。 贝多芬戆,肖邦俗,巴赫迂腐,莫扎特,浅薄,开玩笑。不仅不再迁就,即使提到这些名字,也觉得太那个了。(哪个?直说出来就是:再听再提这些东西是可耻的,枉为现代人) 因为他才不戆、不俗、不迂腐、不许别人开他玩笑。 怎么回事? 这样一回事——是个与古典音乐已经全然不相称的人了,不配听,被古典音乐屏弃。 他不知道,全然不知道原来是这样一回事,这就越发无还价地证明:他确凿不配听。 还有一个雄辩的事实可作旁证:此辈快速超凡入圣的现代唐璜,都老死亦相往来地喜欢或爱好或着迷于北京歌剧、新潮时代曲、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夹缝里的小调,这等于认定:那些东西是永远不戆永远不俗,不会迂腐不开玩笑的。 一个人,单单一个人,会独特进化,进化到扬弃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而“古典音乐”是供“扬弃”的? 希腊雅典全盛期的雕像,谁说对它们已感到烦腻了——一定是雕像在说,它对这些现代人实在感到烦腻,烦腻透了。 (亨利·摩尔认为他自己的雕塑根本不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作品比,古希腊的呢?更不敢较量了——所以摩尔终于有这番业绩) 刚才的那个“他”,还得谈谈。对于他,如果世上从此不再演奏古典音乐,不再,绝响,曲谱悉数焚毁,怎么样?他说:“那好,反正我早就听过了。”(他之所以如此慷慨豁达,是有“底子”的,三十年代郎呀妹呀的小调,雨后春笋般的时代曲,他知道不可能殉古典音乐的葬) 事情又并非如此发展,据说这世界每一秒钟都鸣着贝多芬的乐曲。那个“他”,很快就没了,影子也没了,其实早就什么都没了。 那好。这样的人多的是,将来也多的是。 好的女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一大包爱。 从少艾到迟暮,计成百,方凡千,要把这一大包舍掉。 那一大包,不即是爱,但酷似爱,但绝非爱,但难以指明该归类于什么,但真是结结实实一大包,但这无疑是女人中之尤善者才会有,但这样的女人已经不多,但毕竟还存在而且还能遗传,但你想找不就找得到,但她会来找你,但她不一定找的就是你,但你可以看到她找了别人,但你不必嫉妒,因为也许宁是如此作个旁观者比较安静安全。 有这样两种熟视而无睹的人:一种是本身无意志,缺活力,只有在听从别人的意志时,活动了,活动得很起劲,甚而参与策划,有时也显得颇能决断。另一种,不同,本身也谈不上意志活力,其独处时,十分惫懒,一旦有人跟他,他转,有人跟他转,他便神机妙算,指挥若定,率领弟兄们,一副乘风破浪的样子。此时此境中,前者自以为有了活色生香的方针和道路,后者自以为天生将材、帅座、王者相。 好。前者庆幸:群龙有首。后者自贺:首有群龙。 好。所以这两种人常会天造地设搭配在一起,历朝如此,列国如此,一代代过完他们聪明伶俐浑浑噩噩的好日子。 他们又善于回避果真意志强活力大的人物。又善于把“意志”和“活力”的定义作新解释,就在一阵新的解释中,把价值判断兜底搅混,贬没,于是相视莫逆而笑。 继之相笑莫逆而视,好日子又聪明伶俐浑浑噩噩过下去。没人打扰他们。从未见有一只鹰飞下来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 所以群龙有首者和首有群龙者总是过得很不错,很有意思,很忙,忙极了。不可能有余暇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受宠时像受辱那样抿唇不语,受辱时像受宠那样窃笑不止。两者都是风格,然而都反常,应促使人竭力设法趋于正常,回到不必这样的抿唇不必这样窃笑的天然恬漠中去。 宠辱不惊,此种遭遇和态度(宠辱,不惊)本是很糟糕的,落入了宠或辱的境地,一时摆脱不了,只好睥睨处之,以反常应付反常而已。 高尚其事的营生,并非着眼于构成幸福,只是先为了贯彻安静。一有幸福可言,就意味着灾祸的存在,幸福是指灾祸竟已过去和灾祸犹未到来,那一段时空状态才是所谓幸福,别的还能指什么,别的没有指什么了。 含有宗教情操的哲学家,都明悉福与祸的先验同在。有的设计先去掉祸,使福亦随之而去。有的,设计先去掉福使祸亦随之而去。两种议论用心是一致的,都企图抵达无福无祸的境界和状态,结果是有的,都并不成功。福的种类祸的种类日益增多。 但是(幸亏到时候总有一个亮丽的“但是”)人世虽已定型定局,但是至今还能够宛如存身古代那样地,过着宗教情操十足的哲学家生涯,巧妙摒挡受宠的机会和受辱的机会,不使斑马走在闹市的横道线上,等等。 往往先要在大受其辱的时期自我驾御得法,免以屈死,然后一旦转为大受其宠的当儿赶紧集储足够延长生命的资料,于是消耗得极为经济,清则清其心寡则寡其欲——老练的享乐主义者,在人间过完了一生,又再过一生,或者同时两三种人生合着过,髣髴若古作曲法中之赋格然。 那些三流四等的文学作品中写的,主角发愁,天便下雨,主角乐了,鸟语花香,这样的天作之合是不可能的。人生之逊于电影,最显著的一点,电影有配音,女人和男人邂逅,小提琴之类在暗中嘶嘶价响,这当然是非常看不起观众,然而观众乐于被看不起,观众非常需要有小提琴之类从旁提醒,什么来了,什么去了。生活中,不会到处有一把小提琴等着陌生男女,那么,生活无疑是劣于电影了。 但是(又来了),前面说过的那个带有若干宗教性的哲学家,即哲学到了不成其为哲学的,那个动不动就一贫如洗的享乐主义者,他觉得生活之妙,就妙在没有小提琴在暗中发作,如果他忧闷天就阴霾,他透气阳光立刻普照,小提琴又一天到晚叮住他,他就死了。 能归真返璞的人是禀赋独厚,常见的是无真可归无璞可返。如果大家都有望各归其真各返其璞,那还算什么真什么璞。 ★ 陈丹青(木心美术馆馆长)——多年来庞大的中国文学群体之外,我看见,这个人自始至终单独守护着、同时从不受制于五四开启的价值、精神与世界观,凭一己之身、一己之才,持续回应并超越五四那代人远未展开的被中断的命题——譬如白话文如何成熟?譬如传统汉语在当代文学的命运与可能性,譬如中文写作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譬如在世态与时代的种种变幻中怎样以文学挽救文学…… ★ 陈向宏(木心故里乌镇的总规划师)——木心先生是唯一的。 ★ 铁戈(木心在上海时期的忘年好友)——现在人们看到的木心,都只是他露出水面上的冰山一角。 ★ 陈村(作家)——毫不夸张地说,木心先生的文章在我见到的依然活着的中文作家中最是优美、深刻、广博。 ★ 何立伟(作家)——意外之人,意外之文。 ★ 骆以军(作家)——木心先生是一位全方位的艺术家,他的小说很早就碰触西方现代小说常探讨的议题,包括辜负、遗憾、忏悔及追忆,也讨论人如何站在现代荒原中,仍能保持文明人的尊严。 ★ 孙郁(学者)——读几册木心作品集,像一番奇遇,自叹天底下还有这样的文字在,似乎是民国遗风的流动,带着大的悲欣直入人心。 ★ 陈子善(学者)——虽然姗姗来迟,毕竟还是来了,现在是到了木心先生的散文“墙外开花墙内红”的时候了。 ★ 巫鸿(学者)——在当代中国艺术家中,木心有两点与众不同:其一,他在中西文学和哲学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也能同样娴熟地将这些知识融会于写作和绘画之中。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和最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比美。高行健也是一位相当执着的画家,但是我认为在绘画风格的细腻和作品题材的丰富两个方面,木心都要胜过一筹。 ★ 童明(学者)——木心风格不是“一脉相承”,而是“多脉相承”。他的精神气脉既系于春秋、魏晋、汉唐的华夏文化,又源于古希腊的悲剧精神,而思维特征和艺术格调却又是西方现代派的,且与近三十年来最深思熟虑的西方人文思想息息相关。 ★ 陇菲(学者)——木铎声声,我心摇曳。 ★ 春阳(学者)——木心,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 ★ 李静(学者)——木心寻返久经失落的古典词语,借以拓展思维、感受和想象的边界,由此,他创造了一种真正成熟、华美、丰赡而高贵的现代汉语。 ★ 梁文道(“看理想”主讲人)——木心像是从一个从来没有断裂的传统中出来的,他能够用文字把你整个儿抓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