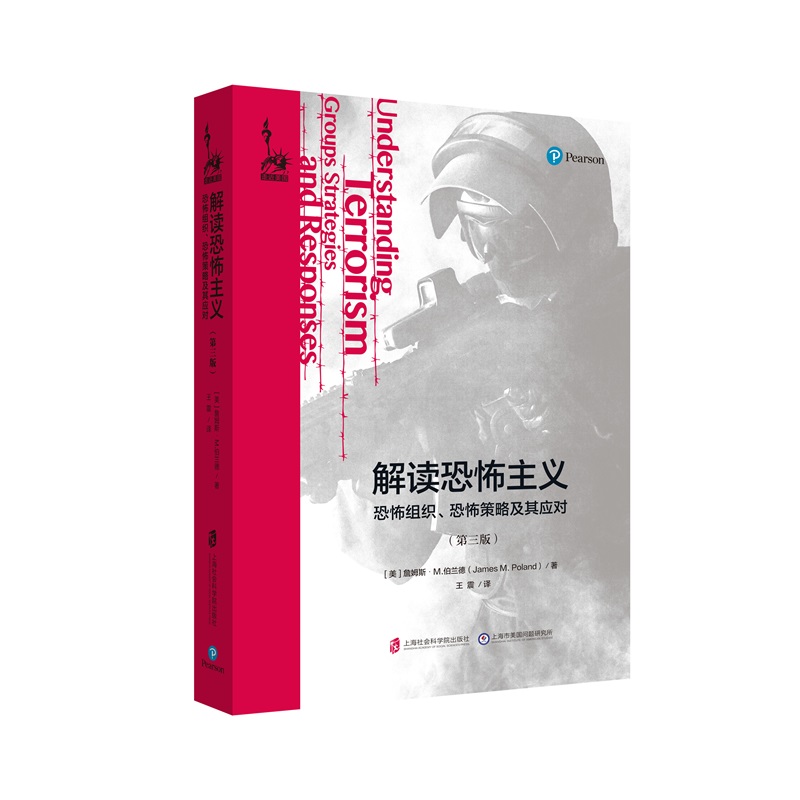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社科院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3.70
折扣购买: 解读恐怖主义(恐怖组织恐怖策略及其应对第三版)
ISBN: 9787552023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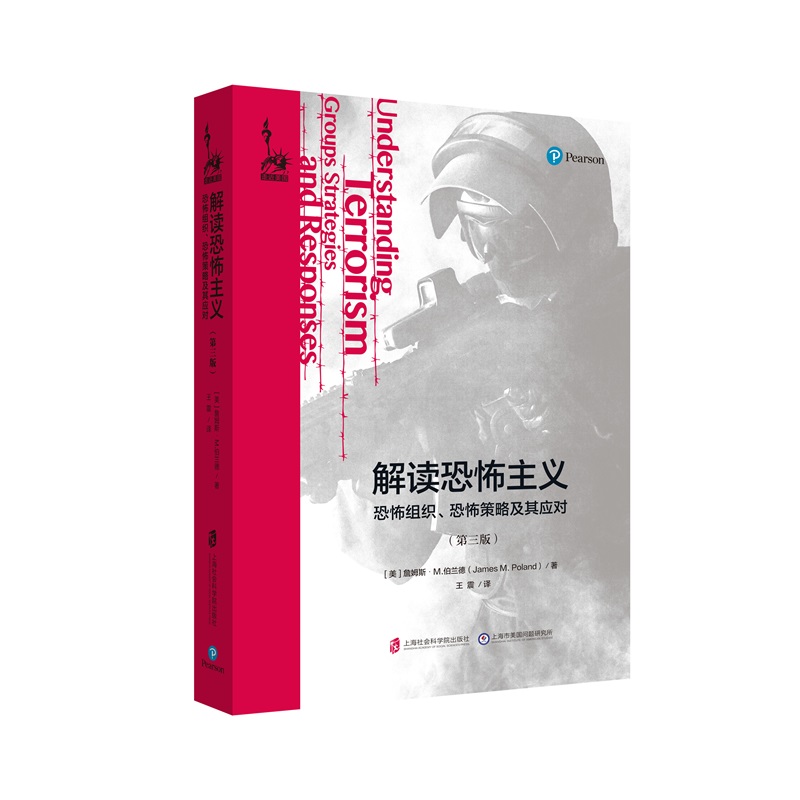
詹姆斯?M.伯兰德(James M. Poland)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现为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刑法学荣休教授。著有《解读恐怖主义:恐怖组织、恐怖策略及其应对》(1988)、《恐怖主义与人质劫持的实践、战术和法律研究》(1999)、《**性**袭击者:一个**性问题》(2003)、《亚文化暴力:青年罪犯价值体系》(1978)等。其中,《解读恐怖主义:恐怖组织、恐怖策略及其应对》一书自1988年问世以来,已经进行了多次修订和再版,成为美国刑法学、犯罪学、反恐学、**安全学等领域的经典教材。 ** 法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和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兼任上海反恐研究中心理事、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等。已出版专著《一个**大国的核外交:冷战转型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1969—1976)》《**反恐战争问题新论》,参与编写专著章节十余部,翻译有《统治史》(**、二卷),并先后在各类学刊和媒体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上百篇,并多次获得省部级学术奖项。
**章 “恐怖”与“恐怖主义”的定义 近年来,被标榜为反叛者、社会革命、民族解放*、游击战士、突击队、“圣战”分子、自由斗士乃至“殉道者”的小型暴力组织一次又一次地证明: 随机性暴力可以在**社会中诱发严重的社会恐慌。此类暴力活动吸引着媒体将其事迹在**范围内广为传播,从而导致有些****反应过度,采取了强化安全控制的措施。在“9·11”事件之前,这种暴力袭击就已在世界很多地方侵蚀着人权和公民自由。比如,根据克莱尔·斯特林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图帕马罗斯游击队(Tupamaros)在乌拉圭全境通过使用“无差别的”恐怖袭击来扼杀**。这场恐怖主义的结果是,*队于1973年掌权并建立了恐怖统治。乌拉圭是*****终被极权统治取代的典型案例。在乌拉圭,政治性政*被**禁止,所有公民都需要向*政当局登记注册,媒体*到了严格控制,数千人变成了政治犯。这种恐怖统治持续了12年,直到1985年4月,乌拉圭才恢复了**。 另一个违背公民权和人权的案例发生在北爱尔兰地区。持续升级的恐怖主义迫使英国议会废除了北爱尔兰**,并通过紧急权力对北爱尔兰地区进行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和紧急权力相伴随的则是大量未经授权的搜查、逮捕、拘留和扣押,以及公开审判的废除。在加拿大,恐怖主义促使当局于1970年通过了《战争措施法》,该法临时性地废除了许多公民权利,比如未经授权的搜查和逮捕等。加拿大当局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应对“魁北克解放阵线”(FLQ)的政治绑架和不加区分的**袭击。 “9·11”以来,西方**再次通过这种可预期的方式来制止“不加区分的”恐怖主义活动。比如,美国通过了《爱国者法案》,给执法部门以*多授权,使之在羁押移民、扩大监听、动用*队进行边境巡逻、进行未经授权的搜查等方面拥有*大权力。为了应对“9·11”事件和“**反恐战争”(GWOT),许多**以保护**安全的名义进行了强制性立法。当一个**处于战争状态时,它会宣称有权搁置**立法程序。在澳大利亚、英国、俄罗斯和以色列,《反恐法》均赋予警察在搜查、羁押和镇压恐怖嫌犯方面以*大权力。 恐怖主义正在成为21世纪的一个划时代问题。恐怖暴力循环,政治和*事性的镇压与报复如今已经司空见惯。这些事实需要我们对那些使用恐怖和恐怖主义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现象进行*为有效的学理性分析。西方****面临的挑战在于通过安保和公共安全来实现公民权和人权之间的平衡,而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则在于维护自由和执法之间的平衡。 恐怖主义及其界定问题 学者们在研究“恐怖主义”时面临的**个工作就是如何界定这一词汇。界定恐怖主义看似**简单,比如那些为了含糊不清的政治目的而劫持人质、对外交和*事人员实施暗杀、对大使馆进行汽车**袭击等均可被视为恐怖主义行径。然而,一旦我们**这些明显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时,就会发现界定恐怖主义并不容易。 “恐怖主义”一词可以让人产生复杂的情感,一部分是作为对无差别暴力的特征及其恐惧的反应,另一部分则是它在哲学层面上的含义。界定恐怖主义既要足够准确,以便能提供一个学术分析的假设;同时,它又要足够简约,使争议各方能够在复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于是,许多学者和观察家绕开了对恐怖主义的界定问题,仅仅参考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比如“一个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斗士”“一些人的恐怖主义是另一些人的英雄主义”“**的恐怖分子就是明天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等。对于那些从事学术研究或是在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上寻求**共识的学者们来说,这些表述体现了他们所面临的困难。 在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上,还有一个*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人们在回答问题或提出反驳时惯常使用的“转折策略”。该策略的要领在于使用“不过”一词的速度和技巧。换言之,“不过”或“但是”等词汇之后往往是另一方所实施的恐怖暴力或恐怖活动事实。试举几例: “基地”组织支持**恐怖主义、大规模杀戮和暴力混乱。不过,美国轰炸塞尔维亚、阿富汗,并对伊拉克进行先发制人的入侵又是什么? 哈马斯、“阿克萨”烈士旅和伊斯兰“圣战”是毫无意义的大规模杀戮和不加区分的恐怖主义行为。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加沙地带的恐怖主义及其对巴勒斯坦***的“定点清除”又是什么呢? 美国海*陆战队驻贝鲁特兵营所遭遇的汽车**袭击是毫无意义的残暴的恐怖主义行为。那么,美国海*为了报复这一**袭击而对无辜的黎巴嫩村庄进行的轰炸又是什么呢? 根据詹姆斯·Q.威尔逊的说法,这类策略的目的是通过转换议题来避免讨论一些特定问题,并能让另一方在道德上低人一等。而且,这些转折性反诘和*初的表述又是相同的,二者之间无法进行区分。这样,人们就无法在“基地”组织和美国**、**性人体**和以色列当局,以及汽车**袭击和美国海*的轰炸之间进行区分。换句话说,转折策略使任何实质性的讨论都变得毫无可能,因为任何分析论证都需要基于有效的划分。 转折策略**聪明,它是一种被称为“罪恶/内疚转移”的古老宣传技巧。毛瑞斯·特格威尔认为,“罪恶转移”是将公众注意力从作恶者的行为转移到对手身上。比如,朝鲜曾在1987年故意击落了一架韩国商用喷气飞机,这架飞机无意间闯入了朝鲜领空,机上载有100多名乘客。事后,朝鲜却回应称这架飞机在为美国充当间谍。这一说法削弱了美国在此事件上为韩国发声的合法性,以及民众对官方的信心。显然,这一策略被朝鲜当局用来为其击落一架没有武装的民航飞机提供了辩护,民众的注意力被从飞机击落事件上转移走,同时剥夺了美韩在此事件上的道义正当性。长期以来,朝鲜一直在美国***拟定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名单之上。 “罪恶转移”还一直被当成是**谣言的策略而备*指责。不少**的**都采用过这一策略。不过,“造谣”(disinformation)来自苏联时期“desinformatsiya”一词,它是指针对目标国、目标团体或个人故意提供或传递某些虚假的、误导的、片面的信息。 通过这种方式,巴勒斯坦人可以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者背信弃义,并以此为其随机的**性**袭击和劫持人质进行辩护。“爱尔兰共和*临时派”通过宣称英国*队为外国领土上的占领*来为其伏击英*的行为辩护,并以此在北爱尔兰地区占了上风。“解放亚美尼亚秘密*”(ASALA)通过宣传1915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来为其暗杀土耳其外交使团的行为辩解。“基地”组织为了对屠杀美国公民的行为进行辩解,宣称美*在阿拉伯半岛的驻扎亵渎了穆罕默德先知。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下去。面对“罪恶转移”策略,当代社会显得尤为脆弱不堪,因为我们在恐怖暴力面前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道德参照。 与此同时,“**恐怖主义”(international terrori**)“跨国恐怖主义”(transnational terrori**)和“**恐怖主义”(national terrori**)之类的词汇又增加了我们界定恐怖主义时的困难。“**恐怖主义”通常是指那些代表主权**利益而进行的恐怖主义行为,比如代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哈马斯。跨国恐怖分子往往跨越主权**边界开展活动,比如真主*,其恐怖活动通常会影响到不止一个种族。**恐怖主义分子通常寻求在某个单一**内的政治权利,比如巴斯克分裂分子。 援引上述各种观点并不是要让读者认为界定恐怖主义徒劳无益。格兰特·伍德劳曾强调说,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定义,我们就无法对被称为“恐怖主义”的现象进行确切认定: 比如,它究竟是对****稳定的一大威胁,还是可以在刑法体系内解决的另一种犯罪?界定一个能够被普遍接*的恐怖主义定义的*根本问题是与之相关的道义问题。通过阅读文献可以发现,恐怖主义的道义性,以及与之有关的词汇如恐怖、胁迫、武力和暴力等确实存在很多歧义。 恐怖主义的道义性 对于恐怖主义“道义性”(morality)的学术分析同样存在很多分歧。比如,尤金·沃尔特将“恐怖”(terror)描述为一种由特定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所造成的情感状态,而“恐怖主义”一词则包含了三个要素: 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情感反应和社会效果。雅各布·本杰明·哈德曼在1934年指出,“恐怖主义”是一种系统地使用暴力的行为,但他也试图对大规模暴力和恐怖主义进行区分。巴林顿·摩尔将暴力与恐怖主义描述为“消极的强迫”,并认为暴力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相似性。戴维·C.拉波波特则认为,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是指那些没有“道德约束”的个人,他们以暴力造成各种**伤害。在拉波波特看来,政治性暴力行为和无差别的随机性恐怖主义之间可以进行道德区分。沃尔特·拉克也承认,恐怖主义在暴力之外还有着*为广泛的含义,故而将其新书命名为《新恐怖主义》。按照沃尔特·拉克的说法,恐怖主义是指那些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系统地使用恐怖主义的运动。事实上,早在1977年,拉克就已经准确地预测到人们对于恐怖主义全面定义的探讨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鲍耶·贝尔提供了另一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学术分析。贝尔呼吁人们重视恐怖分子作案动机的多样性,主张对心理性、刑事性和自我表现型恐怖分子进行区分。贝尔还进一步指出,虽然“**恐怖”(state terror)长期存在,但人们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为数甚少的阴谋和个体暗杀行为。贝尔的首要关注点是跨国恐怖主义,他将其界定为恐怖分子跨越主权**边境的各种活动,并且其行为和政治意愿会影响到不止一个**的民众。 还有学者对如何应对反叛性恐怖主义和如何保护个体权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罗伯特·S.格斯坦认为,恐怖分子并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而是无法无天的暴徒。他指出,恐怖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在社会上造成恐惧、惊慌和不安全感。因此,应当剥夺那些参与恐怖暴力的个体所享有的权利。拉波波特对此持反对立场,他认为无论恐怖分子干了什么,或许可以剥夺其一部分民事权利,但关键的人权和民事权利应当*到保护。在拉波波特看来,西方**在处理较为重大的恐怖案件时,通常也会不按规定程序对嫌犯进行拘留、拷问或审讯。比如,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和调查记者们就曾指责美国、北爱尔兰和以色列为阻止那些不加区分的恐怖袭击,违背正常司法程序,设立了专门的拘留和审讯制度。 除了格斯坦和拉波波特在道德准则与司法条文关系问题上存在分歧外,**政治学家保罗·维尔金森还提出了**或**司法制度在拘押和起诉恐怖嫌犯时的权限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大多数被捕的恐怖分子都宣称自己是“自由斗士”或“反叛者”,他们使用恐怖主义策略具有正当性,故而应当依照战争法来对待。这种论调难倒了不少学富五车的学者们,因为这些学者一直试图在普通的违法者和政治犯之间进行详尽的区分。根据约翰·杜加尔德的观点,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因为总有一些**的**会庇护逃亡的恐怖分子,或是积极支持恐怖主义活动。比如,美国***就将伊朗、古巴、朝鲜、叙利亚和苏丹看成是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政权。美国中情局前局长威廉·凯西曾经表示,**支持下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可以抹杀和平与战争界限的“**系统”。此外,美国***还认定了44个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外国恐怖组织。比如,“基地”组织支持下的恐怖活动训练营就曾先后在阿富汗、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也门和菲律宾扎根。 本书汇集了**反恐研究领域的许多不同理论和方法,试图理清恐怖主义的来源及发展历程,揭开恐怖组织的神秘面纱,分析恐怖活动的发展势头,并提出相关的应对策略。这部潜心之作既为普通读者介绍了恐怖主义的基本内容,也为专业人士提供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实用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