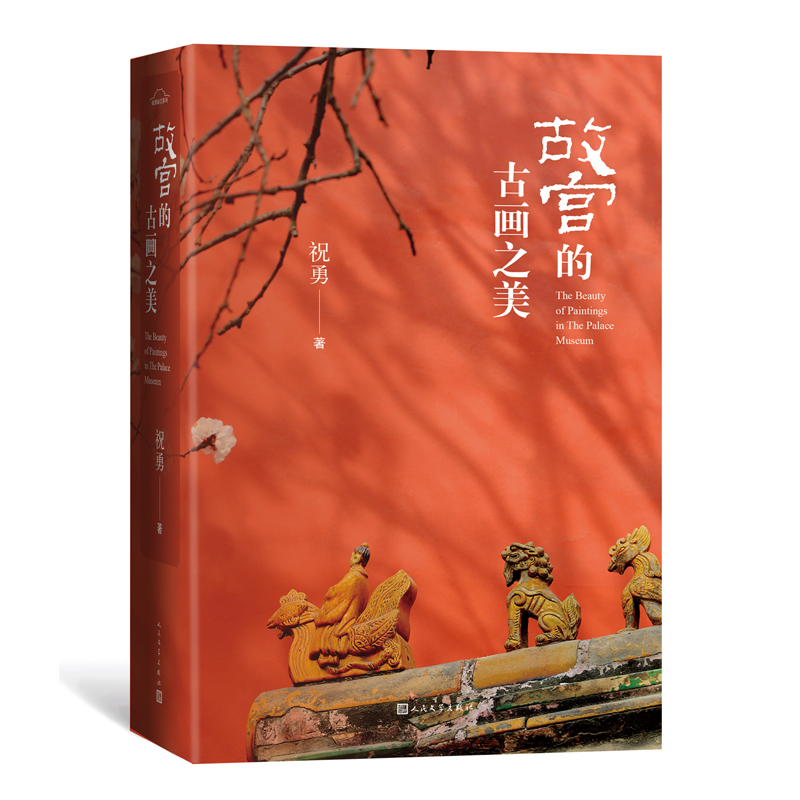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85.80
折扣购买: 故宫的古画之美
ISBN: 9787020145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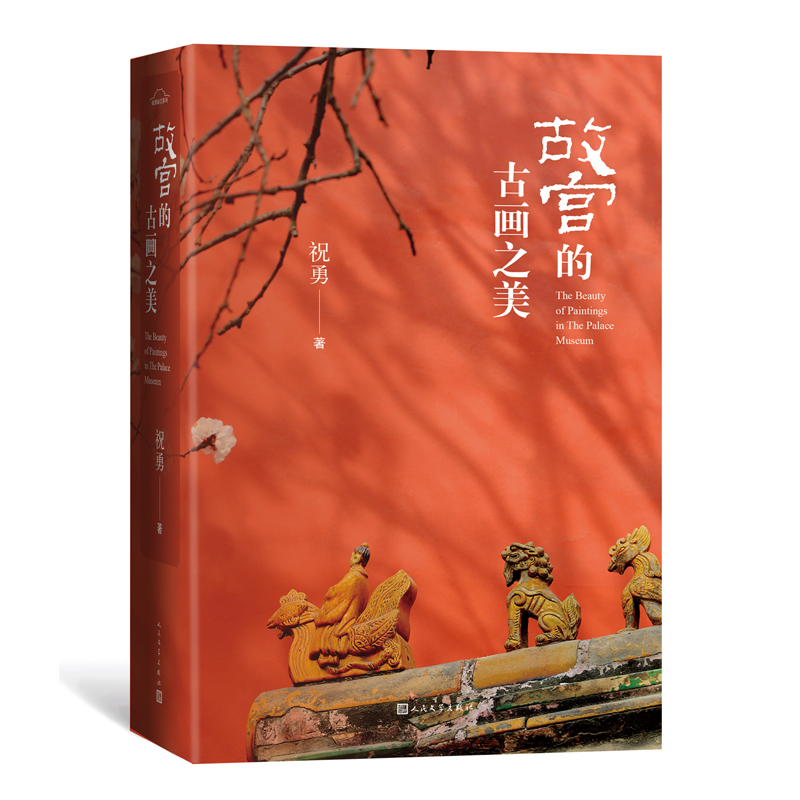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九年的家乡教育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个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儿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儿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胡适母亲冯顺弟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胡适父亲胡传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
一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古画,上起晋唐,下至当代,横亘千余年,总数达十多万件,完整地反映了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历程。这些藏画,大部分来自清宫收藏。许多古画在进入清宫以前,就历经了辗转流离,在进入清宫以后,又经历了曲折动荡。每一幅古画,都像《红楼梦》里的通灵宝玉,经过了几世几劫,才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比庞贝古城的精美壁画幸运得多,因为庞贝壁画中表现的“世俗美意,千姿万态,最终不敌瞬间一劫,化为灰烬。” 每当我面对那些年代久远的古画,都会怦然心动,想去写它们,去表达我心中无限的感动。除了感叹古代画者的惊人技法,心里还会联想到那些纸页背后的传奇,就像我每当看到沉落到飞檐上的夕阳,心里总会想起李煜的那首《乌夜啼》:“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浮现出那些在紫禁城里出现又消失的朝代往事。 二 我想写的,并不是一部美术史的学术著作。那样的著作已有太多,不需要我再狗尾续貂。我所写下的,只是心有所感而记下的文字。贯穿全书的,不是通篇的史论,而更像是内心的独语。我把它看作一场精神上的寻根之旅。我相信那些古时的画者,在完成这些旷世名作时,脑子里也未必会装满那么多的理念、术语,而更多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作画与观画,心动都是第一位的,假若心不动,则一切都不动,尤其对于我们,与古画隔了百岁千载,古人作画的时间空间都已不再,假若心无触动,又如何能够穿透时间的隔膜,去与作画者心神相接?观画即是观人,指向的终究是(古)人的精神脉动,需要触探人性的纵深,仅仅在学理的框架内审视这些古代艺术品,无异于隔靴搔痒。 然而,在这本书的内部,是暗含着一部美术史的,因为所有的个案,又都是在历史的流程中完成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它们是萧萧落木(落叶),它们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滚滚长江。艺术品远比朝代更伟大,像顾恺之、张择端、黄公望这些名字,也远比朝代更加不朽,但反过来说,它们(绘画)也终归是朝代的产物,身上纠缠着各自朝代的气息,挥之不去。它们有独立的价值,却也是时间的肌体上剥离下来的一个碎片,像一支吸水的根须,离不开养育它的岁月山河。所以我相信,这些由不同画作升发出的文字,不是鸡零狗碎的零篇断简,而是可以汇聚成一条历史的长河。晋唐五代、宋元明清,裹挟着艺术,也裹挟着从事艺术的人,一路奔涌至今。面对古画,我们见到的不只是画,而是它们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我们表面上是在看画,其实是透过纸页去体会人的气息,去透视历史的命运。我们可以循着线条、笔墨的指引,一步步往回走,仿佛一场逆光的旅行,去帖近历史原初的形迹,去体会创作者在特定环境下的呼喊与彷徨。 收在本书里的文章,自2012 年开始写起,最早在《十月》杂志的专栏《故宫的风花雪月》中连载一年,后来《当代》杂志又专门为我开设了《故宫谈艺录》专栏,一直写到今天,并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祝勇故宫系列》中,结集为《故宫的古物之美2》和《故宫的古物之美3》两部书稿,出版受到读者垂爱,两年间印行近十万册。为方便阅读,在此将以上二书合并为一册,更名为《故宫的古画之美》。书中所记,皆为笔者的个人心得,在此求教于大方之家。 2021 年8 月18 日 改于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 地平线,就是大地上永不消失的那一条线,是我们无法脱离的世界,所以,我们的美术史,就从一条线开始。 中国绘画,工具是毛笔,生产出来的自然是线,中国画与中国书法一样,都是线的艺术(因此赵孟頫说:“书画本来同”),不似西方油画,工具是刷子,生产出来的是色块,是涂面,是光影。当然,晋唐绘画也重色彩,也见光影,如韦羲所说:“山水画设色以青为山,以绿为水,以赭为土,间以白石红树,因青绿二色用得最多,故名青绿山水。”但那份青绿,亦是依托于线——先要用线条勾勒出山水人物的轮廓,再“晕染出体积感和简单的明暗关系”。 其实在这世界上,“线”是不存在的——画家可以用线来表现一个人,正如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里描绘的众多人物,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还有刚刚吹过树梢的微风,但这世界原本就是一个三维的存在,山山水水、花花草草,都是复杂的多面体,哪里找得到“线”呢? 然而,比顾恺之更早,至少从原始时代的陶纹、岩画,墓室里的壁画,商周青铜器的装饰、漆器上的彩绘,秦汉画像砖(石)上的阴阳刻线等,中国的画家,就把这复杂的世界归纳、提炼成线条,再多彩的世界,再复杂的感情,都可透过线条来表达。尤其在“水墨出现以前,画面上的线条,无论是柔是刚,像蚕丝、铁线,一直都以完整、均匀、稳定的节奏在画面上流动”。线,成为中国画家的通用语言,如石涛所说,“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 线是抽象的,又是具象的——中国的画家,把它由抽象变成具象,以至于天长日久,我们甚至以为世界本来就是由线组成的,忘记了它原本并不存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线,甚至能够驾驭线——一个小孩描画他心中的世界,也是从线,而不是从色块开始。 …… 最复杂的线条,藏在人物的衣缕纹路里。中国画从不直接画人的裸体,不似古希腊雕塑、文艺复兴的绘画,赤裸裸地展示人体之美,而是多了几分隐藏与含蓄,那正是中国人文化性格的体现,半含半露,半隐半显,中国式园林、戏曲、爱情,莫不如此。 ——第一章:如约而至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夜宴的那个晚上,当所有的客人离去,整座华屋只剩下韩载熙一个人,环顾一室的空旷,韩熙载会想起《心经》里的这句话吗? 或者,连韩熙载也退场了。他喝得酩酊,就在画幅中的那张床榻上睡着了。那一晚的繁华与放纵,就这样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连他也无法断定,它们是否确曾存在。 仿佛一幅卷轴,满眼的迷离绚烂,一卷起来,束之高阁,就一切都消失了。 倘能睡去,倒也幸运。因为梦,本身就是一场夜宴。所有迷幻的情色,都可能得到梦的纵容。可怕的是醒来。醒是中断,是破碎,是失恋,是一点点恢复的痛感。 李白把梦断的寒冷写得深入骨髓:“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梦断之后,静夜里的明月箫声,加深了这份凄迷怅惘。所谓“寂寞起来搴绣幌,月明正在梨花上”。 韩熙载决计醉生梦死。 不是王羲之式的醉。王羲之醉得洒脱,醉得干净,醉得透彻;而韩熙载,醉得恍惚,醉得昏聩,醉得糜烂。 如果,此时有人要画,无论他是不是顾闳中,都会画得与我们今天见到的那幅《韩熙载夜宴图》不一样。风过重门,觥筹冰冷,人去楼空的厅堂,只剩下布景,荒疏凌乱,其中包括五把椅子、两张酒桌,两张罗汉床、几道屏风。可惜没有画家来画,倘画了,倒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颓废与寒意。十多个世纪之后,《韩熙载夜宴图》[图3-1]出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陈列展上,清艳美丽,令人倾倒,唯有真正懂画的人,才能破译古老中国的“达?芬奇密码”,透过那满纸的莺歌燕语、歌舞升平,看到那个被史书称为南唐的小朝廷的虚弱与战栗,以及画者的恶毒与冷峻,像一千年后的《红楼梦》,以无以复加的典雅,向一个王朝最后的迷醉与癫狂发出致命的咒语。 ——第三章:韩熙载,最后的晚餐 张著没有经历过六十年前的那场大雪,但是当他慢慢将手中的那幅长达五米的《清明上河图》画卷[图4-1]展开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或许会闪现出那场把历史涂改得面目全非的大雪。《宋史》后来对它的描述是“天地晦冥”,“大雪,盈三尺不止”。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浓重的雪幕,裹藏不住金国军团黑色的身影和密集的马蹄声。那时的汴河已经封冻,反射着迷离的辉光,金军的马蹄踏在上面,发出清脆而整齐的回响。这声响在空旷的冰面上传出很远,在宋朝首都的宫殿里发出响亮的回音,让人恐惧到了骨髓。对于习惯了歌舞升平的宋朝皇帝来说,南下的金军比大雪来得更加突然和猛烈。在马蹄的节奏里,宋钦宗瘦削的身体正瑟瑟发抖。 两路金军像两条巨大的蟒蛇,穿越荒原上一层层的雪幕,悄无声息地围拢而来,在汴京城下会合在一起,像止血钳的两只把柄,紧紧地咬合。城市的血液循环中止了,贫血的城市立刻出现了气喘、体虚、大脑肿胀等多种症状。二十多天后,饥饿的市民们啃光了城里的水藻、树皮,死老鼠成为紧俏食品,价格上涨到好几百钱。 这个帝国的天气从来未曾像这一年这么糟糕,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正月乙亥,平地上突然刮起了狂风,似乎要把汴京撕成碎片,人们抬头望天,却惊骇地发现,在西北方向的云层中,有一条长二丈、宽数尺的火光。大雪一场接着一场,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地冰如镜,行者不能定立”。气象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作“小冰期”(Little Ice Age),认为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上,只有四个同样级别的“小冰期”,最后两个,分别在12世纪和17世纪,在这两个“小冰期”里,宋明两大王朝分别被来自北方的铁骑踏成了一地碎片。上天以自己的方式控制着朝代的轮回。此时,在青城,大雪掩埋了许多人的尸体,直到春天雪化,那些尸体才露出头脚。实在是打不下去了,绝望的宋钦宗自己走到了金军营地,束手就擒。此后,金军如同风中飞扬的渣滓,冲入汴京内城,在宽阔的廊柱间游走和冲撞,迅速而果断地洗劫了宫殿,抢走了各种礼器、乐器、图画、戏玩。这样的一场狂欢节,“凡四天,乃止”。大宋帝国一个半世纪积累的“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匆忙撤走的时候,心满意足的金军似乎还不知道,那幅名叫《清明上河图》的长卷,被他们与掠走的图画潦草地捆在一起,它的上面,沾满了血污。 ——第四章:张择端的春天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