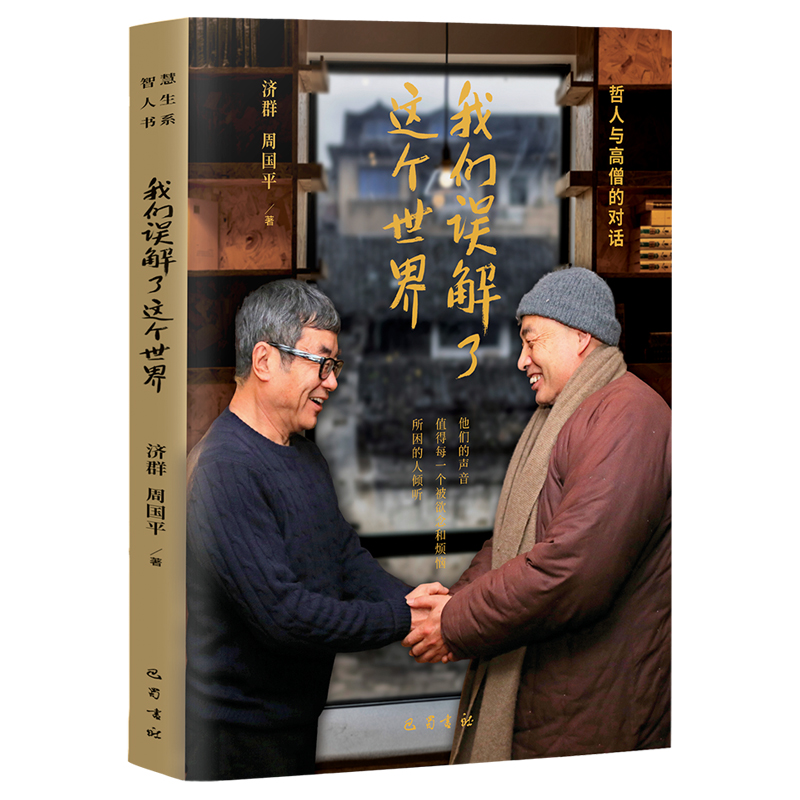
出版社: 巴蜀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6.00
折扣购买: 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2023新版)
ISBN: 97875531199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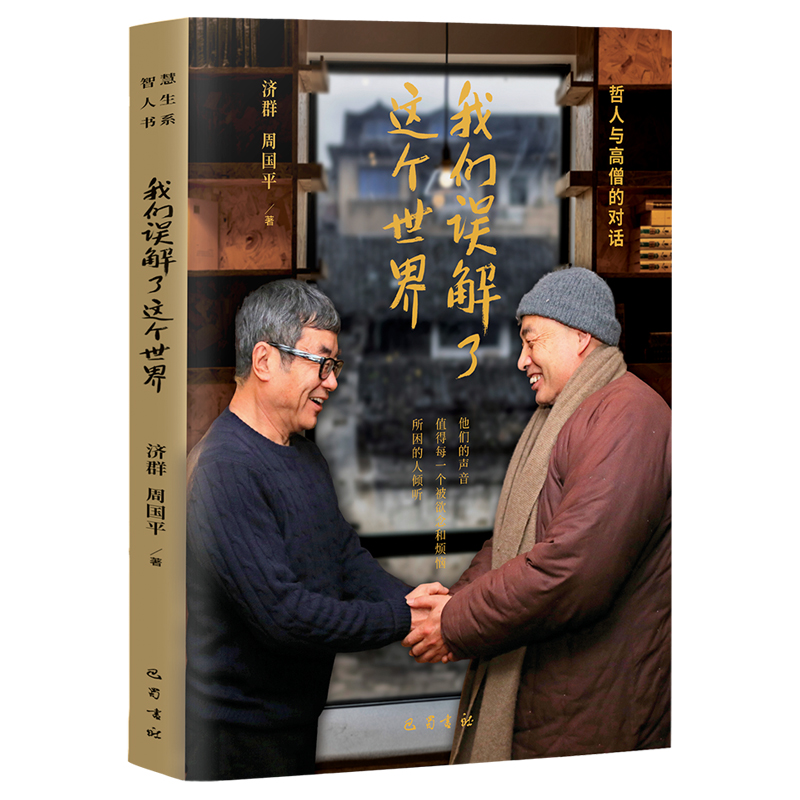
济群:童真入道,出家四十余载。为沩仰宗第十代传人、斯里兰卡佛教与巴利语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特约研究员及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1980年就读于中国佛学院,随后于闽南佛学院、戒幢佛学研究所等地任教。从事教育几十年来,对如何有效修学,有着深入的观察、思考和实践。由此,提出修学五大要素,创建次第修学体系,令许多人蒙益。 1992年起,面向社会及高校举办讲座,开国内弘法之先,法音流布海内外。同时笔耕不辍,出版“智慧人生、修学引导、以戒为师”等丛书四百多万字。以纯正的佛法知见,剖析社会问题,厘清修学误区,提出切实的解决之道。 周国平:1945年7月生于上海,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哲学研究者,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著名学者之一。 主要著作有《苏联当代哲学》(合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人与永恒》《尼采与形而上学》《忧伤的情欲》《只有一个人生》《今天我活着》《爱与孤独》等;译著有《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合译)《偶像的黄昏》《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等。
★ 不要一辈子为身体打工 济:我是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从佛法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认定的“自我”,其实是一种错觉。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自我,但是否想过:究竟什么代表着“我”?我们一定以为,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深究起来,我们会发现,这个回答充满着不确定性:或者觉得身体是“我”,或者觉得身份是“我”,或者觉得想法是“我”,或者觉得情绪是“我”,诸如此类。事实上,我们认为是“我”的这些东西,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这些东西和我们只有暂时的关系,即使这个须臾不离的身体,也不过是今生的一个载体。当这个身体尚未出生或已败坏时,“我”在哪里? 周:在所有的认定中,身体是“我”是最牢固的认定,因为没有了身体,也就没有了今世的生命,没有了今世的“我”。 济:所以说,这种对“我”的认定,只是盲目的、一厢情愿的附会。如果把这种暂时的关系作为“我”的存在,我们就会对此产生深深的依赖,乃至永恒的幻想,痛苦就随之而来了。把身体当作是“我”,就害怕这个身体的死亡;把身份当作是“我”,就担心这个身份的失去。包括这样那样的情绪:我在生气,我在沮丧,我在痛苦……但情绪又是什么呢?就像身上长了一个肿瘤,虽然和我们有关,但并不能真正代表“我”,更不能说这个肿瘤就是“我”。我们之所以会被情绪所控制,就因为把情绪当作是“我”。然后还会找很多理由,让这些情绪合理化。其实,不过是你被控制了而已。 周:无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大多数哲学家,在这个价值判断上是共同的,就是内在的东西比外在的东西重要,心灵比身体重要。在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去掉以后,内在的东西是什么?一辈子为身体打工很糟糕,身体是工具,它是什么东西的工具,它应该为谁打工?人们把非我当作“我”,我们要否定的是非我,而不是“我”。那么“我”是什么?无我的“我”不是我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什么? 济:无我,主要是否定对自我的错误认定。我们把自己设定的一些东西当作“我”的存在,当作“本来面目”,就使我们迷失得越来越深。只有去除这个错误设定,我们才有能力了解自己的本来面目。 周:但我们还要追问,真正的“我”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佛教实际上是否定这个真正的“我”的存在的。“我”没有实体,诸法无我,包括你这个个体,是没有内在的、永恒不变的本质的,佛教否定这个东西。很多人迷恋自我,觉得这个“我”是天下最重要的,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偶然的,按照佛教的说法,就是因缘而起,因缘而灭,没有自身的本质。这里特别关键的是,从根本上否定“我”,所谓的“我”只是一个偶然造成的现象。对这个观点,一般人在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这个道理我懂,但我也无法接受。 济: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从缘起现象的层面,佛教讲无我,是要否定在五蕴的生命现象中有个恒常、不变、主宰的自我。至于缘起的“我”,并不是佛教要否定的。这个因缘和合形成的生命体,会无尽地延续下去,但不是固定不变的。 周:按照我的理解,空性归根到底是对“我”的否定。当然,这个“我”是“小我”,所以空性也可以说是“大我”。 ★现代人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周:我觉得我的疑问还没有解决,把对“我”的错觉排除之后,还剩下什么? 济:“我”的存在由三种感觉造成。第一是重要感,凡是我的东西都特别重要;第二是优越感,凡是和我有关的都要超过别人;第三是主宰欲,希望别人都能听从于我。这三种感觉也需要依托基础,然后通过不断强化而形成。当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到底因为什么重要?是相貌很重要,还是身份很重要,还是学历很重要?总要有一个依托点。优越感也是同样,或是因为能力很优越,或是因为出身很优越,或是因为身份很优越,或是因为相貌很优越……总之,需要有一个依托基础。但我们通过审视会发现,所有这些只是短暂的存在,都在不断变化中。可以说,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抓得住。而作为自我本质性的存在,必须是永久的。正因为没有一种本质性的存在,所以这个自我就像皮包公司那样,只是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概念。现代人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越来越发现,自我所依托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如果自我本身是一个独立不变的存在,我们不可能没有安全感,也不需要依赖外界支撑,更不需要刷什么存在感。正因为我们现在赖以支撑的一切是变化的,不稳定的,才会让我们患得患失,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 周:把这些社会的和外在的东西去掉后,就一个心理个体来说,我所有的心理活动,包括我的感觉、记忆和思想等,都在我这个个体中发生。至于别人发生什么心理活动,我只能去观察和判断,不能直接感知。作为心理活动的主体,人和人之间截然分开,我不能代替你成为你心理活动的主体,你也不能代替我成为我心理活动的主体,这在哲学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能不能把作为一个个体的所有心理活动的承载者称为自我?如果没有载体,心理活动怎么办? 济:作为生命个体的承载者,阿赖耶识就扮演着类似“自我”或“灵魂”的角色,而五蕴构成的生命现象,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特质性,以此作为个体生命延续的基础,同时也是区别于其他生命之所在。 周:很多迷惑是出于自我的存在。别人的自我不能代替我的自我,只有我的自我才能成为我的一切精神活动的载体。我死了,这个自我就没有了。 济:精神活动是不是由内在的、统一的自我在决定?其实不见得。比如有些人人格分裂,严重的可能同时展现十种甚至二十多种人格。他可能一会儿进入这个状态,一会儿进入那个状态,自己是不知道的。心理治疗的时候,会把这些不同人格状态整理出来,让患者了解,这种了解有助于他进行心理整合。常人虽然称不上人格分裂,但在不同状态下,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状态,展现不同的人格特征。高兴或生气的时候,面对朋友或仇敌的时候,往往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每种心理都会遵循自身的活动惯性,基本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生气的时候,想让自己马上不要生气,多数人做不到。你很在乎某个东西,想让自己马上放下,也同样做不到。所以,我们认为的那个具有主宰作用的“我”,其实是不存在的。 周:“我”不是心理活动的主宰,尼采也谈到了,弗洛伊德还把这个观点发展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 济:如果说“我”是生命系统,或是一种综合的作用,那这只是一种缘起的假我。这种假我的思想,佛教也是承认的。问题是,我们对于“自我”的认定蕴藏着自性见,并将这种自性见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高兴,觉得“我”在高兴;不高兴,觉得“我”在不高兴;干坏事,是“我”在干坏事;干好事,是“我”在干好事。这种强烈的自我感,是潜意识进入意识后形成的一种感觉,使我们的任何言行乃至起心动念都会带着这种感觉,贴上“我”的标签。因为有了“我”的标签,我们就看不清事物真相,进而带来种种烦恼。 ★直面生死的困惑 周:人生的问题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现实的烦恼,比如生存的压力、利益的得失、爱怨的困扰等等。二是永恒的困惑,就是生死之惑,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其实,社会性的得失是比较容易看破的,最难看破的是生死。有的人始终陷在现实的烦恼之中,好像完全不存在永恒的困惑,我觉得这种人慧根太差,比较不可救药。尼采说过:面对有根本缺陷的人生竟然不发问,这是可耻的。人有根本性的困惑,这是有灵性的表现。困惑是觉悟的起点,没有困惑的人绝对不可能觉悟。 济:禅宗说,“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可见,产生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有问题的人,你要为他解决问题。至于没问题的人,你要给他制造问题,让他意识到人生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需要找到答案。 周:生命的永恒困惑是根,其他都是枝叶。 济:是体和用。永恒的困惑没解决,就会不断制造现实问题。如果仅仅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涉及永恒的问题,内心是不会踏实的。除非他吃饱喝足就没问题了,但那是动物式的活法。作为有一定思想的人,必然会碰到永恒问题。 周:早期的西方哲学很重视这个问题,比如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预习死亡。斯多葛派哲学家讨论的一个重大主题也是生死问题,在他们看来,哲学的使命就是帮助你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死亡。 济:有段时间,我对介绍宇宙和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科学家讲到,大概过一、二百亿年,宇宙大爆炸后的所有能量会用完,天地会变得一片死寂,什么都没了。 周: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没有意义,等于是现在发生的一样,时间长短不是个问题。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推翻,宗教、哲学必定会产生,因为人不能忍受无意义。宇宙必须有意义,如果人类只有科学,再发达有什么意思?宇宙间为什么会有人类出现?就是因为宇宙要证明自己是有意义的。 济:对芸芸众生来说,没有意义一样可以活得欢天喜地,不需要探讨什么特别的意义。必须有意义才能活着的人,只是少部分的思考者,如哲学家、艺术家、修行人等。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 周:多数人其实也会有感到恐慌的瞬间,因为想到没有意义而恐慌,但很多人都在逃避,感到无奈,觉得想也没有用。我相信每一个有理性的人,总会有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平时看起来就是芸芸众生,但和他深入交谈,发现他心中有这个恐慌。 济:但是不敢去面对,就会本能地回避。 周:最后能找到意义并且让自己真正相信这个意义的人,我觉得是幸运的,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找到都是好的。在这一点上,所有宗教和精神性的哲学是相通的,都是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只是路径有所不同。 济:中国古代三不朽的人生,立德、立功、立言,也是一种解决方式。但作为比较唯物的思想,还是解决得不透彻,这种意义的说服力没有达到百分之百。 周:我觉得还是比较功利性的东西,不论是立功还是立言、立德,无非是说你的功业、文字、品德会流传下去,后人会敬仰你,你的名声可以万古长存。真正的不朽不是名声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流芳百世的问题。 济:古人对宇宙没有太多了解,会觉得世界是永恒的。但在今天来看,地球乃至宇宙都是非常脆弱而渺小的。世间的一切,无论建立多少功业,或者名声流传多久,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 哲人与高僧的对话,一场东方文化与西方哲学相遇的盛典。 每个人都曾经被那些终极的问题困扰,何为人,何为生命,我是谁,谁又是我,人们在现实中混沌地活着,在俗世里被裹挟着前进挣扎,也许终其一生,我们始终无法看清世界的真相,但我们至少应该学会认清自己,过好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