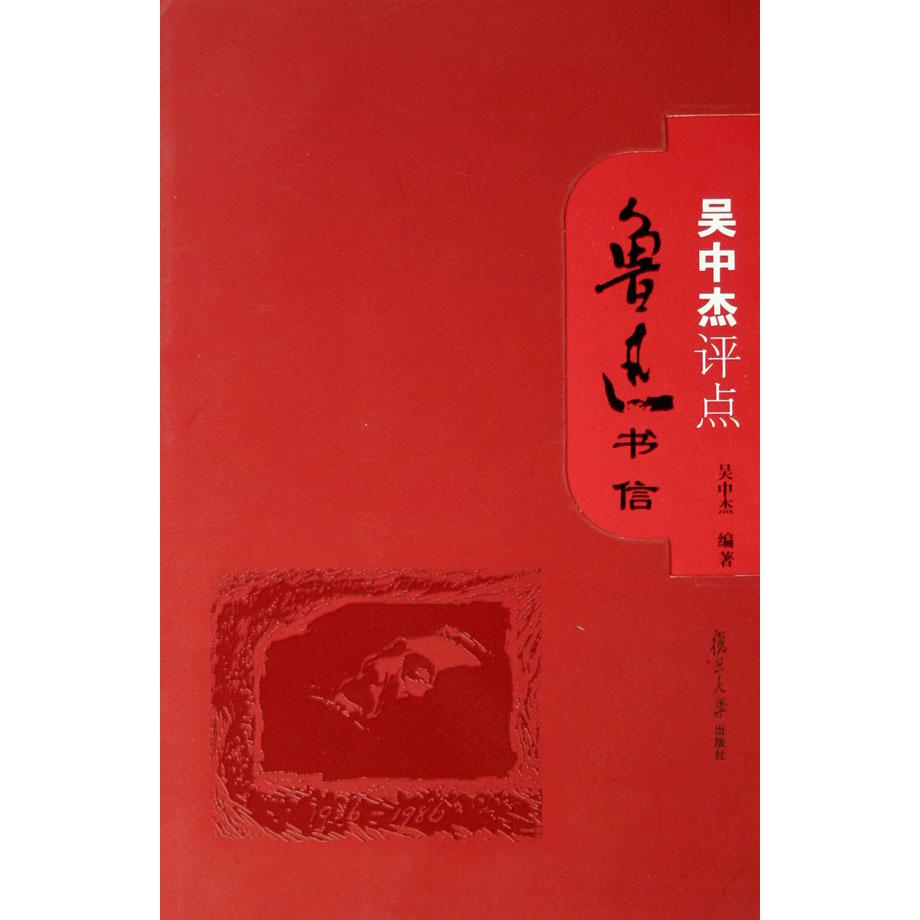
出版社: 复旦大学
原售价: 55.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吴中杰评点鲁迅书信
ISBN: 7309032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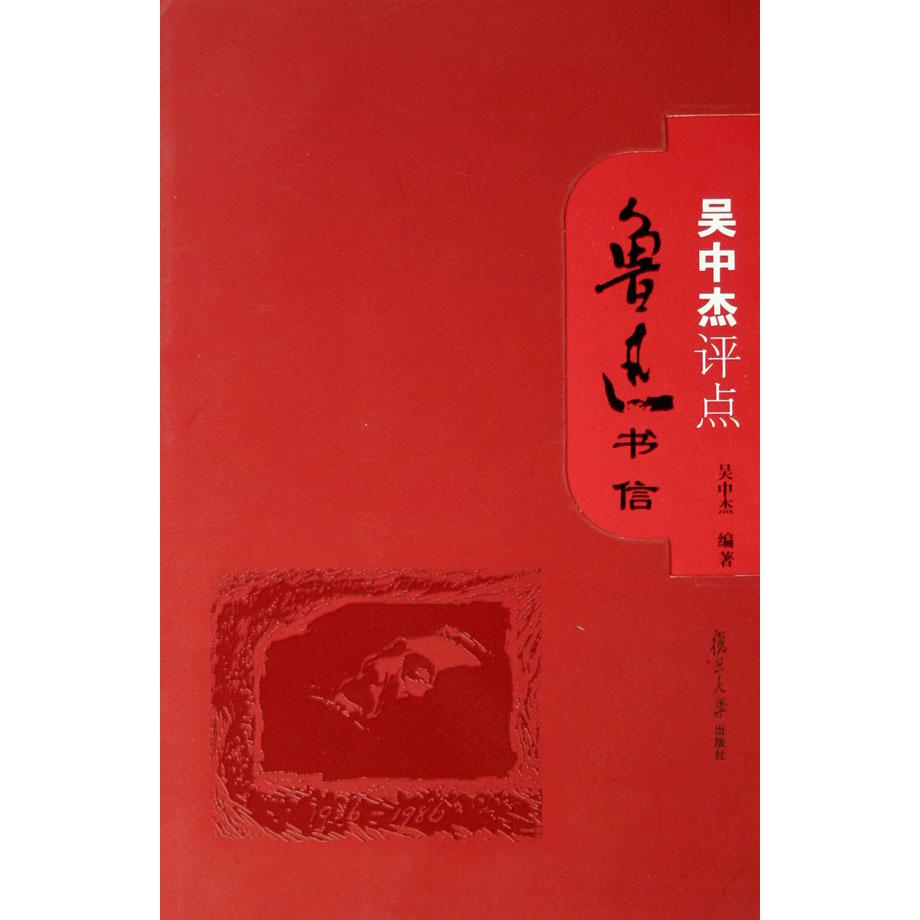
吴中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36年出生。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于鲁迅研究用力尤勤,兼写杂文随笔。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与高云合作)、《论鲁迅的杂文创作》、《鲁迅文艺思想论稿》、《鲁迅传略》、《海上文谭》(与高云合作)、《文艺学导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与吴立昌合作主编)等,又有散文集《人生大戏场》、《海上学人漫记》等。他所主持的“文艺学系列教材建设”项目,于2001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致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十三日的信,早收到了,到今天才答复。其实是我已经病了十来天,一 天中能做事的力气很有限,所以许多事情都拖下来,不过现在大约要好起来 了,全体都已请医生查过,他说我要死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所以也请你们放 心,我还没有到自己死掉的时候。 中野重治的作品,除那一本外,中国没有。他也转向了,日本一切左翼 作家,现在没有转向的,只剩了两个(藏原与宫本)。我看你们一定会吃惊, 以为他们真不如中国左翼的坚硬。不过事情是要比较而论的,他们那边的压 迫法,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他们是德国式的,精密,周到,中国倘一仿 用,那就又是一个情形了。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 人物。凡有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 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 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莲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 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以下,答复来问—— 一、不必改的。上海邮件多,他们还没有一一留心的工夫。 二、放在那书店里就好,但时候还有十来天,我想还可以临时再接洽别 种办法。 三、工作难找,因为我没有和别人交际。 四、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 生长北方的人,住上海真难惯,不但房子像鸽子笼,而且笼子的租价也 真贵,真是连吸空气也要钱,古人说,水和空气,大家都有份,这话是不对 的。 我的女人在这里,还有一个孩子。我有一本《两地书》,是我们两个人 的通信,不知道见过没有?要是没有,我当送给一本。 我的母亲在北京。大蝎虎也在北京,不过喜欢蝎虎的只有我,现在恐怕 早给他们赶走了。 专此布复,并请 俪安。 迅上十一月十七日 【评点】 对于文学家们的变化无常,鲁迅早在1931年写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中 就有所描述,可以参看。他在那篇文章中说:“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 和前年很有点不同了。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 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象两只 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 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 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受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 是文学家了。”所以鲁迅认为,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这样的作家 ,即使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容易把革命写歪。 致母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来信并小包两个,均于昨日下午收到。 这许多东西,海婴高兴得很,他奇怪道:娘娘怎么会认识我的呢? 老三刚在晚间来寓,即将他的一份交给他了,满载而归,他的孩子们一 定很高兴的。 给海婴的外套,此刻刚刚可穿,内衬绒线衣及背心各一件;冬天衬衣一 多,即太小,但明年春天还可以穿的。他的身材好像比较的高大,昨天量了 一量,足有三尺了,而且是上海旧尺,倘是北京尺,就有三尺三寸。不知道 底细的人,都猜他是七岁。 男因发热,躺了七八天,医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现在好起来了。大约 是疲劳之故,和在北京与章士钊闹的时候的病一样的。卖文为活,和别的职 业不同,工作的时间总不能每天一定,闲起来整天玩,一忙就夜里也不能多 睡觉,而且就是不写的时候,也不免在想想,很容易疲劳的。此后也很想少 做点事情,不过已有这样的一个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缩,正如既是新台门 周家,就必须撑这样的空场面相同。至于广平海婴,都很好,并请勿念。 上海还不见很冷,火炉也未装,大约至少还可以迟半个月。专此布达, 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广平海婴随叩十一月十八日 【评点】 鲁迅给他母亲写信,难得说及自己的窘迫状况,以免老人家担忧也。这 次因病,不能不说一点,也说得较为轻松。为了使母亲能够明白是怎么一回 事,就拿她熟悉的事情作比方。比如,说现在的病,就以在北京时生病的情 形作比,说目下的处境,则拿当年绍兴老家的情况作比。“此后也很想少做 点事情,不过已有这样的一个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缩,正如既是新台门周 家,就必须撑这样的空场面相同。”这个比喻极妙,有如《红楼梦》里凤姐 所说的:大有大的难处。鲁迅之所以摆脱不开那些琐事,总是要打杂,时间 被割碎,即此之故也。 致孟十还 孟先生: 五日函奉到。外国的作家,恐怕中国其实等于并没有绍介。每一作家, 乱译几本之后,就完结了。屠格涅夫被译得最多,但至今没有人集成一部选 集。《战争与和平》我看是不会译完的,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 心,他太聪明,又大胆。 计划的译选集,在我自己,现在只是一个梦而已。近十来年中,设译社 ,编丛书的事情,做过四五回,先前比现在还要“年富力强”,真是拚命的 做,然而结果不但不好,还弄得焦头烂额。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 ,他们除想立刻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算的。 我曾在神州国光社上过一次[一次]大当,《铁流》就是他们先托我去拉,而 后来不要了的一种。 《译文》材料的大纲,最好自然是制定,不过事实上很难。没有能制定 大纲的元帅,而且也没有许多能够担任分译的译者,所以暂时只能杂一点, 取乌合主义,希望由此引出几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译者来——其实志愿也 小得很。 稿子是该论页的,但商人的意见,和我们不同,他们觉得与萝卜白菜无 异,诗的株儿小,该便宜,塞满全张的文章株儿大,不妨贵一点;标点,洋 文,等于缚白菜的草,要除掉的。脑子像石头,总是说不通。算稿费论页, 已由我们自己决定了,这回是他们要插画减少,可惜那几张黄纸了,你看可 气不可气? 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版,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 办 一个小杂志,就这么麻烦,我不会忍耐,幸而茅先生还能够和他们“折冲尊 俎”,所以至今还没有闹开。据他们说,现在《译文》还要折本,每本二分 ,但我不相信。 此布,即颂 时绥。 迅上十二月六日 P423-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