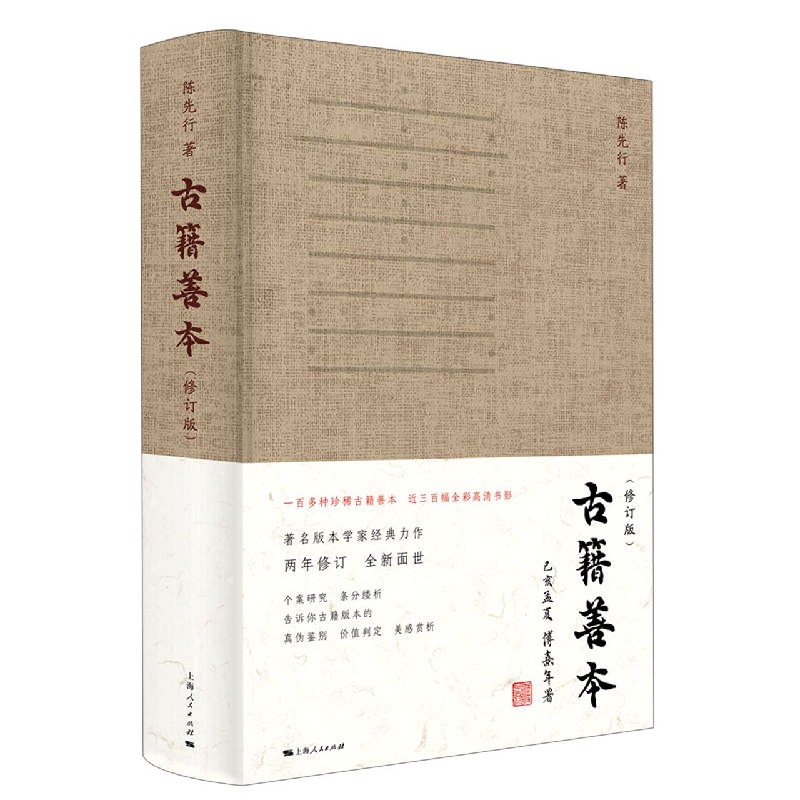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人民
原售价: 480.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古籍善本(修订版)(精)
ISBN: 9787208164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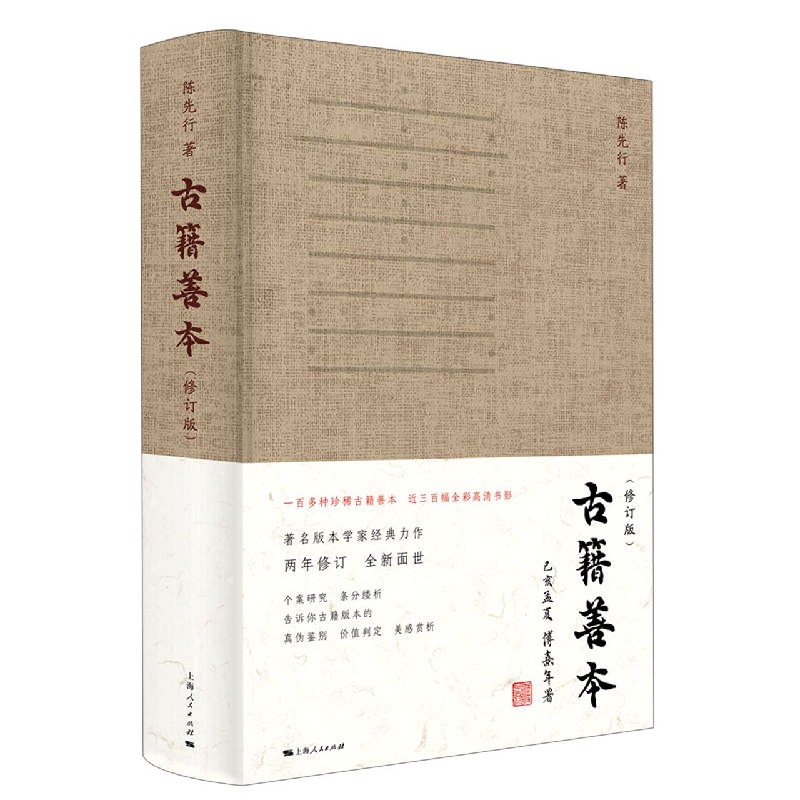
陈先行,195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溧水。1973年入职上海图书馆,从顾廷龙、潘景郑先生习版本、金石之学。长期司事古籍、碑帖考订与编目,先后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图馆藏部分)编纂、《中国丛书综录》修订,并主持编纂上海图书馆普通古籍目录。曾为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访问学者。编著(包括与人合作)有《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明清稿抄校本鉴定》《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等。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北宋刻本《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 2009年以前,孤陋之我,在从事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三十多年中, 没见到过正宗颜书《麻姑仙坛记》字体与柳书《玄秘塔》字体的宋刻本。 自从2009年11月应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邀请访问,相继在宫内厅书陵 部、京都博物馆看到宋版精美颜体小字本《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 绍兴 三年浙江四明刻本)、大字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详刻书年月与刊刻 地),始知之前所见包括北宋《开宝藏》、南宋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在 内的所有两宋蜀刻本,其所谓颜体字都有所变异;同时也了解到,宋代浙 江刻书,并非清一色采用欧体字。因此,当2014 年底西泠拍卖行征集到浙 刻本《妙法莲花经入注》一书时,就其精美的颜书字体,结合其他 相关依据,我认为该本刊刻于北宋末年是完全可能的。 而在此之前,早在2000年上海图书馆购藏常熟翁氏藏书时,因研究 《长短经》的版刻,我已注意到北宋版的欧体字本与南宋版的欧体字本存在 差异。后来数度访书东瀛,又先后经眼了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孝经》《通 典》,大阪杏雨书屋收藏的《史记集解》,京都东福寺收藏的《释氏六帖》 ( 该书日本学界原一直称为《义楚六帖》,定为南宋刻本,经我两度前往鉴 定,得出刻于北宋、剜改修版于南宋的结论,获日本版本学家尾崎康先生 认同)、名古屋真福寺收藏的《礼部韵略》等多部北宋本,了解到北宋版的 欧体字多呈偏狭长形,而南宋版的欧体字(主要是浙刻本),除极个别南宋 初翻刻北宋本尚保留底本旧貌外(如日本天理图书馆藏《通典》),字体大 多已趋方形。故而,以前版本学家们所谓浙刻本“字体方整”的说法,只 能说符合南宋浙本的大致面貌,北宋本则不然。 在认识到北宋及个别南宋初之欧体、颜体字刻本有不同于常见南宋刻本之字体后,有种直觉长期萦绕不去,即历史上应该也有正宗柳体字的北宋版流传。而这部昭庆寺省常上人辑刻的《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卷首那篇大中祥符二年(1009)太常博士通判信州骑都尉钱易撰写的《钱塘西湖昭庆寺结浄社集揔序》,正是正宗的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字体(图2),其余目录、序文、碑铭、正文皆《麻姑仙坛记》字体。若将常见南宋福建刻本流行之柳体字与钱易序文字体相较,其差异洵不可以道里计。 从文本角度判断,此书所收九十人之入西湖昭庆寺莲社诗歌,皆作于 北宋淳化元年(990)至景德三年(1006)之间。苏易简之序撰于淳化二 年(991),宋白之结社碑铭撰于淳化元年,丁谓之序撰于景德三年,而钱 易的总序最后完成,因此,大中祥符二年既是编纂成集的最后之年,应当 亦是该书付梓之时。因钱序写于该年冬十一月,完成雕版未必在同一年, 但相去不会很远。而若从出现颜、柳字体异同,尤其是唯独钱易之序文刻 以柳字的情况分析,还有一种可能或许更加符合版刻实际面貌,即在钱序 撰成之前,该书不但已经编成(可将丁谓之序视为编成时间的断限),而且 在钱易送交序文之时,雕版亦已毕功,则钱易之序为后来增刻者,这从该 书目录未列钱序也可看出端倪。如果包括钱序在内的全书文字同时刊刻, 似无变换字体之必要,因为这些序文等并非著者手书上版,故钱序以柳字 面貌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适成该序文系后来增刻之明证。 由此我甚至认为,即使没有钱氏撰写序文,该书本已成立,故当初很可能已先事开印,即世上曾有无钱氏序文之印本流传也未可知,因为这种现象在雕印古籍的流传中并不鲜见,只是久淹无闻罢了。然则,这篇柳字钱序连同全书得以幸存乃何等可贵,相信伴随研究之深入,人们于其版本学意义的认识将更为深刻。就我目前的经验,这种正宗颜、柳字体同时呈现于一书的宋版,于南宋刻本向所未见,没有刊刻于南宋或更后翻刻的依据。 当然,仅就此本之成书年代及字体变化特点断定为北宋本,尚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人们对宋版字体的接受,还停留在对版本学的传统认识之上。因此,能否找到其他同样“硬性”的凭据证明其确为北宋本,是人们最为关注者。不然,人们对其版刻的认识分歧(或以为是明刻本,或以为是域外刻本)将难以消弭。 虽然迄今没有发现该书有别本单行流传,相关的文献也很缺乏,一时无从考索。但细加检览,发觉原书有一种极易被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实亦该本至迟刊刻于大中祥符年间的有力证据:该书的序文及大多诗歌文字之刊刻,凡遇佛(古佛、毗卢)、法席、宝偈、省常(上人、高人、常师、导师)、昭庆寺(昭庆)、白莲社(社、白莲、莲社)、华严净行品、朝廷(景祚、京师)、君王(圣主)以及三公四辅相关诗社成员等词语,个别作空格抬头,更多的是跳行抬头,以示尊敬。有的从形式上看似未作抬头,然对须表示尊敬之词,特意作了每行字数的调整处理,使其位于行首,实收抬头之效。如钱易之序文,一般每行16字,但“旧相右丞河内向公首缀风骚,相继百数,以国辅之重、辞臣之望”句,为使“国辅”二字抬头,之前一行刻有十七字;“他年入社,愿除陶、谢之俗情”句,为使“社”字抬头,前一行也刻十七字。又如宋白《大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碑铭并序》一文,一般每行十七或十六字,而“杭州昭庆寺僧曰省常”句,为使“昭庆寺”三字抬头,前一行仅刻十五字。而这种现象在正文的入社诗中同样存在,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其正文每行十七字,但第二十六叶上冯亮之诗,首行十八字,次行十七字,即为“除是访师来”句之“师”字、“莲社喜重开”句之“莲社”抬头而设。又如同叶赵干之诗,第三行仅十六字,即为 “况值相君同如社”之“相君”能在第四行抬头而设。因此,该书行字不等者,每出于抬头之需,非率意而为也。然而,也有十数家入社诗遇上述敬词不作抬头者。如李至之诗有“闻师结香社”句,宋湜之诗有“刺身血写华严品”句,张去华之诗有“就中湖上昭庆寺”、“僧有省常方结社”句,李宗谔之诗有“名入莲华社,心依浄行篇”句等,皆不作抬头。尤其是丁谓之作,其所撰《西湖结社诗序》凡遇敬词皆抬头,而其入社诗有“却作莲华社外人”句却又不抬头。 在一书中出现空格与跳行抬头、变更行字抬头以及不作抬头三种情况,告诉人们什么?我的认识是,省常刊刻此集,并未求版式行款的齐整划一而刻意对文字作形式上的编排调整。换言之,他是直接根据序文及入社诗的原稿面貌刊刻的。而且遇敬词抬头并非一律,或有遇此词抬头而他词不抬头者,或有遇他词抬头而此词不抬头者,这也是对原稿未作调整统一的反映。至于更改行字以达抬头目的的情况,也并非省常故意所为,而是一依原稿行款,即原稿看似未换行抬头,实际上是抬头的,为了迎合原稿行文形式,不得不作变更行字处理。省常如此做法极为聪明,也很合理,既表示对作者来稿的绝对尊重,又能藉此真实客观反映当时入社诸人对佛教、结社及省常本人的态度,而后者是省常乐见的,这为其通过结社达到儒佛交融的目的作了最好的宣传。正因为省常采取如此编刻之法,不经意中却为该本乃省常(959—1020,后周显德六年至北宋天禧四年)生前所刻,即该本是此书的原刻本作了最好的证明。如果是后来翻刻,人事、朝代既已变迁,则不可能再出现这种版面“杂乱”的情况,其版式行款也必然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由此想到,通常治版本者对行款都很重视,行款不同,意味本子不同,版本系统可能也不同。然而,对同一本子出现的行字不同,人们往往不怎么重视,以为是刻书者率意而为,于其产生原因缺乏了解。这部北宋本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行字不等在鉴定版本中也是不能忽略的,很可能是定夺系原刻抑或翻刻的一个重要依据。 对于此本是否刊刻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可作进一步研究者尚不止于此,即如避讳与刷印问题,亦是人们聚焦所在,属于绕不开的讨论话题。 此本仅一处出现“竟”字缺笔(第十六叶下谢泌“虎溪人散后,兹会竟谁寻”句),系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之讳。按我们以往的认识,相关之“境”字、赵匡胤始祖名讳之“玄”字也应规避,但书中多次出现,皆未避讳。那么,该本呈避讳粗疏之现象,是否意味着存在版本疑问呢?我并不这么认为。迄今所知,宋代政府对避讳正式提出要求,系从景祐四年 (1037)颁布《礼部韵略》始,之前究竟如何,因未悉官方是否曾有明文规定,不得而知。而南宋学者程大昌、洪迈等凡对宋代避讳有所讨论者,也皆未言及北宋前期文献避讳故实。该本既刊刻在前,自然不能以《礼部韵略》所定之例作为鉴定此本之依据。因此,我们只能将此本视为当时处理避讳的某一种版刻现象,这种现象仅属个别抑或普遍存在,在没有见到更多同时期或更早宋版之前,尚不能妄下结论,但其于研究宋代避讳及鉴定版本无疑具有参考价值。因为此本虽释氏所刻,但该书涉及苏易简、宋白、向敏中、王旦、丁谓等一大批高官政要,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这本来就是结莲社的特质,省常当然不会没有这种政治敏感,倘若当时官方也有像 《礼部韵略》那样对避讳有严格规定,省常岂能轻忽而导致其结社之举功 败垂成?循此思路分析,可以做出推测,在《礼部韵略》颁布之前,避讳 并不严格;这也从另一角度表明,该本至迟刊刻于大中祥符年间是可以确定的。 再谈该本的刷印年代问题。当我甫见此书原本即疑其为北宋所刻时, 书友告知,出于谨慎,已取纸样寄往美国做碳14测试。我虽一向肯定“观 风望气”于鉴定版本之重要作用,同时又强调以“ 观风望气”鉴定版本之 不易,但我也绝不排斥现代科学技术,希望鉴定版本同样能够与时俱进。 然而大家知道,碳14测试只能鉴纸而不能定本,即只能测试出纸张的大概 年代,却无法断定版本的刊刻年代。该本碳14测试的最终结果,其纸张 的制作定在公元1024年至1189年期间,即北宋天圣二年至南宋淳熙十六 年,虽时间跨度较大,宋纸则确定无疑。或许有人会说,是明刻本用宋纸 刷印,甚至说这是一部朝鲜“宋版”,从理论上讲都有可能。但如果结合上 述情况判断,这些说法显然皆不能成立。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即使按 碳14测试出的年代上限,也要晚于大中祥符十数年,又当如何解释?其实 这并不矛盾。稍有鉴定版本经验者,视此本版匡有断缺,文字有残损,便 知其为后印之本。惟此本卷末残缺(其目录所载《紫微舍人孙公结社碑阴》 未见全文),不详是否另有重印跋文,故难以肯定其确切刷印年代。即便如 此,我们结合避讳问题的讨论,并根据其刷印时未及修版的情况,同样可 作出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测:该本之刷印不会晚于景祐四年颁布《礼部韵略》 之后,否则,出于政治因素,虽然省常已圆寂,其后人也必定要对相关避 讳字作重新处理,当然也会对残损之文字进行修补。 此本2015年曾上北京卓德拍卖公司秋拍,最终被海上枫江书屋主人慧 眼收得,在国内二十余年古籍拍卖史上书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从事古籍编目与版本鉴定研究三十余年,本书即为其长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心得的集中体现。全书既有令人信服的实证分析,又有高屋建瓴的理论关照,既有生动有趣的古籍知识,又有简明实用的鉴别方法。对全书所选一百多种珍稀古籍善本细致缜密的版本学考究,足见作者的深厚功力。相比国内本就较少的同类书而言,本书堪称顶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