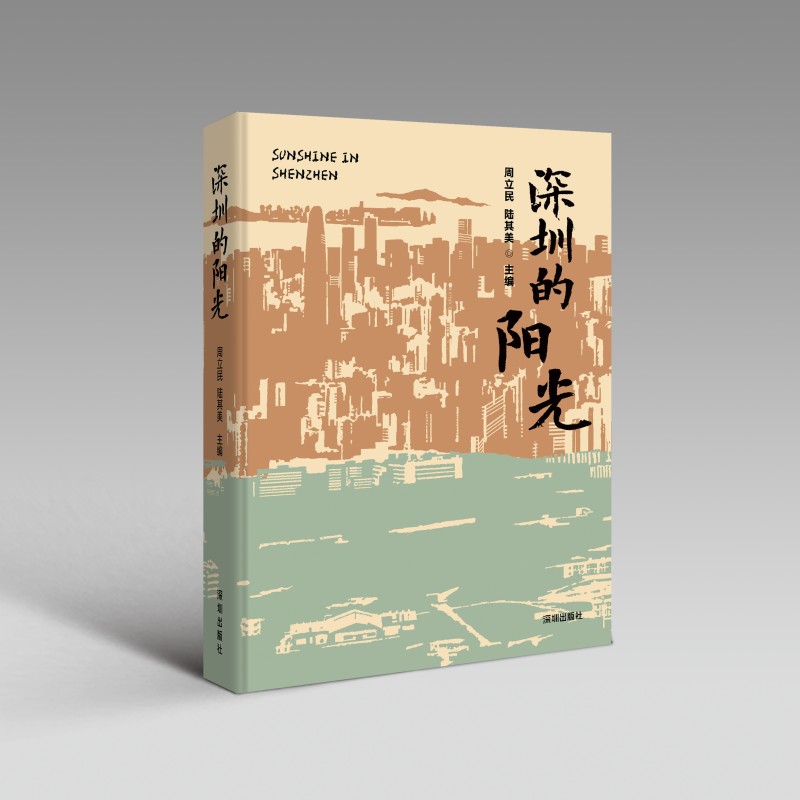
出版社: 深圳
原售价: 89.00
折扣价: 53.40
折扣购买: 深圳的阳光
ISBN: 9787550740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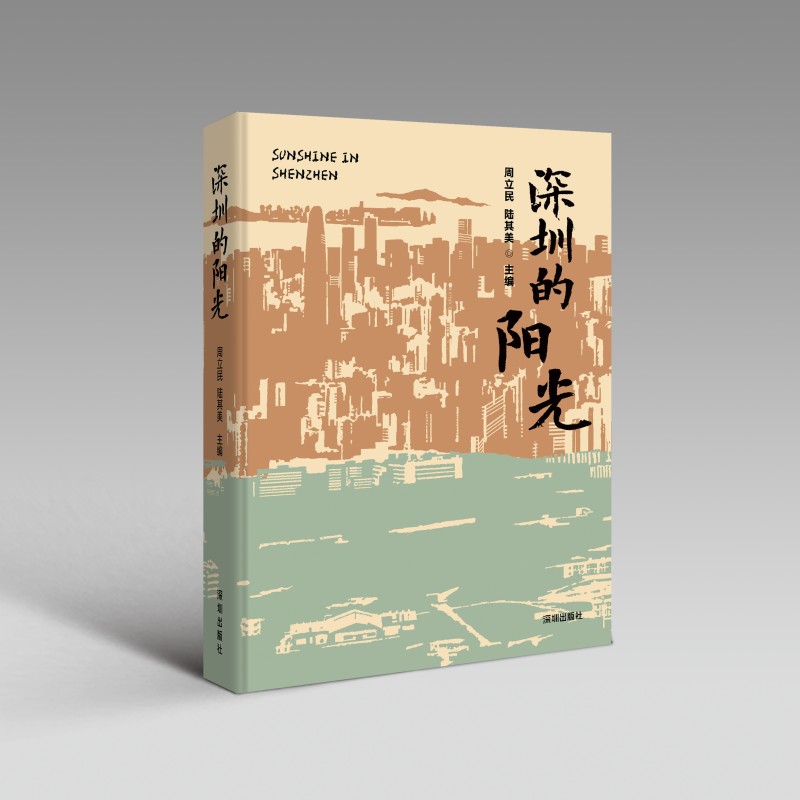
周立民,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出版和全民阅读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坪山文化智库专家、坪山图书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之一,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兼职教授。以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及散文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世俗生活与精神超越》《人间万物与精神碎片》《闲花有声——当代文学研读札记》《巴金画传》《〈随想录〉论稿》《〈随想录〉版本摭谈》《甘棠之华》《躺着读书》等多种。 陆其美,坪山图书馆执行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广东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建设与管理、公共阅读推广等,参与主持国家,省,市课题数项,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主要参与《书话坪山》一书的编辑出版。
我耳朵里的深圳 王? 俊 我很幸运,由于从小喜欢音乐,成年后又恰好从事了跟音乐有关的职业,从而 得以从声音的角度切入我爱的这座城 —深圳。在过去的 20 多年间,我从未间断 与深圳音乐千丝万缕的勾连,用手中的笔,不仅参与创作,也认真地记录在这座城 市上空飘过的歌声,亲身见证了深圳的音乐骄子们如何从这里唱响中国乐坛,又如 何用他们的歌声在这块热土上洒下彩色的音符。 我的耳朵,曾经为这座城市的脉动见证。在密切关注深圳音乐的这些年中,我 能清晰地感受到,在这里震荡着一个强大的声场,无数活泼灵动的音乐形态在这 里摇曳生姿。来自深圳的歌声,实际上推动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起伏跌宕的进程, 映射着一座东方新城拔节生长的声音。 细数歌声的年轮 1998 年 7 月,我大学毕业。坐了 30 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北京辗转来到深 圳,进入深圳电台做一名广播记者。 当我的领导问我想“跑”什么线的时候,我脱口而出就是“音乐”。部门主任当 时还有点诧异,因为音乐乃至文化这条采访线,由于过于“清淡”,其他记者都唯 恐避之而不及的。但我来到深圳,进入电台,为的就是通过各种“曲线救国”的方式,离音乐近些,更近些。于是,从那一刻起,我背起当时沉重如砖头的磁带录音 采访机,就这样进入了深圳音乐的年轮。从音乐记者、音乐公司 CEO、音协主席、 歌词作者到文化馆馆长,我从来没有与音乐脱离干系。 刚刚开始写音乐的时候,注定要面对一种无力感。因为声音的无形性,决定了 它无法像文学、雕塑、绘画、书法那样,为后世留下可以触摸或感知的有形载体。 事实上,在人类所有的精神遗产中,音乐是最难延续流传的。所以,录音手段出现 之前的那几千年的音乐,我们只能通过类似《琵琶行》那样的介质来不靠谱地揣摩 它们本来的样子。谬之千里自然难免。 如今,音乐本体的记录虽已非难事,然而,蕴藏在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情 感、气息和种种外延,依然是那样难以尽录。许多留在我们耳边的音乐,在岁月的 磨砺之后都失去了细节和注解,附着在音乐身上的信息在一遍又一遍的“转录”后 不断衰减,使那些声音与孕育它的生活、土壤和感情断裂开来。 我在深圳采访的第一位本土音乐人,就是作曲家张平老师。张老师当时在市 文化馆工作,人很瘦削,其貌不扬。但很多人都难以想象,他是深圳音乐早期历史 的最权威见证者和亲历者。张平和其兄张钢,是著名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作曲 者张敬安先生的一双儿子。早在 1979 年,刚刚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哥俩就来到 深圳,介入了深圳原创音乐萌芽阶段的发轫。 那时,在深圳经济特区西北部的西丽湖度假村,每到节假日,就有一些港商在 那里的湖边搭起帐篷,举办当时在香港非常流行的“音乐茶座”。张平由于弹得一 手好键盘,成为伴奏乐队的重要一员。乐队的歌手中,有后来由于《血染的风采》 和《让世界充满爱》而走红的著名歌星王虹。 在张平翻箱倒柜给我找出的照片中,我看到了他们这几位深圳早期音乐奠基人 在西丽湖的合影。张平指给我看:“这是周峰、陈汝佳,这是王虹、戴军……”深 圳音乐的滥觞,被他细细讲来,让人不禁感慨。后来,我陆续采访了李盾、陈立等 很多当年的见证者,我们在歌声中回望,到那些承载着岁月印记的旋律中,细数这 座城市的青春 — 上世纪 80 年代的罗湖桥头,返乡探亲的港澳同胞手中拎着的三洋录音机,为 这块最接近“外面的世界”的土地带来了最早的流行之声。在竹园宾馆茶座、香江 凯旋门歌舞厅等当代中国最早的娱乐场所中,响起了电吉他、爵士鼓和内地听众闻所未闻的奔放歌声。 可以说,深圳这座传奇之城的每一段历史,无不有一段与之相配的歌声来佐 证。人们在《夜色阑珊》中品味那改革初期美好的憧憬,在《春天的故事》里重温 那波澜壮阔的激情;听着《丁香花》的倾诉,体会那份清新的感动;和着《最炫民 族风》的节拍,人们将欢乐簇拥。 我常常问这些历史的亲历者,深圳究竟“何德何能”,能够集聚起这样一个澎 湃的声场?在这块被视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土地上,曾经蔓延过怎样的音乐风景?后 来的很多年,我都抱着这份疑惑,细心倾听这座城市里涌动过的声韵。 从《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到《又见西柏坡》《走向复兴》,每到中国当 代历史的重要时刻,总有来自深圳的歌声唱响大江南北,成为时代的重要印迹。从 音乐剧《白蛇传》《卖火柴的小女孩》到《蝶》《酒干倘卖无》,许多崭新的音乐品 种在深圳热土上生根发芽。 从 80 年代的黄格选、戴军、陈明、周峰,到新世纪的周笔畅、陈楚生、唐磊、 姚贝娜、凤凰传奇,深圳为中国流行乐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生力军,成为内地流行 音乐名副其实的“黄埔军校”;从蒋开儒、王佑贵、姚峰,到唐跃生、田地、何沐 阳,深圳让这些一流的词曲作家焕发了他们艺术的“第二春”。 作为一名音乐的记录者,我开始和那些亲历过歌声历史的人们对谈,因为我深 知,我脚下的这座城市,正处在一个介于铭记和遗忘之间的时光节点 —过去的 迅速隐去,未来的如潮而至。我担心一代人与一代人的更替,会让那些美好的声 音细节以一种我们不曾察觉的方式流失。所以,我开始尝试回到那些歌声飞起的源 头,用自己的寻访和记述,为那些过往的声音留下它们应有的刻度。 我深知这种尝试的有限性。毕竟,文字永远无法还原声音本身的那种在场感 和冲击力。对于作为成品的那些音乐作品是怎样地美好、怎样地动听、怎样地渗透 人心,我放弃了描述的努力。我只把自己的工作重点移向那些歌声背后的人,我想 知道,在他们难抑喉嗓、开口歌唱之前,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灵冲动,被卷进了怎样 的人生故事,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动情地释放自己的声音? 聆听中感受城市脉动 2009 年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那端的人自称是“韩阿姨”,她说因为看了我写的深圳音乐史文章,想告诉我一件事:她的儿子 —周峰,现在就 在深圳!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直到我听了韩阿姨讲的周峰那些往事。过了两天,在 深圳特区报业大厦 34 楼的空中花园,我见到了当年叱咤风云的深圳歌坛巨星周峰。 在英国游历 20 多年的他,回到了他事业发端的城市。 上世纪 80 年代初,特区百废待兴之时,周峰的一首《夜色阑珊》,成为深圳飘 向全国的第一首歌。随后他与张平合作,推出了《我是一只孤独的小船》。这两首 歌成为了深圳原创歌曲的闪亮发端。自此,依托于这里兴盛的歌舞厅文化和较早成 熟的文化市场环境,一批有实力的歌手在这里崭露头角。这就是“中国流行音乐始 于深圳”这一说法的由来。 周峰不只是周峰,他的背后,还有一长串响当当的名字。由于深圳的歌舞厅文 化名冠全国,率先成熟的市场环境锤炼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流行歌手。吴涤清、李 春波、黄格选、陈汝佳、戴军、陈明、潘劲东,这些日后赫赫有名的歌手,都在 深圳得到了最早的音乐营养。自然,也留下了无数值得叙说的故事。他们相继从这 里的小舞台走向全国的大舞台,深圳一度成为中国流行歌坛一线歌手的输送基地 之一。 这是深圳音乐的第一波高潮。经过在深圳歌舞厅里“久经沙场”的淬火历练, 这一批台风成熟、魅力四射的歌手成为 1994 年前后中国内地流行歌坛勃兴的主力。 不过,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歌舞厅文化的转型,深圳流行音乐一度陷 入低谷,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歌手更是凤毛麟角。 1996 年,一首旋律优美、角度独特的《春天的故事》,把准了时代的脉搏,传 递着中国的呼吸,体现了深圳音乐人高度的政治敏感与大局意识。从这首歌开始, 深圳的主旋律歌曲创作呈现出“井喷”之势。《在灿烂阳光下》《走进新时代》《长 大后我就成了你》《又见西柏坡》《亲爱的中国我爱你》……每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背后都有精心的策划与词曲作家的呕心沥血。蒋开儒、王佑贵、姚峰、唐跃生、田 地,每一位创作者都有满腔的话在音乐中倾吐。这批唱响大江南北的主旋律佳作, 令深圳音乐形成了第二波高潮,也奠定了深圳原创音乐的基础,形成了较具规模的 词曲作者队伍。他们成为推动深圳歌坛不断创新的原动力。 我和蒋开儒老先生相识 20 多年,我一直认为,他是主旋律歌词创作的天才。 248 | 深圳的阳光 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对当下的时代脉动有着极其敏感的触觉,并能够用 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将这种发自心底的感动投注于笔端,而且具有天然的音 乐性。当然,没有深圳这块热土,就不可能有蒋开儒的“老树开花”;但没有蒋开 儒的热情与敏感,也不可能有后来深圳主旋律歌曲的遍地花开。 进入新世纪,深圳的新移民和城市新一代逐渐成熟,为音乐文化的衍生提供 了更适宜的气候与土壤。深圳市音协与深圳电台音乐频率适时推出了“鹏城歌飞 扬 —原创音乐推动计划”,启动了音乐工程。有了这样的条件,周笔畅、陈楚 生、唐磊、姚贝娜、徐千雅、刘力扬、凤凰传奇、因果兄弟等新生代音乐人和歌手 全面崛起。何沐阳、秋言、张祖嘉等流行音乐作者和制作人也成为深圳音乐的中坚 力量。 2002 年的一个冬夜,我在深圳振华路的“老树咖啡”第一次听到唐磊的歌唱, 那时他还没有成名。唐磊后来跟我说,当他背着一把吉他来到深圳时,只是一个理 科专业出身的音乐门外汉。可是深圳没有因此漠视他的才华,他凭借自己的艺术特 长考进了深圳水务集团,生存得到保障后,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在深圳酒吧舞台上获 得了一席之地。深圳电台音乐频率率先发现了唐磊的才华,屡屡在电波中放送他的 作品。 在电台主持人夏冰、刘洋等的鼓励下,2004 年,唐磊把自己制作的一首简朴的 情歌小样传到互联网上,优美动听而且朴实真挚的歌声很快赢得了网民的追捧。这 首歌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丁香花》,它的点击下载量超过了1000 万次,成为中国 网络音乐的一个奇迹。如今,唐磊的歌唱事业如日中天,然而他在与我的私下交流 中还是由衷地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深圳都是我的家。” 如果说唐磊是移民到深圳的音乐人的代表,“超级女声”亚军、如今已站上歌 坛一线的周笔畅则代表了从小成长在深圳的本土原生音乐力量。周笔畅 6 岁时就来 到了深圳,从小学到中学,她汲取着这座年轻城市的文化营养,她的演唱才华也受 到了很多师长的注意与鼓励。我去过周笔畅的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移民家庭。 周笔畅的父亲周中展对我说:“深圳给了我女儿太多的机会,要不然她不会有今天 的成绩。” 从 2005 年开始,在各大流行音乐比赛和颁奖的星光大道上,走来了越来越多 的深圳人。在各大媒体上和大型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名单中也见到了越来越多的 深圳记忆 | 249 深圳歌手的身影。凤凰传奇组合在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 获得年度亚军。酒吧歌手陈楚生获 2007 年“快乐男声”冠军。深圳女孩刘惜君获 2009 年“快乐女声”第五名。深圳流行音乐星光璀璨的态势令无数人瞩目称奇。 陈楚生夺冠的那晚,我正好在湖南卫视演播厅的现场,看到他披上“金色战 衣”的那一刻,我心里激动难抑。这是深圳音乐的第三波高潮。在这段时期内,深 圳流行音乐的创作和演唱渐渐走向平衡。从深圳走上歌坛的音乐人与歌手呈现出鲜 明的城市特色:他们往往有着内向、笃定、从容淡定的性格,曾经为自己的音乐梦 想蛰伏多年,最初或许并不被人看好,依然把梦想坚持到最后,凭借独树一帜的气 质和出众的音乐才华征服人们的耳朵与心灵。 2010 年后,以“90 后”为力的“深二代”在深圳乐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杨 胜、TooPhat 为代表的说唱音乐人以独特的音乐语言和铿锵节拍直抒胸臆;白天不 亮、陆正为代表的电子音乐高手自成一家,在电脑上鼓捣出了惊艳众人的声音;而 邹锦龙、孟瑞雪等音乐人则把民族音乐元素融入自己的旋律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 的无间融合。 感谢这么多年来我所接触的那些歌手、乐手、制作人。他们其中的不少人虽已 是一线歌星和大牌音乐人,前呼后拥,时间金贵,但冲着对深圳的那份昔日情分, 还是慷慨而耐心地接受了我的询问,细细还原当年。 我把歌声看成植物。在一片荒芜的河滩,与在一片生机勃勃的原野,它们的生 长状态将是那样地不同。为什么偏偏在深圳这座传奇之城,歌声的生长竟能够那 样茂盛?为什么在这块人们来往生息、行色匆匆的新土上,竟然也能沉淀下那样富 有生机的声音?谁赋予了深圳这样的精神造化?谁让这座城市歌声满天? 在这里种下歌声 2020 年,我受聘担任新成立的坪山文化馆馆长。从接受任命的那一天起,我 就暗自下决心,要把原创这件事情,在坪山这块“一张白纸”的土壤上坚定不移地 做下去。 2021 年和 2022 年,两个秋季,在坪山金龟露营小镇的山谷里,有一种歌声回 荡不息。坪山音乐创作营连续两届,分别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同吃、同住、同 创、同唱,25 首新歌整整齐齐、簇新而发,接受人们耳朵的检阅。 歌声一旦种下,就会在雨水中发芽,在阳光里拔节,在心灵的洗礼中壮大。当 歌声响起的那一刻,我心是满足的。我们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闭关而作,心怀理想, 头枕溪流,耳沐山风,笑谈明月,对这块土地报之以歌。如果说深圳歌声有三千 尺,我们又为其增高一米。 我在很多场合都坚持认为:原创音乐,是深圳这座传奇之城胸前最闪亮的一 枚徽章。四十年歌声未辍,名贯大江南北。论影响力和成就,深圳其他艺术门类 都难与音乐比肩。 然而,不必鸵鸟埋头的事实是,近 5—10 年,深圳原创音乐由于缺乏一以贯之 的生态养护,不乏涸泽而渔、焚林而猎,导致后继乏力,多少年没出过有全国影响 的新人大作了? 我至今记得 2009 年 4 月,我和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陈圆圆女士执笔起草 “深圳音乐工程十年规划”时的那些心潮澎湃的日子,那是一个涉及原创音乐全产 业链条的完整规划。那时我们对深圳音乐的未来充满了阳光般的热望,憧憬着有 朝一日这座城市歌声满天。 如今陈圆圆女士已经故去 10 年,她所盼望的那一天仍然有些遥远。我们的城 市对“原创”力量的珍贵性认知匮乏,导致了系统性的政策支持和实质举措波动起 伏,音乐人对环境改善的可感知度有限,直接导致了自发创作的原创冲动萎缩,生 存状况日渐逼仄,体现在明面上,就是“深圳之声”的金字招牌渐趋黯然。 无原创,不文化。在这座城市里,大小明星如鲫过江,喧嚣堂会轰轰烈烈, 如果没有属于自己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声音,那都是过眼烟云。 正是因为深知原创之珍贵,我们才在偏处一隅的坪山创立了坪山音乐创作营。 为的就是让那些光芒未敛的唱作人们,能够暂时地抛开生存焦虑,在明月清风的山 间濯洗初心,为自己而歌,为土地而作,为时代而唱,为这座城市找回那失传已久 的感动。 我当然知道,面对着周围强大的功利惯性,我们的力量是微薄的。坪山文化 馆是个小馆,杠杆有限,我们甚至没有能力把这些无比优秀的作品录制为成品。然 而,能量有限,声量无限。只要我们以杜鹃泣血的精神,把创作营一年接一年地办 下去,让好歌一茬接一茬地破土而出,“在这里种下歌声”就不会是一句空话。这 座城市终将证明,我们歌声里的倔强。 这就是我耳朵里的深圳。每个时间跨度里的深圳音乐,既承接了前行者留下 的精神“锦囊”,又为后来人保存了音乐的火种。深圳在发声,中国在倾听。这些 赤诚的声音,必将与时代的心声形成美妙的共振。 我越来越深知,我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我只愿朝着光亮的地方,蒙眼狂奔。 1.62个人的记忆与情感,一座城市的生长与奇迹 2.茅盾、萧乾、季羡林、黄宗英、南兆旭等人记忆中的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