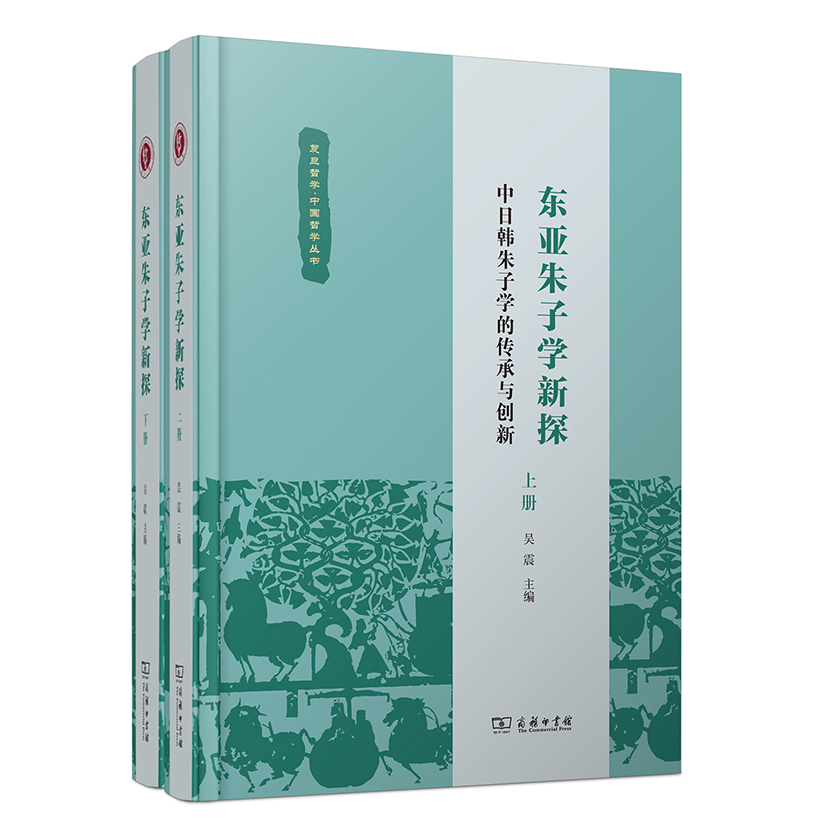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260.00
折扣价: 179.40
折扣购买: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全2册)(复旦哲学·中国哲学丛书)
ISBN: 97871001894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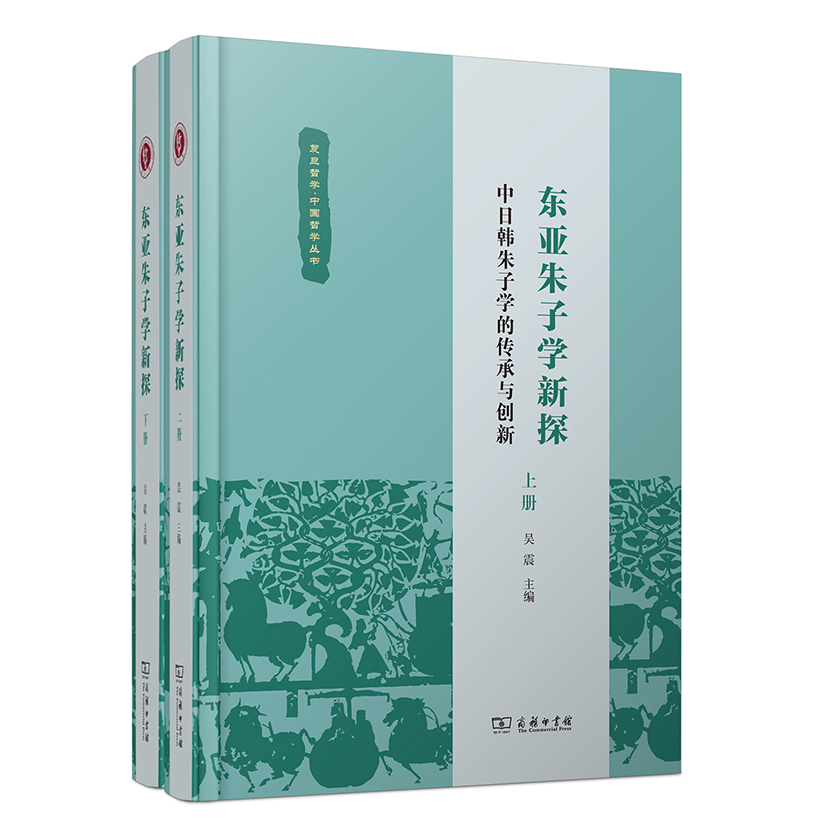
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儒联理事暨学术委员会会员、中国朱子学会理事、日本东洋大学国际哲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日本源了圆国际学会理事。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双聘研究员、台 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日本东洋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COE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等。
第十二章徂徕学对朱子形上学的颠覆 吴 震 前言 日本德川幕府享保十三年戊申(1728)正月十九日,江户城内,漫天大雪,荻生徂徕(字茂卿,1666—1728)病重垂危,他留下的一番“临终”感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海内第一流人物茂卿将殒命,天为使此世界银。 徂徕以“海内第一流人物”自诩,并且说上天为他的行将离世而感动得降下大雪,将世界大地披上银装,语气中透露出徂徕的狂放性格。 徂徕曾在回答学问之外有何爱好的提问时,这样说道: 余无他嗜玩,惟啮炒豆,而诋毁宇宙间人物而已。 所谓“诋毁宇宙间人物”应当是徂徕的一句大实话,这一点从其思想的强烈批判性可以得到印证,徂徕除了孔子以外,孟子、程朱、陆王乃至日本的仁斋等一大批中日儒学史上的第一流人物均不在他的眼里,都是其思想的批判对象。可以说,徂徕学的批判性在“诋毁宇宙间人物”与“海内第一流人物”这两句自述中已经表露无遗。 不仅如此,徂徕还期望着中国“圣人”在日本重现,据徂徕二传弟子汤浅常山(1708—1781)《文会杂记》所载,徂徕平时常念叨一句话: 徂徕每自言:“熊泽之知,伊藤之行,加之以我之学,则东海始出一圣人。” “东海”这是古代中国对日本的一个称呼,熊泽即阳明学派中江藤树(1608—1648)弟子熊泽蕃山(1619—1691),他的“经世论”在江户时代很出名,伊藤即古学派代表人物伊藤仁斋(1627—1705),以恢复儒学古义为一生事业。关于熊泽,徂徕所言不多,至于仁斋,则是徂徕中年以后的攻击对象,但他对此二人都表示了尊重,徂徕曾说熊泽和仁斋是德川之世百年来的两位“儒者巨擘”,余者皆碌碌之辈。 可证上引汤浅常山之记述当非虚言。 其实,“圣人”概念在徂徕的心目中分量很重。按照他的历史观来判断,“圣人”产自中国,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广义上还可包括伏羲、神农和黄帝,孔子因其诏述六经有功而亦可算是圣人。徂徕对圣人有一项严格定义:“圣者作者之称也”。 所谓“作者”盖谓圣人“制作礼乐”, 据此,圣人必须是能为天下制定礼乐秩序的拥有君主地位的天子,故圣人又等同于“天子”, 不仅如此,圣人制作礼乐须符合“天时”,只有在“革命之秋”才可能实现。 因此,中国圣人唯存在于上古“而今无圣人”, 至于日本则从未有过圣人,他说:“东海不出圣人,西海不出圣人”。 然而,现在我们却得知徂徕心中其实渴望着“东海”有圣人重现于世。只是徂徕纵有冲天之豪气,尚不至于以“圣人”自许。 可是,若从学术立场出发,徂徕却坚信圣人之道在孔子之后的彼邦中国既已踏上日薄西山之一途,及至宋儒以降则已完全失传,甚至宋代大儒朱熹或者德川大儒仁斋都无以承担起重振圣人之道的大任,惟有他才有资格担此大任,这由其亲口所述可以为证: 呜呼,孔子没而千有余年,道至今日而始明焉,岂不佞之力哉!天之命之也。不佞藉此而死不朽矣! 若与徂徕自许“海内第一流人物”合观,可以断言上述这句徂徕语不啻是说“孔子之后第一人”非他莫属,而且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他亦可藉此而“永垂不朽”了。 至此,我们不禁会想:徂徕到底是何许人也?徂徕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 问题由来:“近代性”与“日本化” 在德川(1603—1868)思想史上,荻生徂徕可谓是一位尽领时代风骚的人物,没有他的存在,整个德川思想史将会索然无趣、褪色不少。而他的学说及其所开创的“蘐园学派”在享保年间(1716—1735)既已“风靡一世”,引起了“海内翕然,风靡云集,我邦艺文为之一新”的巨大反响。 然而与此同时,徂徕学在德川中期直至幕末所引发的争议也从未中断过,甚至有一股“反徂徕学”的思潮出现。 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徂徕“诋毁宇宙间人物”过甚,故其引发的反弹也就格外强烈, 但更重要的原因显然在于徂徕学的产生在德川思想史上意味着一场“事件”,甚至也是东亚儒学思想史上的一场“事件”, 因为徂徕学不仅是仁斋学的“反命题”,更是孟子学、朱子学的“反命题”, 所以说徂徕学的“事件性”不仅限于日本,也正由此,故有必要将徂徕学置于东亚儒学的视野中来加以审视和评估。 徂徕学在18世纪初诞生以来,对于德川儒学而言,从来就是一个热议话题,近代以后更是不寂寞。虽然在1790年由幕府推动的以尊崇朱子学为口号的“宽政异学之禁”中一度受到严厉打压,但在明治维新一切向西方看齐的近代化运动中,徂徕学的“近代性”很快被不少进步知识人重新发现,明治早期的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和加藤弘之(1836—1916),还有明治晚期的山路爱山(1865—1917)《荻生徂徕》(1893)以及近代的“御用学者”井上哲次郎(1855—1944)《日本古学派之研究》(1902),都从徂徕学那里发现了近代西方思想特别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因素,以此证明日本“近代化”是有本土思想资源的。直至1945年战后日本学界,这种探寻“近代性”思想根源的研究方式依然强势,例如徂徕学之研究大家今中宽司也将徂徕学的特质定位为功利主义,只是他将视角转向中国宋代,以为叶适和陈亮的功利主义可能与徂徕学具有某些亲缘性,构成了东亚形态的功利主义而并不尽同于西方近代的功利主义形态。 对于战后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具有奠基作用的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虽然其审视角度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功利主义,但他认定徂徕为日本近代精神的先驱,是日本由近世(前近代)迈向近代的代表人物,故“近代性”恰恰是其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丸山认为近代性思维的形成有两个主要指标:一是政治与道德由浑沦不分趋向分离的过程;一是由自然的秩序原理向人为的秩序观发生转化的过程(即秩序规范不再是自然之理所规定的而是人为的重建)。这两个分离过程意味着思想的重大转型,在德川思想史上主要就表现为朱子学的瓦解到徂徕学的确立。按照丸山的分析,徂徕学的“近代性”就表现为:朱子学的“规范与自然的连续性被一刀两断”,“治国平天下从修身齐家中独立出来另立门户,这样,朱子学的连续性思维在此已完全解体,一切都走向了独立化。” 对于丸山的这套徂徕学解释,子安宣邦不无严厉地指出,徂徕学的历史图像就这样被近代主义者丸山真男“虚构”了出来,直至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毫不犹疑地用徂徕学来叙述日本近代思维的产生。 可见,徂徕学几乎成了如何理解日本“近代性”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须指出,徂徕学是否具有日本近代思维的萌芽等问题则有近代日本走过的那段曲折历史的背景因素在内,非本文所能深论。质言之,日本的“近代性”问题之实质其实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性”(即“现代性”)问题在日本社会的一种折射。就丸山的徂徕学研究而言,甚至“何谓近代”也不是他关注的核心,他所要努力寻求的是,在日本人的意识深处到底什么是“日本性的东西”(“日本的なもの”)成了明治以降近代化道路的阻碍因素,在他看来,日本的近代化甚至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无疑,我们不能否认丸山的问题意识相当重要,他的徂徕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典范意义,但问题在于经过他的解读之后,徂徕学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徂徕学,而是经过他自己的“近代主义”的想像而重构起来的。当然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看,任何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必然伴随着诠释者的“前见意识”,不可能达到解释结论的纯粹客观,在这个意义上说,丸山的徂徕学研究带有强烈的时代批判意识,因而其诠释结论也就带有其强烈的时代色彩,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就徂徕学研究而言,“近代性”问题的预设是否必要,确有反思的余地。 在当代日本的徂徕学研究领域,无论是赞成者还是批评者,人们都无法绕过丸山的徂徕研究。在众多的批评者当中,尾藤正英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虽然也赞同儒学传入日本之后必然遇到“日本化”的问题,但是他反对由“近代主义”的视角来为徂徕学定位,他认为与其将徂徕思想放入由“封建”向“近代”挺进这一时间序列中加以定位,还不如转换我们审视问题的视角,将徂徕思想置于“由中国思想向日本思想发生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更能真切地把握徂徕学的特质。 另一位日本思想史研究家泽井启一对于上面提到的种种从日本近世当中努力寻找“近代性”的研究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丸山的徂徕研究之问题就在于其审视眼光仅仅集中在徂徕身上,而中国儒学(朱子学)则被置于视域之外,于是,“近代”的问题似乎只是日本的问题,而明治以降的近代日本的历史走向才是“东亚唯一的近代”而被“特权化”。 为此,泽井主张应当把徂徕学置于“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的交错背景中来考察,如此才能发现和理解儒学在日本“土着化”(意同“本土化”或“在地化”)过程中徂徕学所具有的意义。 须注意的是,泽井特意指出“土着化”不同于“日本化”,因为在“日本化”这一概念中已经先预设一种“日本固有的东西”存在,然后外来文化都必然与此“同化”——即“日本化”。泽井认为这其实是一种“闭止域”(即“封闭性”)的思维态度,是不可取的,而“土着化”则是指“东亚各地域共通的儒学渗透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土着化”过程。 诚然,这种与日本“同化”的所谓“日本化”缺乏建设性和开但是如果我们不以辞害意,在中国思想转入日本之后必发生思想转化这层意义上使用“日本化”恐怕也未尝不可,犹如佛教传入中国而有中国佛教,传入日本而有日本佛教一样,都是中国化和日本化的结果。泽井倡导使用的“日本儒学”其实就是“日本化”的儒学,在此场合,若使用“土着化儒学”反而不能显示出“日本儒学”的蕴涵。本文也正是在“日本化”的意义上,使用“日本儒学”这一概念,凡是日本历史上的儒者所建构的思想学说,都属于日本儒学的范围。 本文所关心的是,通过对后孔子时代的儒学理论进行全面批判而建构起来的所谓“徂徕学”对于我们理解德川思想乃至日本儒学究竟有何意义的问题。当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待本文的展开,但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不妨将几句简单的结论揭示如下,以便在进入徂徕学的思想世界之前,有一条基本线索可供参考: 徂徕学的思想特质是:以回归孔子为口号,以批判宋儒为手段,以古言古义为依托,以制度重建为归趣。对其思想的历史定位不妨可以这样表述:徂徕学将山鹿素行、伊藤仁斋等着手推动的“儒学日本化”的事业全面提速,加快了中国思想转化为日本思想的历史进程,徂徕学对朱子学的公然挑战意味着中国文化一家独大的局面将被改观,预示着德川思想的下一波新动向是在与中华文化一元论的对抗背景中,日本文化自负情结逐渐高涨乃至趋向膨胀。 ………… 山川异域,风月何必同天,本书是汉语学界对中日韩东亚三国朱熹哲学近500年研究传播史的首次整体展示。这本论文集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日韩儒家哲学的部分,它为中国知识界的非该领域的读者提供了新视野、新知识,相关篇章,比如对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王朝时代几位思想大家的朱子学研究的论述,极为精彩! 由此可知,所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者,并非实情可言。日本儒学的独立性,也即日本文化的独立性,在朱子学的发展上特色非常鲜明,这一点,日本人比中国人要清醒得多;倒是历来有事大传统的朝鲜半岛,其儒学的发展明显体现出对中国传统的亲和性,这个特征在朱子学的发展上也得到了深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