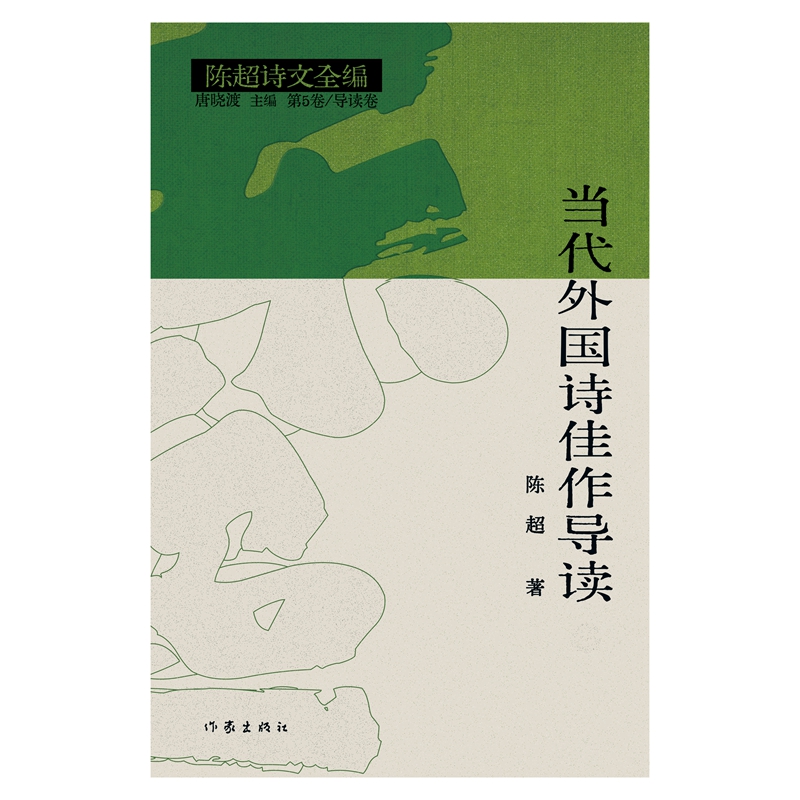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198.00
折扣价: 152.16
折扣购买: 当代外国诗佳作导读 (上下)
ISBN: 97875212305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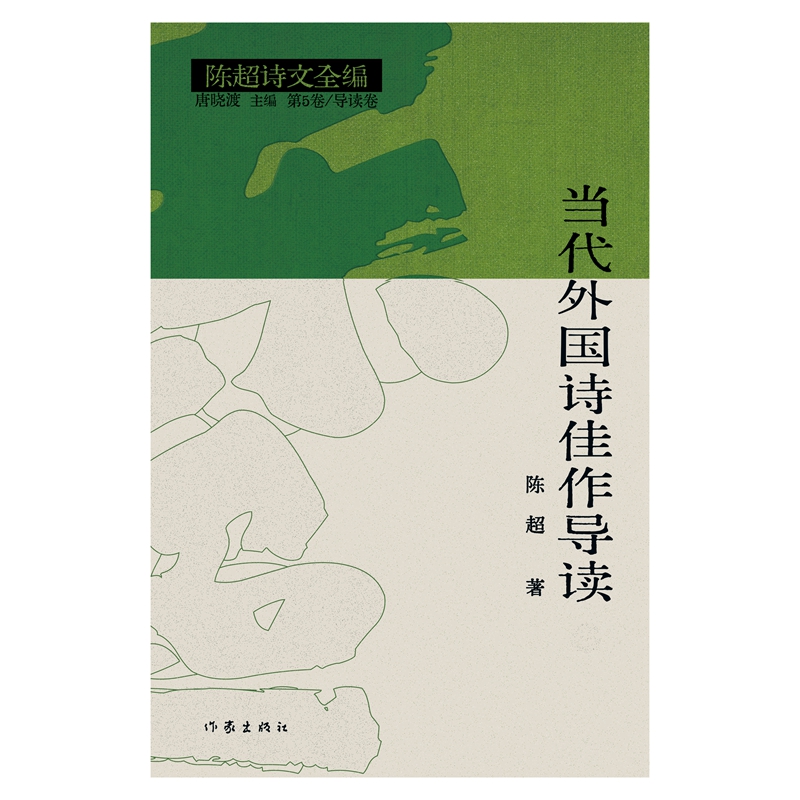
陈超(1958一2014),当代诗歌评论家、诗人。生于山西太原,辞世前系河北 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的诗学和批评论著包括《中国先锋诗歌论》 《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游荡者说》《精神重 力与个人词源》《诗与真新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20世纪中国探索诗 鉴赏》(两卷本)《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两卷本)等;著有诗集《热爱,是 的》《陈超短诗选》(英汉对照)等。
美国 罗伯特?潘?沃伦 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 Warren,1905—1989)生于肯塔基州,1925年毕业于范德比尔特大学,后在加利福尼亚和耶鲁大学继续求学,1927年获硕士学位。沃伦是当代美国诗坛承上启下的人物之一。十六岁认识兰色姆,参加“流亡者”诗派。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新批评派”重要批评家。他提出的“诗必须包含复杂的相互矛盾的因素”,反对狭隘的纯诗论,扩大诗歌处理复杂经验的范围,对当代诗人有很大影响。他与布鲁克斯合著的《理解诗歌》《理解小说》,是“新批评派”影响最大的著作。 沃伦长期在美国南方各大学执教,1950年起任耶鲁大学教授,主持该大学文学系,是“新批评派”后期中心“耶鲁集团”核心人物。早期诗作语象曲折繁富,有较重的智性/玄学色彩,晚年作品清朗而内在,在处理日常经验中含有形而上品质。沃伦在诗歌、小说、文学理论、文学编辑等方面都有显著成就,他的作品体现了对生存/人性和技艺的双重关注。 沃伦的代表性作品有:诗集《诗三十六首》(1935),《同一主题的诗十一首》(1942),《1923—1943年诗选》(1944),《龙族的兄弟》(1953),《自选集》(1981)。论著《理解诗歌》(1943),《文选》(1958)。长篇小说《国王的全班人马》(1946)等。1947年获普利策文学奖(小说),1948年获普利策文学奖(诗歌)。1985年根据美国国会决定,沃伦成为美国第一位桂冠诗人。 未来的旧照片 那注意力的中心—— 一张幼稚的脸 多年以前(想必是)白里透红—— 现已褪色;在相片里只剩一点 灰白,没有多少表情显现。 那注意力的中心,在白色襁褓里, 那是妇人的宝贝;她漂亮而年轻, 面带蒙福的讶异神色,偎依 那迸生出的神秘奇迹。 在稍后的地方,那雄伟的身材 朦胧浮现,脸上闪烁着成就和自豪。 穿着黑色外套,礼帽罩在胸前,他迫不及待 要向你保证世界太平——把烦恼抛开。 相片已经褪色得厉害。岂不合理? 到了七十五岁上下事事都显得老旧, 而这张相片正是那年纪。 那对夫妇,当然,已经不在人世。 他们带着剩下的爱情,并排躺 在绿草,或白雪,之下;那婴儿,多年后,站在那里; 旧景模糊,而他满怀罪咎地神伤 于无名的许诺未践,颓然莫可名状。 (彭镜禧 夏燕生 译) [导读] 这首诗带有很强的叙述性。但它不是线条式的平铺直叙,其叙述时间在这里颇为讲究。它采取了倒叙、预叙、现在时叙述三者交错扭结的方法,使整体叙述的时间段不仅具有长度,更有着深度和幅度,成为既有现实经验重量,又有浓郁象征意义的对生存和生命情境的命名。 所谓“未来的旧照片”,是诗人叙述的基点之一。“预叙”在时态上提醒你,“我是预先向未来看的”。诗中所言“那婴儿,多年后,站在那里”缅怀双亲,暗示了生命虽有诸多偶然,但唯一的必然乃是人生命的衰朽和终有一死。人是世间万物中唯一能预知自己有“时间境域”的生物。 然而,奇异的是,诗人的“预叙”又与倒叙混而难辨,“预叙”的内容已被时光证实。这样一来,说话人的时间基点变得飘移不定,时间在此不是线性的物理时间,而成为主体经验着的时间;诗人穿插进行了三种暧昧的时态叙述,使作品在广泛的暗示功能中,具有着具体本真的特指性。这张照片上有一家三口人,是体面的中产阶级“成功人士”之家。你瞧,那年轻的父亲,有“雄伟的身材”,“脸上闪烁着成就和自豪/穿着黑色外套,礼帽罩在胸前,他迫不及待/要向你保证世界太平——把烦恼抛开”。那母亲,“漂亮而年轻/面带蒙福的讶异神色”,偎依着她的小宝贝——“那迸生出的神秘奇迹”。这里的“蒙福的讶异”和“神秘奇迹”,在措辞上模拟了圣经《新约》中玛利亚蒙圣灵之福受孕,耶稣降生的神秘奇迹。父母亲的意象用在这里,含着微微的反讽性质。早期自由社会的竞争理念和新教伦理已渐渐丧失了活力,今天,世界仍不“太平”,新的“烦恼”又滚滚而来,他们的“后代”已是“满怀罪咎地神伤/于无名的许诺未践,颓然莫可名状”。 “那注意力的中心”究竟是什么?既是指人生命的衰败,又是指人类精神历史荒诞的蜕化。但诗人不屑于采用滥情的方式说出,而是将三种叙述时间交错扭结,于冷静、克制中传导出了对生命和生存淡淡的缅怀和内在的宿命感。 爱的诞生 季节已晚,日子已晚,太阳刚落,天空 铁锌般寒冷但带着一朵盛开玫瑰的鲜艳,而她, 天空的颜色从水中跃出只有 她的动将它破碎,震颤着银色的碎片 伫立在初生的草丛上。在云杉新凝固的夜幕下, 赤裸闪烁,自胸怀和两肋 滴洒流银。人, 游出十臂远,此刻一动不动 悬在铁锌般的水中,双足 被深处的寒冷冷却,所有的 历史在他身上消溶,只溶为 一只眼睛。只一只眼睛。看见 身体带着有用的标志,时光 升起,在空气那急迅而不持久的元素中 摇摆、倾斜,扭住了池塘的岸。看见 女性难堪的姿势 怎样突然间变得优雅 那是乳房的一侧,由它们的重量和臀部的纯曲线鼓满 升起的月亮,在那膨胀的一体 都是银,和微光。于是, 身体竖起,她恢复了原状,无论 她的原状是什么,将浴巾的两端抓在两手 缓缓地来回曳拉越过背和臀,但 脸庞向着高空举起,那里 玫瑰已被洗得褪色。褪色了,尽管 没有星星在那里悸动。目光仍固定在空中。身体 侧对着云杉的黑暗,仿佛 要被它吸引,浓缩为它的白色,什么光 在天空仍依依不去,或者从 水中金属和抽象的严肃中提起。身体, 浴巾此时已从一只手中滑落, 是一根白色的茎管,脸庞从中向天空 郑重地开放。 这一时刻不会持续而且绝对,不接受 任何定义,因为它 为其他的一切归类,持续性、时刻 这些定义才会可能。女人 尚未抬起脸,裹在运动里, 仿佛站立在睡梦, 她身上的浴巾,盖在乳房以下 如湮没的埃及那种神圣的屹立 走上那条梯级陡峭的路,迂回 走进攀登和生物的交织。在 黄昏垂下的树叶网络中,白色 幽暗地忽闪而去。忽闪而去,男人 悬挂在他暗淡下来的媒介上,向上凝望 虽然什么也不见,但他知道她在动 他在心中呼喊,假如他有这般力量 他将伸出手放在她身上守卫,在她所有的 去和来中,阻止一切天空的冷酷 和世间的污染。他在心中 呼喊。在 云杉夜的高度和远山的喘息中,他看见 第一颗星星,蓦然诞生。它在那儿闪耀。 我不知道他许了什么诺言。 (汤潮 译) [导读] 这首诗仍然带有叙事性。但优异的诗歌叙事不是只有单一的时空维度,它应饱含着超越叙事的寓言功能。这是一幅“窥视”浴女的场景,然而读后我们并不感到一丝猥亵。对生命之美、人体之美,诗人充满了纯洁的赞叹和深沉的省思。 “他”在深秋黄昏的河水中游泳,不期然中见到河畔草丛上洗浴的姑娘。她像铁锌般寒冷笼罩的时空中一朵鲜润的玫瑰,像人类远古时代的埃及美神。诗人限制了叙述速度,甚至分解了浴女的动作,使她的美、和谐、纯真,细腻地一点点呈现,令人凝神。“身体/浴巾此时已从一只手中滑落/是一根白色的茎管,脸庞从中向天空/郑重地开放”。这里,茎管的意象,表现了她与大地相连的蓬勃生命活力;而“向天空郑重地开放”,则昭示了生命和精神汰洗后的升华,她与“第一颗星星蓦然诞生”构成对称,互为隐喻。 “他”望着这一切,生命瞬时变得单纯而美好:“所有的历史在他身上消溶,只溶为/一只眼睛。只一只眼睛。”这是“绝对”的一刻,“不接受任何定义,因为它/为其他的一切归类”——守卫人类的爱、美、善、自由,这责任是绝对的,是从“水中金属和抽象的严肃中提起”的“向上凝望”。为了这些,人类要“在她所有的去和来中/阻止一切天空的冷酷和世间的污染”。至此,浴女已进入寓言范畴,像画家塞尚的名作《大浴女》(1805)一样传导出渴望生命和灵魂双重洞开的澄明心境。 诗人最后说,“我不知道他许了什么诺言”。这个句型饶有深意。首先对诗中之“他”而言,这是无疑而问。但其潜台词对更广义的“我们、你们、他们”而言,则带有深深的祈使、质询乃至痛惜色彩。 世事沧桑话鸣鸟 那只是一只鸟在晚上鸣叫,认不出是什么鸟, 当我从泉边取水回来,走过满是石头的牧场, 我站得那么静,头上的天空和水桶里的天空一样静。 多少年过去,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有的人已谢世, 而我站在远方,夜那么静,我终于肯定 我 最怀念的,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而是鸟鸣时那种宁静。 (赵毅衡 译) [导读] 在美国文学的源头,我们常常看到诗人、作家对宁静的大自然和动物的赞叹,惠特曼写过“我愿意自己能回头,去与动物共同生活,它们是如此宁静和自足……全世界没有一头动物是有名望的或不幸的”(《自我之歌》)。而爱默生则说,“喜爱自然的人,其内、外的感觉一致;他把童年的精神状态保留到成年。与自然的交流成为他每日的需要。在那里我知道此生不会有什么遭遇——没有耻辱、没有困苦(只要我尚保持眼望自然的视力):大自然会帮助解决”(《自然和精神》)。不是说人生没有困苦,世事不再沧桑,而是说人心应有更内在的静谧澄明之境,与大自然开合注息,领悟那超逾世俗功利的宁静之美。 沃伦的诗也秉承了先辈的审美慧命。他更将抽象的大自然和统称的动物界凝缩成一只鸟,而且这还不够,又具体为“鸟鸣”,就更为智慧而准确地传达了对宁静的大自然以及与大自然对等同构的心境的缅怀与渴慕。多少年过去,见过的人已渐渐远逝,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我最怀念的”,不是功利性的“世事沧桑”,“而是鸟鸣时那种宁静”,是人返回其自然之根时体验到的永恒之美。 伊丽莎白?毕晓普 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生于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她是“二战”之后美国“中间代”诗人中最负盛名的女诗人。1934年她即将于伐沙尔学院毕业时,结识了女诗人玛丽安?摩尔。摩尔以对动植物生命体的细节描绘来展开诗歌隐喻的方法给了她很大的启示。她的第一本诗集《北与南》于1946年出版,引起广泛注意。此后,连续出版多种诗集,以意味和形式的优异质地建立了国际声誉。1952年至1969年,诗人客居巴西,并多次游历了欧洲和非洲等地。 毕晓普诗歌的特性是避免浮泛的抒情、自我迷恋,她力求深入客观事象,既细致、准确、犀利地呈现它们,又于其中寄寓着揭示生存和生命的深刻的暗示性。正如西默斯?希尼在《数到一百:论伊丽莎白?毕晓普》一文中所说:“没有人比她更醉心于认识世界细枝末节的奇迹,也没有人更小心翼翼地容纳下那些共同阐释了生活的危险的负面因素”,“在滔滔不绝的方面,看来她证明了越少即是越多。借助于对传统的认知与分寸感,她创造了一种与往昔经典诗作保持连续性但又完全是个人的、当代的风格。她的写作技艺精湛、形式完美,从专业角度看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 毕晓普的主要诗集有:《北与南》(1946),《诗集》(1955),《旅行之间》(1965),《诗全集》(1969),《地理第三册》(1976),《诗选:1927—1979》(1980)。1955年《北与南》获普利策文学奖,1969年《诗全集》获全国图书奖。 小习作 想想天空中徘徊的令人不安的风暴 像一只狗在寻找安身之处 听听它的咆哮 在黑暗中,那些红木门栓 对它的注视毫无反应 那粗制纤维组成的巢穴, 那里偶然有一只鹭鸟会低垂自己的脑袋 抖着羽毛,嘴里发着无人理解的自语 当周围的水开始闪亮。 想想林荫大道和小棕榈树 所有行列中的躯干突然闪现 像一把把柔弱的鱼骨。 那里在下雨。人行道上 每一条缝隙里的杂草 被击打、被浸湿,海水变得新鲜。 现在风暴再次离去,轻微的 序列,猛然照亮了战争的场景 每一个都在“田野的另一个地方”。 想想拴在红木桩或桥柱上的游艇中 某个沉睡的人 想想他似乎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一丝惊扰。 (马骅 译) [导读] “小习作”这一命题有双重寓意。其一,从写作技艺上说,是诗人在进行某种修辞和结构实验。它的修辞实验体现在,诗人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分别对独立的事象细节进行了素描,天空、小狗、鹭鸟、树木、杂草、海水、游艇、沉睡的人,无不形神毕肖,呼之欲出。它的结构实验体现在,几项彼此似乎是独立的事象,被结合在一个有机的话语场中,像一组群雕,以其空间感的均衡,“共振”出其内在的统一暗示性。在写作技艺的意义上,它的确是“小习作”(取其修辞与结构实验之意)。其二,反讽性克制陈述的寓意。我们注意到,诗中描述的事象在冷静的日常情境状态下却又充满内在的紧张感:天空中徘徊着令人不安的风暴,像狗在无告地咆哮着寻找安身之处。鹭鸟脑袋低垂,嘴里发出无人理解的自语。树木像一把尖利又柔弱的鱼骨。海水因涨潮变得新鲜,而某人还沉睡在游艇中。在此,平静感与不祥感奇异地反向拉开,诗中“和弦”般的隐喻系列使人既迷醉又惊悚。 这首诗写于1947年,“二战”的硝烟刚刚平息,“风暴再次离去”,但令人恐怖的惨痛经验已噬心地刻在人的记忆中,它们随时会在心象的“轻微序列,猛然照亮战争的场景”。有如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名画《内战的预感》一样,对战争的恐怖甚至已点点滴滴侵入了人的梦境。在此,“某个沉睡的人/想想他似乎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一丝惊扰”,就含有沉痛的反讽性。诗人祈愿“他”和平的不受惊扰的人生成为恒久的现实,而不是即刻的“小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