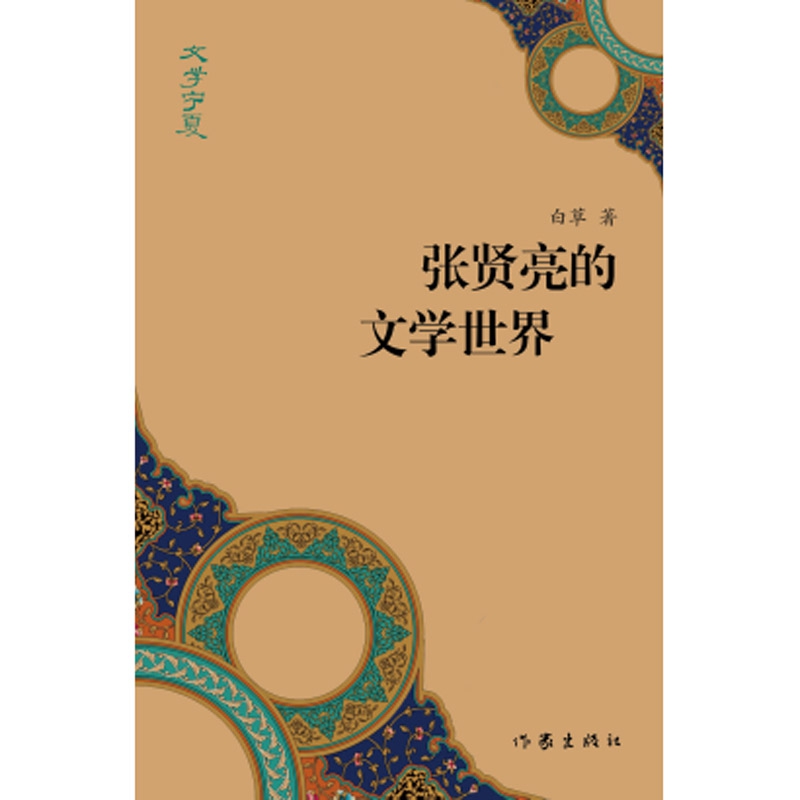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4.00
折扣价: 30.82
折扣购买: 张贤亮的文学世界/文学宁夏
ISBN: 97875212017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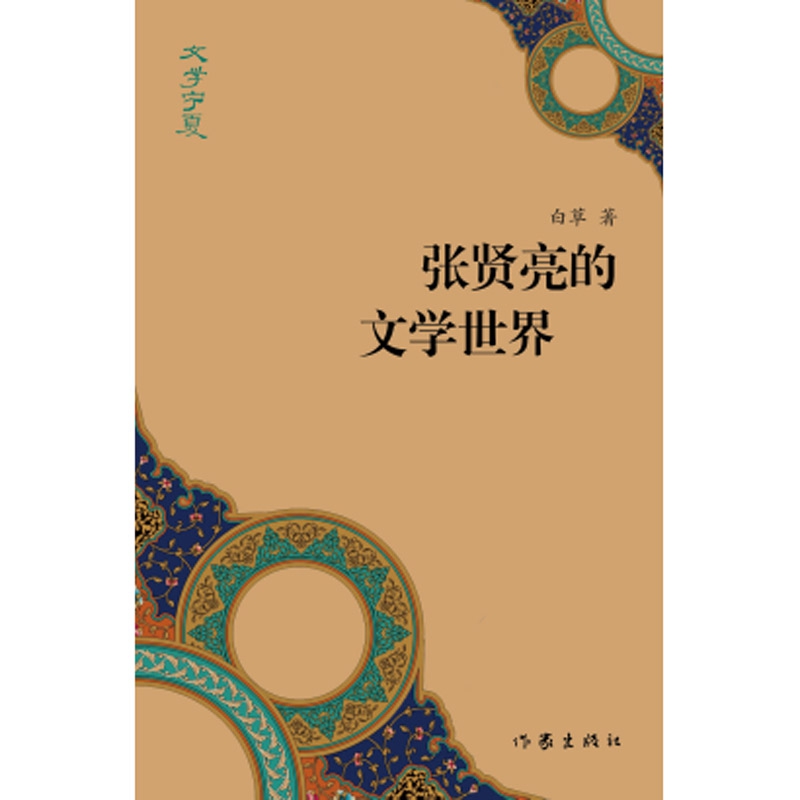
白草,宁夏海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专著《文学大家笔下的回族》《宁夏当代文学十四家》,另有论文多篇。2001年获宁夏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三等奖,2002年获宁夏第六次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二等奖,2006年获宁夏第七次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三等奖,2016年获第二届《朔方》文学奖,2017年获《黄河文学》双年奖。
绪论 张贤亮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作家,尽管他的影响自《我的菩提树》(1992年)之后日渐式微,终至淡出文坛,但事实上他已成为一个文学传统——一个优秀的传统,一个复杂的传统。 面对传统,无法绕行:喜欢也好,讨厌也罢,它会曲曲折折地与后来者产生联系,并施以影响。 诗人张贤亮 了解一个作家,须顾及其全体。张贤亮曾经是一个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诗人张贤亮,就没有后来的小说家张贤亮:诗歌创作,是他的一次出色、出众的文学预演,如果不是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中断写作,当代文学史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诗人。 历史有时颇冷酷,然而文学力量或许更为强大,文学史上被夺走了一个诗人,却多出了一个小说大家。 张贤亮有三首诗歌,全部作于1957年,皆为上乘之作,充分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以下试各摘录数节,以见其一斑。 《夜》: 夜 我躺在星空下面, 在垦荒队的帐篷旁边。 周围是一片寂静, 风从小树林那边 吹来了槐花和土地的香气。 星星…… 我眷恋地听着,我久久地听着, 我激动地听着,我流着泪听着, 啊!我的祖国,就是夜里你也醒着! 你和我们播种的小麦一样, 你永远在生长着、成熟着、产生着新的种子, 不管白天或黑夜, 你永远在前进、在燃烧、在喧闹、在诞生着新的歌。 啊!祖国,就是夜里你也醒着!①[① 张贤亮:《夜》,《延河》1957年1月号。后收入《张贤亮选集》(一)。 ] 《在傍晚唱的歌》: 在这傍晚的时刻, 在这爱情和劳动的边缘, 我站在高高的麦垛上, 大地,从那空濛的雾气中上升, 向我伸过来 母亲丰满的嘴唇。 …… 我站在最高的麦垛上, 从心灵的窗户向世界瞭望, 我的情思,我感激你! 你告诉了我祖国现在做的、将来做的、永久在做的事情。 啊!祖国,你是我爱人的爱,你是我母亲的亲, 你是每日每夜伴着我的身影, 你是一条欢乐的河, 奔流着、翻滚着大大小小的波涛, 扬弃无用的轻浮的泡沫, 冲碎了古老的顽固的暗礁, 你不分昼夜地奔腾, 远远地,一片汪洋在 天际颤动, 大海 被你所吸引过来。①[① 张贤亮:《在傍晚唱的歌》,《延河》1957年3月号。后收入《张贤亮选集》(一)。 ] 《大风歌》: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是从被开垦的原野的尽头来的 我是从那些高耸着的巨大的鼓风炉里来的 我是从无数个深藏在地下的矿穴中来的 啊!我来了! 我是被六万万人向前飞奔所带起来的呀! 我来了! …… 大风呀! 让你那滚滚滔滔的雷似的声响 让你那澎湃着的浪与浪冲击的音调 让你那强有力的和声去宣布 新的时代来临了! 需要新的生活方式! 需要新的战斗姿态!②[② 张贤亮:《大风歌》,《延河》1957年7月号。后收入《张贤亮选集》(一)。 ] 二十年后张贤亮小说中表现出的美学风格,在这几首诗歌中已初见端倪:星空、静夜,土地和槐花散发着香气,于此氛围和前景上,则是一个不眠的年轻人内心世界巨大的不安、激动、向往、求变,动态与静态相宜,柔美与雄壮相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弥漫的生命力,汩汩涌涌,不择地而出,在长短有序、张弛合度的诗歌节奏中,化为“强有力绪论 张贤亮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作家,尽管他的影响自《我的菩提树》(1992年)之后日渐式微,终至淡出文坛,但事实上他已成为一个文学传统——一个优秀的传统,一个复杂的传统。 面对传统,无法绕行:喜欢也好,讨厌也罢,它会曲曲折折地与后来者产生联系,并施以影响。 诗人张贤亮 了解一个作家,须顾及其全体。张贤亮曾经是一个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诗人张贤亮,就没有后来的小说家张贤亮:诗歌创作,是他的一次出色、出众的文学预演,如果不是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中断写作,当代文学史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诗人。 历史有时颇冷酷,然而文学力量或许更为强大,文学史上被夺走了一个诗人,却多出了一个小说大家。 张贤亮有三首诗歌,全部作于1957年,皆为上乘之作,充分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以下试各摘录数节,以见其一斑。 《夜》: 夜 我躺在星空下面, 在垦荒队的帐篷旁边。 周围是一片寂静, 风从小树林那边 吹来了槐花和土地的香气。 星星…… 我眷恋地听着,我久久地听着, 我激动地听着,我流着泪听着, 啊!我的祖国,就是夜里你也醒着! 你和我们播种的小麦一样, 你永远在生长着、成熟着、产生着新的种子, 不管白天或黑夜, 你永远在前进、在燃烧、在喧闹、在诞生着新的歌。 啊!祖国,就是夜里你也醒着!①[① 张贤亮:《夜》,《延河》1957年1月号。后收入《张贤亮选集》(一)。 ] 《在傍晚唱的歌》: 在这傍晚的时刻, 在这爱情和劳动的边缘, 我站在高高的麦垛上, 大地,从那空濛的雾气中上升, 向我伸过来 母亲丰满的嘴唇。 …… 我站在最高的麦垛上, 从心灵的窗户向世界瞭望, 我的情思,我感激你! 你告诉了我祖国现在做的、将来做的、永久在做的事情。 啊!祖国,你是我爱人的爱,你是我母亲的亲, 你是每日每夜伴着我的身影, 你是一条欢乐的河, 奔流着、翻滚着大大小小的波涛, 扬弃无用的轻浮的泡沫, 冲碎了古老的顽固的暗礁, 你不分昼夜地奔腾, 远远地,一片汪洋在 天际颤动, 大海 被你所吸引过来。①[① 张贤亮:《在傍晚唱的歌》,《延河》1957年3月号。后收入《张贤亮选集》(一)。 ] 《大风歌》: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是从被开垦的原野的尽头来的 我是从那些高耸着的巨大的鼓风炉里来的 我是从无数个深藏在地下的矿穴中来的 啊!我来了! 我是被六万万人向前飞奔所带起来的呀! 我来了! …… 大风呀! 让你那滚滚滔滔的雷似的声响 让你那澎湃着的浪与浪冲击的音调 让你那强有力的和声去宣布 新的时代来临了! 需要新的生活方式! 需要新的战斗姿态!②[② 张贤亮:《大风歌》,《延河》1957年7月号。后收入《张贤亮选集》(一)。 ] 二十年后张贤亮小说中表现出的美学风格,在这几首诗歌中已初见端倪:星空、静夜,土地和槐花散发着香气,于此氛围和前景上,则是一个不眠的年轻人内心世界巨大的不安、激动、向往、求变,动态与静态相宜,柔美与雄壮相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弥漫的生命力,汩汩涌涌,不择地而出,在长短有序、张弛合度的诗歌节奏中,化为“强有力的和声”,令人血脉偾张。这种充满生命力度的美学风格,后来更为完美地体现在《河的子孙》《绿化树》等中篇小说中,许多人只看见比如《绿化树》里的改造与性爱主题,哲学家李泽厚却敏锐地注意到,除了显见的主旨外,作品中还有“对那原始、质朴、粗犷、富有生命力的阔大的美的歌颂”①[① 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96—97页。 ]。由此可见,张贤亮的美学风格其来有自,一以贯之,二十多年的苦难折磨,并没有伤及其内在生命元气。 然而在1957年,这个内心涌动着生命风暴的年轻诗人,这个有如夜莺般不歌唱则不得安宁的诗人,当他唱着《大风歌》并欢呼“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的时刻,却遭遇了一场更为猛烈、席卷一切的大风暴:仅仅为着他以非工农的身份歌唱了土地和槐花的香气,仅仅为着他以知识者的身份歌唱了人民和祖国,他不得不赔上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②[② 《延河》1957年7月号发表《大风歌》,8月号即发表《本刊处理和发表〈大风歌〉的前前后后》,将作品定性为“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期发表张贤亮给编辑部的信及《〈大风歌〉后记》,详细解释创作初衷:不满于部分只追求享乐、精神麻痹的青年,想做一只“牛虻”把他们从蛰居状态中惊起来。同期发表安旗的批判文章《这是一股什么“风”?——评张贤亮的〈大风歌〉》,将张贤亮的“大风”意象污名化为中国北方春天刮的“黄风”、海洋上刮来的十二级“飐风”(原文如此。应为“台风”,疑“台”繁体字“颱”误作“飐”),结论是“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恶风”。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刘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对《大风歌》的批判升级。随后,张贤亮被打为“右派”。 ]。 文学观念 张贤亮是一个大气的作家,此种阔大气象源自他早年充分的文学准备,他的非同寻常的天赋,尤其是他对个人二十多年来苦难经历的不间断省思,这一切综合并最终形成一种文学气象。 张贤亮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视野和眼光的作家,不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他提供了一种资源,以之为观察、反思、剖析的视角;同时他也将个人命运与民族、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站在了一个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同代作家中,很难找出第二个人像他那样于文学出道之前即已精熟地掌握了一种哲学理论。 张贤亮更是一个清醒的作家。在为英国《卫报》所作文章《参与、逃避和超越》中,他对当代中国文学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所谓当代文学,“全是参与型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作品”①[① 张贤亮:《追求智慧》,《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3期。 ]。在开始创作小说时,张贤亮多次谈到自己并不想做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而是把文学创作当作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个人痛苦的经历,让他确立了带有功利性的文学观念:文学离不开政治,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改革家”,推动社会进步,共同创造能够让艺术繁荣的良性社会环境,否则,“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②[② 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683页。 ]。今天更为年轻的一代作家和读者,很难理解张贤亮所说的社会参与,更难理解张贤亮把个人创作当成对抗“左”的思想倾向的一种方式:1983年至1984年,的和声”,令人血脉偾张。这种充满生命力度的美学风格,后来更为完美地体现在《河的子孙》《绿化树》等中篇小说中,许多人只看见比如《绿化树》里的改造与性爱主题,哲学家李泽厚却敏锐地注意到,除了显见的主旨外,作品中还有“对那原始、质朴、粗犷、富有生命力的阔大的美的歌颂”①[① 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96—97页。 ]。由此可见,张贤亮的美学风格其来有自,一以贯之,二十多年的苦难折磨,并没有伤及其内在生命元气。 然而在1957年,这个内心涌动着生命风暴的年轻诗人,这个有如夜莺般不歌唱则不得安宁的诗人,当他唱着《大风歌》并欢呼“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的时刻,却遭遇了一场更为猛烈、席卷一切的大风暴:仅仅为着他以非工农的身份歌唱了土地和槐花的香气,仅仅为着他以知识者的身份歌唱了人民和祖国,他不得不赔上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②[② 《延河》1957年7月号发表《大风歌》,8月号即发表《本刊处理和发表〈大风歌〉的前前后后》,将作品定性为“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期发表张贤亮给编辑部的信及《〈大风歌〉后记》,详细解释创作初衷:不满于部分只追求享乐、精神麻痹的青年,想做一只“牛虻”把他们从蛰居状态中惊起来。同期发表安旗的批判文章《这是一股什么“风”?——评张贤亮的〈大风歌〉》,将张贤亮的“大风”意象污名化为中国北方春天刮的“黄风”、海洋上刮来的十二级“飐风”(原文如此。应为“台风”,疑“台”繁体字“颱”误作“飐”),结论是“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恶风”。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刘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对《大风歌》的批判升级。随后,张贤亮被打为“右派”。 ]。 文学观念 张贤亮是一个大气的作家,此种阔大气象源自他早年充分的文学准备,他的非同寻常的天赋,尤其是他对个人二十多年来苦难经历的不间断省思,这一切综合并最终形成一种文学气象。 张贤亮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视野和眼光的作家,不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他提供了一种资源,以之为观察、反思、剖析的视角;同时他也将个人命运与民族、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站在了一个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同代作家中,很难找出第二个人像他那样于文学出道之前即已精熟地掌握了一种哲学理论。 张贤亮更是一个清醒的作家。在为英国《卫报》所作文章《参与、逃避和超越》中,他对当代中国文学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所谓当代文学,“全是参与型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作品”①[① 张贤亮:《追求智慧》,《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3期。 ]。在开始创作小说时,张贤亮多次谈到自己并不想做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而是把文学创作当作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个人痛苦的经历,让他确立了带有功利性的文学观念:文学离不开政治,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改革家”,推动社会进步,共同创造能够让艺术繁荣的良性社会环境,否则,“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②[② 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683页。 ]。今天更为年轻的一代作家和读者,很难理解张贤亮所说的社会参与,更难理解张贤亮把个人创作当成对抗“左”的思想倾向的一种方式:1983年至1984年,正当写作中篇小说《绿化树》时,社会上传来了种种谣言,如:说要批评电影《牧马人》,要从他的作品中“专门寻找精神污染”等等。这反而激起了作家“理智上的义愤”: ……于是我倾注了全部情感来写这部可以说是长篇的中篇;在写的时候,暗暗地还有一种和错误地理解中央精神的那些人对着干的拗劲。我写了爱情,写了阴暗面,写了1960年普遍的饥饿,写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黄色”的东西;主人翁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人”,却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我正是要在这一切中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彩,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大感召力,写出社会主义事业不管经历多么艰难坎坷也会胜利的必然性来。①[① 张贤亮:《小说编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7—98页。 ] 安定、文明的社会环境,是文学得以生存、繁荣的前提和保证,这是张贤亮那一代作家们的共识,此共识由其血泪经历结晶而成。对张贤亮来说,甚至到了1995年,那噩梦般的经历、那积淀于内心深处的恐惧还不时浮现心头、闯入梦中,梦见自己又无端被捉进了劳改队,中篇小说《无法苏醒》记录的就是这种梦境和忧虑。在他带有艺术实验的长篇小说《习惯死亡》(1989年)中,对此种恐惧的描写达到了极致,“还你一个血窟窿”绝不仅仅是叙事艺术上的符号和象征,那其实也是一种喑哑的、绝望的呼喊。或许我们应该由此重新认识张贤亮早期的几部小说,如中篇小说《龙种》(1981年),类似于一幅国营农场改革蓝图;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1983年),则近似于一份中小城市改革及规划提案。这两部热情有余、文学性不足的作品,却是作家真诚然而又过于急切地奉献给社会的礼物——改变现状、改革社会,则为避免重蹈历史错误的有效途径。在他有意识地、强烈地写出相当于建议、规划、蓝图等理念化的文字时,无意中也“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彩,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而后者至今仍然能够以其清新、质朴、向上的气息,打动我们的心。 参与性的文学观念,是以损伤文学性为代价的。这不只是张贤亮的局限,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局限。 张贤亮的清醒还表现在,对自己文学实绩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在《小说中国》一书中,他谈到了“新时期文学”,亦可视为对自己文学的一个定位: …………正当写作中篇小说《绿化树》时,社会上传来了种种谣言,如:说要批评电影《牧马人》,要从他的作品中“专门寻找精神污染”等等。这反而激起了作家“理智上的义愤”: ……于是我倾注了全部情感来写这部可以说是长篇的中篇;在写的时候,暗暗地还有一种和错误地理解中央精神的那些人对着干的拗劲。我写了爱情,写了阴暗面,写了1960年普遍的饥饿,写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黄色”的东西;主人翁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人”,却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我正是要在这一切中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彩,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大感召力,写出社会主义事业不管经历多么艰难坎坷也会胜利的必然性来。①[① 张贤亮:《小说编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7—98页。 ] 安定、文明的社会环境,是文学得以生存、繁荣的前提和保证,这是张贤亮那一代作家们的共识,此共识由其血泪经历结晶而成。对张贤亮来说,甚至到了1995年,那噩梦般的经历、那积淀于内心深处的恐惧还不时浮现心头、闯入梦中,梦见自己又无端被捉进了劳改队,中篇小说《无法苏醒》记录的就是这种梦境和忧虑。在他带有艺术实验的长篇小说《习惯死亡》(1989年)中,对此种恐惧的描写达到了极致,“还你一个血窟窿”绝不仅仅是叙事艺术上的符号和象征,那其实也是一种喑哑的、绝望的呼喊。或许我们应该由此重新认识张贤亮早期的几部小说,如中篇小说《龙种》(1981年),类似于一幅国营农场改革蓝图;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1983年),则近似于一份中小城市改革及规划提案。这两部热情有余、文学性不足的作品,却是作家真诚然而又过于急切地奉献给社会的礼物——改变现状、改革社会,则为避免重蹈历史错误的有效途径。在他有意识地、强烈地写出相当于建议、规划、蓝图等理念化的文字时,无意中也“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彩,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而后者至今仍然能够以其清新、质朴、向上的气息,打动我们的心。 参与性的文学观念,是以损伤文学性为代价的。这不只是张贤亮的局限,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局限。 张贤亮的清醒还表现在,对自己文学实绩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在《小说中国》一书中,他谈到了“新时期文学”,亦可视为对自己文学的一个定位: ………… 了解一个作家,须顾及其全体。张贤亮曾经是一个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诗人张贤亮,就没有后来的小说家张贤亮:诗歌创作,是他的一次出色、出众的文学预演,如果不是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中断写作,当代文学史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诗人。 历史有时颇冷酷,然而文学力量或许更为强大,文学史上被夺走了一个诗人,却多出了一个小说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