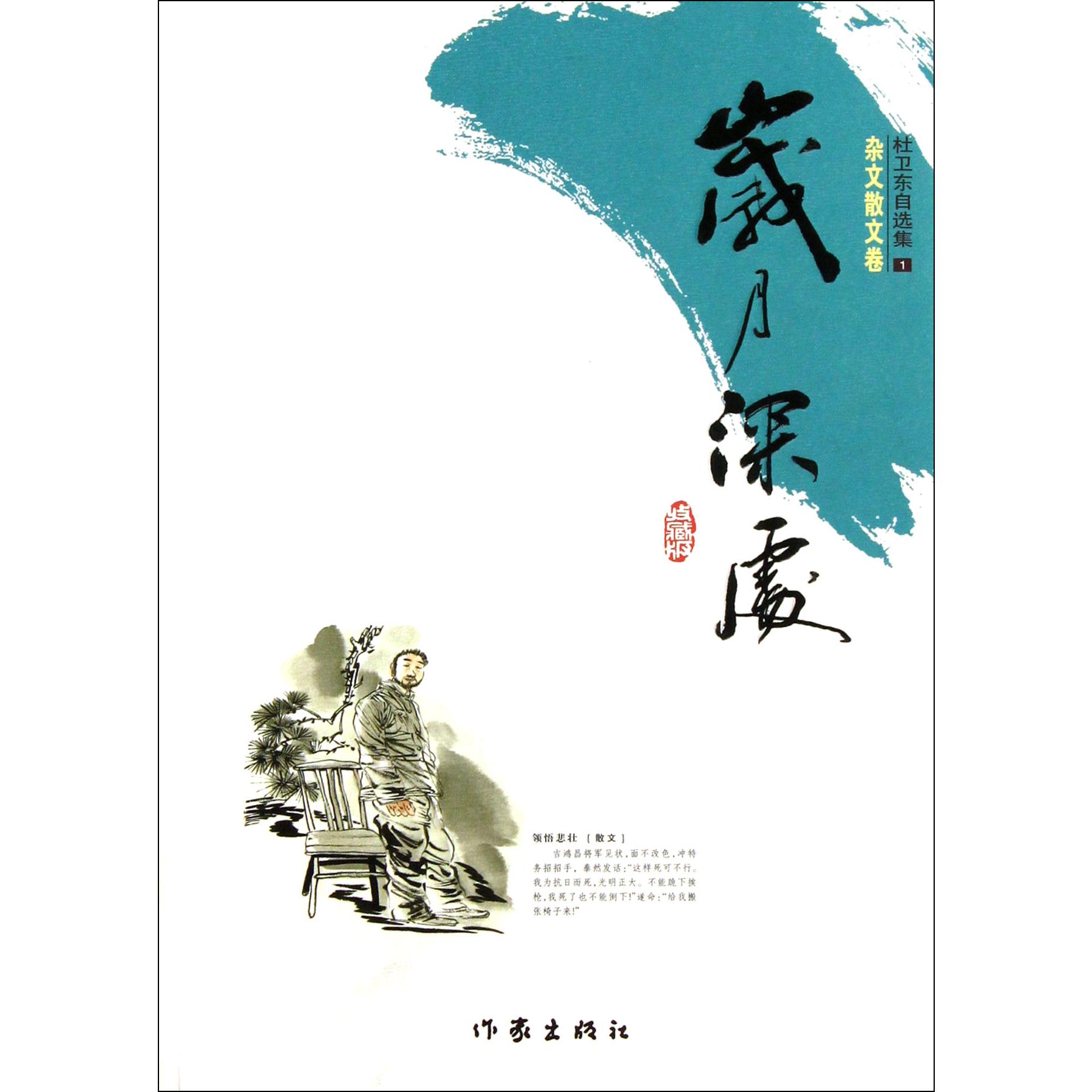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9.50
折扣价: 40.59
折扣购买: 岁月深处/杜卫东自选集
ISBN: 9787506349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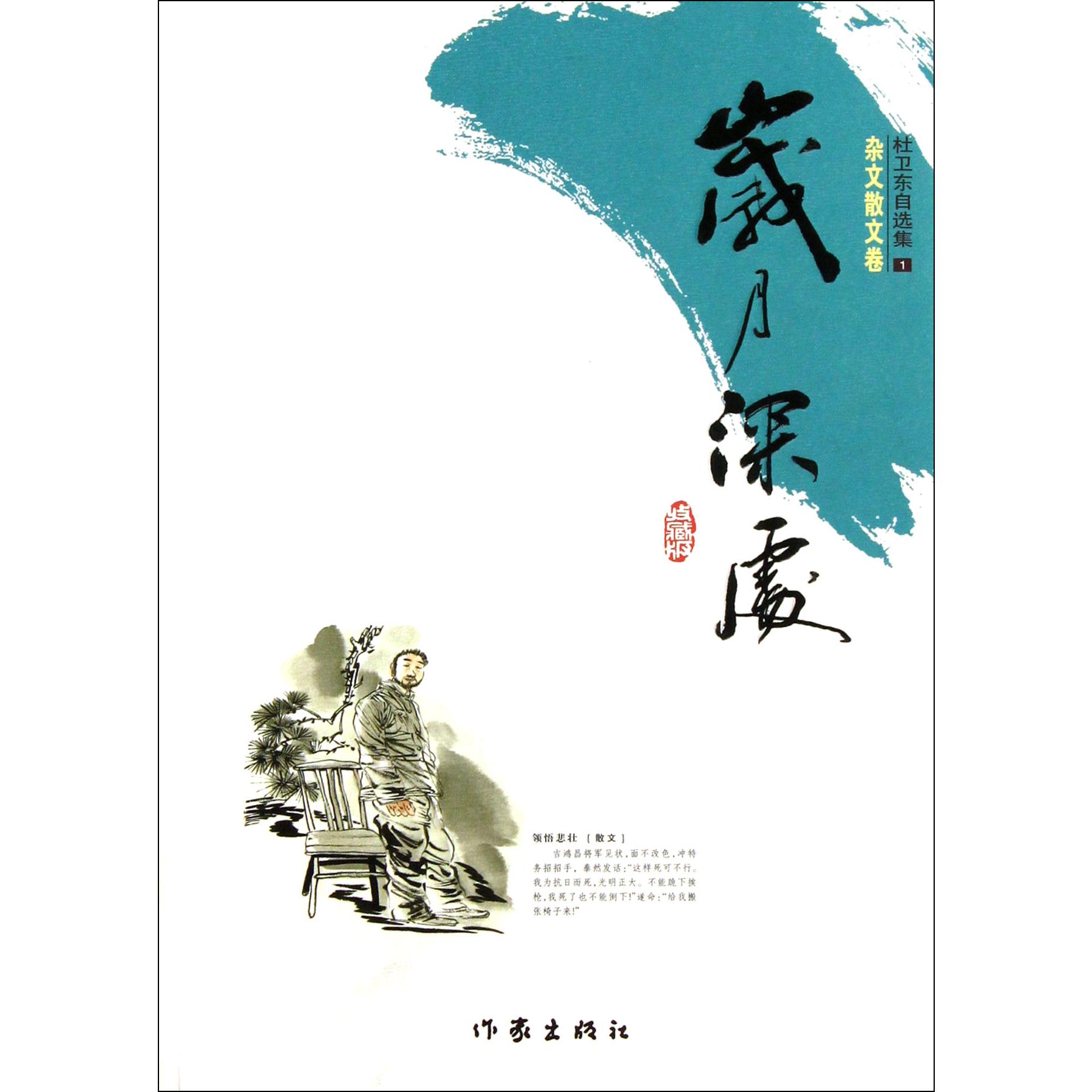
杜卫东,著有杂文随笔集《青春的思索与追求》《山花与刺梅》《走出人生的梦境》《人情·人言·人格》《两步斋夜话》《让生命去等候》《放逐心灵》《营造恬静》,报告文学集《茫茫人海启示录》《外交部里的小字辈》《爱神和她的宠儿》《中国的恋爱角》《都市里的保姆世界》《京都女警》《农军百万闹京华》《权延赤旋风——汪国真印象》《红墙里的少男少女》《苍茫人间》《世纪之泣》,长篇纪实文学《共和国秘使》(与权延赤合作)《昨夜星辰》《探入女性魂》(与阿爱英合作),电视剧本《洋行里的中国小姐》12集连续剧(编剧之一)、《新来的钟点儿工》单本剧。曾获人民文学报告文学奖、中日潮报告文学奖、时代文学报告文学奖以及青春宝杂文奖、法制日报杂文奖等奖项十余次。
马季有一段拿手的相声《打电话》,讽刺了不讲公共道德,在电话里 无休止地扯淡闲聊的人,听来令人在捧腹之余颇受教益。其实,打电话有 “学问”,接电话同样有讲究—— “丁零零”,电话铃一响,您拿起听筒:“喂,请问找谁?好。请稍 等……老张,您的电话。”或者:“噢,老张到医院看病去了,您有什么 事需要转告吗?”态度亲切,言语得体,犹如三月的春风,使对方倍感温 暖。 可是,也有人不这样接电话。且看—— “丁零零”,A君拿起听筒:“找谁?!……不在!”没有瞬间的停顿 ,啪!话筒还原。神态凛然,如高傲的公主;语调冷峻,似断案的法官。 “丁零零”,B君拿起听筒:“你找谁?你是哪儿?你是哪一位?你是 他的什么人?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其实,被找的人也许就在咫尺之内, 或埋头书案,或品茗看报。 应该说,A、B两君的电话,接得都不够得体,不够礼貌。 现代工业社会,自然要注意时间,讲求效率。说话啰啰嗦嗦、哼哼唧 唧,显然不能适应正在加快的生活节奏和思维节奏。但是,为人处世的起 码礼貌还是要的。像A君那样,还不待别人把话讲完,便啪地将话筒挂上, 丝毫不能说明他的时间观念强、办事效率高,倒是十足证明了其无知与浅 薄。因为对于现代人,较强的应变与社交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而要做到这 一条,就需懂得尊重与体谅别人。 至于说B君,则实在“热情”得有点过分。据说,美国人很讲究尊重“ 隐私权”,他们崇尚个人独立的精神,不过多地干涉他人,这就大大减少 了人们在无聊的争斗中被伤害的可能性,使人们得以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 与学习上。而在我们的同胞中,则有一些人专以窥探别人隐私为乐事,并 以此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其实,如果没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人家是谁 ,在哪儿工作,有什么事,大可不必打听得那么详细。对周围过多地关注 与干预,往往会为谗言与妒忌的滋生提供温床,而许多人的精力与才气, 不是常常在不必要的猜疑与争斗中消耗掉了吗? 俗话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未必。张君对李君发了一通脾气,是 因为刚受了王君的奚落;王君所以奚落张君,是因为接到了女友发出的中 止“外交关系”的“照会”;而这位女同胞所以要对王君施加压力,则是 单位里的女友对他们的结婚用品评头品足使然。所以,张李二君的矛盾, 和王君的女友的女友也搭上了界。再以电话事为例,倘若一个人因为一件 急事给另一个人打电话,结果或受呵斥,或受盘问,心里自然有气;而这 气又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在某个人身上释放出来,环环相因,岂不是将造成 一种恶性循环,以至影响到社会的心理平衡吗? 由此观之,接电话一类的小事不小,倘若每一个人都能“恰当”地打 电话和接电话,那么,我们的生活中,就可以多一些微笑,少一点烦恼; 多一些理解,少一点误会和猜疑了。 门第、血统与成才 近来,各类新兴学科兴旺得很。据说,连如何介绍对象也大有繁衍成 所谓“新红学”的势头。但不知,血统之研究,是否也可成其为“学”, 并且据此而招收硕士以至博士研究生。比如,A的先祖因为是刚正廉洁的B ,A所以正直坦荡便是由于脉管里奔涌着B的血液;这其中就大可研究。B刚 正廉洁是有据可查的,A正直坦荡也确实不假;然而,相反的例证也俯拾皆 是。秦桧奸佞无耻,卖国求荣,杭州西湖边上有他的铸像,跪在岳飞的墓 边为万人唾骂;他的曾孙秦钜却为国捐躯,血染疆场;其七世后裔秦硐更 是颇知廉耻,在先祖的像前题诗日:“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 以此观之,血统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并非灵验得很。狼孩一类的报道已 揭载多篇。本是人的后代,在狼群中生活了几年,便也四肢着地,口食生 肉了。可见,决定一个人品德操行的,主要是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本人的努 力程度。我猜想,假如让一个英国绅士带着儿子从小生活在原始部落,那 么,不但其公子长大后会缺少绅士风度,说不定父亲也会一改脱帽行礼的 习惯;再假如,一个血统“高贵”的孩子每每与一群小偷无赖为伍,胡作 非为,尽管他的父母对他寄以厚望,将来怕也戴不上真正的博士帽。这还 只是一代,更何况几代之后。这个道理,古今许多睿智之人是通晓明白的 :“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盖得之于时势也”,“积乱之后,当生大贤 ”,都从正面肯定了社会环境和后天努力在一个人建功立业中的作用。当 然,我们并不否定家庭的影响,但如果把它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就会陷 入歧途。 注重血统,强调门第,不过是一种封建意识。两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 是颇重视这一点的。他们修订家谱、族谱,把祖上的世系源流,即上代都 做过哪些大官,明确记载下来,以显示自己的血统高贵。宋齐以后,更是 专设谱局,找一些精通家谱、族谱的人任职。一时,谱牒之学成为一种专 门的学问——谱学。精通此学的人可日对千客,不犯一人家讳。而且,为 了保持血统纯净,门阀士族还严格选择通婚对象,即使是破落的士族也不 可与有钱的寒门通婚,否则,便会以玷辱同类的罪名而被弹劾。那么,这 些自恃出身高贵、门第显赫的南朝门阀士族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个个熏 衣、剃面、抹粉、涂脂,穿高底鞋,戴大帽子,出门或车或轿,走路要人 扶持,不学无术,对社会生活全然无知。一个叫王复的县令见到马又嘶又 跳,吓得惊慌失色道:“这明明是虎,为什么叫马呢?”血统门第的显赫 没有能够挽救这个腐朽阶层必然衰亡的命运。东晋以后,士族地位开始衰 落,到了唐宋,不是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史无前例的十年,曾经流行过一副极荒唐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绝对如此”。这对联造成的灾难有目共 睹,多少人被划归另册!后来,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词取而代之 ,算是落实了政策。一个红旗下长大的青年,只因为爸爸以至爸爸的爸爸 是地主、豪绅,自己便也要终生背上个“狗崽子”的十字架,是封建的“ 血统论”。反过来,如果某君的家谱上曾出过一位名士,这“光圈”便要 代代相传,“受用”不尽,不是也同前理吗?所以,与其说A在抗战烽火中 投身革命,是因为血管里流着B的血液,毋宁说是由于时代的感召和现实生 活的激励更符合实际情况。 或许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吧,它身上的封建胎记总是不 易抹掉。而这种封建思想残余对人的影响又是潜移默化的。A就是A,我不 明白,谈论他的时候,总是把他和其先祖硬扯到一起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或许,这是出自好心——想“历史”地去看一个人。殊不知,这样一来, 血统论的鞭子便打在了自己的身上。P7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