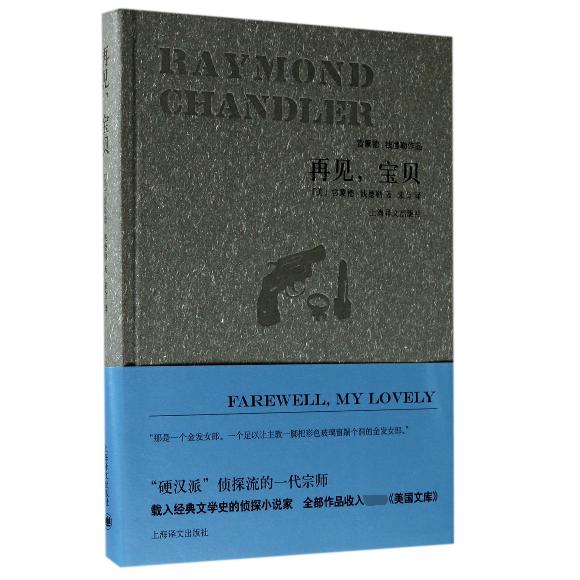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9.82
折扣购买: 再见宝贝(精)/雷蒙德·钱德勒作品
ISBN: 97875327748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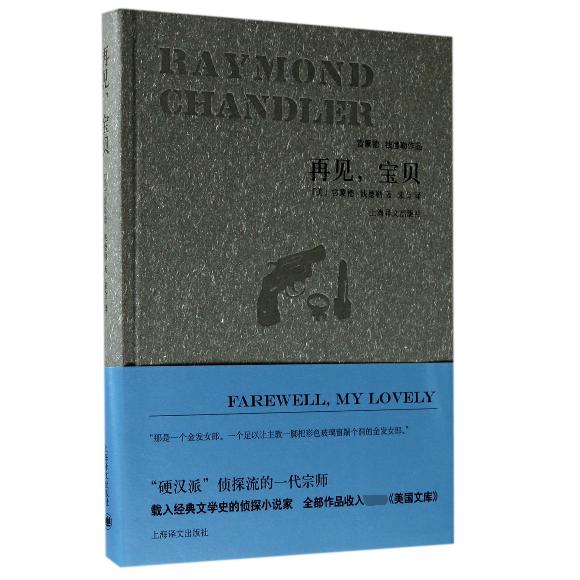
雷蒙德·钱德勒(1888-1959)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其作品被收录到权威的《美国文库》中,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票选150年侦探小说创作史上最优秀作家中的第一名。 钱德勒以其黑色冷峻的故事风格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形成了教科书式的硬汉派文体,备受村上春树、艾略特、加缪、钱钟书等中外大师级作家所推崇,被人称为“大师的大师”。他还与希区柯克、比利·怀尔德等大牌导演合作,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编剧,其担任编剧的电影《双重赔偿》和《蓝色大丽花》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奖提名。
又有一扇弹簧门挡在了楼梯顶端,不知紧闭的门 后面究竟有什么。大个子用两根拇指轻轻地把门推开 ,随后我们进了房间。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不太干 净,不太明亮,也不太欢乐。 角落里,一道光锥下,一群黑人围在一张双骰儿 赌桌边唱着歌,聊着天。紧挨着右手边那面墙的是一 个吧台。房间里剩余的地方差不多摆满了一张张小圆 桌。屋里有几个顾客,男男女女,全都是黑人。 赌桌边的歌声顿时停了下来,桌前的亮光也忽的 一下灭了。一阵突然的沉寂,沉重得就像一条进水的 船。一双双眼睛望着我们,栗色的眼睛,嵌在一张张 肤色从暗灰到深黑的脸孔上。一颗颗脑袋慢慢地转向 我们,脑袋上的眼睛在一片属于异族的、怪异的死寂 中闪着光,瞪视着。 一个脖颈粗实的黑人正靠在吧台的一端,他的衬 衫袖筒上缠着粉色的吊袖带,宽阔的后背上背着粉白 两色的吊裤带。此人浑身上下都写着两个字:保镖。 他慢慢地把那只抬着的脚放下,然后慢慢地扭头盯着 我们,一边把两脚缓缓张开,伸出一条宽大的舌头舔 了舔嘴唇。他长着一张几乎报废的脸,看上去好像被 人用各种物品轮番砸过一遍,就差掘土机的铲斗了。 它曾被人划上疤痕,被砸扁,再碾粗,脸上的口子有 的一格一格,有的一条一条。这是一张无需再有恐惧 的脸。它已然经受了所有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摧残。 他的一头短发皱巴巴的,发色中带着一抹灰。一 只耳朵缺了耳垂。 这黑人生得肩宽体阔。他两腿粗壮,看上去有一 点罗圈,这在黑人当中可不太常见。他又舔了舔嘴唇 ,露出一个微笑,然后身子动了起来。他以一种放松 的、拳击手式的半蹲姿势朝我们走了过来。大个子一 言不发地等着他。 这个胳膊上缠着粉色吊袖带的黑人伸出一只巨大 的棕色手掌贴在大个子的胸膛前。这手虽大,可这样 看起来却显得像根大头针。大个子一动不动。保镖挤 出一个温和的微笑。 “白人不能进,伙计。这是给有色人种的。对不 起。” 大个子转动着那双小小的、哀伤的灰眼睛,往房 间里四下张望着。他的脸颊微微泛红。“臭擦鞋的。 ”他压低了嗓子,愤怒地说了一句。然后他又提高了 音量。“维尔玛在哪儿?”他问那保镖。 保镖没有放肆地大笑。他端详着大个子的衣服— —他的褐衬衫和黄领带、他粗陋的灰外套,还有上面 的白色高尔夫球。他微微地转动着那颗厚实的脑袋, 从各个角度审视着这一切。他又低头看了看那双短吻 鳄皮鞋,轻轻地笑出声来,像是被逗乐了。我有一点 为他感到难过。这时他又轻声地开了口。 “维尔玛你说?这里没有维尔玛,伙计。没有婊 子,没有马子,什么都没有。这里是饭馆儿,伙计, 这里是饭馆儿。” 又有一扇弹簧门挡在了楼梯顶端,不知紧闭的门 后面究竟有什么。大个子用两根拇指轻轻地把门推开 ,随后我们进了房间。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不太干 净,不太明亮,也不太欢乐。 角落里,一道光锥下,一群黑人围在一张双骰儿 赌桌边唱着歌,聊着天。紧挨着右手边那面墙的是一 个吧台。房间里剩余的地方差不多摆满了一张张小圆 桌。屋里有几个顾客,男男女女,全都是黑人。 赌桌边的歌声顿时停了下来,桌前的亮光也忽的 一下灭了。一阵突然的沉寂,沉重得就像一条进水的 船。一双双眼睛望着我们,栗色的眼睛,嵌在一张张 肤色从暗灰到深黑的脸孔上。一颗颗脑袋慢慢地转向 我们,脑袋上的眼睛在一片属于异族的、怪异的死寂 中闪着光,瞪视着。 一个脖颈粗实的黑人正靠在吧台的一端,他的衬 衫袖筒上缠着粉色的吊袖带,宽阔的后背上背着粉白 两色的吊裤带。此人浑身上下都写着两个字:保镖。 他慢慢地把那只抬着的脚放下,然后慢慢地扭头盯着 我们,一边把两脚缓缓张开,伸出一条宽大的舌头舔 了舔嘴唇。他长着一张几乎报废的脸,看上去好像被 人用各种物品轮番砸过一遍,就差掘土机的铲斗了。 它曾被人划上疤痕,被砸扁,再碾粗,脸上的口子有 的一格一格,有的一条一条。这是一张无需再有恐惧 的脸。它已然经受了所有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摧残。 他的一头短发皱巴巴的,发色中带着一抹灰。一 只耳朵缺了耳垂。 这黑人生得肩宽体阔。他两腿粗壮,看上去有一 点罗圈,这在黑人当中可不太常见。他又舔了舔嘴唇 ,露出一个微笑,然后身子动了起来。他以一种放松 的、拳击手式的半蹲姿势朝我们走了过来。大个子一 言不发地等着他。 这个胳膊上缠着粉色吊袖带的黑人伸出一只巨大 的棕色手掌贴在大个子的胸膛前。这手虽大,可这样 看起来却显得像根大头针。大个子一动不动。保镖挤 出一个温和的微笑。 “白人不能进,伙计。这是给有色人种的。对不 起。” 大个子转动着那双小小的、哀伤的灰眼睛,往房 间里四下张望着。他的脸颊微微泛红。“臭擦鞋的。 ”他压低了嗓子,愤怒地说了一句。然后他又提高了 音量。“维尔玛在哪儿?”他问那保镖。 保镖没有放肆地大笑。他端详着大个子的衣服— —他的褐衬衫和黄领带、他粗陋的灰外套,还有上面 的白色高尔夫球。他微微地转动着那颗厚实的脑袋, 从各个角度审视着这一切。他又低头看了看那双短吻 鳄皮鞋,轻轻地笑出声来,像是被逗乐了。我有一点 为他感到难过。这时他又轻声地开了口。 “维尔玛你说?这里没有维尔玛,伙计。没有婊 子,没有马子,什么都没有。这里是饭馆儿,伙计, 这里是饭馆儿。” “维尔玛以前在这儿工作的。”大个子说。他的 语调像是在做梦,就好像他正独自一人在树林里采着 野紫罗兰。我掏出手帕,又擦了擦脖子后面的汗。 保镖突然放声大笑。“没错,”他边说边飞快地 扭头瞅了一眼身后的人群,“维尔玛以前在这儿工作 。可维尔玛现在不在这儿工作了。她退休了。呵呵… …呵呵。” “麻烦把你那只该死的手从我衬衫上拿开。”大 个子说。 保镖皱了皱眉。他可不习惯听别人这么跟他说话 。他把手从衬衫上拿开,握成了拳头,它的大小和颜 色都像极了一只巨大的茄子。他得考虑他的饭碗、他 好勇斗狠的名声,还有他的公众信誉。这些问题他考 虑了一秒钟,然后犯下了一个错误。他又狠又快地挥 了一记拳,胳膊肘猛地向外一抽,拳头落在了大个子 的下巴一侧。房间里四下传出一阵轻轻的喘气声。 这可是结结实实的一拳。大个子肩膀一垂,身子 紧跟着晃了一下。这一拳力道十足,挥出此拳的这个 人平时一定没少练过。大个子的脑袋只歪了不到一英 寸。他没有试图招架。他承受了这一击,微微抖了抖 身子,喉咙里轻轻地哼了一声,然后一把抓住了保镖 的喉咙。 保镖想要用膝盖顶他的裆部。大个子让他在半空 中转了个身,他那双花里胡哨的鞋一下子在粗糙的油 地毡上滑脱了。他把保镖的身体向后一弯,腾出右手 去抓他的腰带。那腰带就像绑肉绳一样一下子断了。 大个子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直直抵住保镖的脊柱, 然后奋力一推。他直接把保镖扔到房间那头去了,这 家伙在空中转着圈,左摇右摆,两手乱舞。三个人跳 起身来躲开他。保镖翻身倒地时带翻了一张桌子,接 着狠狠地砸在了踢脚板上,声音响得你在丹佛都能听 得见。他两腿抽搐了一下,然后就躺倒不动了。 “有些家伙,”大个子开口道,“总是不知道什 么时候不该狠。”他朝我扭过头来。“对了,”他说 ,“你跟我喝一杯吧。” 我们走到吧台前。那些顾客或单身或三三两两, 全都成了一言不发的影子,他们无声地从地板上飘过 ,又无声地从楼梯尽头的那扇门里飘了出去。无声如 草地上的黑影。他们甚至都没有让弹簧门摇摆。 我们在吧台上倚着身子。“酸威士忌,”大个子 说,“你的自己点。” “酸威士忌。”我说。 于是我们拿到了酸威士忌。 大个子顺着又厚又矮的玻璃杯壁面无表情地把酸 威士忌舔下肚去。他严肃地盯着酒吧招待——这是个 愁眉苦脸的瘦小黑人,穿着一件白外套,脚痛般地动 来动去的。 “你知道维尔玛在哪儿吗?” “维尔玛,是吗?”酒保哼哼唧唧地说,“我最 近没在这块儿瞅见她。最近没见着,没有,先生。” “维尔玛以前在这儿工作的。”大个子说。他的 语调像是在做梦,就好像他正独自一人在树林里采着 野紫罗兰。我掏出手帕,又擦了擦脖子后面的汗。 保镖突然放声大笑。“没错,”他边说边飞快地 扭头瞅了一眼身后的人群,“维尔玛以前在这儿工作 。可维尔玛现在不在这儿工作了。她退休了。呵呵… …呵呵。” “麻烦把你那只该死的手从我衬衫上拿开。”大 个子说。 保镖皱了皱眉。他可不习惯听别人这么跟他说话 。他把手从衬衫上拿开,握成了拳头,它的大小和颜 色都像极了一只巨大的茄子。他得考虑他的饭碗、他 好勇斗狠的名声,还有他的公众信誉。这些问题他考 虑了一秒钟,然后犯下了一个错误。他又狠又快地挥 了一记拳,胳膊肘猛地向外一抽,拳头落在了大个子 的下巴一侧。房间里四下传出一阵轻轻的喘气声。 这可是结结实实的一拳。大个子肩膀一垂,身子 紧跟着晃了一下。这一拳力道十足,挥出此拳的这个 人平时一定没少练过。大个子的脑袋只歪了不到一英 寸。他没有试图招架。他承受了这一击,微微抖了抖 身子,喉咙里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一把抓住了保镖 的喉咙。 保镖想要用膝盖顶他的裆部。大个子让他在半空 中转了个身,他那双花里胡哨的鞋一下子在粗糙的油 地毡上滑脱了。他把保镖的身体向后一弯,腾出右手 去抓他的腰带。那腰带就像绑肉绳一样一下子断了。 大个子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直直抵住保镖的脊柱, 然后奋力一推。他直接把保镖扔到房间那头去了,这 家伙在空中转着圈,左摇右摆,两手乱舞。三个人跳 起身来躲开他。保镖翻身倒地时带翻了一张桌子,接 着狠狠地砸在了踢脚板上,声音响得你在丹佛都能听 得见。他两腿抽搐了一下,然后就躺倒不动了。 “有些家伙,”大个子开口道,“总是不知道什 么时候不该狠。”他朝我扭过头来。“对了,”他说 ,“你跟我喝一杯吧。” 我们走到吧台前。那些顾客或单身或三三两两, 全都成了一言不发的影子,他们无声地从地板上飘过 ,又无声地从楼梯尽头的那扇门里飘了出去。无声如 草地上的黑影。他们甚至都没有让弹簧门摇摆。 我们在吧台上倚着身子。“酸威士忌,”大个子 说,“你的自己点。” “酸威士忌。”我说。 于是我们拿到了酸威士忌。 大个子顺着又厚又矮的玻璃杯壁面无表情地把酸 威士忌舔下肚去。他严肃地盯着酒吧招待——这是个 愁眉苦脸的瘦小黑人,穿着一件白外套,脚痛般地动 来动去的。 “你知道维尔玛在哪儿吗?” “维尔玛,是吗?”酒保哼哼唧唧地说,“我最 近没在这块儿瞅见她。最近没见着,没有,先生。” “你来这儿多久了?” “让我瞧瞧,”酒保放下毛巾,额头上现出一条 条皱纹,然后扳起了手指头,“大概十个月吧,我猜 。大概一年。大概-” “到底是多久?”大个子说。 酒保两眼瞪得像铜铃,喉结上上下下地扑腾着, 像只没头的母鸡。 “你们这笼子变成黑人夜店有多久啦?”大个子 粗声盘问道。 “谁说是?” 大个子的手捏成了拳头,手中那只装着酸威士忌 的玻璃杯几乎顿时消失在了无形之中。 “五年吧,”我说,“至于这个叫维尔玛的白人 姑娘,这家伙肯定什么也不知道。这里没人知道。” 大个子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刚刚从蛋里孵出来一 样。那杯酸威士忌好像没有让他高兴起来。 “混蛋,谁让你来插一脚的?”他问我。 我挤出一个微笑,一个大大的、温暖的、友好的 微笑。“我就是那个跟你一起进来的家伙。想起来了 吗?” 他咧嘴回了我一个笑容,一个干巴巴的笑,只见 白牙,没有意义。“酸威士忌,”他吩咐酒保,“把 你裤裆里的跳蚤抖干净。上快点儿。” 酒保迈着小碎步子跑前跑后,骨碌碌地翻着白眼 。我背靠吧台,抬眼看着房间。屋里现在空了,只剩 下了酒保、大个子和我自己,当然还有那个一头撞在 墙上的保镖。那保镖开始动弹了。他慢慢地挪着身子 ,像是忍着剧痛、十分吃力的样子。他沿着踢脚板不 声不响地爬着,像缺了一只翅膀的苍蝇。他挪到了桌 子后头,精疲力竭的样子就像一个人突然之间苍老了 、幻灭了。我看着他挪动身子。酒保这时又拿来了两 杯酸威士忌。我朝吧台转过身子。大个子漫不经心地 瞥了一眼那个在地上爬行的保镖,然后就不再留意他 了。 “这夜店里现在什么都没有留下了,”他抱怨道 ,“以前这儿有一个小舞台,有乐队,还有一个个漂 亮的小房间,男人可以进去找些乐子。维尔玛在这儿 唱过歌。她是个红头发,媚得就像蕾丝内裤。我们那 时都要结婚了,结果他们陷害了我。” 我喝下了第二杯酸威士忌。这场冒险已经快让我 受够了。“怎么陷害的?”我问道。 “你以为我这八年都上哪儿去了?” “捉蝴蝶。” 他用一根粗得像香蕉的食指戳着自己的胸膛。“ 蹲在牢里呐。我叫马洛伊。他们叫我驼鹿马洛伊,因 为我个儿大。大本德银行劫案。四万大洋。我一个人 干的。厉不厉害?” “你现在打算把钱花掉对吧?”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这时我们身后传来一阵声响 。那保镖站起身来了,左摇右晃地走了几步,伸手握 “你来这儿多久了?” “让我瞧瞧,”酒保放下毛巾,额头上现出一条 条皱纹,然后扳起了手指头,“大概十个月吧,我猜 。大概一年。大概-” “到底是多久?”大个子说。 酒保两眼瞪得像铜铃,喉结上上下下地扑腾着, 像只没头的母鸡。 “你们这笼子变成黑人夜店有多久啦?”大个子 粗声盘问道。 “谁说是?” 大个子的手捏成了拳头,手中那只装着酸威士忌 的玻璃杯几乎顿时消失在了无形之中。 “五年吧,”我说,“至于这个叫维尔玛的白人 姑娘,这家伙肯定什么也不知道。这里没人知道。” 大个子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刚刚从蛋里孵出来一 样。那杯酸威士忌好像没有让他高兴起来。 “混蛋,谁让你来插一脚的?”他问我。 我挤出一个微笑,一个大大的、温暖的、友好的 微笑。“我就是那个跟你一起进来的家伙。想起来了 吗?” 他咧嘴回了我一个笑容,一个干巴巴的笑,只见 白牙,没有意义。“酸威士忌,”他吩咐酒保,“把 你裤裆里的跳蚤抖干净。上快点儿。” 酒保迈着小碎步子跑前跑后,骨碌碌地翻着白眼 。我背靠吧台,抬眼看着房间。屋里现在空了,只剩 下了酒保、大个子和我自己,当然还有那个一头撞在 墙上的保镖。那保镖开始动弹了。他慢慢地挪着身子 ,像是忍着剧痛、十分吃力的样子。他沿着踢脚板不 声不响地爬着,像缺了一只翅膀的苍蝇。他挪到了桌 子后头,精疲力竭的样子就像一个人突然之间苍老了 、幻灭了。我看着他挪动身子。酒保这时又拿来了两 杯酸威士忌。我朝吧台转过身子。大个子漫不经心地 瞥了一眼那个在地上爬行的保镖,然后就不再留意他 了。 “这夜店里现在什么都没有留下了,”他抱怨道 ,“以前这儿有一个小舞台,有乐队,还有一个个漂 亮的小房间,男人可以进去找些乐子。维尔玛在这儿 唱过歌。她是个红头发,媚得就像蕾丝内裤。我们那 时都要结婚了,结果他们陷害了我。” 我喝下了第二杯酸威士忌。这场冒险已经快让我 受够了。“怎么陷害的?”我问道。 “你以为我这八年都上哪儿去了?” “捉蝴蝶。” 他用一根粗得像香蕉的食指戳着自己的胸膛。“ 蹲在牢里呐。我叫马洛伊。他们叫我驼鹿马洛伊,因 为我个儿大。大本德银行劫案。四万大洋。我一个人 干的。厉不厉害?” “你现在打算把钱花掉对吧?”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这时我们身后传来一阵声响 。那保镖站起身来了,左摇右晃地走了几步,伸手握 住赌桌后面一扇黑门的把手。他打开门,几乎是摔进 去的。门哐的一声关上了,然后咔哒一声上了锁。 “那是什么地方?”驼鹿马洛伊厉声问道。 酒保的眼珠在脑壳里飘忽不定,然后才费力地定 睛望着那扇门,保镖刚刚跌跌撞撞地从那里钻了进去 。 “那——那是蒙哥马利先生的办公室,先生。他 是老板。他的办公室就在那后面。” “他说不定知道。”大个子说。他把杯里的酒一 饮而尽。“他最好不要也跟我说笑话。已经碰着两个 这样的人了。” 他慢悠悠地穿过房间,步履轻快,心中没有一丝 顾虑。他巨人般的后背遮住了那扇门。门锁着。他拉 住门摇了摇,一块门板飞到了一边。他走了进去,门 在他身后关上了。(P4-9) 住赌桌后面一扇黑门的把手。他打开门,几乎是摔进 去的。门哐的一声关上了,然后咔哒一声上了锁。 “那是什么地方?”驼鹿马洛伊厉声问道。 酒保的眼珠在脑壳里飘忽不定,然后才费力地定 睛望着那扇门,保镖刚刚跌跌撞撞地从那里钻了进去 。 “那——那是蒙哥马利先生的办公室,先生。他 是老板。他的办公室就在那后面。” “他说不定知道。”大个子说。他把杯里的酒一 饮而尽。“他最好不要也跟我说笑话。已经碰着两个 这样的人了。” 他慢悠悠地穿过房间,步履轻快,心中没有一丝 顾虑。他巨人般的后背遮住了那扇门。门锁着。他拉 住门摇了摇,一块门板飞到了一边。他走了进去,门 在他身后关上了。(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