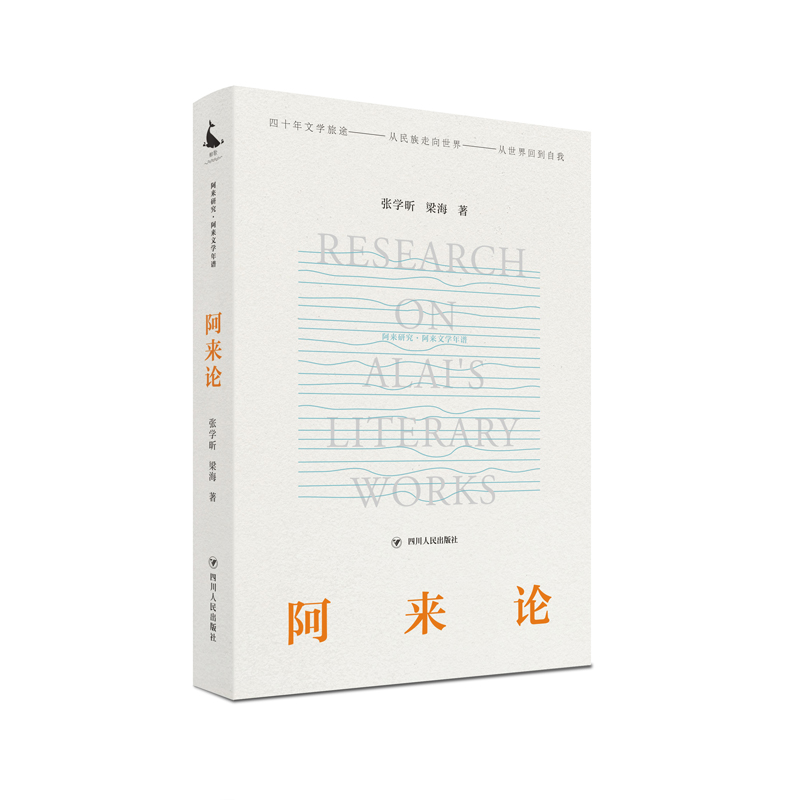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人民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8.20
折扣购买: 阿来论(精)
ISBN: 97872201208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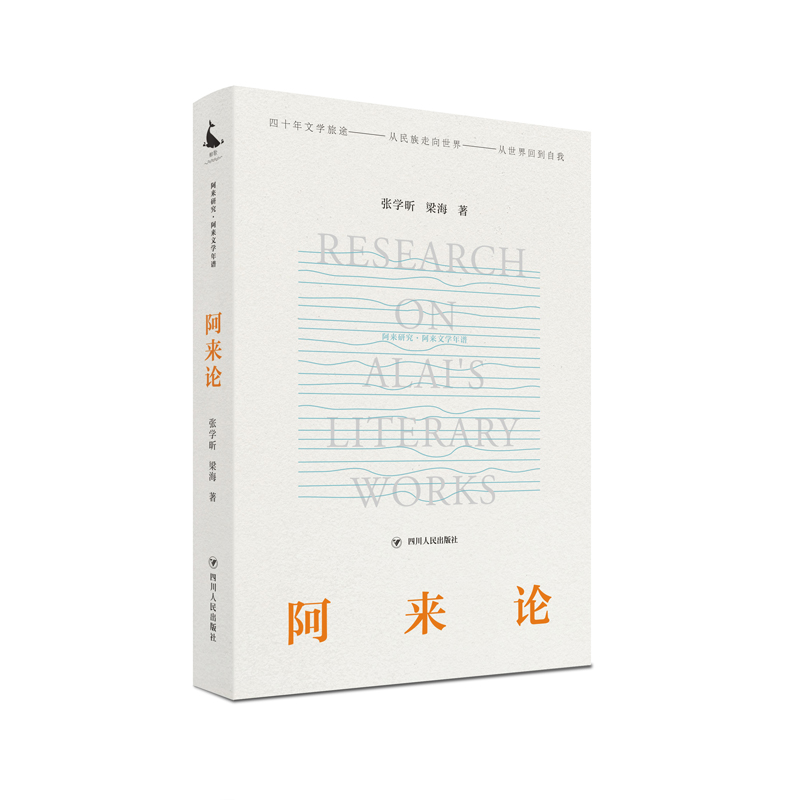
张学昕,文学评论家,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理工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曾多次获得“当代作家评论奖”“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奖项。2008年获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 梁海,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负责人,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获第七届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第十四届、十五届大连市社会科学进步奖等。专著《小说的建筑》获2012年度大连市文艺界十大有影响力作品称号。
阿来论 样章 王啊,今天我要把你的故事还给你,我要走出你的故事了。这是一个小说家的宿命,从一个故事向另一个故事漂泊。—— 阿来《德格:湖山之间,故事流传》 人类操着不同的语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一种只要愿意倾听,就能懂得的语言——质朴、诚恳,比所有人类曾经创造的,将来还要创造的都要持久绵远。 ——阿来《大地的语言》 一 阿来是一位寻找故事的人。这仿佛是一场宿命的安排。生于一九五九年的阿来,今年六十岁,他写了将近四十年,我相信,他还将继续写下去。我的愿望是,努力去发现阿来是如何找到故事的,又是如何处置或者说如何安放这些故事的,而这些故事,又是如何面对现在和未来的。多年以来,每当我们谈论阿来的文学创作时,都会将“历史”“民族”“地域”“诗性”“空灵”,或者“救赎”诸如此类的关键词置入对阿来及其文本的评价、判断和描述。其实,阿来写作及其发生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词语:“行旅”。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阿来是一位诗人,并且是一位“行吟诗人”。这些年来,他的写作,总是厚积薄发,张弛有度,沉静持重,读他的文字久了,就会深感他叙述的结实、朴素,在历史、自然和纷繁的现实面前,能够体察到他感性和理性的平衡度,体会到他书写时那种触动心灵的力量。这些年来,他循着地理的面貌,勘察那些承载着川藏人文印迹的历史、自然、文化地形图。在他的文字中,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他对行旅的热爱,在大自然里对生命的无限沉醉的情绪和感怀。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是永远“在路上”,因为,在历史、现实和自然的交会处,才会有沿途的风景和沉潜的秘密。 我曾经猜想,一个作家的写作,以及他的审美视阈和叙述维度,究竟与他对社会、人生、人性、自然、生态的现实性体验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联系?我渐渐清楚了,阿来在始终略显密集的行旅中寻找着什么。可以肯定,在他灵魂、精神世界的深处,一定存有一个巨大的隐秘,这个隐秘也可能来自一种巨大的隐忧和期待。或许,这就是他期待文字之外,存在一个没有因时代的过渡递进而变迁的人的安详、坦然和平静的状态。无疑,当阿来无数次穿越峡谷、群山、荒野和川流的时候,他所渴望的,一定是生机处处的美丽的植物的冠冕,而不是被现代挖掘机械践踏过的、被无序补缀过的人工丘陵。明显地,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与自然的进程相比,早已经呈现出格调和色泽上的极大不一致。整个生态系统并非静态,它们随着时间以一种有序的、可以预测的变化而发展,甚至,很多时候,这个变化系列是由植物和动物自身所更改的环境而导出的。我们在与其他物种,包括植物和动物打交道的时候,总是过于自信和高傲,甚至毫无理由地显示出无厘头的嚣张。即使是那种想象上代表着高于自然力量的某种驯化能力,也被我们自己大大地夸张了。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从植物本身所发出的信息中感知,或者,我们在审视它们在四季中的性格时耐心思考,这样也许可以看出,它们其实根本就不想与人类做什么交易。它对于我们更具有启示性的预警。所以,阿来与自然的贴近,就更让我们掩面沉思。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常常背着聂鲁达的诗集,在我故乡四周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漫游。走过那些高山大川、村庄、城镇、人群、果园,包括那些已经被丛林吞噬的人类生存过的遗迹。各种感受绵密而结实,更在草原与群山间的村落中,聆听到很多本土的口传文学。那些村庄史、部落史、民族史,也有很多英雄人物的历史。而拉美爆炸文学中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家,比如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卡彭铁尔等作家的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实践,就是把风行世界的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与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土著的口传神话嫁接到一起,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只属于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语言系统。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描述一个杰出作家的写作及其文本形态:一个作家的写作,除了与自身的经历、生命体验和才情息息相关之外,他的文本生成还与他所处的环境、地域、地势有着不解之缘。所谓“地气”,就是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催生其创作灵感频发的写作发生地。就是这个场域,使得一位作家对历史和生活的感悟,获得了一种独到的文化方位和叙述视点。可以想见,一位作家的写作,一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心理、精神坐标及灵魂“方位”、叙述视点,才有可能形成与众不同的、富于个性化的气势、气脉、气象。有了这些,他对文字的轻与重,叙述的把握,对存在世界、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才可能更加逼近事物本身。文本中的故事、人物、叙述、结构才会逶迤而来,流溢而出,天然浑成。我们会看到,阿来的叙述里总会有一个目光,一种眼神,起起伏伏,不时地透射出神性的色泽。虽然,在其间还看不到那么明显的哲人的影子,但是,作家对生活、存在世界的体味都非常自然地浮现着,不离不弃,妙义横生。阿来文本叙述的单纯性、含义的适量,就像是有一股天籁之声,他无须用文字刻意地给生活打开一个缺口,使生活在某种刻意设置或操作之下运转,而是作家擅于从容地发现存在世界本身的品质或隐秘,洞悉那些裸露或者被表象所遮蔽的形态。 的确,我在阿来的文字中,根本看不到丝毫的浮躁。存在世界,在他的笔下也就不显得臃肿,而是形态飘逸、轻逸又扎实牢靠,不折不扣。无论他叙述的是什么题材和人物,都非常清净、细致、自然。这恐怕是缘于他对一切事物的态度——不苛求、不抱怨、不造作,可谓是有甚说甚,从容不迫。他崇尚简洁、清晰、明确,他具有“四两拨千斤”的艺术感觉和功力。生活的结构,在他的文本中从不闪闪烁烁,他对俗世生活没有调侃、没有戏谑,也没有苛刻的批判;另一方面,其文本还蕴藉浪漫的飞扬、灵动,使作品具备了令人尊敬的品质。有时候,时代、社会的面貌在叙事里经常显得模糊、含蓄、难以辨认,但作为作家正直的人格始终坚实地存在着。历史、现实、生活、生命的存在形态,消长枯荣,或具有超然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定律,或嵌入世道人心变迁的个人命运史。其中荡漾着恒久、持续的经典气息,呈现出深沉、厚重的表情。正是这样的文字,才会让我们拿起来放不下,既令人沉浸其中、引人深思,又常让我们对历史、生活世界恍然间有深刻感悟。也许,阿来的文字真正是素朴到了极处,才会境界全出,气定神闲一如他的镇定的表情。可谓是大道至简,大雅小雅,从容道来,即便是俗世的云影水光,也会流溢着汉语的神韵。 阿来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个自然之子。作为一个并不生活在西藏的、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他一直在讲述四川藏区阿坝的嘉绒大地上发生的故事。二十年前,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出版,使世界开始知道藏族大家庭中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文化群落的坚实存在。阿来作为一位嘉绒子民,一个部族的儿子,也为此感到一种巨大的自信。他以他的文字,表达着他对这片大地由衷的情感和深沉的情怀。数年来,他不断地回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阿坝,回到那片旷远的群山和辽阔的草原,一次次地出发,又一次次地归来。阿来的写作,是行走在“大地的阶梯”上的写作;阿来的行走,是文学的行旅。他对世界和人的爱及所有的情感,都聚焦在对生活在大地上一切事物的热爱。 那部《大地的阶梯》,曾经令我迷恋和沉醉。表面上看,《大地的阶梯》就像是阿来绘制的、循着地理的坐标,寻访川藏人文历史足迹的一幅文化地形图。在这里,川藏高原历史、文化、人类的踪迹,与大自然的雄伟、神奇、浩荡之气,在时空的浩渺中,就像那落不定的尘埃,随风飘散。在这些文字中,我们也会不断地体会到阿来在大自然中无比沉醉的情绪和感怀:“就是这样,我从尘土飞扬的灼热的夏天进入了山上明丽的春天。身前身后,草丛中,树林里,鸟儿们歌唱得多么欢快啊!我就是这样,一次一次,感谢命运如此轻易地就体会到了无边的幸福。”“在我久居都市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会打开一本又一本青藏高原的植物图谱,识得了许多认识却叫不出名来的花朵的名字。今天,我又在这里与它们重逢了。” 鲜红的野草莓、紫色的马先蒿、蓝色的鸢尾,生机处处;白桦、红桦、杉树、松树、柏树,蓊郁如海。阿来在那次漫长悠远的行旅中,似乎在无数植物茂密的植被下,玄想、推断出在这样的环境里曾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和曾经发生的故事,包括那些土司家族的宿命,政治、经济、环境与文明的崛起和衰落的历程。那么,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就如同在纯生物繁衍意义上,一种家族的基因和血统,历经几百上千年的风霜雨雪,终于因为穿越得越来越疲惫,而失去最后一点动力?我曾在《阿来的植物学》一文中,描述过阅读这部美文时最初的感想:“整个人类社会的里程,就像大地的阶梯,在无数的阶梯上面,零星散散的村落,宛若那些有名字或叫不出名字的小小花朵,映现、记载着大千世界的四季流转,风云变幻的轮回,与存在世界对视的不仅仅是人的面孔,还有摇曳在大自然中植物的生命力。那么,人的力量和美好,就体现在向上攀登的行旅之中,体现在人与自然美轮美奂的呼应之中,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乃至天人合一的境界,才是人与自然相互的赋予、相互的求证。我开始猜想,一个作家的写作,以及他的审美视阈,究竟与对自然、生态的体验之间,存在着怎样神秘的联系?我也渐渐明白,阿来在始终略显急促的脚步中寻找着什么。可以肯定,他的精神世界的深处,一定有一个巨大的隐秘,这个隐秘也可能来自一种巨大的隐忧和探寻的渴望。或许,那就是他期待文字之外,存在一个没有因时代的过度递进和变迁的人的安详、坦然和平静的状态。尤其当阿来无数次穿越峡谷、群山、荒野和川流的时候,他所渴望的,一定是生机处处的美丽的植物的冠冕,而不是被现代挖掘机械践踏过的、被无序补缀过的人工丘陵。” 2013年的春夏之交,我因为参加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一个文学活动,随同阿来一起来到川北藏区,在十余天的时间里,访问了包括阿来的故乡马尔康在内的许多县、乡镇,算是真正身体力行地“重叠了”阿来在《大地的阶梯》中描述的许多山川河流。在马尔康的住处“嘉绒大酒店”,每天晚上,我枕着梭磨河湍急不息的流水声入睡,梦中的马尔康,仿佛是千呼万唤,变得可亲可近,可摸可触。阿来叙述文字中的情境,如同一部空间诗学,纷至沓来。一切都变得那么鲜活,那么亲切,像嘉绒、土司、风马、喇嘛、寨楼、磨坊、酥油,等等,都已经不再只是拥有一个简单的释义的词语,它们能够让你猜测、想象、延伸出历史、现实、世道人心和文字叙述之间的隐秘关系。隐隐约约地,阿来的小说似乎变得离我越来越远,而阿来的“现实世界”,开始向我“扑面而来”。 也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行旅,必定就是文学的行旅。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阿来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旅途中写就的。行旅之于阿来,更有别样的意味和意义。但是文学,也必然要在历史、时代和生活的行进途中向前延展。对于一个阅读者而言,如果想要真的读懂一位作家的文字,恐怕不仅要揣摩文本、思考作家,还应该用心去丈量作家与作品之间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的维度。因为,写作是一件太过神奇的事情,只有体验和感觉到作家饱含思想的最大纵深处,感受其对具体事物的体悟和对世界整体的沉思,才可能会理解一个伟大作家的文本结构及其深邃内涵。我在想,我们如何才能接近阿来的“大地的阶梯”呢?在阿来的不同的阶梯之上,会有怎样不同的风景呢?阿来的阶梯与阶梯之间的距离,又有多远呢? 若干年前,就知道有这样一句话:诗比历史更永久。后来,我又读到美国批评家、史学家海登·怀特那本《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了解到他对历史文本的形成曾有独到的看法:历史也是一种写作、一种修辞的灵活运用,历史不仅仅是对于史实面貌的再现,它还是一种埋藏在历史学家内心深处的想象性建构,而这种建构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着一个时代特有的精神结构。历史写作,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仔细想想,历史这个曾经在我们内心无比神圣的字眼,具有多么强大的不可颠覆性,原来竟然也是一种“想象性建构”。说到底,它也不过是依据某种规则和“模型”进行的“创作”。如果按着海登·怀特的理论,历史可能是一部凭借着某种意志力撰写的“花腔”,虚构的元素常常会覆盖事实本身。如此说来,史学和诗学,在建构的某些方面倒是可能存在着某种“共性”和“相似性”,两者之间甚至存在不可忽略的“互文性”。那么,历史的撰写与文学的虚构,究竟有多大的差异性和本质性区别呢?慢慢地,我开始理解这些话的深意,也更有兴趣思考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现在,在我们的时代,这个问题似乎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微妙起来。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变得比以往更加微妙和复杂。这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可能“肆意”发生的时代,是一个会经常令人猝不及防、倍感错愕的时代。即使我们会看见、发现、记录下来关于这个时代的种种事件,通过现在的文学,或将来的历史写作为“此时”留下痕迹,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必须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和时代高度的“不可把握性”。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真正地“看见”什么?“看见”之后,我们能够或者应该记录下什么?阿来说:“这是一个一切事物都有多种媒体争先呈现的时代,对个体来讲永远信息过量的时代。个体的人在这样一种境况下,所有的‘看见’,都可能是被动的,匆忙的,看见后又迅速遗忘的。环顾四面八方,看见那么多人用卡片机、用手机不断拍照时,我总是想,人们试图用留下图像的方式抵抗遗忘。我也喜欢用照相机,喜欢通过不同功能的镜头去‘看见’。但不是为了保存记忆,而是试图看见与肉眼所见不太相同的事物如何呈现。” 我知道,阿来所担心的是,消费时代的“看见”,有一个巨大的缺失,那就是缺乏内省。这个时代提供给我们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它在提供巨量信息的同时,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我们的某种判断方向,很容易让我们在“阅读”和“经历”这个时代生活的时候,迷失个性的体验及其判断。阿来希望“看见”的,是经过自己主动选择的。而“所有经历过、打量过、思虑过的生活与事物,要很老派地在自己的记忆库中储藏,在自己的情感中不断地发酵。一切经历、打量和思虑的所有意味,要像一头反刍动物一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记忆库中打捞出来细细咀嚼”。b可见,阿来的“看见”是文学的看见,他追求的是更加个性化的审美,他努力摆脱的则是历史写作中不可避免的外来意志的驱动,拒绝另一种极易丧失鲜活生命气息的“虚构”,他喜欢个人在时代和生活中的“意识流”“生活流”。无论是《尘埃落定》《空山》,还是《格萨尔王》《瞻对》《云中记》,以及《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都是阿来的“生活流”和“思想流”,飘逸、凝练、自由、奔放、厚重。因此,在阿来的诸多文字中,我们感受到在对历史的焦虑和疑问里,他执着地梳理,充分地舒展精神和语言个性及其纵深度。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阿来在写作中 似乎有意无意地混淆现实和写作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他灵感的泉源,都是在大地上行走时用心“看见”的、思考过的。 在这里,我用这么多的文字来铺垫、引申出我对阿来小说写作及其发生学的理解,完全是为了能更好地阐释和说明阿来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阿来是如何“看见”和处理我们所面对的、复杂喧嚣的生活,阿来的审美活动是如何完成的。我们会看到,阿来文学的“阶梯”与“阶梯”之间,不仅架构着历史、现实,还延展着自然和人性,阿来所要呈现的,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所“看到”的一切内在的真实和美好,在这里,我们能够深刻地感触到阿来小说的“写作发生学”。 《阿来论》是张学昕与梁海两位评论家对作家阿来创作生涯的一次完整回顾。张学昕为大连理工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曾获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另一位评论家梁海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文艺评论界也颇有建树。两位评论家对阿来长期“跟踪式”考察,他们对阿来所*作品的分析、梳理和阐释,让我们深入了解了阿来之所以成为“阿来”,而非其他任*一个作家的原因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