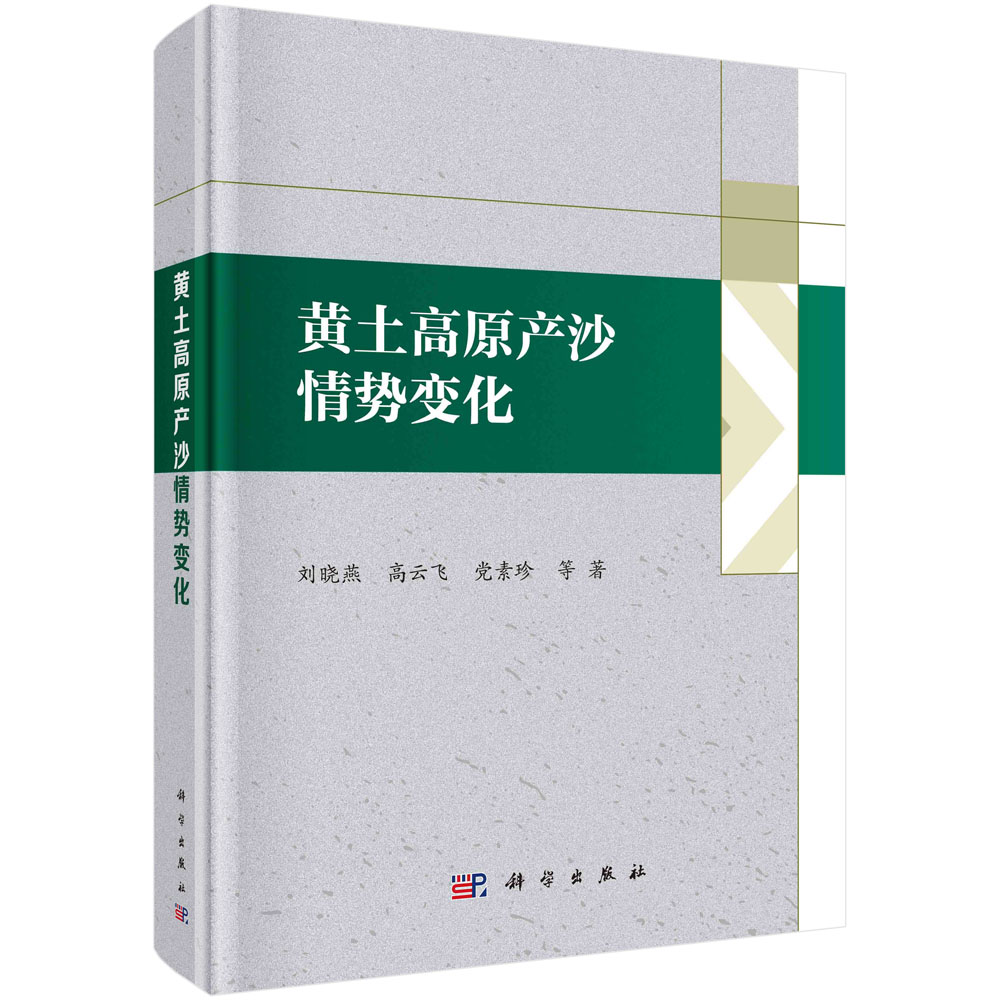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268.00
折扣价: 211.80
折扣购买: 黄土高原产沙情势变化
ISBN: 9787030675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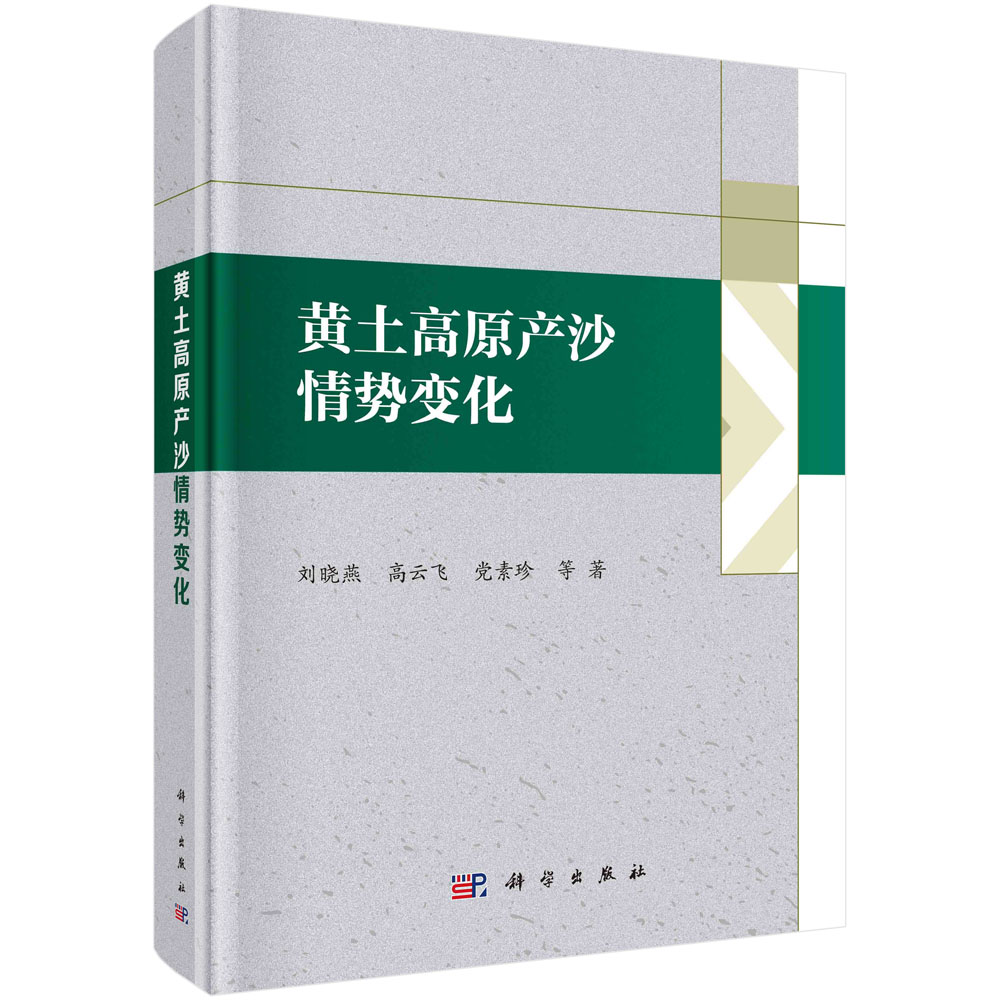
第1章 总论
1.1 研究背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全长约5464km,流域总面积约79.5万km2(含内流区面积4.2万km2),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九省(自治区),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注入渤海。
黄河流域地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三个台阶。兰州以上地区多属青藏高原,局部属黄土高原,年均降雨量490mm,是黄河径流的主要来源区,年均贡献约57%的径流,取用水量仅占全河的7%。流域中部是群山、平原和沙漠环绕的黄土高原,年均降雨量440mm,是黄河泥沙和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地。黄河下游是地上悬河,汇入水沙和废污水很少,为黄淮海平原的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便利。
黄河以“水少沙多”著称于世。1919~1959年,黄河陕县水文站实测输沙量16亿t/a(该站输沙量占全河的98%以上)、实测径流量426亿m3/a、7~9月汛期含沙量59.7kg/m3、最大含沙量716kg/m3,含沙量居世界大江大河之首。巨量的泥沙不仅是下游河床淤积抬高、防洪形势严峻的症结,也给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带来很大困难。因此,黄河泥沙问题研究历来受到高度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来沙持续减少,见图1.1。统计表明,1980~2020年潼关年均来沙5.15亿t,其中2000~2020年年均来沙2.45亿t、7~9月汛期平均含沙量20.6kg/m3、最大沙峰含沙量431kg/m3。
图1.1 1919~2020年黄河沙量变化
1919~1959年为陕县水文站数据;因三门峡水库修建,陕县水文站1960年撤销,之后被位于其上游约100km的潼关水文站取代,故1960~2019年为潼关数据
黄河中游的河口镇至龙门区间(以下简称河龙区间)、渭河咸阳以上、泾河张家山以上、北洛河头以上和汾河河津以上不仅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也是对黄河下游危害最大的产沙区。1980年以来,该区来沙同样持续减少,其中7~9月汛期含沙量在2003年后大幅降低,见图1.2。
图1.2 1933~2020年黄河中游沙量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来沙的大幅减少,尤其是2000年以来的锐减现象,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其核心关切点是,黄河来沙大幅减少的原因是什么?黄河水沙变化的未来趋势如何?
2011年以来,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若干专项研究经费的支持下,我们以潼关以上黄土高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查、遥感调查、实测数据分析和数字试验等研究手段,分析了1919年以来的降雨和下垫面变化、植被和梯田对流域产沙的影响规律、过去百年和未来不同水平年的流域产沙情势,旨在为客观评价黄河水沙情势提供决策支持,本书即为该项研究成果的总结。
1.2 研究范围
众所周知,黄河泥沙主要来自黄土高原,这里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黄土高原地跨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和河南等省(自治区),涉及黄河流域大部和海河流域局部,是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也是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大的高原。
有关黄土高原的范围和面积,曾经出现过几个不同的数据:据《黄土高原现代侵蚀与治理》(陈永宗, 1988)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组, 2002),黄土高原包括青海日月山以东、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面积62万km2;而据《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孟庆枚, 1996)和《中国江河1000问》(董哲仁, 2001),黄土高原西起日月山,东至太行山,南抵秦岭、伏牛山,北达阴山,面积64万km2。
本书关注黄土高原,旨在分析其产沙情势变化,以阐明黄河近几十年来沙减少的原因和未来情势,而黄河泥沙的标志断面是潼关(陕县)断面。鉴于此,本书所称的黄土高原,是指黄河循化—青铜峡区间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以下简称黄土丘陵区或黄丘区)(年均降雨量≥200mm)、内蒙古十大孔兑流域上中游、黄河河龙区间、汾河流域、渭河咸阳以上、泾河张家山以上和北洛河头以上地区。该区不仅包括了长城以南的黄土高原,也涉及黄河内蒙古段与长城区间的黄河流域,总面积约39万km2,见图1.3,图中的“多沙区”是20世纪80年代界定的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区范围(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2012)。
在图1.3所示范围内,不仅有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黄土高塬沟壑区(以下简称黄土塬区),还有水土流失轻微的土石山区、关中平原、汾河平原区、黄土丘陵林区(包括子午岭林区和黄龙山林区)、干旱草原区和风沙区。因此,为进一步聚焦研究对象,我们将“黄河循化—兰州区间黄土丘陵区(不含庄浪河,以下简称兰循区间)、祖厉河流域、清水河流域、十大孔兑上中游、河龙区间(不含土石山区和风沙区,以下简称河龙区间黄丘区)、汾河兰村以上(不含土石山区,以下简称汾河上游)、北洛河刘家河以上(以下简称北洛河上游)、泾河景村以上(不含土石山区,以下简称泾河上中游)、渭河元龙以上(不含土石山区,以下简称渭河上游)”作为重点研究范围,即图1.3中的黄色区域,面积21.5万km2。若包括区内的土石山区和风沙区,该区面积为26.4万km2。据1950~1969年实测数据推算,该范围流域产沙量为17.4亿t/a,占潼关以上黄土高原产沙量的94%。
1.3 研究现状
黄河来沙减少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研究工作,并延续至今。90年代和近几年是两个突出的研究高潮期,其中,90年代的研究者主要来自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及相关省(自治区)水保部门,近几年则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加入了研究队伍。
回顾过去30年的研究结果,已经达成的共识是,黄土高原入黄沙量的减少是降雨和下垫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由于各年降雨丰枯变化较大,若选择的“现状年”和“基准年”时段不同,降雨和下垫面的减沙贡献有所不同。例如,在1980~2009年,黄河主要产沙区几乎一直处于降雨偏枯的时期,因此降雨一直是人们心中的减沙因素。但在汛期降雨大幅偏丰、暴雨明显偏多的2010~2019年,显然不能再将降雨视为减沙因素。可这样的结论会对有些人的思维定式造成“冲击”。未来,只要汛期降雨再度转枯,降雨必将再次成为减沙因素。由此可见,如何讲好黄河水沙变化的“故事”,是每个研究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图1.3 研究区范围
在减沙原因辨析方面,人们似乎更愿意划分成“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两方面,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近几十年黄土高原输沙量大幅减少,既有植树造林、种草封禁、梯田建设、坝库拦截和引水引沙等人类活动的贡献,也有农牧民“自愿”进城务工、经商或陪子女读书等使大量耕地撂荒、“荒草”丛生等人类“不活动”的贡献,还有降雨增加、气温升高、风力减小、CO2和N2浓度增加等有利于植被生长的气候条件贡献。降雨不仅是产水产沙的动力,也是植被生长的动力;气温变化对植被生长有重要影响,也会影响冻融侵蚀强度;CO2和N2等因素变化则对植被生长有显著影响。基于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仍难以准确剥离降雨因素、其他气候因素、人类活动和人类“不活动”等对林草植被恢复的贡献率,将它们笼统划分为降雨因素和下垫面因素两大类因素,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其中下垫面是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和人类“不活动”的总效应。
剥离淤地坝、水库、梯田和林草植被的减沙贡献也一直是黄河水沙变化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一方面,面对潼关以上39万km2的黄土高原,甚或21.5万km2的黄河主要产沙区,如何科学、准确地掌握这些因素的真实情况,包括5万余座淤地坝和水库在不同时段的实际拦沙量、能够发挥减沙作用的梯田面积变化及其空间分布、能够客观反映对地表土壤保护程度的不同时期林草植被覆盖状况,是研究者面临的首要困难。其原因在于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往往与科研需求相差甚远,科学且高精度的全面调查又投资巨大、耗时费力。另一方面,面对地形和土壤类型复杂多样的广大黄土高原,如何在流域尺度上定量刻画出梯田和林草植被变化对流域产沙的影响规律,也是研究者面临的突出难题。无论是常用的“水保法”,还是用于描述坡面土壤侵蚀的国外模型改进版,或存在空间尺度的转换问题,或需要解决从“土壤侵蚀”到“流域产沙”的过渡问题,否则均难以全面反映地表要素变化所引发的“本地+异地”减沙作用。
即使说清了过去某时段的来沙减少原因,仍然不一定能回答现状下垫面在长系列降雨情况下的产沙量。众所周知,常被人们视为黄河天然时期输沙量的“16亿t/a”,指的是1919~1959年下垫面在此40年长系列降雨情况下的年均输沙量。显然,如果降雨条件与此不同,即使仍然基于1919~1959年的下垫面,黄河沙量也不可能是16亿t/a,降雨越丰、沙量越大。因此,采用现有的研究方法或模型,即使能回答近20年或近10年的降雨、植被、梯田和坝库的减沙量,也不一定能回答该下垫面在1919~1959年降雨条件下的可能产沙量、可持续和暂时的减沙量,故不易实现研究成果与用户需求之间的“无缝衔接”。
预测未来不同水平年黄土高原的产沙情势和入黄沙量,是黄河水沙变化研究最重要的目标。为此,人们一方面要准确阐明未来的气候尤其是降雨的情景,另一方面还要科学且定量地阐明未来下垫面的发展情景,尤其是植被发展情景。对于未来的降雨情景,目前可接受的处理方式是“设定一个或几个可能的降雨情景”。对于未来下垫面的植被情景,不少生产单位或管理部门似乎更倾向于采用规划的植树造林和封禁退耕规模,但受气候和社会条件制约,规划数据很难与实际的林草植被覆盖程度挂钩。当然,除基础数据外,科学的计算方法仍然是预测未来产沙情势面临的难题。笔者自2011年投身黄河水沙变化研究,并在2016年提出了阶段性研究成果(刘晓燕等, 2016)。虽兢兢业业、不敢懈怠,但限于个人学识和能力禀赋,加之研究时间限制,早期阶段对以上问题的解决仍不能令人满意。
2016年以来,笔者一方面继续高度重视基础数据的采集与处理,另一方面加强了流域产沙变化规律的研究力度,希望通过基本规律和基础数据的双轮驱动,使研究成果更可信可靠。
本书侧重服务于黄河治理与开发重大工程布局及其运用原则、水资源配置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对策等重大问题的宏观决策者和规划制定者,而非场次暴雨的洪水泥沙实时预报,故偏重在较大的时空尺度上开展工作。土壤侵蚀是流域产沙的前提,但侵蚀产物不一定都能输送到流域出口,本书重点关注流域产沙量,即无坝库拦截情况下能够输送至出口断面的沙量。
1.4 成果与创新
2011年以来,研究团队利用中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解译了林草植被变化和梯田面积信息,结合大量实地查勘和文献查询,揭示了黄土高原产沙环境演变过程与趋势;通过对基础数据的科学定义和处理,发现了林草植被和梯田变化对流域产沙的影响规律;多方法协同,科学诠释了黄土高原产沙变化的原因和趋势。
(1)提出了更能科学反映黄土高原产沙环境状况的林草植被、梯田和降雨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方法,形成了长时间序列的产沙驱动力因子数据集,揭示了黄土高原产沙环境演变过程与趋势。
高度重视基础数据采集与处理、广泛开展野外查勘,是本书的突出特点。基于空间分辨率为30~56m的1978年、1998年、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8年等典型年份的遥感影像,提取了黄土高原各支流的林草地面积和林草植被盖度、旱耕地面积等信息;基于空间分辨率为250m、1km和8km的遥感影像,提取了1982~2020年逐年植被盖度。基于空间分辨率为2.1m的遥感影像,提取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