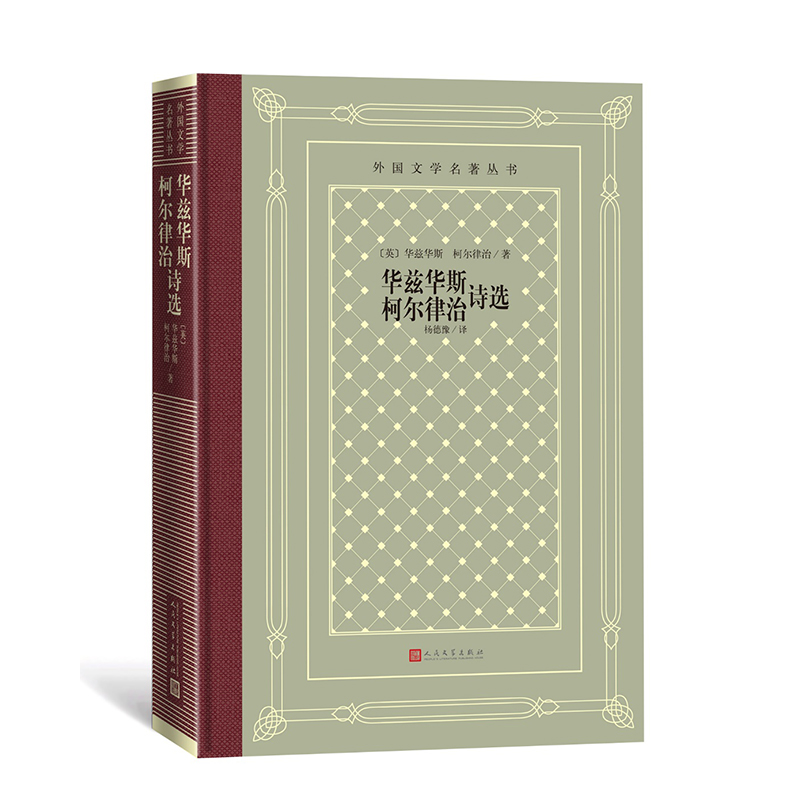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2.20
折扣购买: 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020152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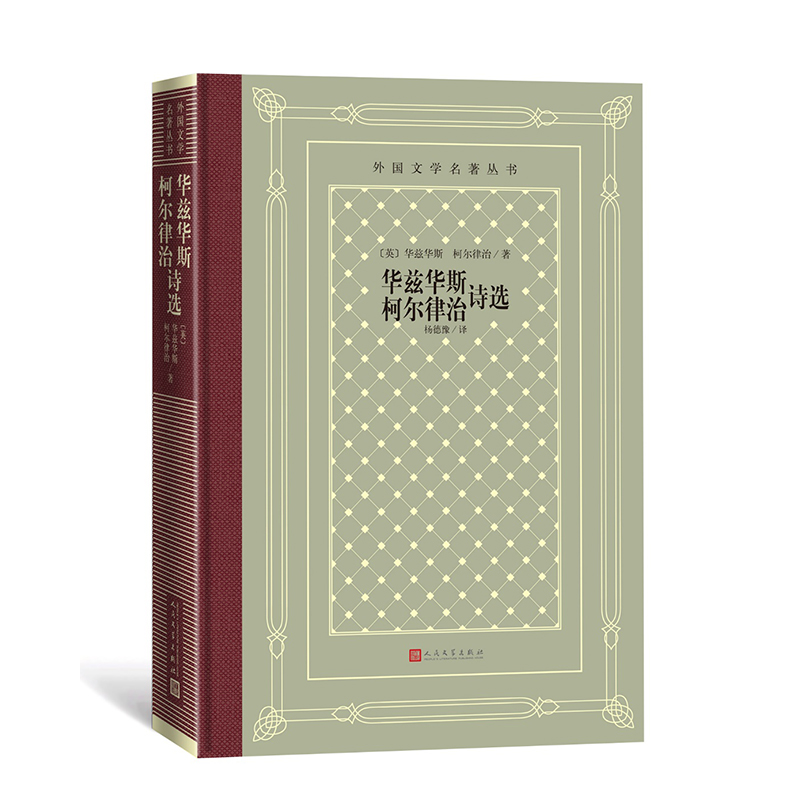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与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浪漫派诗人。合著的《抒情歌谣集》(1798)发起了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他们的交往始于1797年,华兹华斯兄妹二人甚至搬至柯尔律治附近居住。华兹华斯生活经验较多,对故乡的自然风貌十分熟悉,柯尔律治受过极好的教育,尤擅长抽象的哲学思维。他们主张诗歌应该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强调激情和想象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译者简介: 杨德豫(1928—2013),笔名江声、张四等。湖南长沙人,国学大师杨树达之子。少年时代即发表旧体诗。代表译作有《朗费罗诗选》《鲁克丽丝受辱记》《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等,其中《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获萧乾、屠岸、绿原、孙绳武、文洁若等翻译大家联名推荐,并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
译本序 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英国十九世纪初叶文学地平线上两颗明亮的星,通过历史的暗夜远眺,从那一特定的空间传送入我们视野的首先是他们的光辉,毕竟距离并不遥远,这两颗明星不平坦球面上起伏凹凸的阴影也都清晰可辨。 如果在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时过分看重阴影而宁愿忽略其光照深远的明辉,只读中文译本的读者就难以一窥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渊源、流程和全貌。杨德豫这个选译本的问世,是中国读者之幸,也是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之幸。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一七七○年出生在英格兰西北部坎伯兰郡的一个律师家庭。八岁丧母,十三岁丧父,由舅父照管。童年就读于湖区的寄宿学校,深受当地自然景物的陶冶。一七八七年进入剑桥大学。一七九○年和一七九一年两次游历欧陆,对法国大革命充满热情。一七九二年回国。后来,舅父因他同情法国革命而中止对他的接济,在窘迫中,一个患重病的朋友由于仰慕他的诗才,在去世之前把九百镑遗产留赠给他,使他得以不愁衣食,写诗度日。一七九九年定居于湖区;一八○二年结婚;一八一三年被任命为印花税务官;一八四三年,继骚塞之后被任命为年金三百镑的桂冠诗人。一八五○年,度过八十周岁之后去世。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比华兹华斯年轻两岁,是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一个乡间小镇清贫牧师的儿子。九岁父死,十岁被送往伦敦基督慈幼学校。一七九一年入剑桥耶稣学院;一度化名从军,当过几个月龙骑兵;一七九四年,不曾获得学位便离开了大学。同年,与当时的牛津大学生罗伯特·骚塞相识,二人曾有过前往北美建立一个“大同邦”的计划,并合作写成了一部三幕剧《罗伯斯庇尔的覆亡》。 对于英国文学和对他们本人都更重要的,是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相识和合作成果。一七九五年九月,柯尔律治第一次见到华兹华斯便断定他是“当代最优秀的诗人”。他们出身不同,境遇各异,但是这时却都在思想上经历着青少年时代的民主共和观点、劳动人民悲惨处境所激起的愤怒、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欢迎,逐渐被放弃一切政治活动而寄希望于人类精神完善的态度所代替的类似过程。 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亲密交往开始于一七九七年,这种交往甚至导致华兹华斯兄妹二人搬到了离这位新朋友更近的地方去住。华兹华斯有较多的生活经验,能理解现实中的各种现象,对故乡的自然风貌十分熟悉。柯尔律治受过极好的教育,对抽象的哲学思维有更优异的能力。他们出色地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了许多极为一致的观点:他们都认为英国诗歌自弥尔顿以后早已江河日下,都反对所谓新古典主义或伪古典主义的矫揉造作、陈词滥调和清规戒律,都主张诗歌应该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强调激情和想象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振兴英国诗歌,他们相识不久便酝酿着合写一部诗集。据柯尔律治后来回忆,“华兹华斯和我成为邻居的第一年,我们经常谈起诗歌中的两个问题:在遵循自然真实性的情况下唤起读者共鸣的能力;借助想象力改变一切的色彩赋予诗歌以新颖趣味的能力。当时决定出版一部两种诗的合集:一种诗中的事件和出场人物应该是超自然的(即使部分是也行),以便用描绘不可避免要和有关环境伴随在一起的戏剧性感情来吸引读者”;另一种诗则写普通人普通事而“赋予日常现象以新颖的魅力……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昏睡中唤醒,使之转向我们这充满奇迹和无尽宝藏的美丽世界”。 柯尔律治只为合作的诗集写了四首较短的诗和一篇长诗《老水手行》,其余均为华兹华斯所作。这部诗集就是一七九八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一八○○年再版时,华兹华斯又增写了一篇长序,竟成了浪漫主义诗歌在英国正式诞生的里程碑。这篇序言既是两位诗人共同的宣言,也隐伏着导致他们日后激烈争执的分歧。 处理超自然题材而表现出非凡才能的杰作《老水手行》,和以未完成残篇传世的《克丽斯德蓓》和《忽必烈汗》,就几乎构成了柯尔律治大诗人声誉的全部基础。他认为“没有一个伟大诗人不同时又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因为诗是人类一切知识、一切思想、激情、感情、语言的花朵和芳香”。柯尔律治本人就同时是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美学奠基人的独特贡献,更是没有人能望其项背。 华兹华斯以平凡的语言写平凡人物、平凡事件的成功尝试,仿佛是单枪匹马在诗歌领域实现了他已在政治领域退出甚至反对的一场民主主义革命。他相信只有最普通、最朴素的语言才能和真理相称,“诗歌是强烈的激情送到人们心里的真理”。他的长诗《序曲》及其实际上的前奏《廷腾寺》,在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赋予哲理诗以强烈的个人色彩,给哲学理念插上了能够有效叩开人们心扉的感情羽翼。 柯尔律治在他那部最重要的自传性散文著作《文学传记》(1817)中对华兹华斯有精辟的评论。虽然写在他们交恶之后,他仍公正地肯定,华兹华斯的突出优点是“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感情的结合,所观察到的事物的真实性和使观察的事物发生变化的想象力之间的惊人的平衡;尤其出色的是将观念世界的色彩、气氛、深刻性和崇高性推及在习惯的观念中失去光泽的人物、事件、情景的独特天赋”。同时,他也指摘华兹华斯修辞的前后不一,文体上雅俗变化的突兀,诗人强烈感情与所写无足轻重事物的不相称,人物语言与作者语言的不协调或混同,特别对他关于诗的语言应是实际生活语言,而最好的语言是社会下层田间地头语言的理论提出异议,并正确地指出,华兹华斯的好诗恰恰是摆脱了这一理论影响的作品。 两位诗人的大多数优秀诗篇都完成在他们密切交往期内,甚至可以认为是那段美好友情的成果,因为他们对彼此的创作都互有贡献,以至有些诗句并见于双方的作品。一八○五年后,柯尔律治就很少写诗了,此后健康日渐恶化,而于一八三四年病逝于伦敦。华兹华斯活得更久些,创作生命也更长一些,却由于政治和社会思想日甚一日保守乃至于反动,充当桂冠诗人的条件是具备了,诗的灵感却渐告枯竭而鲜有佳作。 杨德豫这个选译本,不仅收入了柯尔律治的全部杰作,也包罗了华兹华斯较短篇幅的全部精品,因而既是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代表作合集,也是英国早期浪漫主义和湖畔诗人诗作的精华。他们正是或主要是凭借这些作品开了一代诗风,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司各特、雪莱、济慈、拜伦、德·昆西、兰姆、赫兹利特、亨特,和较晚的胡德、丁尼生、勃朗宁、罗斯金、斯蒂文森、哈代、吉卜林等人。 这部诗集也可以认为是杨德豫的译诗代表作。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都不用汉语写作,没有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就不会有这部汉语诗集;如果译者在译作中不追求既要忠实于原作内容又要忠实再现原作形式,汉语读者也就无从通过近似于英语原貌的汉语形式去领略这两位英国大诗人的原作内容。 杨德豫是已故国学大师杨树达的哲嗣,于诗、于文、于驾驭语言文字,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自幼聪慧过人,而且博闻强记,凡有所事莫不精益求精,对于译诗艺术的不懈探求更是从不知有穷尽。译《朗费罗诗选》和莎士比亚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起点就很高;主持编译“诗苑译林”丛书期间又有机会较深入地明辨译诗各家之长短、不同方法之优劣,并因而创造性地接受了卞之琳有关“以顿代步”翻译英语格律诗的主张,译《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又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应该说是他更高的成就,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我国以现代汉语格律诗译外国格律诗的典范之作。 江枫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日 北京昌运宫 关于《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译后记) 把华兹华斯、柯尔律治两人的诗选合为一书,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出的安排,译者是奉命行事。 一 对诗人的评价问题 如何评价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这一问题,既有相当广泛的共识,也有截然相反的论调。 这里想着重谈谈华兹华斯,谈谈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们对他的或褒或贬的说法。 十九世纪,华兹华斯在国外远没有拜伦那样大的名气和影响;在英国国内也是毁誉不一,沉浮不定。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才由权威评论家、诗人马修·阿诺德郑重指出: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个,也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以后英国最重要的诗人。二十世纪以来,这种评价逐渐得到英美文学界多数人的认同,也被各种文学史、传记、辞书所沿用。现在,在英美各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文学史家中间,对这一结论提出重大异议的已经不多了。 英美多数学者的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如下的论据之上的:(一)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奠基人,他和柯尔律治共同开创了英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时代,在诗艺上实现了划时代的革新。(二)他是二十世纪欧美新诗理论的先驱,他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论点和主张,把诗和诗人的地位、使命和重要性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三)他的代表作《序曲》《廷腾寺》《永生的信息》和其他若干作品,以发掘人的内心世界为主旨,开了二十世纪现代诗风的先河,是英诗向现代诗过渡的起点,他因此而被称为“第一位现代诗人”。(四)他是“讴歌自然的诗人”(雪莱语),他以饱蘸感情的诗笔咏赞大自然,咏赞自然界的光景声色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在自然与上帝、自然与人生、自然与童年的关系上,他用诗歌表达了一整套新颖独特的哲理。(五)他首创了一种洗尽铅华的新型诗歌用语,用以前的英国诗人从未用过的清新、质朴、自然、素净的语言来写诗,体现了深刻思想、真挚感情与朴素语言的完美结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直至今日的诗人。(六)他终生定居于田园乡野,比其他任何浪漫派大诗人都更加接近和关切农村下层劳动群众;他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观点,以满腔的同情和敬意,描写贫贱农民、牧民、雇工、破产者、流浪者直至乞丐的困苦生活、纯良品德和坚忍意志,创作了诸如《迈克尔》本书第46页。《玛格丽特》(即《村舍遗墟》)等许多篇传世杰作。(七)他热心关注国家命运和欧洲政治形势,为当时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反抗拿破仑帝国侵略压迫的各国人民写了不少激情洋溢的赞歌;而在拿破仑力图跨海进犯英伦三岛,祖国处于危急关头的日子里,他又写了若干首慷慨壮烈的爱国诗篇,号召国民挺身捍卫祖国的自由和尊严,起到了振奋国魂、激扬民气的巨大作用,他本人也因此而名垂青史。(八)在诗歌体裁方面,他使素体诗和十四行诗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力量。 英美学者在对华兹华斯做出高度评价的同时,也从未讳言或忽视诗人的令人遗憾的另一面,诸如:他中年以后政治立场转向保守甚至反动(在英美,人们对此也同样持批评态度);他诗才焕发、佳作迭出的鼎盛时期只持续了十年左右,此后即渐趋笔涩神枯;他的好诗与劣诗相差如天悬地隔,好诗“标志着十九世纪诗歌的最高水平”(爱默生语),劣诗则伧俗鄙陋,味同嚼蜡;他与英国另几位浪漫派大诗人相比,在不同的方面各有短长,在若干方面他确有逊色;等等。但是学者们认为,这些问题并不影响上文所述的对这位诗人的总体评价。 而在英美以外的某些国家里,对华兹华斯等人的看法和说法却与此大不相同。最激烈的反对声浪来自旧日的苏联,在我国也曾洋洋盈耳。义愤填膺的批评家们振振有词,把华兹华斯贬斥得几乎一无是处。他们的论据主要有以下这些:(一)华氏美化英国农村的宗法制小农经济,以小有产者的落后反动意识来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企图让历史倒退。(二)对于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华氏不但不鼓励他们奋起抗争,反而极力宣扬和赞美他们忍辱负重的性格,并用宗教精神和道德说教来劝诱他们安于现状。这种批评确有事实依据,但事实还有另一面:华氏也写过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诗,如《罗布·罗伊之墓》。(三)对法国大革命,他只同情温和的吉伦特派,而反对激进的雅各宾派,在革命深入发展时便惶惑、动摇以至变节转向。(四)他中年以后转而支持英国托利党政府的反动内外政策,晚年甚至写诗把革命咒骂为“瘟疫”。(五)他的历史观是反动唯心论的,认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神圣的“天意”,带有浓重的宗教神秘色彩。(六)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也从反基督教的泛神主义者退化为英国国教的信奉者。(七)他的诗集里充斥着思想和艺术都很平庸甚至低劣的作品。应当承认,苏联等国的批评家们所指出的这些,也并非凿空之谈,而是凿凿有据。问题在于,从这几条论据不难看出,这些批评家论证作家和作品的优劣,基本上只用一个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那么,他们做出把华兹华斯全盘抹杀的结论也不足为奇。 至此,对上述正反两方面的说法,我们已做了一番全景式的鸟瞰。看来,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到华兹华斯的作品中去,去感受,去体察,去吟味,去领悟,去思索,去辨析。有了自己的主见,才能对上述正反两种说法做出恰当的判断和抉择,也才能对这位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做出较为全面、较为公允的评价。 柯尔律治的经历与华兹华斯颇有相似之处。在政治思想上,他也是从激进到保守;在诗歌创作上,他也是从健笔凌云到才情耗尽。所以他也像华兹华斯那样,既受到一些人的盛赞,也遭到另一些人的丑诋,详情就不再缕述了。这里不妨举《烈火、饥馑与屠杀》一诗为例。对这首诗持肯定态度的人们认为:这首诗是柯氏二十六岁所写,当时他还站在反对皮特政府的立场上,诗中对皮特抨击的猛烈程度,一点也不下于拜伦、雪莱对卡瑟瑞、艾尔登等人的抨击,皮特曾任首相,卡瑟瑞曾任外交大臣,艾尔登曾任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三人都是英国反动政治家。诗的结尾甚至扬言要把皮特捉起来“砍成几段”,还要用烈火烧他,造反精神可谓臻于极致。而在苏联,批评家们却说:这首诗把皮特吹嘘为法力无边的魔王,凡人奈何他不得,全诗笼罩着恐怖气氛和绝望情绪,意在震慑人民使之不敢造反。这样两种针锋相对的论断,究竟是见仁见智,各具慧眼呢,还是盲人摸象,各执一端呢?我们别无他法,唯有去研读那首诗本身,到那八十一行戏剧对白中去寻求答案。 二 本书翻译的情况 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绿原先生之约,开始译华兹华斯的时候,女儿晓煜正准备从幼儿园升入小学;现在将《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向出版社交稿的时候,晓煜已经进入首都的高等学府了。回想起来,她读小学的六年,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译华兹华斯(只需扣除住院大半年,修改和增补《朗费罗诗选》大半年);她读中学的六年,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译柯尔律治(扣除住院一年多,修改《鲁克丽丝受辱记》大半年,以及出差几个月)。总之,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除了译出《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以外,十余年的精力和心血(在“痴儿了却公家事”之后),差不多都倾注在这本书上了,比古人所说的“十年磨一剑”犹有过之。可惜这把剑虽磨了十年以上,锋刃仍未能削铁如泥,说来令人惭愧。 本书共收华兹华斯的诗一百零八首(四千一百九十五行),柯尔律治的诗三十三首(二千八百行)。本来还想从华氏长诗《序曲》中选译数百行,无奈近来缠绵病榻,力不从心,只得作罢。在我国,《序曲》已有广州楚至大教授的全译本,北京大学英语系也将推出另一种全译本。 翻译时所据的原文华兹华斯诗集有以下四种:欧内斯特·德·塞林科特和海伦·达比夏校注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五卷全集(1940—1949);伦敦邓特父子公司“人人丛书”中的四卷全集(1913);马修·阿诺德编选的、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的一卷选本(1936);牛津大学“世界名著”丛书中的一卷选本(1913)。所据的原文柯尔律治诗集也有四种:欧内斯特·哈特利·柯尔律治校注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两卷全集的两种版本(1912,1931);威廉·迈克尔·罗塞蒂编选的、伦敦莫克森父子公司的一卷选本(出版年份不详);约翰·比尔编选的、伦敦邓特父子公司“人人丛书”中的一卷选本(1974)。此外,译华兹华斯时,曾参照《英诗金库》(牛津大学出版社,1929)的有关注释;译柯尔律治时,曾参照梁实秋《英国文学史》(台湾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1985)第三卷的有关部分。 华兹华斯曾明确反对把他的诗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来排列,本书华氏诗篇的分类和排列顺序,都依照他本人生前编定的版本有三首诗,作者本人没有把它们编入集子,本书把它们归入《杂诗》一类。。与华氏相反,柯尔律治则明确表示他的诗应该以写作年月为序,本书柯氏诗篇即据此编排。 入选的华、柯二氏作品基本上都是格律诗,有格律甚为严格的,也有不甚严格的。译者坚持以格律体译格律体,力求做到译诗每行顿数都与原诗音步数一致,韵式(包括行内韵)也仿效原诗。素体诗每行以五顿代五音步,像原诗一样不用韵。综观全书,译诗的格律(顿数或韵式)与原诗有出入的,在华氏一百零八首中只有九首(这九首的题注中都有说明),在柯氏三十三首中只有两首(《克丽斯德蓓》和《失意吟》,详见第341页题注和第436页注①)。此外的一百三十首,诗行顿数和韵式都恪遵原作。 译华兹华斯诗选时,曾得到一些师友的指点或帮助,已在拙译《湖畔诗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的后记中一一致谢,这里不再重复。译柯尔律治诗选时,承钱锺书先生解答《克丽斯德蓓》一诗中的疑难问题,殷宝书先生细心审读《孤独中的忧思》一诗译稿,改正了其中若干谬误和不当之处,在此特向他们敬表谢忱。老友江枫先生惠允为本书撰写前言,更应该向他施礼道谢。 本书大概是译者最后一本译作了。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业余译诗,至今已将近四十年,其中有二十多年光阴无端虚掷,剩下的十几年,成果也寥寥可数。日忽忽其将暮,未免去意徊徨。记得华兹华斯说过:“我们只求:自己的劳绩,有一些/能留存,起作用,效力于未来岁月。” 倘能如此,于愿足矣,夫复何求! 杨德豫 一九九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