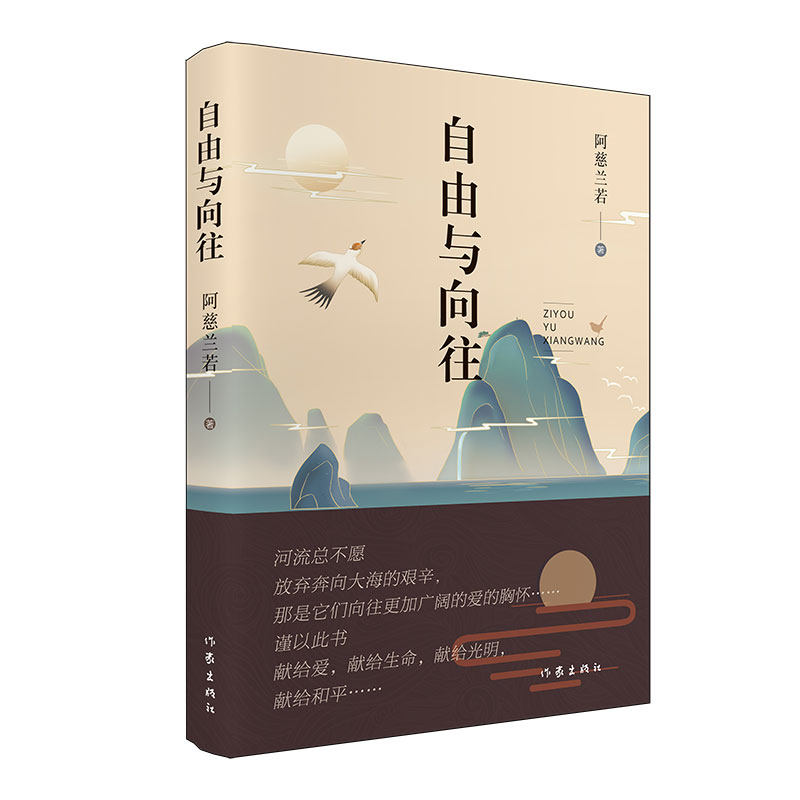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6.00
折扣价: 29.50
折扣购买: 自由与向往
ISBN: 9787521208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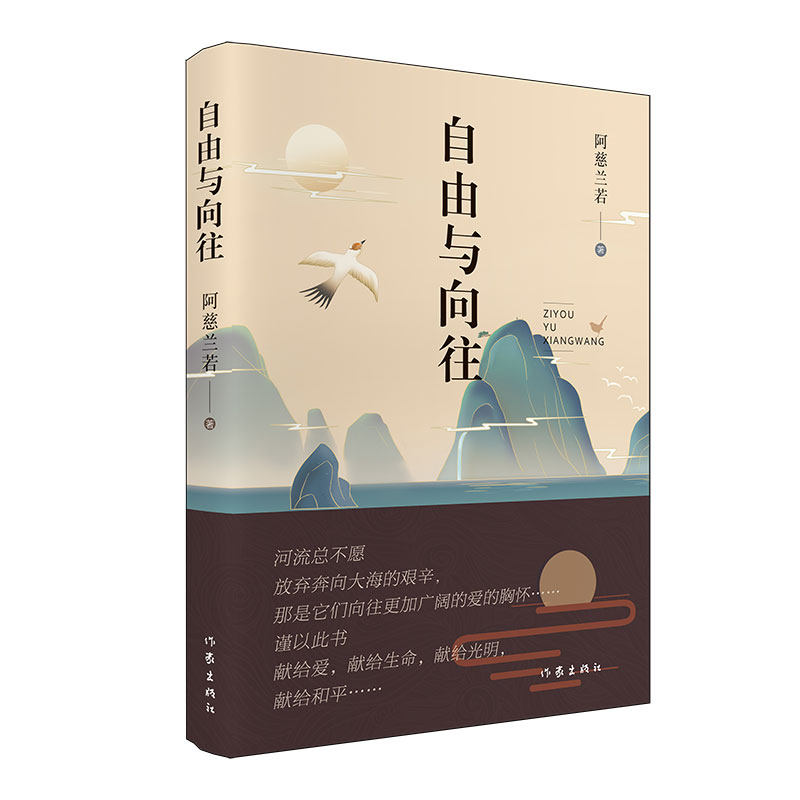
阿慈兰若,又名阿慈、智行,原名孙云乾,生于1967年,祖籍甘肃。文化学者,中国当代著名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浙江舟山市、浙江海洋学院港台侨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有散文、散文诗、诗歌、小说、文学剧本等多种题材、体裁作品问世并获奖。曾出版散文诗集《阳光的手指》《葵花的语言》,散文集《月上溪头俗笔选》和散文与诗之合集《太阳里的扎龙》等专集;警世书籍《栖月庐笔记选》;长篇小说《菊香》《遗忘与宽容》《复活的世界》《有因有缘》《说缘》等;文学剧本《上辈子我曾是你什么人》(二十一集)。长篇系列小说《复活的世界》获第九届敦煌文艺奖,其中第一部《灵魂史》(原名《遗忘与宽容》)的删节本获第五届黄河文学奖并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曾整理校订并编著了《大清三藏函序及目录检索》一书,完善了从古及今藏经系统,在海内外颇有影响。
和平之歌 ——遥想故乡的雪 写在前面的话 为创作长篇小说“生命三部曲”——《灵魂史》《大地史》和《生命史》三部大书,算来已将自己关闭了近四个年头。 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年的元月下旬,正值旧历年的腊月,几乎大半个中国都经历了罕见的大雪洗礼。大年三十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机场、码头、火车站、汽车站……凡是能够运输的站点都云集着大批急于回家过年的人。 我抱着一个硕大的暖水袋望着窗外厚厚的积雪,朦胧中似乎融入了万里之遥的故园北国…… 我写了一篇散文,漫漫漶漶如飘洒无尽的雪花…… 小说写完了,奥运开过了,冬季又来了,地上,桌上,书架上……积雪似的稿子堆放得到处都是。又要下雪了,终于决定好好清理一下屋子,好让心灵回归到清宁的最初,让久违的纯洁再一次掩埋住久已积垢的尘世。我明白,一定要从心开始…… 又过了四年,小说也出版了,获奖了,雪片样地发行了。我从积稿中拣出这篇每年都要重读几遍的散文,由衷地以一种欢喜布施的心情供养大家,和大家分享一点记忆中快乐的时光,以及那无与伦比的中国凝聚精神——当国家民族面对困难时集体不约而同所迸发出的团结力量,这种天然的文化的灵魂精神,也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不灭火种,我们有必要时时让它把我们的心空照亮。 于是,这篇文章,这篇大型散文,我还是决定拿出来发表了。更有意义的是,今年又是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的一年,真是令人振奋不已。 一 从几千米的高空,到大地上的电线和早已凋尽叶子的老榆树上,还有杨树和杏树的干枝杈间,黑色的花朵冰雹那么密集地下着,又雪花般无边无际地飘飞着。真不知道我这种愚笨的比喻是否得当,但我只能这么来形容。 每年到了这种季节,数以万计的乌鸦、鸬鹚和鸽子像春天来临之际,一时不知从何种神秘的空间里雨点似的布满所有房屋以外的地方,接着又是燕子和山雀们重复着同样的情景。 真的,我简直无法形容它们的数量之众,和飞行时间之长,它们像4月的北极朱海雀与绒海鸥一年一度的大迁徙,铺天盖地那样密集地飞行和盘旋,大概要持续半月之久才见稀疏。 此时,田野里的麦子、糜子、谷子、扁豆和胡麻等作物,早已从七八月份收割完在田地里晾晒后运回场上垛成了大垛子。荞麦也已收割,大片的洋芋田也已翻犁打耱,一车一车的洋芋均已被驴车拉回家,下了地窖。除了麻雀和白头翁们继续云集在新翻犁的田野中,抠食苟延残喘的一些虫子和遗落在泥土里又发了芽的粮食外,山坡和河谷中,就连田鼠和黄鼠的叫声都再也听不见了,只有一群一群像鹌鹑似的半翅子(坚鸡),呱啦呱啦地在坡上从容地边走边唱,如同刚下过蛋四下炫耀的老母鸡,昂首挺胸,声音亢奋,会把山中方圆几公里的宁静打破,但这种声音并不烦人,好像更增加了山里特有的清宁。它们的家建立在远离人烟的山谷中那些大墩的吸呼茅、燎眉子蒿和浓密而高大的野苜蓿地里,我与伙伴们像狐狸那样幸运地找到过它们并不隐秘的居所,还盗窃过它们整窝整窝的蛋,一窝就有十几枚之多。唉,人的出现,使得世上的逻辑都变得那么不符合逻辑,让一切逻辑看上去显得那么的尴尬和无奈。假如没有人类的威胁,那该多好啊,它们一定会生活得更加从容。可是,人类自己在今天的时代里,谁敢那么从容地在同类们生活的环境里走走啊?你敢随便走夜路吗?即使是光天化日底下,你敢随便单独去陌生地方,或者走僻背的胡同吗?至少我们已经失去了往昔的从容,而失去的从容,恰恰就是人生至为宝贵的根本内容。 太阳整天躲在灰蒙蒙的云层深处睡懒觉,气温一天天爬竿猴似的迅速下降,看上去,万物一时都清瘦了几圈,疏松了许多,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晰、宽泛。风明显变得有些金属的感觉,冷而劲,像无数无形的细铁丝不停地抽着,所有阻挡它的事物,都会发出痛苦的呻吟,荒野和坡地上万紫千红的草木,像卸了妆的戏剧演员,素雅清瘦,花果凋零殆尽,枯叶更像是被撕碎的戏袍,脏兮兮、皱巴巴地随风飘舞,狼藉四野。一些草木的茎秆依然坚定地站立着,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空气很干冷,地皮上的植被干得只要掉一个烟蒂,便立刻燃起火苗,顷刻间烧掉一大片。最可怕的就数茵陈蒿了,它们简直是两块石头敲击时,溅出来的一点火星也能点燃,“噗轰”一声,一平方米面积就被烧尽了。它们体内的水分像烤箱里烘干了一般,它们身上星子样稠繁的小黄花缩成了小米粒大,和硫黄一样易燃。我们一般不会把燎眉子蒿叫作茵陈蒿的,它们到处都生长,全然不顾忌生长的地方合宜与否,而且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拽着脖颈似的疯长,只要有空间,无论大小,人家屋顶的瓦缝里它也绝少放过,田边、堤埂、崖头、道旁……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和一大墩一大墩的八瓣兰、山马兰、大戟、益母草、骆驼蓬、狼毒花和红头大蓟们一样随处都是,就连那些开着黄花,个头一米五六的菊科植物,以及臭绣球、铁蒿和枸杞们,也很愿意与之毗邻。除了我情有独钟的开着金色的星星样碎花的柴胡另择地方外,马苦苣和大翠雀就是这样很没有意思的一类。虽然我喜欢大翠雀把花朵的腰部作为与茎秆们接触的地方,而不是屁股,虽然我也喜欢把花儿的角尖咬破,吮舐掉里面蜜汁似的花粉,但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因为它们没有像柴胡那样很有个性地、但绝非清高地另择地方。 小时候,放学后去山坡,或地埂和山里面拔柴草,如果贪玩时间长了,一时无法填满背篓,那就只好扯几墩子燎眉子蒿,只要几墩就足可填满一大背篓,但往往是硬着头皮背回家的,因为每次这样回去,都少不了母亲一顿狠狠的责骂。理由很简单,燎眉子蒿蓬茸茸的非常轻,而且占地方,晒干后更是轻似鸿毛,腰粗的一捆,拿起来尚不如一个鸡毛掸子重,所以本地人都叫它是燎眉子蒿,听说它们小时候的名字叫茵陈蒿。我从医学书籍上查到它的名字的写法前,一直认为它叫茵陈,我总在潜意识中,把有一次从一户搬了家的荒宅院子里拔来的几十捆燎眉子蒿联系在一起,便死死地认定了它就叫茵陈。我将那十几捆蒿子码在院中园子的矮墙上,半月不到,它们就干透了,每拿起一捆,下面都会有数百只八脚长颈鹿腿蜘蛛和各式各样的大小蜘蛛与甲虫,还有一些粪虫,像天牛的多样变种,更有趣的是里面爬满了豌豆大的黑色、褐色和灰色的小蝶,当然,蜈蚣和蚰蜒自是少不了的了。因此,对这种植物很反感,不知为什么,老是和“阴沉”二字联系在一起。阴沉,故装深沉,看似充实,实则空虚,外显高洁,内则轻薄。可见表面上看似深沉的人或事物,一定大有虚伪不实之处,善加伪装才显深沉呢?大智若愚这种话可能多体会一下,会增加人一些好眼光,或深刻认识人和事物的能力呢。 信不信由你,我们家院墙上那几墩狗尿苔和野蔷薇,也会比它们显得实在。我决定就叫它们阴沉了。因为我前两天在查阅资料时发现,白蒿叫茵陈蒿,儿时还吃过用它来和面粉的烙饼呢,于是心稍慰藉。幸亏没有将燎眉子蒿真格儿当作了茵陈蒿,张冠李戴搞出笑话来。 茵陈蒿也开碎米黄花,叶子正面稍绿,背面绒白,长不高,丛中少有燕麦鸟做窝;燎眉子蒿大而叶稠,易于隐蔽,丛之根部常有禽鸟栖居。绒脚大黑蜂和瘦身斑马纹蜂,以及小麻蝇等依其生存,而蚱蜢和螳螂类昆虫,则喜欢在茵陈蒿和结着浆果类的低矮草木中生活,黄蜂和类似家蜂的几种蜂群,与一些美丽得妙不可言的小草蝶们一起,都愿意绕着苜蓿类开着和它们形象酷似的小碎花的植物不停地飞。它们的手脚快速而持久忙碌,一点都看不出有些许的抱怨,它们以劳动为乐,并不计较有关自身的太多得失,它们的人生态度比那些自认为是灌木丛,或树林中生存的大生灵们强得多。它们只有劳动的快乐,比那些自认为在大森林中,做着大事业的生灵,自在而踏实得多。它们的健康、善良和阳光态度,很有些酷似在沿海一些私人工厂和作坊间超强度劳动,而只拿微薄薪金的农村小姑娘小伙子。真是太恰当了,它们简直就是劳动的精灵,不看欢乐中的烦恼,只看烦恼中的欢乐,愉快地默默地创造着。我尊敬它们,也尊敬它们这些整体为大自然增加灵瑞的朋友们,它们在冬雪到来之前离开了世界,而世界也因为它们的爱,而周而复始地供它们繁衍和创造。 我无法想象一生中从没有用心体验,或接触过大自然,没有与大自然真诚相处过的人,是怀着怎样的心境感悟人生,感悟他所生存的世界的。他们在谈论劳动的愉快和爱的诗情时,真不知心灵是何等的荒芜和缺乏生机。我从来不相信,爱会健康而完整地在这样贫瘠的心灵中滋生。我不相信,真的无法相信这样完全如钢筋水泥样坚硬的心灵中,会生发出无限宽怀和柔情饱满的爱。一切有生命力的爱与美,必将来自向往阳光和鸟鸣,领悟得透风与花木和云朵的微语,能看得穿万里雪飘之外的春的微妙心思。 纵使冬天的寒风在荒野上零星的几家院墙上嘶鸣,听起来,也一定会比电焊机、电锯和马达等声音舒服和有益健康得多。 天气已经进入了冬季,我总愿意在这种时候细心地回味一年来阳光、花木、云雀儿和蜂蝶们给予我的每一种闪着灵光的启悟。我从它们那里忘情地采蜜,它们也从我对它们真诚的爱心里采蜜,我一直和它们一样辛勤地劳动,一起愉快地体味生命的点滴华辉。 现在天气虽然已经很冷了,我坐在城市的钢筋水泥房里,依然和它们的心凝结在一起,我依然把整个故乡和它们的所有季节带在心坎上。 我知道,那里早已经下雪了,比南方任何一处都大的雪花…… 敦煌文艺奖获得者、作家阿慈兰若的散文自选集,收录了他发表过的及近年新创作的散文精品百余篇。作品从一草一木,一花一果等生活细微处入手,讲述了作者隐居山野,读书写字,养花种菜的生活趣闻,雅致恬静,深含禅意,表达出作者真善美慧的人生追求和豁达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