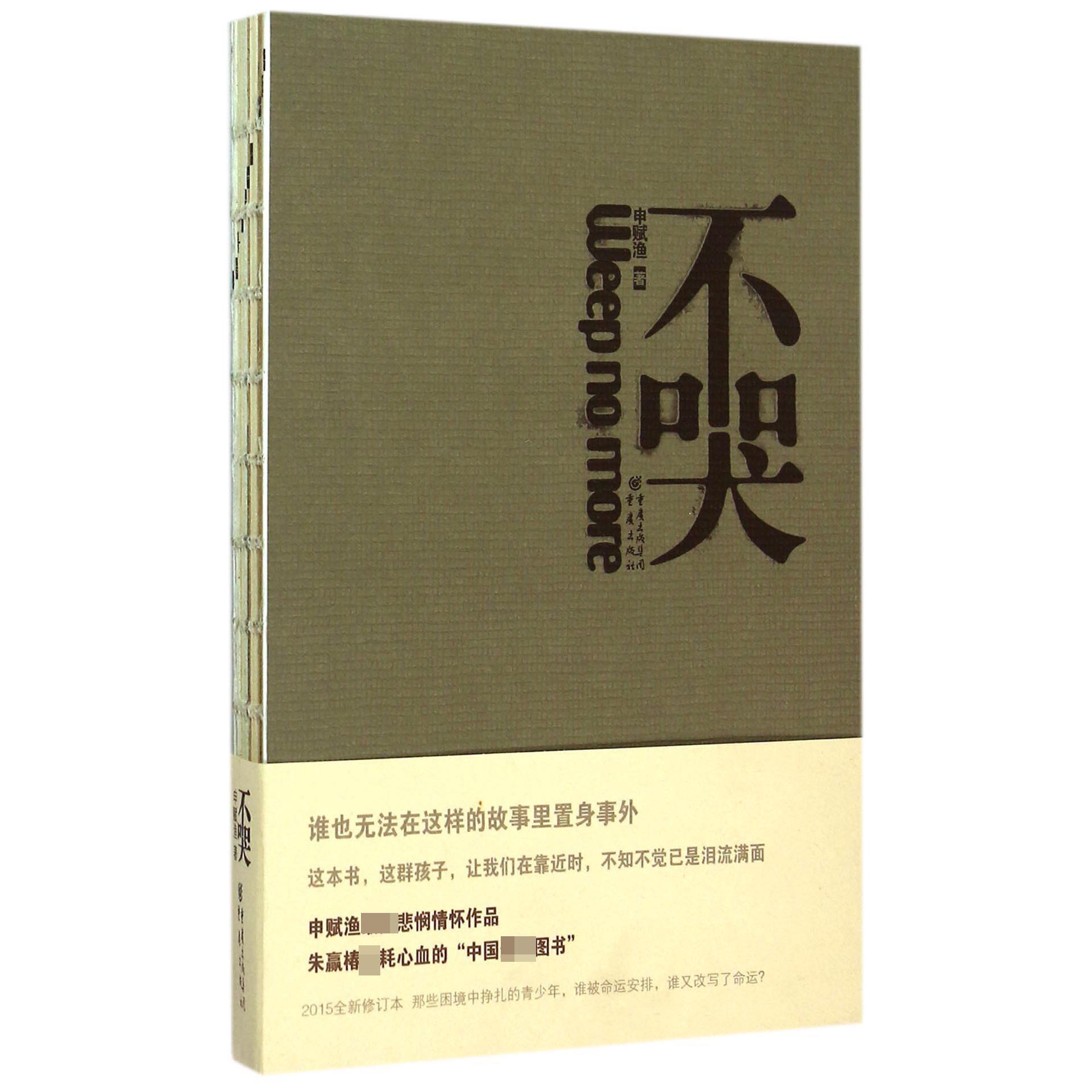
出版社: 重庆
原售价: 39.80
折扣价: 30.12
折扣购买: 不哭
ISBN: 97872290995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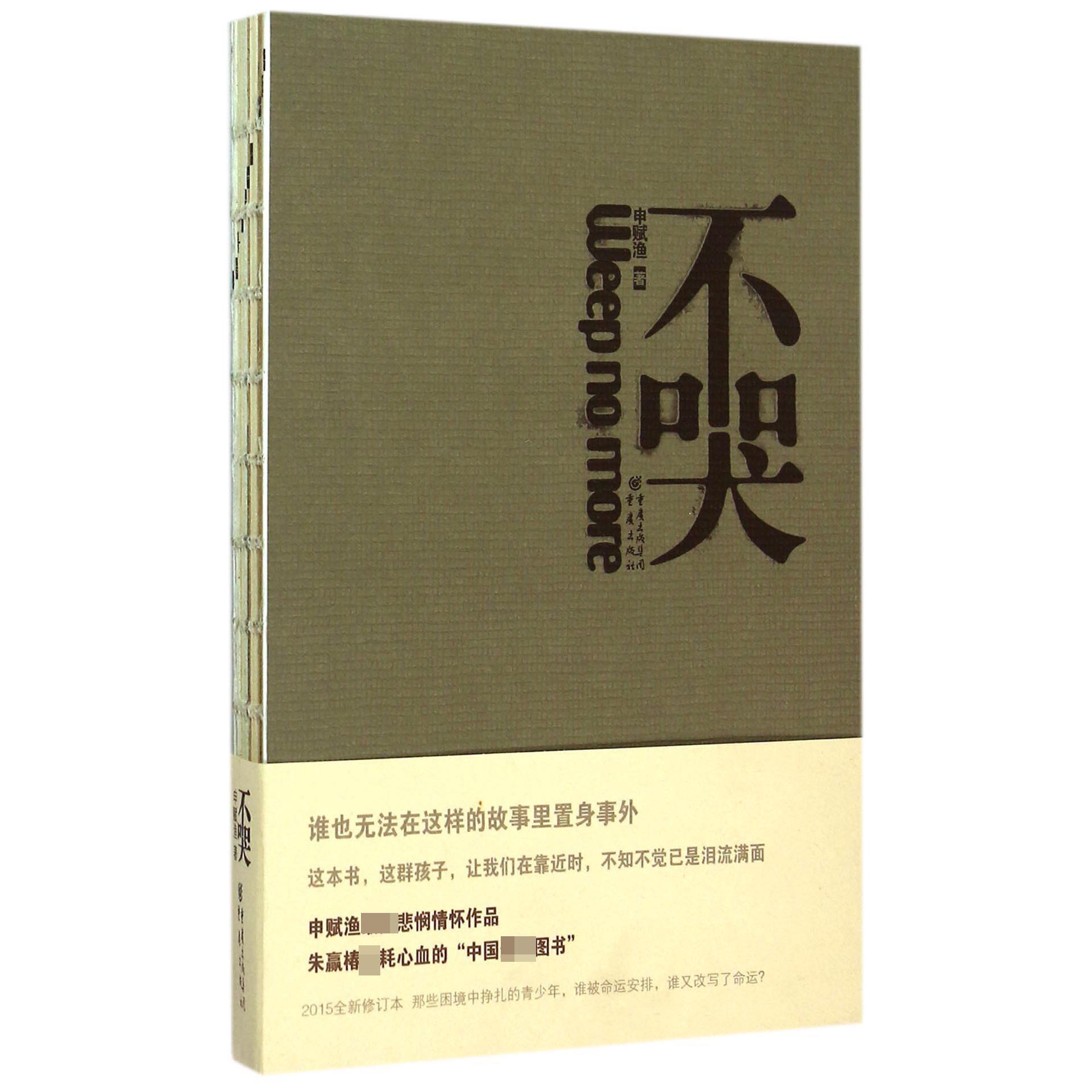
朱赢椿,南京书衣坊主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美术编辑部主任。所设计图书曾数次被评为“中国*美的书”,其中《不裁》被评为“世界*美的书”、《蚁呓》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颁发的“*美图书特別制作奖”。 申赋渔,作家、记者。著有《不哭》《逝者如渡渡》《光阴》《一个一个人》《阿尔萨斯的一年》等。先后在《天津*报》《杭州*报》《福州*报》《扬子晚报》《石家庄*报》等十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导演有《龙的重生》(中法合拍)《不哭》《寻梦总统府》等纪录片。曾任南京*报驻法国记者。现为南京*报“申赋渔工作室”主持人。
宝宝,不哭 她才一岁半,父亲把她一个人,丢在医院。 麻醉过后。光亮一点点从她的眼睛里消失,熄灭 了。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在慢慢合上之后,缓缓地 ,从眼角落下。 麻醉过后,她抽泣着,轻声地喊:“妈妈,妈妈 。”慢慢睡去。 病房很大,静静的。一个小不点,孤零零地躺着 ,*显得特别大。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就是那个 *伤的,一岁半的女孩。 她张了张嘴,想哭,脸上挂着泪。她的父亲送她 到医院,就走了,不再出现。留下她一个人,躺在重 症监护室的病*上。 她的一条腿缠着绷带,悬空吊在架子上,架子很 高。她全身都裹了绷带。她这样躺着已经一个月,身 边没有亲人。 “42%的面积被烧伤,35%是三度重伤。”主治 医生说。 女孩哭起来。 护士摸摸她的手:“宝宝不哭。” 医生说:“宝宝不哭。” 我也说:“宝宝不哭。” 孩子哭得*厉害,喊:“妈妈,妈妈。” 妈妈不在。没有人知道,她还能不能见到她的妈 妈,她的爸爸。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的家人是谁。 她一个人,被丢在医院。南京红十字医院。 2004年3月9*。白下路,南京红十字医院。 晚上8点,7病区,烧伤科。门卫打来电话:一个 小女孩烧伤,很重。护士赶忙下楼,去接。 “我到一楼电梯口,两个男的,前面那人手里抱 着个孩子。用棉被严严实实地裹着。上了电梯,他说 两天前火烫的。小孩她妈妈回四川老家弄钱了。他在 镇江打工。孩子在句容医院治过。医生让转来这里。 那人后面跟着的是他朋友。”护士说。 病区处置室。乔骋医生已经在这里等,他是烧伤 科主任。“烧得**重,**危险。左侧下肢已经炭 化。用手敲,硬梆梆的。血管也烧焦了,血管就像树 枝形状,僵化凝固着。孩子休克了。” “孩子上肢全是针眼,没法打针。包扎也很专业 ,显然在医院抢救过。”病区进入紧张状态。 “切静脉。输蛋白血浆、输抗生素、输抗休克药 物、输维生素。” “全身检查。换药,重新包扎。” 孩子的父亲靠着*,蹲在地上,用手按着胸口。 他的朋友去办住院手续。“我身上只有1000元,孩子 她妈妈明天就来,带钱来。”办完住院手续,他的朋 友说妻子也在住院,得走。孩子的父亲守着孩子。他 站不住,他说三天没吃饭了,也没睡觉。他蹲着。 一个小时过去,孩子从处置室被推进重症监护病 房。 孩子在输液。父亲在*边看着孩子。孩子又黑又 瘦,脸上皴得厉害,或许是哭的原因,皴的地方甚至 结了痂。 父亲摸着孩子的手、孩子的头,孩子昏睡着。他 趴在孩子的*边,看她的脸。他两眼充血。 父亲在孩子的*边趴了40分钟,孩子始终睡着。 “我要吃点东西。”父亲一脸痛苦,只在登记表 上写了孩子的名字:李霞,年龄:一岁半。家庭地址 :四川内江。就捂着胸口,要下楼吃饭。 父亲走了。从五楼的楼梯走下去。 有护士下楼去,在三楼楼梯口看到他。他趴在栏 杆上吐,吐完了,一直趴着。 他的表情痛苦而伤心。 他没有来。他再也没有出现。他把自己的孩子, 一个人,留在医院。 这是一个一岁半的孩子,独自承*着身体的痛苦 ,无助地,在痛苦中喊着“妈妈”。 “孩子处于休克期。四肢发冷,血压低,心率快 ,发烧,39℃。”乔骋主任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 **、两天、三天,孩子的情况在慢慢好转,孩 子的家人杳无音信。 “3月12*,上午8点。我们给孩子进行**次手 术。 手术必须尽快进行。孩子左下肢被火烧坏的部分 深达两厘米:皮肤——皮下组织——浅筋膜——脂肪 ,只有深筋膜、肌肉、骨头未曾伤及。 “坏死组织是病灶,是细菌繁殖的土壤。休克期 过了,要立即动手术去除坏死组织。” 3月12*的**次手术是对左下肢进行切痂—— 清除坏死组织,然后敷上生物敷料。3月15*进行植 皮手术。从孩子的头上取下7%的皮,植在她的左下 肢。 3月23*,对右下肢进行切痂。 3月28*,对右下肢进行植皮。 “手术都很成功。”乔骋主任微笑着说。 孩子的家人一直没有出现。 孩子不会说话,只会喊“爸爸、妈妈”。偶尔喊 一声,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或者哭泣。不笑。不知 道是因为痛苦,还是因为对于陌生人的恐惧。 没有人知道孩子到底是怎样烧伤的。孩子父亲当 时的描述是,妈妈不在,他们住在二楼,他上厕所。 发现起火了,跑进来,孩子就烧成这样。他没有带病 历,说全部忘在了出租车上。他除了登记的那点点不 知真假的信息,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他的说法太简单,对于起火的原因,被烧的当 时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从孩子的伤情来看,火源在 她的左下侧。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孩子被烧得如此之 重,至少被烧了有四五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孩子为 什么没跑,为什么没人救她?孩子一个人在上面,怎 么会燃起这样的火?” 由于忙于抢救孩子,没有人想到仔细盘问。当时 火灾情形只能猜测,无法证实。知道内情的孩子的家 人竟然从此全无音信。孩子在遭*火烧之后,又失去 了*亲的人。 “我喜欢女孩。”他的父亲曾这样对护士讲。 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没有人知道他 在想什么。而他所喜欢的女儿,一个一岁半的孩子, 独自承*着身体的痛苦,无助地在痛苦中喊着“妈妈 ”。 医生、护士,**打乱了自己的工作规律。她们 要给孩子买牛奶、买“小馒头”、买尿片,甚至小玩 具。她们要给孩子喂奶、把大便小便,她们要明白孩 子的哭,是因为疼痛、饥饿还是恐惧。 “我们3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烧伤科人力 紧张,可是孩子现在成了中心。 4月6*下午,我站在孩子的*头。孩子紧张地看 着我,眼睛圆圆大大的,惊恐不安。给她东西,她的 手一动不动。只是惊恐地看着,嘴一扁,哭出声来。 护士给她喂小馒头,她噙着泪,停止哭泣,眼睛还是 紧张地看着病*边的不速之客。 她已经是个漂亮的女孩了。“跟刚来的时候不能 比。”护士说,“她会笑了,昨天笑了一次。” 总有病友来看她。吊着手臂的、驻着拐杖的。他 们静悄悄地站在她的*头,看一会儿,再悄悄地离去 。他们在过道中叹息。 乔医生又来看她。孩子哭起来。“她怕我。”乔 医生说,“给她换药。每次总是十二万分的小心,用 消毒水把纱布沾湿了再揭,肯定还是会疼。” 孩子大声地哭。隔壁病房的一个小伙子,拿了自 己的随身听,放在孩子的*头。音乐缓缓飘动,孩子 奇妙地安静下来,眼睛盯着。音乐响着,孩子的眼睛 渐渐蒙胧。睡着了的孩子,不知道梦里能不能见到她 的妈妈,她的爸爸。 “明天还要动手术。”乔医生说。 4月7*,8点。住院医生、护士,越来越多的人 聚集到孩子的*边。**,是孩子的第五次手术。“ 手术成功,这就是*后一次手术了。”乔骋主任说。 孩子身上被烧坏的,没有植皮的地方这次全要补 好。 住院医生剃去孩子头上的头发,用刀刮成光头。 手术中要从这里取头皮,植到她的身上。“头部血供 好,头皮再生快。另外,以后头发长出后,**看不 出伤痕。她是个女孩。”医生说。 女孩哭了,轻轻地。她也许知道会发生什么,也 许不知道。她都会哭。 8点36分。护士把孩子推进电梯。手术室在7楼。 3号手术室。 孩子被送进手术室。围着孩子的只有医生,还有 我。家属等待区的走廊里空空荡荡。 一个夹子夹住孩子细小的手指,监视器接通。很 普通的夹子显得很大,不知道孩子的手指会不会很疼 。心率正常,血氧饱和度正常,血压正常。 “给氧。”护士给孩子接上氧气管。 “麻醉。”麻醉主任给孩子实施全身麻醉。 两位担任助手的住院医生拆开孩子身上的绷带, 开始对创面用碘伏清毒。一定很疼。 医生轻轻拨弄着金属器械,碰撞的声音让我的心 一阵阵发紧。我盯着孩子的眼睛。亮光在她的眼睛里 慢慢地消失,像渐渐地小了并终于熄灭的油灯的火苗 。她的眼睛**失去了光亮,眼角噙着泪,无声地望 着天花板。 “孩子睡着了吗?”我问。 “不是睡着了,是麻醉了。” 孩子的眼睛慢慢地合上,手术要开始了。 手术室充满监视器发出的孩子的心跳声。怦、怦 、怦、怦,声音不大,可是**有力,**稳定。每 分钟145下。9点50分。孩子身上的伤口清理完毕。血 袋里的血一滴一滴地滴进孩子的体内。“为了防止失 血过多。昨天夜里已经输了75毫升的血,现在还要输 225毫升。”乔主任说,“孩子太小,身上血量少。 ” 10点10分,乔主任开始在孩子头上取皮。怦、怦 、怦、怦,脉搏正常。孩子安静地熟睡着,什么也看 不到,什么也不知道。我退出手术室。她只是一个一 岁半的孩子,这个孩子现在正遭*的一切,我不敢面 对。穿着无菌的白色大褂,我突兀地站在手术室外的 走廊上。 孩子在7楼手术室。5楼,她的病房里空空荡荡。 病*上洁白的*单铺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一个布 娃娃放在枕头旁边。那只随身听悄悄地,摆放在*头 柜上。 12点30分。从孩子被推进手术室到现在,已近4 个小时。 乔骋主任开门出来:“手术顺利。” 48*。 护士给孩子喂着稀饭。“她能吃不少。”护士小 姐给我看她手中的杯子。孩子看着我,眼神鲜亮。 孩子的腿还是用绷带吊在支架上,两只手也用带 子拴着,怕她乱抓。她的头可以动,眼睛可以四处张 望。 “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了。”乔主任说。 乔主任所说的出院,是指通常意义上,有家的人 。 没有人知道,一个月后,等待这个孩子的是什么 。 她父亲留下的**线索便是孩子曾在句容人民医 院治过。可是经过调查,句容医院没有收治过这样的 幼儿。 她还要经历很多痛苦,每年都要做一次手术,直 到发育成熟。 她无处可去。 “孩子出院后,要护理,要帮她锻炼。路还很长 。” “以后,她能走。她的手没有问题,她的智力不 会*影响。她能自食其力。” “但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 从乔主任办公室出来,我再去看孩子。 “她一直喊着妈妈,喊个不停。现在睡了。”护 士说。 孩子睡了,脸贴着布娃娃的脸。护士用湿纱布擦 去她脸上的泪痕。 “她还要经历很多痛苦。每年都要做一次手术, 直到发肓成熟。”医生说。 她才一岁半。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经历,因为采访对象已经走 进我的内心,影响着我,牵扯着我。我是一个幸福的 4岁女孩的父亲,我为另一个陌生的不幸宝宝而痛苦 ,她的痛苦我甚至感同身*。因为这,我想替她,感 谢这些善良的人们,并且记下他们的名字——虽然, 也许他们并不需要:南京红十字医院烧伤科的乔骋主 任,是他给孩子带来新生、医院工会郭明**,是他 的奔波呼喊,让*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孩子;还有烧 伤科医生:杨永胜、陈勇;护士:王燕,丁小燕、田 亮、梁凌虹、仝开棉、兰志红,她们是真正的天使, 是她们把孩子从噩梦中牵引到温馨的人间。感谢的名 单中还应列上没有留下全名的钟小姐,她为孩子带来 了**笔捐款。还有小李霞的病友们,他们给了孩子 *贴近的温暖。这个感谢名单很不完整,因为只要用 心去关注孩子的,哪怕为孩子的命运有过一声叹息的 善良的人们,都体现着人性的美好。 *后,我想对孩子的爸爸妈妈说一句:孩子她想 你们。痛苦时,她呼喊着你们,恐惧、饥饿时她喊着 你们,她在梦中喊你们,在无助孤单时,她要你们。 在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年半的时间里,她*亲的是你 们,她*可以依靠的是你们。*疼她的,也是你们。 也许,你们有着自己的无奈,也许,你们有着太多不 得已的理由。可是谁都没有权利让一个无辜的宝宝永 远哭泣。请你们给孩子一个未来,不要让一岁半的孩 子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永远找不到爸爸、妈妈。 她想回家。 两年过去,孩子的父母始终没有出现,经过多方 努力,两年之后,孩子终于被一个合适的家庭收养。 她家的附近,就有一座大型医院。(P0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