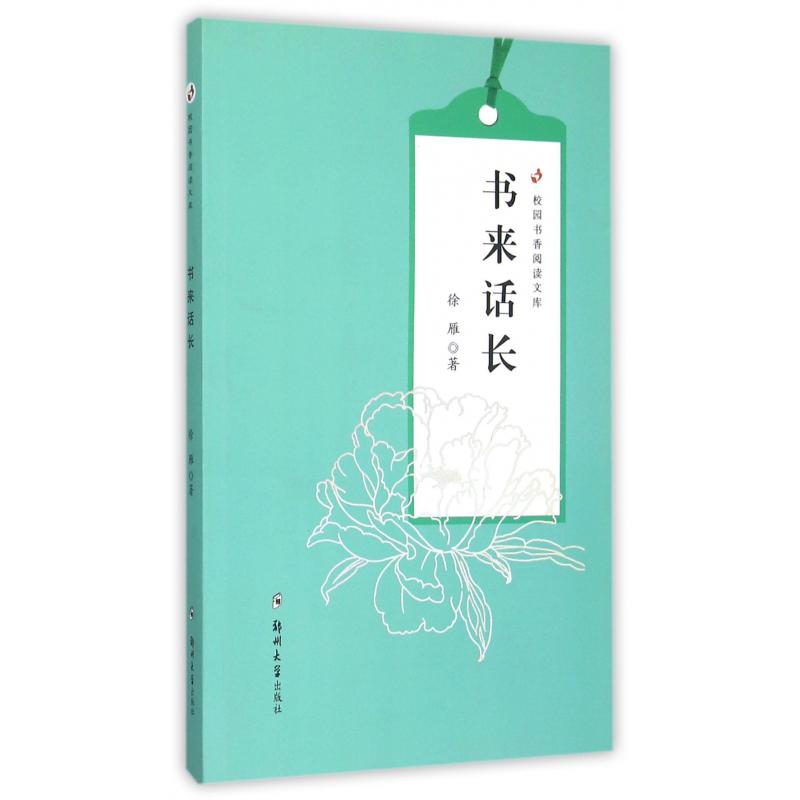
出版社: 郑州大学
原售价: 39.80
折扣价: 28.70
折扣购买: 书来话长/校园书香阅读文库
ISBN: 97875645233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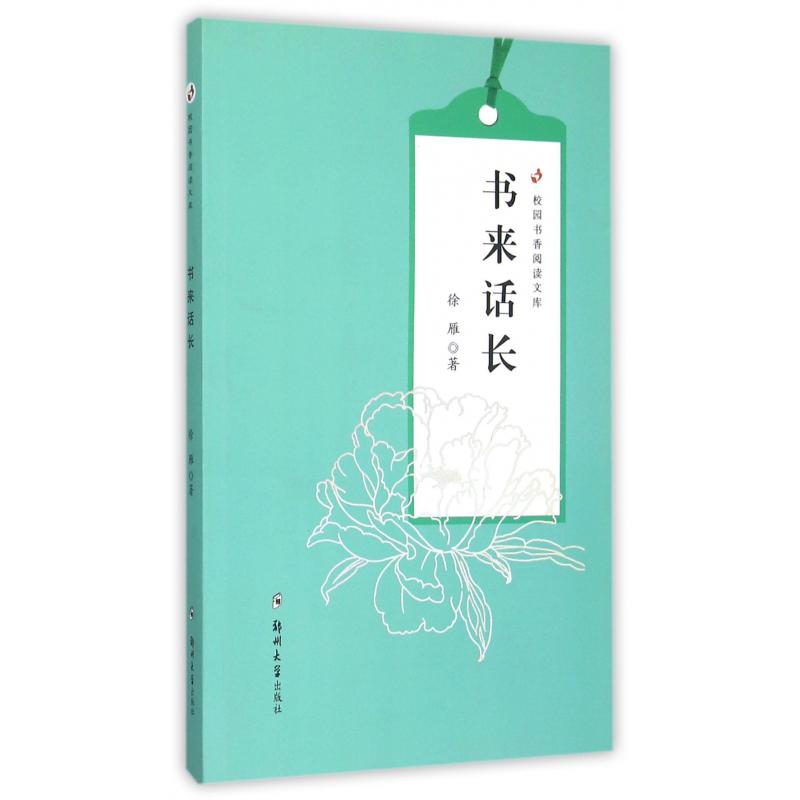
徐雁,笔名“秋禾”,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江苏省政协常委,兼任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等。家有藏书万余册,著有《秋禾书话》《书来话多》《阅读的人文与人文的阅读》等。所做“人生惟有读书好”“读书与人生:阅读名人传,汲取正能量”“‘耕读传家’:读物选择与幸福追求”等专题报告,受到读者和听众们的欢迎。
在北大,我学“图书馆学” 1963年9月1日,我在雷暴雨时分出生于江苏吴县 光福镇,但我完成小学、中学全程学业的地方,却是 在太县。整整十七年后的那一天,我带着一份复读一 年后391.80分的高考卷面总成绩,在俗称“北大大饭 厅”的图书馆学系迎新台前,怯生生地完成了入学注 册手续。 当年的图书馆学系,秉承老系主任王重民(1903 一1975)、刘国钧(1899—1980)教授所主张的“图 书馆员应当有至少一门专科的知识基础”这一优秀专 业教育理念,安排1979、1980两级文理科新生,分为 中文、历史、经济、物理、生物等组,跟随对应系科 的同级新生学习基础课,为时两年。 王、刘两位先生,是被马嘶《负笈燕园 1953— 1957:风雨北大》(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提名的“ 学养深纯”的本系两位知名教授,我虽然都没有见过 ,但沐浴到了他们的教泽。因此,在两位先生百年诞 辰的纪念会上,我先后提交了两篇万余字的论文,弘 扬了他们的生平、学行和事功,表达了一个专业后生 对先辈的承恩和怀念。当然,这是后话。 (一) 我入学后没多久,就被编进了中文组,随1980级 中文系文学专业共同学习。古代汉语课,用的是王力 先生主编的四大册教材。我由对诗词楹联的爱好,突 然生发了对古诗中各种另类句式的兴趣,醉心于从各 种诗选和诗话著作中搜集案例,如白居易“残暑蝉催 尽,新秋雁带来”,杜甫“青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 须斩万竿”等“诗家语”。 后来,我增补改定为一篇六千余字的文章。开篇 引用的就是王力先生《略论语言形式美》里的论断: “诗词有了固定的格律,可以容许特殊的句型。”这 篇文章定题为“格律诗中的特殊句法结构”,后来被 北大出版社的胡双宝大学长推荐到了《语文研究》杂 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 却说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本科生都有资格把清版 线装书一函一函地借回到宿舍中慢慢看的,而“工具 书阅览室”两边的书橱里,更开架陈列着《太平御览 》《文苑英华》《古今图书集成》等备检的原版书, 足以供有兴趣又用心的学生自由“汲古”和自在“修 学”。 我这一程凭兴趣自在读书之“得”,是在于初尝 了随意求索“未知”的乐趣;而那“失”呢,则极易 走偏锋、入斜谷,寻不到中国古典文化的正道,登不 了大堂,入不了雅室。所幸我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 期,就邂逅了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三联书店 1980年9月版),这部书让我找到了对中国文学的兴 趣与将学习的图书馆学专业的结合点,那就是中国藏 书史研究。 从事这项自发兴趣的所谓“研究”,让我切实体 会到了知识发现的乐趣,也因此结网般地浏览了不少 好书,知道了一点检索资料、组织资料的实践经验, 这对于我感觉图书馆知识宝库的魅力,在毕业以后逐 渐脱离 机关和南京大学有关机构的行政工作, 在岑寂中甘坐“冷板凳”,潜心读书、淘书、研书、 教书和写书,是一种极其有益的学术情意积累。 1982年11月10日,我还为北大创建了一个大学生 学术社团——“学海社”,先后请到王力、冯友兰、 宗白华、张舜徽、蔡尚思、顾廷龙、许大龄、阴法鲁 、张荣启、楼宇烈、金开诚、朱天俊、沈天佑、白化 文、叶朗、孟昭晋、肖东发等十余位北大内外的专家 学者为本社学术顾问。 创社的成功,完全是我随中文系求学的另一大收 获,它让人有了系际整合的宽视野。学海社一度发展 成为当年与北大五四文学社、学生书法社鼎足而立的 跨系学生团体,编辑了十余期社刊《学海》。当年, 我们还积极组织了一系列“学海讲座”。至今还记得 的,有梁容若“祖国文化遗产在台湾”、严绍鋈“日 本古代诗歌形式与中国文学关系”、曾孟辉“图书馆 古籍问题”、唐弢“关于‘现代文学版本学’的建立 ”、王余光“试谈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和研究”,等等 。 (二) 当两年中文、历史、经济系的基础课程学罢,在 体制上回归图书馆学系以后,首先“苦”了的,是本 系执教专业课的那些老师们。 才从舞文弄墨的文学、博古通今的史学、经才济 世的经济学课堂中走出来,要让只有百余年学科史的 “图书馆学”(产生于19世纪初德国,确立于19世纪 8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 获得长足发展),通过课堂讲授赢得眼高手低、少不 更事的同学们的青睐,肯定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 事。 在经过了叽叽喳喳却又不得要领的多次“卧谈会 ”以后,大家终于认起“命”来,开始在图书馆学里 做起各自的“道场”来:有的思考着“图书分类”的 问题,有的探索起“图书馆要素”的学说,还有不知 天高地厚的,竞钻研起什么“图书馆学定律”来了呢 ! 不知怎的,我对于图书馆这个实体“形象”始终 没有“思维”(感觉),兴趣全在于它所收藏的传统 文献——书、报、刊;但对于当时被视作“高科技产 品”的缩微资料,我又没啥兴趣了。所谓“兴趣”, 体现为到馆阅览,乱读瞎翻,一目十行,自美其名, 日“博览群书”。 读熟了《晦庵书话》,尤其是其中的《书城八记 》后,我开始把读书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藏书家史实 上来了。同时也像前辈那样,留意起海淀、西单商场 、东风市场、新街口,以及琉璃厂的中国书店门市部 来了。那两年,在星期天借一辆同学的自行车去城里 各处的旧书店巡阅一番,是我很大的一种乐趣。 如今回想起来,1983年5月4日,我在本系主办的 “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发表有关中国古代藏书保护的 “论文”,该是我专业形成偏好的一个标志。难怪本 系的师友们,从此就把我指为想钻故纸堆搞业务的“ 夫子型学生”了。那“夫子型”的出典,该就是《青 春之歌》中被无情讽刺的“老夫子余永泽”。 P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