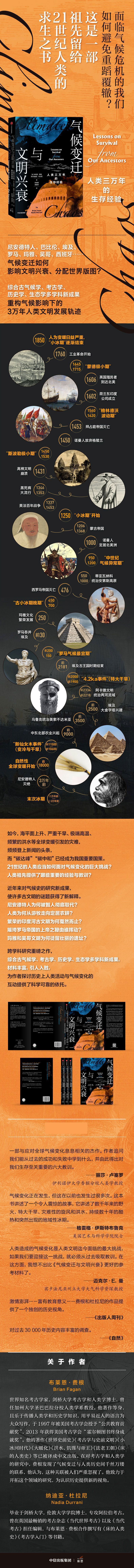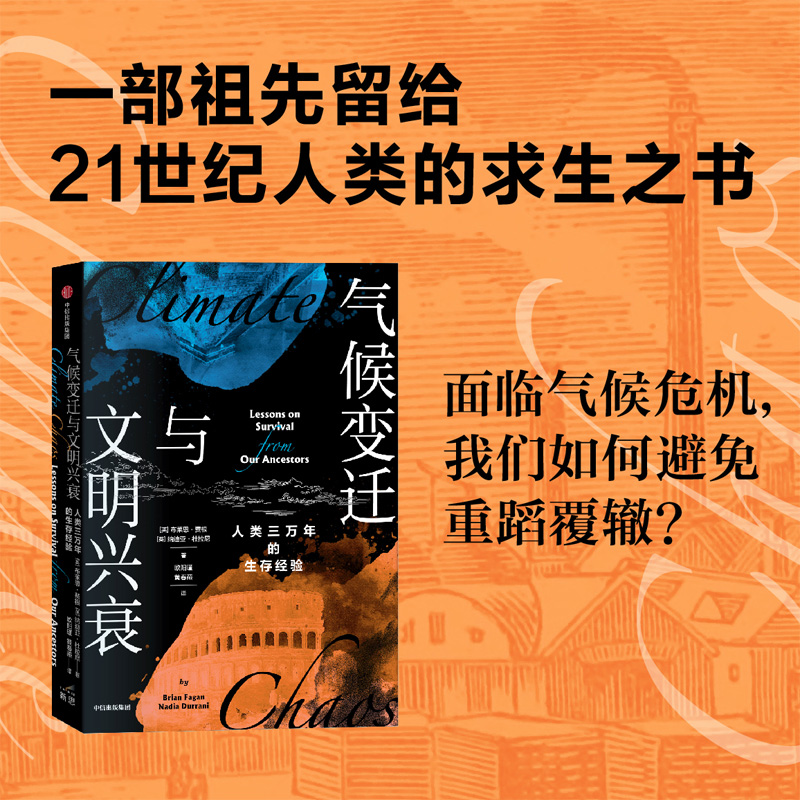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50.70
折扣购买: 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
ISBN: 9787521743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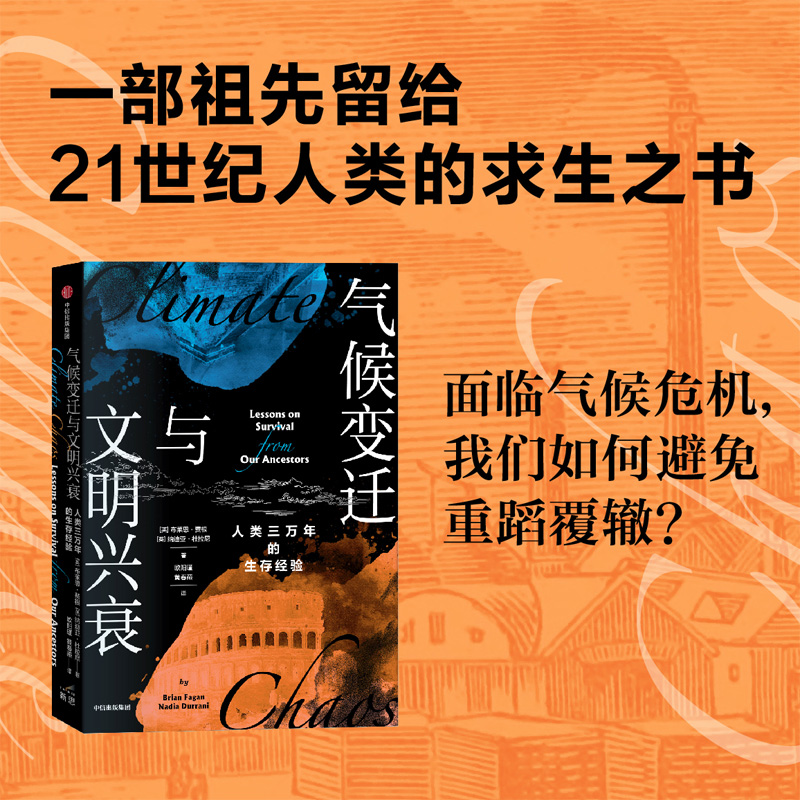
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 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他著作等身,且乐于传播人类学和历史学知识,用平易近人的语言为大众写作,于1997年被美国考古学会授予“公共教育贡献奖”,2013年获得美国考古学会“霍尔顿图书终身成就奖”。他的著作《世界史前史》《考古学与史前文明》《小冰河时代》《大暖化》《洪水、饥馑与帝王》《法老王朝》《床的人类史》等已被译成中文出版。 在对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费根发现了气候变迁与人类历史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认为,这种关联被人们严重忽视了。他致力于开拓这个领域的研究,为认识历史提供新的视角。 纳迪亚?杜拉尼(Nadia Durrani),毕业于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博士,专攻阿拉伯考古。曾在英国最畅销的考古杂志《当代世界考古》以及《当代考古》担任编辑,与布莱恩?费根合作撰写有《床的人类史》《考古学入门》等书籍。
马匹、匈人与恐怖场面(约公元370年至约公元450年) 西罗马帝国的东边,坐落着广袤的欧亚大草原,上面没有树木,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地与灌木丛。那里的降雨毫无规律且变幻莫测,全然取决于来自西部的暴风雨的移动路径。古罗马人很瞧不起那些在无法耕作的大草原上到处流浪的游牧民族。古罗马人与中国的汉族都属于定居的农耕民族,可游牧民族却在不停地迁徙;他们骑马放牧,同时挤占定居民族的土地,先是袭扰中国中原王朝,后来又向西进犯。公元4世纪,一群群游牧的匈人出现在罗马帝国东部的边境。青藏高原的一系列桧树年轮表明,那里属于一种大陆性气候模式与季风气候相结合的环境。从公元350年前后至公元370年间,这个地区遭遇了2 000年来最严重的一个大旱时期。这一点,可能就是游牧部落开始向西迁徙的原因。 气候导致人们进出干旱环境——人们在降水较充沛的时期进入这些地区,而在气候干旱时则离开——这种效果开始发挥作用。匈人应对干旱的办法,就是跳上马背、四下散开,为他们的牧群寻找水源较为充沛的牧场。大草原上的政治权力中心,也从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向西转移。这次突然迁徙的时间,与游牧民族形成的不同联盟之间展开激烈竞争的一个时期相一致。古罗马军人兼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凯林努斯,曾经生动直观地描绘了匈人的情况:“虽具人形,然皆丑陋,生活坚忍,乃至无须用火,无须美食……几至臀不离鞍。”他们那种威力强大的反曲弓,据说射程达到了150米。他们所用的战术极其凶狠,令人生畏。 随着游牧民族不断从多瑙河中游地区向西迁徙,匈人的处境也到了紧要关头。公元378年,瓦林斯皇帝在阿德里安堡附近的一场血战中被打败。有多达2万名罗马士兵在这场屠戮中丧生。公元405年至410年间,面对哥特人和后来其他民族的不断入侵,西罗马帝国逐渐衰亡了;入侵民族越过莱茵河,洗劫了高卢,并且向西征伐,远至西班牙。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皇帝死后,罗马帝国的东、西两半就再也没有统一到一个君主治下。公元410年,哥特人的统治者阿拉里克进入罗马。西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而罗马的实力也随之瓦解。阿提拉是所有匈人头领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位,曾大肆劫掠了巴尔干地区。直到遭遇一场瘟疫,此人才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前止了步;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已因公元447年的一次大地震而遭到了重创。随后,阿提拉进军高卢和意大利,但因出现饥荒和军中流行在潮湿低地感染的疟疾而撤退,回到了大草原上。到6世纪时,由于始终须靠其他地方生产的粮食才能维生,故罗马的人口也急剧减少了。 公元4世纪之初,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两位皇帝已经加强了对帝国行政的控制。他们宣称自己是神圣的君主,崛起于东部诸省的繁荣兴旺之中。戴克里先让皇帝变成了一位高高在上的国君,极其倚重礼仪上的治国方略来扩大自己的权力,与早期那些从一座城池迁往另一座城池的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君士坦丁大帝则把自己的都城建在海上,建在连接东方与西方的贸易线路上。他的统治,是罗马帝国晚期的根基。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成了国际贸易的十字路口和一个重要的希腊文化中心。原本运往罗马的粮食,如今则转道往东而去。 没有什么比每年对帝国粮库进行审计更能突出皇权之显赫。归根结底,皇帝最基本的义务,就是养活手下的臣民。都城有50万居民,皇帝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靠运气。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控制着税收与粮食供应。都城的安全至关重要,而这种安全是靠提供粮食来保证的。饥荒的威胁曾经在罗马引发内乱,故首都有了大量的粮食储备,足以养活50万人;其中光是获得免费面包口粮的人,就达8万之多。与数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一样,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也来自埃及。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每年都从亚历山大港运来31万升小麦。 每一年,皇帝都会登上自己的战车。整个帝国中权力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禁卫军首领,会亲吻皇帝的双脚。皇家的游行队伍开进城中繁忙的市场区,然后朝着金角湾那些巨大的公共仓库进发;一艘艘装载着货物的船只,就停泊在金角湾里。到了这儿,掌管粮仓的庾吏就会呈上他的账簿。如果一切都没问题,庾吏及其会计就会获得10磅黄金和丝绸长袍,以资奖励。这场煞费苦心、精心上演的公开盛事向所有人表明,帝国的粮食供应很安全。 查士丁尼大帝统治着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和很不稳定的城市,其中到处都是来自已知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与货物。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位于众多较小城市组成的广袤网络的中心。不过,就在皇帝率领群臣巡察粮仓时,生态系统中的另一个成员却在暗中冷眼旁观着:那就是学名为Rattus rattus的黑鼠。这种无处不在的啮齿类动物身上携带着鼠疫杆菌,也就是导致腺鼠疫的那种微生物。 瘟疫于541年传播到埃及,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蔓延到了罗马帝国全境。史称“查士丁尼瘟疫”的这场疫病,起源于中国西部的高原地区。到了6世纪,无论是经由陆路还是横跨印度洋的那些古老的贸易线路,罗马帝国与亚洲之间的贸易都已是一桩大生意,尤其是胡椒与其他香料贸易。丝绸也是一种珍贵的商品,但其生产大多集中在红海地区。红海以西,是埃塞俄比亚地区信奉基督教的阿克苏姆王国,以东则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希木叶尔王国,该国当时信奉犹太教,并且脚踩两只船,与罗马和波斯都结了盟。这个地区极具战略意义。因此,公元571年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选定在红海沿岸阿拉伯半岛一侧的麦加降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病菌随着商人而来,而藏在船只运载的货物当中、已经感染了瘟疫的黑鼠也是如此。瘟疫首先出现于培琉喜阿姆,那里靠近红海北部的克莱斯马港(Clysma),从印度而来的船只经常在此停靠。从那里开始,瘟疫轻而易举地传到了尼罗河流域,然后进入了罗马帝国。登陆之后,瘟疫便朝着两个方向传播:一是往西传至亚历山大港,然后沿着尼罗河流域而上;二是往东,不但蔓延到了地中海沿岸,还传播到了整个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帝国那个高效的网络将瘟疫带到了内陆地区,但瘟疫经由海路传播得尤其迅速。1542年3月,疫情扩散到了君士坦丁堡,并在城中持续了2个月之久。在疫情高峰期间,据说每天都有16 000人丧生。城中的50万居民当中,死了25万至30万人。当地社会崩溃,市场关门,结果出现了饥荒。就连各级官吏,也十去其一。尽管人们将死者集中安葬在一座座大坑中,可尸体还是到处堆放着。许多死者层层叠叠,陷进“下方尸体渗出的浓液中”。以弗所的教士约翰曾目睹了当时的恐怖场景,并且撰文声称他看到的是“神烈怒的酒醡”。整个国家在这场灾难中摇摇欲坠。小麦价格暴跌,因为要供养的人口大幅减少了。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帝国几乎无力调动一支军队,更别提支付军饷了。东罗马帝国的人口,行将骤减。从542年至619年,君士坦丁堡平均每15.4年就会遭到一场瘟疫重创。公元747年,由于有太多的人死于新的瘟疫,皇帝只得通过强制移民的方式往这座几乎荒无人烟的城市重置居民。 汲取历史经验,为应对当下气候危机提供借鉴 如今,海平面上升、严重干旱、极端高温、频繁的洪水等全球变暖引发的灾难,频频登上新闻的头条。而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成为我国重要国策,人类与气候的关系已进入人们关注的中心,超越环境保护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气候变化既是现实,在历史上也长期存在,关乎人类社会的命运。21世纪的人类应当如何面对气候变化的巨大挑战?人类祖先提供了哪些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透过气候史独特视角,探讨文明兴衰成败 近年来对气候史的研究新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使许多古文明兴衰的谜题获得了气候方面的新解释。尼安德特人为何被智人彻底取代?人类为何从游牧走向定居农耕?繁荣的印度河古文明为何戛然而止?摧垮罗马帝国的上帝之鞭由谁挥动?玛雅和吴哥文明为何徒留壮丽的遗址?对于历史爱好者,本书十分值得一读。 综合多学科新成果,还原古人与环境的互动 跨学科研究重磅之作,综合古气候学、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学多学科新成果,材料丰富,引人入胜,为作者探讨历史上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互动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托。书中也设专门章节叙述这一研究方法的技术原理和进展历程,能够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气象学、博物学、地质学爱好者都能找到感兴趣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