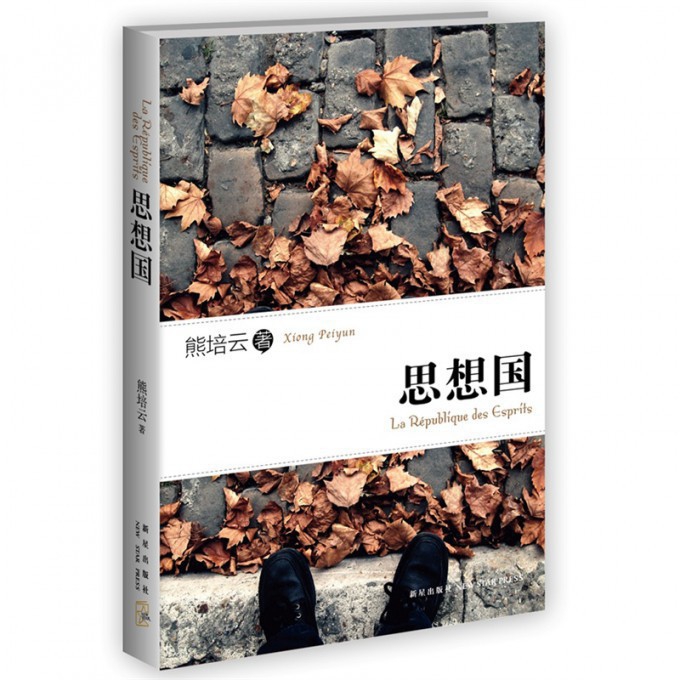
出版社: 新星
原售价: 35.00
折扣价: 22.10
折扣购买: 思想国
ISBN: 9787513307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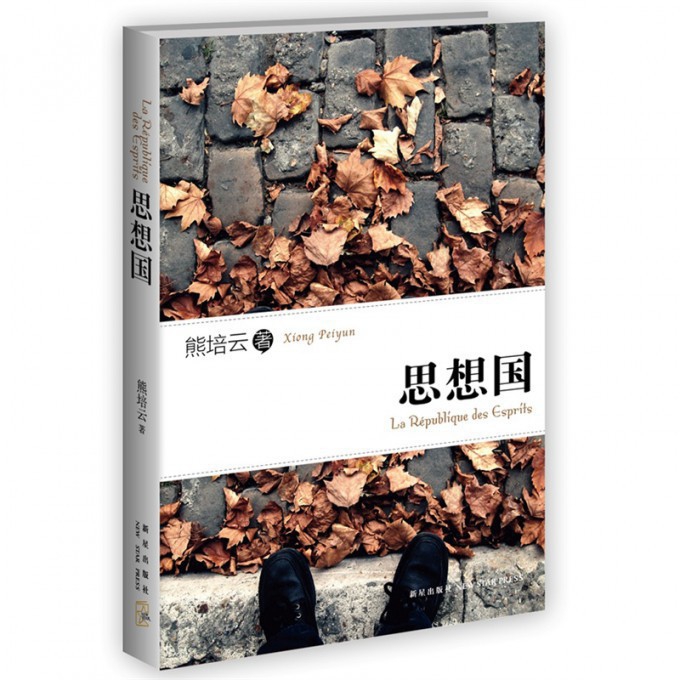
熊培云,生于20世纪70年代江西农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思想国网站(www.21pinglun.com)创始人。 过去或现在与熊培云写作相关的职业主要有:《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代表作有《思想国》(2007)、《重新发现社会》(2009),译著有《中国之觉醒》(法文,香港田园书屋)。
米哈博桥上的眼泪 三十而立,飘在巴黎。 新近搬了家,我住在一首诗的旁边。十六区,右岸偏左。 初次见面,和其他法国朋友一样,房东太太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 来法国?对于这个问题,我很少自问。我的南开校友、戴思杰先生在他的成 名作《巴尔扎克与中国的小裁缝》中有很好的解释:一个小裁缝受到巴尔扎 克作品的影响,最后走出天高文化远的小山村。它说明,文化无孔不入、魔 力无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回想我这些年读过的书,无意有缘,大多都 和法国文化有些渊源。因此,来到法国继续学习,对我自己来说,并不意外 。 对我最有影响的人不是巴尔扎克,而是罗曼·罗兰。罗兰这样描述法式 乌托邦:“世界安宁、博爱、在和平中进步、人权、天赋平等。”其实,我 对法国怀有某种情感,除了对这些大道理心存信念,还有一种近乎朴实的乡 土之情——怀旧。在我仰望未来浩瀚的星空时,同样深爱着承载现在与过去 的大地。道理是,只要你站得足够高,就会发现大地是星空的一部分。 法国人的怀旧之情是举世无双的。有的电台就取名为№stalg-e(怀旧 )。怀旧,其实就是抚摸文明发黄的书页,怀念短暂一生的美好,它让人生 与历史相逢,在眷恋到心痛的回味中,穷尽过去与未来。所以普鲁斯特意味 深长地说,天堂只在那些已然逝去的日子里。 一个雨水涟涟的冬天,我在塞纳河边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队,第一次走进 了奥赛博物馆。很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印象派的画,尤其钟情凡·高的《向 日葵》与《星空》。当我爬着楼梯,快要走向凡·高的展厅时,想着这些年 来痴心不改,在愿望即将实现时忽然觉得愿望也疲惫不堪。手扶着楼梯,只 是喃喃自语,“凡·高,我来看你了!” 尽管在所有的藏品中,没有《向日葵》,也没有《婴孩》与《吃土豆的 人们》,但我却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晒场上的生命、自画像、星空与教堂。 油画不是印刷品,它是只能到现场看的,透过斑驳的画布、甚至已略显黯淡 的色彩,你更可以看到无尽的岁月沧桑与隔世的心灵抚慰。在这里,画框虽 已陈旧不堪,却为我们细心保留了文明的现场。 社会就是人类,历史就是人生。在法国,流通于欧元之前的法郎纸币是 值得追忆的。 如今,无论是在大商场,还是跳蚤市场,除了欧元标价外,商人还会不 厌其烦地换算出法郎。那里栖息的不只是拿破仑与黎塞留的政治野心,更有 自启蒙时代以来思想巨子的人文之情——伏尔泰、孟德斯鸠、笛卡尔、莫里 哀、哈辛、高乃依、夏多布里昂、雨果、德拉克瓦西、塞尚……法国人怀旧 ,其实更多的是怀人。 铜臭里飘着书香。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在五十法郎的纸币上看见圣·埃克绪佩里与小王子 ,犹如第一次在巴黎书店里看到无数个版本的《小王子》、绢着法文“不要 用眼睛,而是用心灵看”的方巾以及绣着“Le Petit蹦nce”(小王子)的 金色狐狸与白色小绵羊时,我因此明白一个民族是如何呵护一颗心的。它不 像袁世凯,甫一“当选皇帝”,便心急火燎将自己的脑袋铸成“大头”上了 银元,以示“袁某人到此一游”,呵护一顶轮流坐庄的帽子。 书香里飘着些什么?都是些故人名字。 在西岱岛旁,塞纳河两岸,排满了旧书摊。除了卖巴黎名胜的卡片与素 描外,大多都是近一两百年间的旧书。那是一些固定在河沿上的简易铁箱子 。从市容上考虑,这大概算是“私盖”或“官搭”,当被拆除。但很多年来 ,塞纳河边的旧书商并没有被清理走。政府对文化之重视与宽容使塞纳河水 也有了一缕书香。 法国出版社十分重视作者的名字(有时会占到封面的三分之一),而不 是用花里胡哨的书名,或忧国忧民担心你有了快感不喊;或“礼贤下体”, 派“此处删去下半身数两”的庄之蝶将你诱奸。在法国,性是自由的,以“ 力比多”来勾引读者钱财的任务已交给了色情杂志或情趣商店的老板。出版 商重视推出作者之名而非作品之名,一方面推销并鼓励了作者,同时也让作 者因此对自己的名字负道义之责,不至于使小说家们集体“卖身不卖艺”。 常有人文学者悲叹近代中国沦为“文化小国”,究其根源,与国人重标签而 非思想,重书名而轻作者,重市场而轻人心不无关系。二十世纪后半叶,吾 国剪刀加糨糊的学术武工队和著作装修队鱼贯而出,于是有了书香不足、腋 臭有余的虚假繁荣。 初到巴黎,我的索邦校友、政治评论家陈彦先生给了我很多关怀。对于 中国,他最痛心的是当下犬儒主义流行,冷漠与世故正在成为人们的护身符 与安慰剂。几个月前,陈先生在一篇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中说, “当代中国 反思的特点不是思想的高度,而是步履之维艰。”让我唏嘘不已。细想下来 ,中国所以沦为“文化小国”,与吾民健忘、自卑或“自寻短见”亦不无关 系。我们在制造天堂与将来时,却将过去或手边的美好扔掉了。我们不但遗 忘了过去,也正在遗忘现在。 中国人常说,人走茶凉。其实,一个民族,若不能热情地拥抱自己的祖 先与子孙。茶从来就是凉的。就像黄宗羲、胡适、傅雷、顾准这些名字,只 是星星点点地出现在几个淘书人的脑子里,却从未在道路上见着。旧朝新朝 ,路牌上多半是一统天下的“事迹”,却很少见到些民族精神的“人迹”。 华族亿万,岂能在“人迹罕至”的道路上再造文明? 一个民族,不能只纪念一个人,否则它就被自我轻视。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