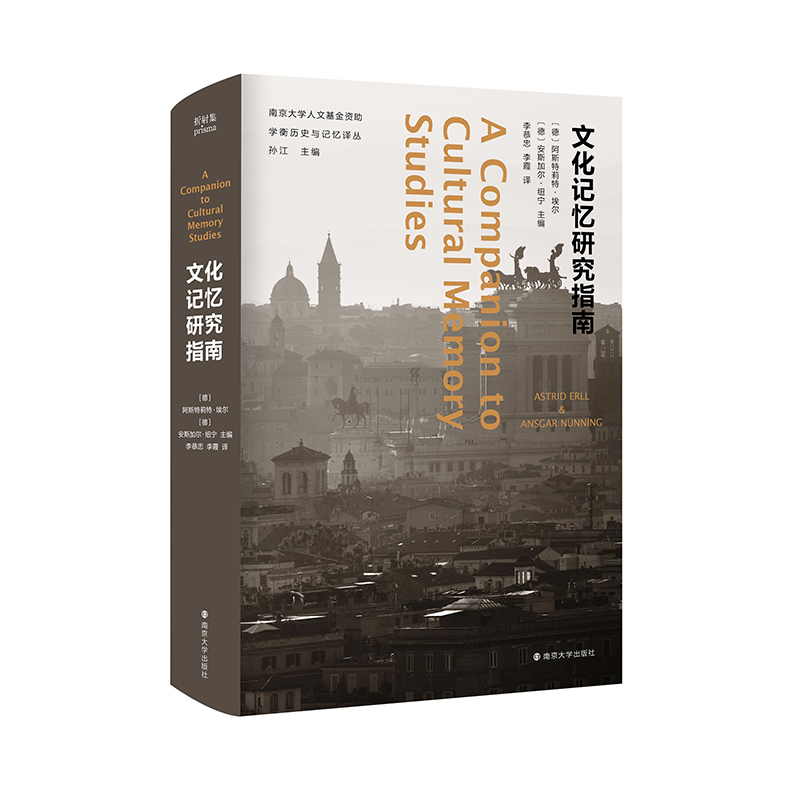
出版社: 南京大学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79.40
折扣购买: 文化记忆研究指南
ISBN: 9787305211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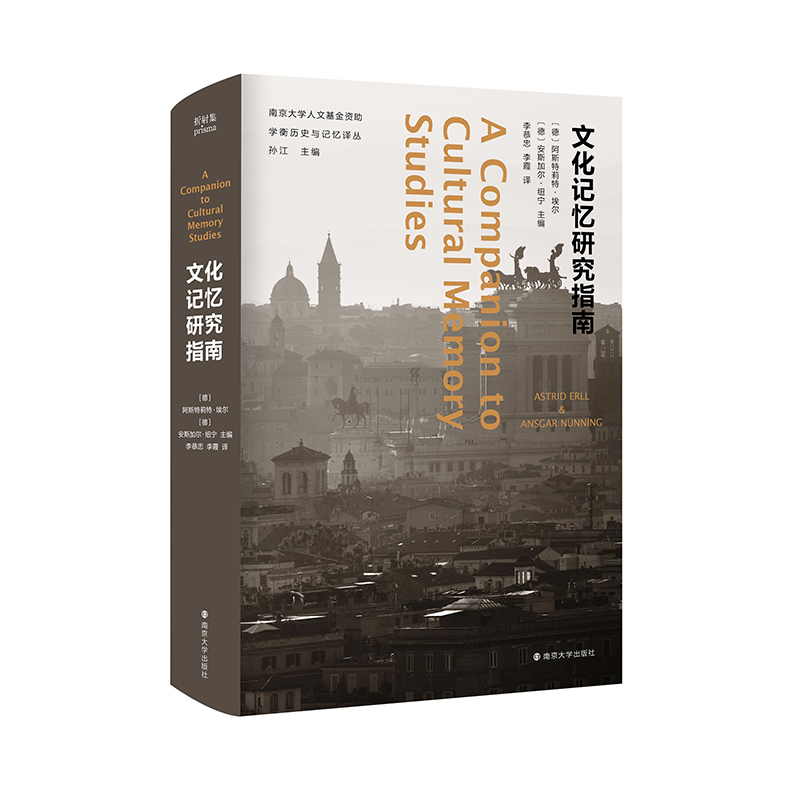
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德国伍珀塔尔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文学和英国文化史、文化记忆、后殖民研究媒介体理论以及叙事学。与安斯加尔?纽宁共同担任“媒介与文化记忆”丛书联合主编。 安斯加尔?纽宁(Ansgar Nünning):1996年起担任德国吉森大学教授,在英美文学、记忆文化、叙事学、文学和文化理论等方面著述颇丰。他是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生院和文化研究国际研究生院的创建者,也是国际博士项目“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主任、“记忆文化”协同研究中心成员。
一、 构建文化记忆研究的基础概念 文化和记忆之间的关系作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涉及历史学、社会学、艺术、文学、传媒研究、哲学、神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广泛领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相关研究在世界多地兴起,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人文学科、社会研究和自然科学整合在一起。文化记忆概念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为1980年代以来有关特定民族、社会、宗教和家庭记忆出版物的快速增长,而且体现为一个更新的趋势,即在这一风起云涌的领域内提供该技艺状况的概览和整合不同研究传统的努力。理论性论文选集的出版,比如《集体记忆读本》(Olick et al)、新杂志《记忆研究》,都表明有必要以这一广泛的讨论为聚焦点,去思考这个充满希望但仍显散乱零碎的领域里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准(参见Olick; Radstone; Erll)。这部指南展现了41位作者的共同努力,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从多种多样的跨学科视角致力于该新兴领域的发展;同时,它也是将记忆研究整合为一个更加连贯一致学科的努力的一部分。它决定性地开启了记忆研究的文化和社会视角,并为奠定其概念基础迈出了第一步。 “文化的”(或如你们喜欢用的词,“集体的”“社会的”)记忆当然是一个内涵五花八门的概念,其用法通常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在这把宽泛的术语大伞之下,而今汇集着神话、纪念碑、史学、对话记忆、文化知识形态、神经元网络等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职业活动以及结构。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此后,“文化记忆”便因其内涵的复杂性而引起极大争议(特别是在1925、1941和1950年)。哈布瓦赫的同时代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指责他不过是将此概念从个人心理学的层面转换至集体心理学的层面。甚至直到今天,学者们仍在挑战集体记忆或者文化记忆这个概念,例如,有人声称,既然我们已经建立了像“神话”“传统”“个人记忆”之类的概念,就没有必要在现有的知识库里增添一个看似新颖实则常常误导他人的词汇(参见Gedi and Elam)。当然,这些批评者忽视了一点,就是这些相对新颖的“记忆”用法的涵盖效力有助于我们理解(有时功能性的,有时类推的,有时比喻的)诸如古代神话之类的现象与现时体验的个人回忆之间的关系,亦使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学诸学科可以展开令人振奋的对话。 这部指南基于对文化记忆的一种宽泛理解,暂且将其界定为“社会文化语境中现在和过去的互动”。这样来理解该术语,我们就有可能把广泛的现象谱系纳为文化记忆研究的对象:从社会语境中的个体记忆行为到(家庭、朋友、退伍老兵的)群体记忆,再到带有“被发明的传统”的民族国家记忆,最后到诸如大屠杀、“9?11”之类的众多跨国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同时,文化记忆研究并不局限于赋予过去意义的研究,或者意在通过叙事来践行,或者与身份认同建构携手并行——虽然到现在为止,大部分记忆研究无疑关注的正是这一纽带(有意图的记忆、叙事以及身份认同)。因而,本研究领域仍对无意识、模糊的文化记忆方式保持开放(见本书哈罗德?维泽尔的文章),对诸如视觉、肢体之类与生俱来的非叙事记忆形式保持开放立场. 但是,如果记忆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实际上无所限制(一切事物都或多或少与记忆有关),那么,我们的新领域跟其他学科有何区别?针对阿龙?康菲诺的观点,我认为文化记忆研究的特征并不在于大量无限可能的主题,而在于其概念,即构想研究主题和接近研究对象的特殊方式。然而,尽管有了二十年紧锣密鼓的研究,文化记忆研究概念工具盒的设计仍在初兴阶段,因为(用康菲诺在本卷中的话来说)记忆研究当前“更多的是在实践,而不是理论化”,即以各自的词汇、方法和传统在不同学科和民族国家学术文化内得到实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审视记忆研究中使用的概念,从而通过这样的做法跨越智识和语言的边界。 即便粗略检视一下莫里斯?哈布瓦赫以来记忆研究中出现的大量不同术语,都能清楚地显示出那些探求该领域概念基础的研究者面临的挑战:集体记忆(mémoire collective/collective memory),记忆的社会框架(cadres sociaux/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mnemosyne), 记忆技巧(ars memoriae),位置想象(loci et imagines),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sites of memory),被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s),神话(myth),记忆(memoria),遗产(heritage),纪念仪式(commemoration),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chtnis),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代际性(generationality),后记忆(postmemory)。该清单不胜枚举。 首先,如此丰富的记忆概念表明,文化记忆并不是单一学科的研究对象,而是跨学科的现象。记忆研究不存在独享权威的立场、方法(有关这一点的系统性历史原因,参见本书第二、三编)。文化记忆研究是一个许多学科利用各自独特的方法和视角做出贡献的领域。这不仅导致了相关术语的丰富性,而且导致了术语间的相互脱节。同时很清楚的是,文化记忆研究也只有从一开始就基于不同学科的合作才能成功。因此,文化记忆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而且从根本上是一个交叉学科的项目。许多令人兴奋的合作形式已经促成。的确,文化记忆中最强大、最令人震惊的研究正是基于交叉学科的互动——媒介研究和文化史(阿斯曼夫妇)、历史学和社会学(杰弗里?奥立克)、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哈罗德?维泽尔;汉斯?马科维奇)、认知心理学和历史学(大卫?马尼尔、威廉?赫斯特)以及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杰拉德?埃希特霍夫;均见本书)之间的互动。学科间更密切的对话将有助于揭示记忆和文化之间丰富多彩的交集。然而,这就要求对术语进行细致入微的处理,仔细区别某些概念独特的学科性用法,以及字面的、比喻的和转喻的意思(参见本书第二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