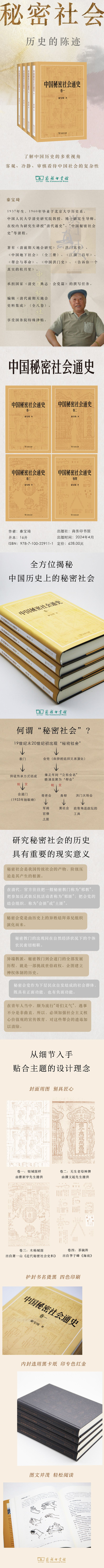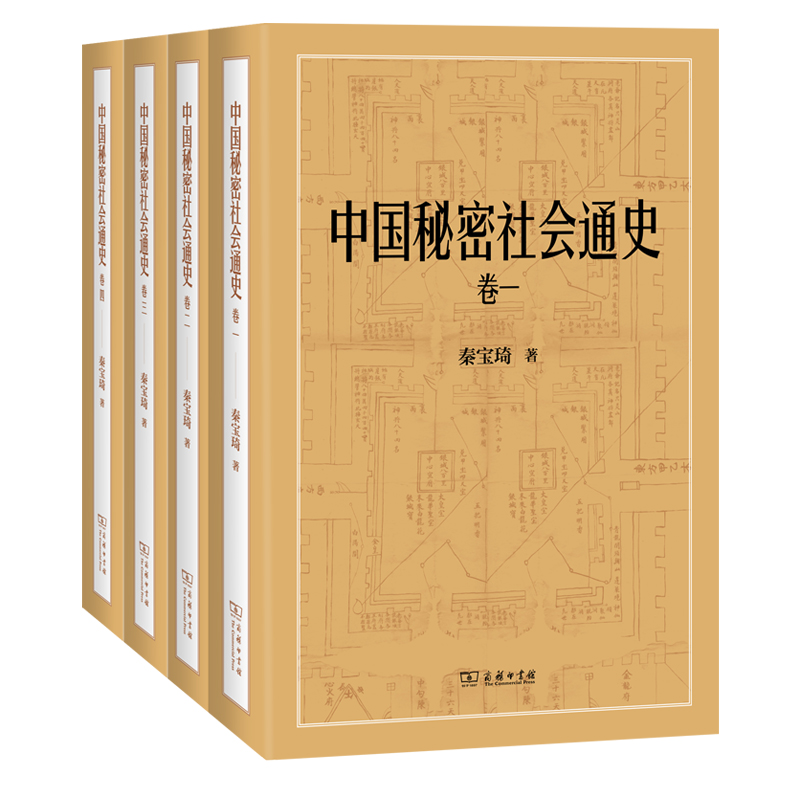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628.00
折扣价: 439.60
折扣购买: 中国秘密社会通史(全四卷)
ISBN: 9787100229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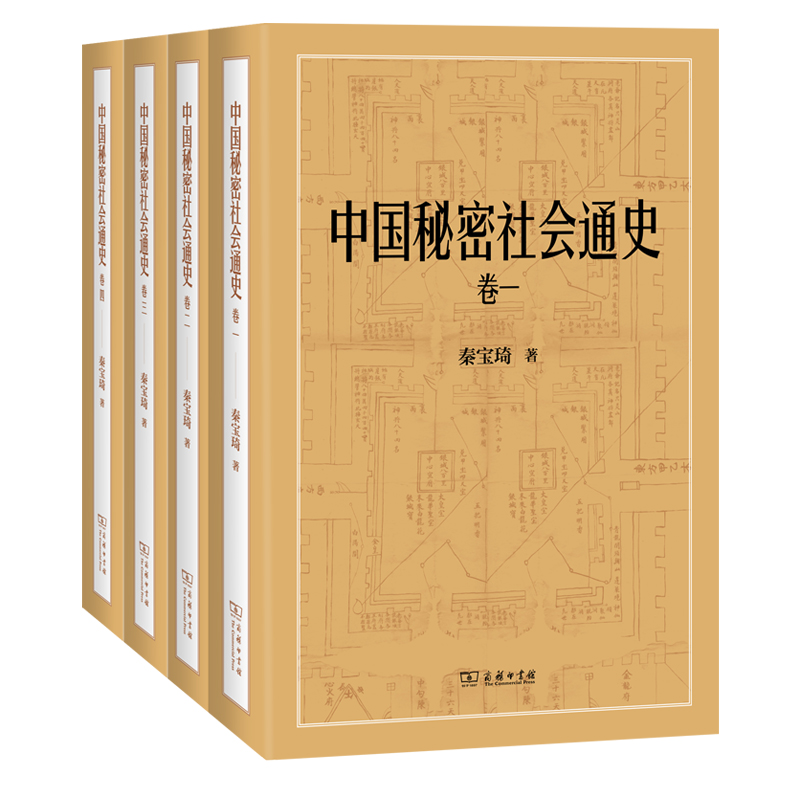
秦宝琦,1937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校内为研究生讲授“清代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等课程。在校外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澳门大学及日本学习院大学做学术演讲和学术交流。著有《清前期天地会研究》、《洪门真史》、《中国地下社会》(全三册)、《江湖三百年》、《帮会与革命》、《中国洪门史》、《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杜月笙》等十余部专著和近百篇学术论文,编辑《清代前期天地会史料集成》(全八卷),承担国家《清史·典志·会党篇》的撰写任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导 言 秘密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也是历代政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秘密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均有过重要影响,因而一直受到中外史学家、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的关注。近年来,随着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发展,秘密社会的历史更为人们所瞩目。 一、何谓秘密社会? 中国秘密社会这个概念,最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一般是把主流社会称为“庙堂”,非主流社会称为“江湖”。在清代,朝廷把民间流传的会党和教门视为叛逆组织,称会党为“会匪”、“土匪”;称教门为“邪教”或“邪匪”。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人平山周来到中国考察华南秘密社会的情况,后来把考察报告作为专著出版,名曰《中国秘密社会史》,这是最早把中国的两大秘密团体——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置于一起的著作。后来中国学术界便引进了“秘密社会”这个概念,把教门和会党合称为“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那么,应该如何界定和解读“秘密社会”这个概念呢? 秘密社会这个概念,对一般民众来说,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意味,不了解秘密社会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其实,秘密社会只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因为它有秘密的组织结构、活动方式与隐语暗号,有神秘而独特的礼仪、教义和严格的规约,从事历代政权所禁止的政治、经济或宗教活动,为主流社会所不容,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因而被称为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 中国秘密社会,从其组织形式与活动内容来看,可以分为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两大系统。 秘密教门是带有宗教性的秘密结社,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以“弥勒救世”、“末劫说”和“无生老母”崇拜融合而成的“天盘三副”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和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以入教可以消灾获福或避劫免厄来吸引信众,要求徒众茹素食斋,诵经礼佛,但不要求信众脱离家庭,服饰同常人无异,故自称为“在家出家”。秘密教门表面上与佛教和道教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也被人们界定为宗教团体,称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像明清时期的白莲教、罗教、闻香教、八卦教等,皆属秘密教门。 秘密会党是由历史上的异姓结拜弟兄组织演化而来。异姓结拜弟兄的具体情况,在元明时期流行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里有生动的描绘。这类组织最初仅仅是为了抱团取暖而结拜弟兄,并没有名称,雍正年间才开始“立有会名”,如父母会、铁尺会、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边钱会、兄弟会、忠义会、哥老会、江湖会等。清朝廷将其界定为“结会树党”的违法行为而加以打击,后来被简称为“会党”。会党是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以江湖义气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要求会众服从首领,忠于誓言,恪守规约,严守会内机密,以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吸引会众。由于受到清廷的打压而奋起反抗。由于清代满汉民族矛盾比较突出,故多以“反清复明”相标榜,借以获得汉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晚清时期,青帮、丐帮等出现后,人们便习惯性地把帮与会统称为“帮会”。 二、秘密社会产生的社会根源 秘密社会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产物,阶级压迫是其产生的根源,而小农经济则是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基础,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和其他下层民众不仅身受官府的压迫、胥吏的勒索,还遭受地主、富商及高利贷者的剥削。终岁辛勤劳动,却仍然难获温饱。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使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难以团结起来为某一政治和经济目标而奋斗。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面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艰难的处境,只是抱着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默然处之,把一切苦难与不幸归之于命运的安排。也有少数人不甘于此,他们试图同这种命运抗争,因而自发地结成各种秘密结社,来维护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所以,秘密社会乃是作为朝廷的对立面存在的。 秘密教门的出现同在自然经济状况下的个体农民密切相联。个体小农在经济上是脆弱的,经不起天灾人祸的冲击,总是担心失去自己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和微薄的财产,缺乏安全感。秘密教门便利用个体农民这种心态,向人们宣传世界将面临“劫难”,只有入教才能消灾免厄。入教之后,不但今生可以获福,死后不堕轮回,来世可托生好人。当劫难降临时,还可获得无生老母的拯救,回归“真空家乡”,得到“永生”。秘密教门的这种宣传,对广大个体小农和城镇下层民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而获得长足发展。到了晚清,小农经济日益萎缩,秘密教门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破坏,因而也随之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清末民初,秘密教门蜕变为会道门,成为军阀、官僚的工具,得到政府的庇护,秘密教门又发展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大多数会道门同日本侵略者合作,成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得到恶性膨胀。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会道门的人数竟超过了当时国内所有正宗宗教信徒的总和,并且不断挑战人民政权的权威。人民政府为保护新生的政权、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对一贯道、同善社等反动会道门的反革命活动,予以严厉打击,对一般会道门也依法予以取缔。 秘密会党的产生和发展,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清代前期,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虽然仍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南方有些地方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个体农民内部阶级分化的加剧,许多人由于经营不善或家庭成员发生变故等因素,被从农村中排挤出来,涌入城镇市圩,或到异地他乡去谋生,成为小商小贩、雇佣劳动者、兵丁差役,甚至投身寺庙,成为僧侣、道人,有的干脆靠乞讨为生,成为乞丐。他们来到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要想立足,并非易事,因而亟须互相帮助,以求得生存。秘密会党宣传的入会之后可以互相帮助,免人欺凌,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会照应等内容,这对于离家在外、谋生艰难的下层民众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尽管会党不断遭到清廷的禁止和打击,但仍然不断有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加入其中。所以,有清一代,秘密会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清政权潜在或公开的威胁。 三、秘密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功能 中国秘密社会或称为秘密结社,按照其活动内容与行为方式,可以分为宗教性的秘密教门、会道门和世俗性的秘密会党、帮会及黑社会。 如何看待中国秘密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功能,值得深入探讨。 在秘密教门的性质问题上,以往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持“宗教说”,认定白莲教等教门属于宗教团体,称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另一种意见则持“秘密结社说”,认为白莲教等教门,属于宗教性秘密结社。经过长期探讨、沟通,两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共识,即将白莲教等教门组织,界定为宗教性秘密结社,称为“秘密教门”,简称“教门”。在新修《清史》的“典志”部分,设立的“教门会党志“,就是介绍清代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新修《清史》并未把白莲教等教门视为宗教团体而归入“宗教志”,而是将其归入新设立的“教门会党志”,从而拉近了两种学术观点的距离。当然,仍有不少学者仍坚持把秘密教门视为宗教团体。 在如何看待秘密教门的社会功能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主张“宗教说”的学者,大多对教门的社会功能持正面看法,认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在教理、教义方面,“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呼声”,其武装反抗活动,属于农民起义的范畴,应该充分肯定。有的学者甚至把教门誉为“革命的宗教”、“人民的宗教”。认为秘密教门发动的武装反抗活动,打击了历代封建统治,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元末白莲教起义,最终颠覆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清中叶的五省教门起义,纵横五省,历时九年,导致了大清帝国由盛转衰。而历史上教门连绵不断的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而持“秘密结社说”的学者,则对教门的教理、教义及其武装反抗活动,多持负面评价。认为秘密教门在其肇始之初,就具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企图干预世俗社会的政治运作。早在东汉末年,以张角为首的天师道发动的黄巾起义,几乎将东汉政权颠覆。以张鲁为首的五斗米道,还在汉中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维持了三十年之久。在天师道和五斗米道之后,佛教的各种异端教派和秘密教门也继承了挑战世俗政权的传统,不断发动暴动。 异端教派和秘密教门的教理、教义,乃是其挑战世俗政权暴力活动的神学依据。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异端教派——弥勒教,利用“弥勒救世”说进行造反,其载体乃是《佛说法灭尽经》。隋唐五代时期弥勒教又利用“末劫说”反抗世俗政权,其载体便是《转天图经》。《转天图经》又名《五公经》、《五公末劫经》,内容是宣扬劫难将至,将要改朝换代。明代中叶秘密教门兴起后,在罗教、黄天道教、闻香教等教门的经卷里,又将民间流传的“无生老母”信仰,融入“弥勒救世”、“末劫说”,形成完整的“天盘三副”教义。宣扬人类将面临最大和最后的劫难,届时无生老母将派遣弥勒佛降临尘世,成为教门的教主。他将在尘世建立一个“人间天国”——银城或云城。在这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里,由弥勒佛转世的教主,将成为人民的主宰,而教门的教理教义,则是臣民的唯一信仰和必须遵循从的行为准则。 异端教派、秘密教门到会道门的全部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挑战世俗政权、企图建立神权体制的历史。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世俗国家,自西汉以来,就一直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思想,倡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高于教权,各种宗教均服从于世俗政权。儒家思想在我国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可能被异端教派和秘密教门的暴力活动所撼动。元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元末农民起义是由白莲教所发动和领导的,起义军首领朱元璋本人不仅是白莲教世家,而且是通过白莲教造反起家的。他深悉白莲教的教义和政治诉求,对世俗政权的威胁,于是在起义胜利的关键时刻,毅然放弃白莲教的“弥勒救世”信仰,改奉儒家思想。他在众多儒生的帮助下,最终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世俗的大明王朝。此后,中国的历代政权,均沿着世俗化的道路前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和社会生活。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依法取缔了一贯道、同善社等会道门,之后,又在法律、法规上明令禁止会道门和邪教的活动,彻底粉碎了教门、会道门企图取代世俗政权、建立神权体制的迷梦。 历史学界在如何看待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性质上的研究和探讨,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对于秘密会党的性质,学者最初大多沿袭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说法,认定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会党,乃是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是为了反对清朝统治而结成的“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如何看待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性质方面,出现了新的看法。学者们依据清代档案和《大清律》等史料,发现在康熙年间仅存在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真正意义上的秘密会党,是在雍正年间才出现的。雍正四年(1726)开始出现父母会、铁尺会、铁鞭会、桃园会、一钱会等秘密会党。在雍正年间修订的《大清律》里,将这些组织界定为“结会树党”的“会党”。乾隆前半期,在闽南一带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的加剧,在下层民众中出现了更多的会党,如子龙会、小刀会、边钱会等,其他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不同名目的会党,如湖北的箩筐会、江西的关帝会、江苏的顺刀会等,在秘密会党大量涌现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天地会。所以,以天地会为代表的秘密会党,乃是清中叶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分化的产物,是下层民众为了生存而结成的互助性组织,并不是因为满汉民族矛盾而产生的反满“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 关于秘密会党的社会功能,秘密会党作为下层民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既具有正面功能,也有负面功能。其正面功能主要表现为:在下层民众之间施行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进行抗争。如乾隆年间的林爽文起义、陈周全起义;嘉庆年间广东的陈烂屐四起义、江西的廖干周起义等;咸丰、同治年间的闽南小刀会起义、闽中红钱会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两广地区的天地会起义,还建立了大成国、升平天国以及多个天地会政权。在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在革命党人引导下,积极参与了反清革命。革命党人在两广和云南先后发动十次反清起义,起义军的队伍里多为天地会的成员。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海外洪门也在财力、物力方面给予革命党人以强有力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的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几乎遍地开花,除了东北三省和直隶、山东外,其他各省,甚至地处边疆的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的辛亥武装起义,均有哥老会的身影。总之,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会党,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秘密会党作为下层民众的结社组织,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也很明显。清代会党在发动反清起义的同时,也有过抢劫夺财和杀人越货等反社会活动。会党的局限性和消极方面,在辛亥革命中更充分暴露出来。一些会党首领,不理解革命的真正意义,以为革命无非是“打天下,坐天下”。辛亥起义成功后,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是“洪家天下”,同革命党人争夺领导权,从而走上歧途,最终被革命党人所抛弃。 民国年间,西南地区的哥老会,蜕变为军阀和官僚争夺的势力范围和压迫人民的工具,有的袍哥组织干脆成为土匪;上海青帮蜕变为典型的黑社会,在政府的庇护下,从事大规模烟赌娼及走私活动。洪门天地会组织,则成了政客们角逐政坛的工具。 近年来,由于黑恶势力的猖獗,人们往往把历史上的会党同后世的黑社会混为一谈,只看到会党和黑社会的相似之处,而忽视二者间的严格区别。 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虽然也进行过诸如打架斗殴、抢劫夺财、绑架勒赎以及走私贩毒等反社会活动,但其规模远非后世黑社会可比拟。据清档记载,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在进行上述反社会活动中,一般规模有限,大多为数人或数十人,使用的武器,无非是刀矛棍棒;抢劫的数额也不大,无非是几千文铜钱,或几两、几十两白银,几件衣服或农具,牵走几只牲畜。而后世的黑社会在打架斗殴方面,动辄就有几十人或数百人参与,往往使用枪械等致命武器,抢劫的数额则多达数万元甚至数百万元。在走私贩毒方面,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等秘密会党的数额也远非后世黑社会可比,前者无非为了维持生计或取得活动经费,后者则往往暴富,甚至“富可敌国”。在残害民众方面,秘密会党一般是把对方打伤、打残,而黑社会则往往将受害者杀害,甚至灭门。在清代会党的活动中,尽管也有少数差役和兵丁参与,但会党并没有得到过官府的庇护。而后世的黑社会,则由当权者充其当“保护伞”,上海青帮得到上海行政当局和英、法租界当局的保护,其走私贩毒活动,往往由法租界的军警提供保护。 总之,清代会党和后世黑社会,二者在性质上有严格的区别,不应混为一谈。 四、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秘密社会史,作为人民群众历史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当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在清代,官方往往把一般秘密教门称为“邪教”,把参加反武装反抗活动者称为“邪匪”;把会党的结会组织,称为“会匪”或“土匪”。旧时代的史学家们沿袭了官方的立场,对历史上秘密社会的历史或者加以污蔑,或者不屑一顾。在旧史学领域的论著里,把帝王将相作为历史的主人,根本没有广大民众的地位,更遑论秘密社会的历史。在他们的笔下,仅仅在打击、镇压其反抗活动时,顺便提及。新中国建立后,历史学界改变了旧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始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秘密社会作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受到了历史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在社会史研究领域,更成了研究的热点之一。近些年来,国外历史学界也在大力倡导研究下层民众的历史,而加强对中国的秘密社会历史的研究,也适应了国外这种学术潮流。 其次,秘密社会(教门和会党)的反抗斗争,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秘密社会的成员大多为农民、手工业者或小商贩以及江湖流浪者。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遭受到官府及地主、富商的剥削与压迫,被逼无奈之下,被迫铤而走险,举行武装反抗斗争,成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反抗斗争,尽管也有局限性,但毕竟打击了封建统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秘密社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该受到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视。 研究秘密社会的历史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秘密社会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它所遗留下来的遗毒和消极影响,却不容忽视,应该予以清除。 首先,在我国的干部队伍里,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拉帮结伙,搞小圈子,无疑是受到了历史上帮会的影响。为了反腐斗争的顺利进行,必须深入研究秘密会党和帮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做到“以史为鉴”。 其次,在青年人当中,颇为流行“哥们义气”,遇事不分是非曲直,只要是自己的“哥们”,就加以袒护。一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哥们义气”进行犯罪活动。所以,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对这些帮会的遗毒加以清除。 第三,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猖獗,也是帮会的遗毒之一,必须予以打击和肃清。黑恶势力利用拉帮结伙勾结在一起,形成黑社会组织。一些不法分子,模仿历史上帮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进行有组织犯罪活动,为害一方,残害平民百姓。人民政府虽然对之多次采取专项打击行动,但黑恶势力和黑社会组织,往往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对于黑恶势力和黑社会组织,必须不断揭露其反社会的本质,坚持不懈地进行打击,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把打击惩治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作为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内容,将其彻底根除,以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 全方位揭秘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