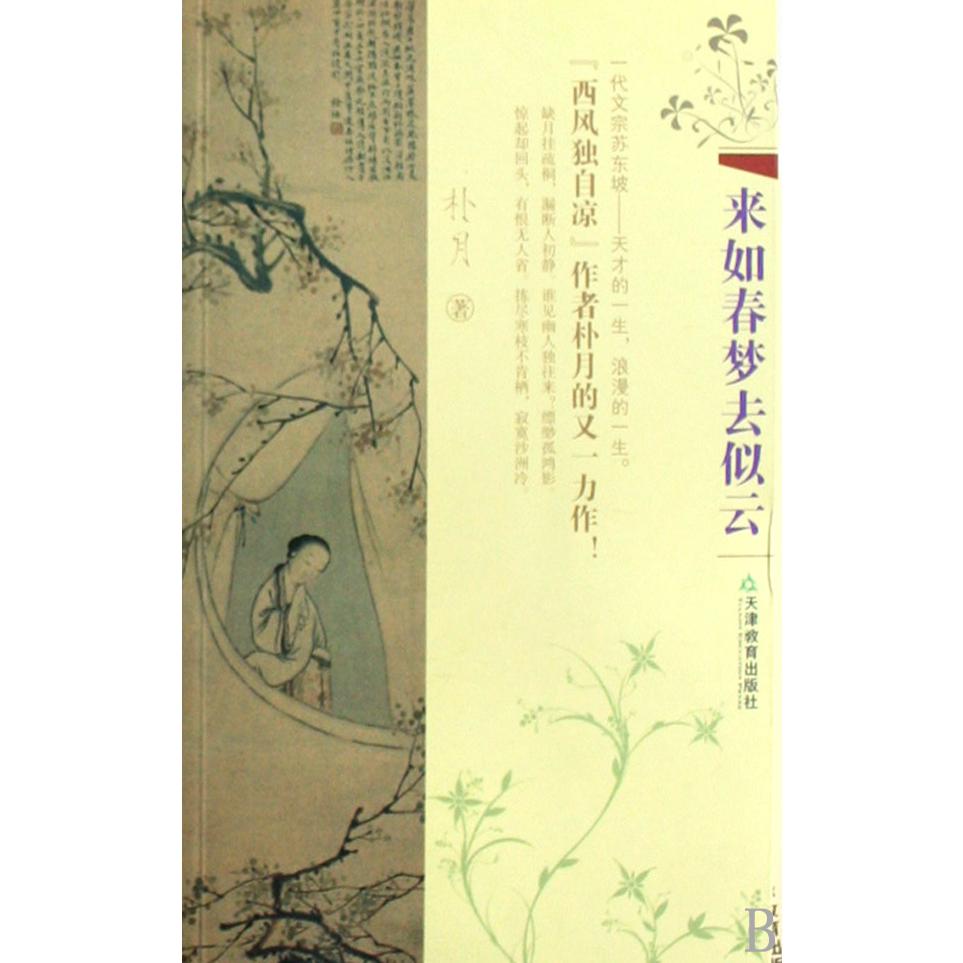
出版社: 天津教育
原售价: 16.00
折扣价: 10.70
折扣购买: 来如春梦去似云
ISBN: 978753095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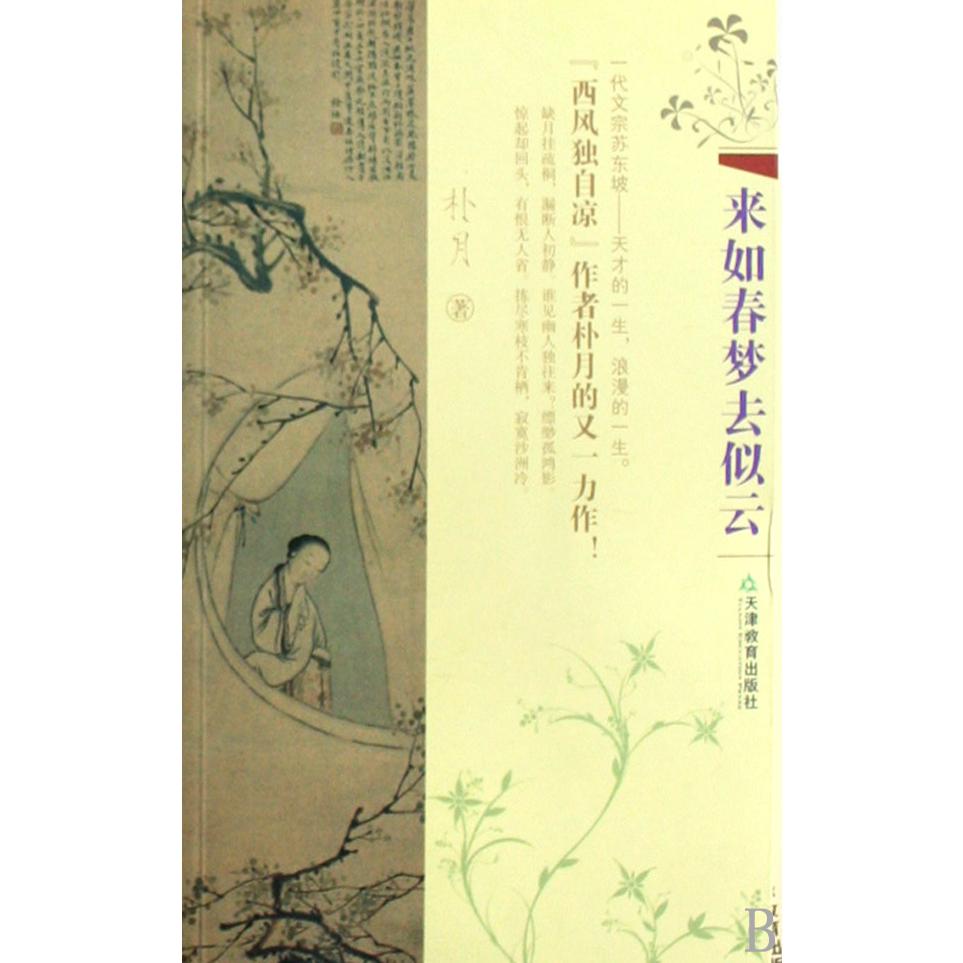
朴月,本名刘明仪,著名历史文学作家,曾出版散文集、历史小说、传记小说等。代表作除本书外,还有《西风独自凉》。现任台湾历史文学学会秘书长。
壹 那迤逦如山水横幅,清幽绝俗的富春江,诚然是红尘中的人间仙境,奈 何,他们都没有坐视民间疾苦而不动心的修为。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 惫,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 长,云山乱,晓山青。 素笺上,潇洒脱尘的行草,在柳瑾惊叹中,落下了最后一个字。苏轼濡 墨,另行写下“过七里濑”“调寄行香子”,才放下笔,抬起头来。 柳瑾捋着髭须,笑道: “都道你文章好,诗好,不意作歌词,也出色当行!我本有心难你,没 想到……我还是甘拜下风,藏拙了吧,珠玉在前,也不必献丑了。” 指着“君臣一梦,今古空名”八字,叹道: “子瞻正当盛年,何以透彻至此?这该是如我辈老朽才有的感慨。” 苏轼想起当日过“严子陵钓台”时的感触,道: “当日,光武中兴,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事!功成后,再三诏请,严子 陵却宁隐于富春山垂钓,不愿立身庙廊,其人志行之高洁淡泊,令人忻慕向 往,古来君臣恩义,似此能几?然而,而今安在?” 他缓缓道: “如果严子陵生当此际,目睹天灾人祸,是否还能动心忍性,高蹈避世 ,独善其身?” 他忍不住把满腔忧世忧民之情,向辈分比他高一辈,却堪称忘年知己的 柳瑾倾泻。柳瑾,是他堂妹小二娘的公公,与王安石同年及第,却半生偃蹇 ,在贬谪中,寄情诗酒,消磨了壮志豪情。眼见昔日同年,如今飞黄腾达, 位列公卿,自己却不遇如此,又哪能没有感慨? 这一回,他往杭州访苏轼,苏轼热诚接待,陪他遍游两湖胜景。眼见苏 轼的焕发、秀杰,他喜慰之余,又不禁担心:子瞻锋芒太露,忧民济世之心 又太切,而这二端,却正是官场大忌,想当年自己,何尝不以经国济世之才 自许?如今,一纸任命,监灵仙观,看来,这就是这一生的仕途终点了…… 一念及此,不禁唏嘘。 苏轼这一回,是奉命往常州、润州赈济,因柳瑾家居京口,准备先回家 ,再往灵仙观去,正好同路,所以附载同行。对这位老世伯的怀才不遇之情 ,他是了解的,也充满了同情。但,更令他萦怀的,却不是个人的际遇,而 是天下苍生。 风不调,雨不顺,旱蝗为灾,五谷不登,他,一个小小的通判,除了禀 一念之诚,灵隐祷雨,更能为百姓做什么?天灾如此,还加上种种人为因素 。饥年乏食,尚有可说,丰年,百姓又何曾因而受惠? 他想起家中的小丫鬟子云,子云初到他家,瘦伶伶的,面有菜色,对“ 做官”的他惊畏如虎。后来,他才慢慢知道,子云家中原本小康,只因不堪 青苗贷款,胥吏逼迫,才落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牙婆上门,怂恿叔叔卖 侄自救……子云道: “姊姊说,不能怪叔叔,要怪,只怪‘青苗法’。要不是为了还青苗欠 款,我爹娘不会死,叔叔也不会卖我们的。” 相处渐熟,子云天真地对他说: “若我早些卖到官人家就好了。官人是做官的,必肯发善心,免了我爹 娘的欠款,爹娘就不会死了。” 他哑然苦笑:他通判杭州,前后两任太守沈立、陈襄,都堪称是好官了 ,犹不免有百姓迫于逋欠,家破人亡的事。若换了一心巴结执政,努力推行 新法的官守,那百姓的悲惨,更当百十倍于他的所见所闻。 “爱民如子”,官吏每以此阿谀自我陶醉,实则如何?天下岂有为父母 者,眼见儿女饥馑,还忍雪上加霜的?这几年,他看多了这一类的惨剧:五 谷丰登,而农夫乏食;蚕桑鼎盛,而织妇乏衣。年年“良法美意”,逼民青 苗贷款,只令债上滚债,永无清偿之日! 他,身为“民之父母”,竞白匡救无力,甚至在朝廷法令下,还不能不 扮演“助纣为虐”的角色! 他努力尽责,做一个好官:春口劝农,蝗灾捕蝗,干旱求雨,汤村开运 盐河,他陪着百姓淋雨督役……他以此求心安。他能心安吗?他家中,现搁 着一个朝廷“德政”的受害人,他又如何能无动于衷? 因此,他再三以病为由,推却太守陈襄邀宴招饮,却独自一人到孤山, 访高僧惠勤。惠勤,是他的恩师欧阳修的方外知交,欧阳修死后,他不免把 惠勤视如师友,以寄孺慕。 惠勤见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把他迎进禅房,烹茶相待。在茶炯袅袅、 苦后回甘中,他知道,已跳出红尘的惠勤,对于世事,跟他一样有心无力。 甚至,便算欧阳公在世,又何力抗命朝廷,挽狂澜于既倒? 严子陵早已作古,苏轼和柳瑾却各怀心事地沉默着,那迤逦如山水横幅 ,清幽绝俗的富春江,诚然是红尘中的人间仙境,奈何,他们都没有坐视民 间疾苦而不动心的修为。 “二哥!” 柳仲远夫妇双双出堂,迎接远归的老父和同舟而来的苏轼。柳夫人尤其 欢喜,苏轼见到堂房中仅存的小堂妹,也欣喜莫名。他本行二,长兄景先早 卒,出道之时,便只与弟弟苏辙子由并称“大苏”“小苏”了。 “小二娘,可有好多年不见了!” 小二娘笑着唤两个孩子: “闳儿、辟儿,快来拜见舅舅!” 两个男孩,大的不过十岁,带着弟弟,中规中矩地向他磕了头,直喜得 苏轼一手一个,连忙拉起来,笑向柳仲远道: “仲远,这可是一门双璧!” 柳仲远笑道: “柳家双璧,只要能及苏家双璧一半,我就心满意足了。” 苏轼笑指小二娘: “有我这位贤妹督教,还怕他们不青出于蓝?” 回头唤僮仆: “把娘子预备的礼物取来!” 原来,苏夫人知他要到京口,早打点了礼物馈赠。送小二娘的是丝绸锦 缎,送外甥的是文房四宝。 “季章说,外甥都启蒙上学了,我们这样人家,别的用不着,文房四宝 必不可少,日后赴试中举,也全仗佳笔佳墨,所以,以此表祝福之意。” 小二娘命两个孩子拜谢,道: “多谢嫂嫂金口。二哥,子安哥正好有信来,你此番不来,我还要托人 捎去。二哥先看信,我去看看酒饭好了没有,待会儿再来请!” 目送小二娘带着孩子姗姗而去,苏轼依稀见到她幼时双鬟垂肩的娇稚模 样。她总在下午黄昏时分,他和子由完了功课时,披着一身日影而来,磨着 他和子由把一天所学讲给她听。有时他感觉,她娇憨相求,对他的督促力量 ,竞比他启蒙师张道士还大。 他只有这一个小堂妹,他和子由对她疼爱呵护有如亲妹妹,而她对他们 的亲爱,甚至胜于对她的亲哥哥。 往事依稀,昔日幼女,今已为人母,兄妹之情,依旧是逾于手足。尤其 他亲姊妹相继夭折,小二娘,是他世上唯一的姊妹了。 抽出家信,堂兄子安照例叙述一下家中亲友的近况,然后是对他的关切 期勉,最后,问他何时能返乡一行,以扫先人墓丘,并叙兄弟之情。 他深深叹口气,把信珍重收好:他知道,故乡亲朋,每以他为荣,也总 认为,他“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却不知,他在仕宦途中,方才起步 ,却已深觉“身不由己”了。就如他和小二娘,一在杭州,一在润州,相距 并不远,却若不是他奉命赈济,也难得一见。 回到家中,彼此姻娅至亲,柳瑾便以家宴接待,家中笛婢,一边吹笛助 兴,却比急管繁弦,别有一番幽雅情味。酒酣耳热,柳瑾笑指两个孙儿: “子瞻,听闳儿说,二十七娘送他们文房四宝,你这位学富五车的舅舅 ,难得来此,秀才人情,还不送一张吗?有你开笔,也望他们文章书法,都 能日益长进,不辱没舅家!” 两个孩子一听祖父如此说,立时向前跪下,道: “求舅舅赐字。” 苏轼搀起外甥,笑道: “家里现放着以书法、诗文名家的祖父,还要舍近求远?” 小二娘一边接口: “孩子们仰慕舅舅多时了。先前小,不知舅舅文名,如今启了蒙,直把 舅舅敬如天人。二哥,你又何必谦辞呢?” 苏轼向柳仲远道: “我这贤妹,我是从来未敢拂逆的。家父三女,二人是幼年夭折,一姊 ,也在嫁后不久去世。小二娘承欢二老膝下,解慰二老失女之痛,使我和子 由由衷感念。我三人,虽非同胞,不啻手足。子玉仁丈传谕,再加上贤妹有 命,我倒真不敢推辞!” 小二娘含笑让到书案前,吩咐孩子发笔磨墨,苏轼裁了纸,振腕落笔: 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 ! 柳瑾哈哈而笑,道: “家鸡毕竟不如野雉,老朽不能不服!” 家鸡,典出晋代。王羲之书法称擅一时,庾翼本以书法名家,而家中子 弟,却竞学王羲之,他因此有“小儿辈厌家鸡,爱野雉”之叹。 小二娘却向孩子们道: “‘读书万卷始通神’,这是二舅舅的金针法门,你们可要切记此语。 ” 苏轼道: “小二娘知我!” 说着,换一枝笔,续写另一绝: 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如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 ! 诚悬,是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字,他曾在皇帝问他用笔法时,答:“心 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以此来隐喻劝谏皇帝,使皇帝感悟。苏轼用这 个典,其中的期许,便不言而喻了。 柳瑾神色一整,吩咐孙儿: “还不快拜谢舅舅赐诗垂教!” 柳志远也动容: “子瞻,这两首诗,可当我柳家传世的家训了,子孙只要以此为安身立 命之道,何愁不振家风!” 小二娘抬头望着苏轼,泪光隐隐: “二哥,只怕,你一生志业,也就在其中了……” 苏轼点点头,的确,他是以心正、笔正为立身、立朝的准则的。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以笔谏匡救天下,但他知道,他会见贤思齐,勉 力而为的! 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