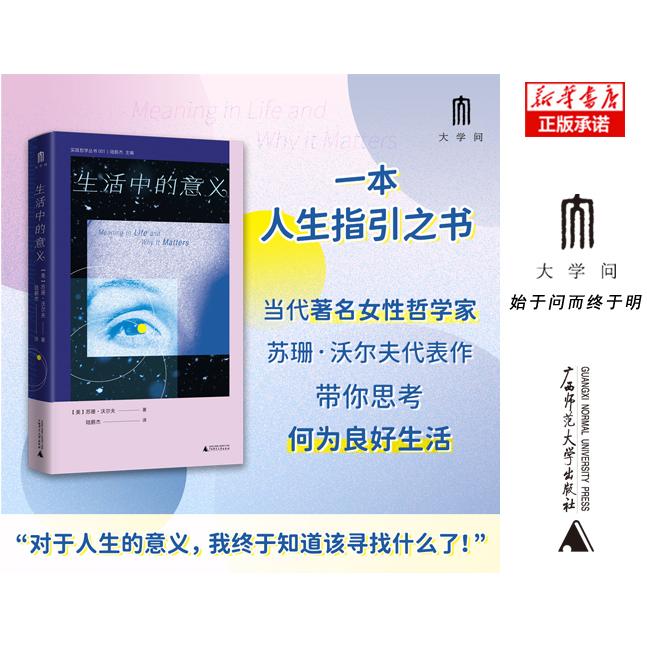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79.00
折扣价: 47.40
折扣购买: 实践哲学丛书 生活中的意义
ISBN: 9787559865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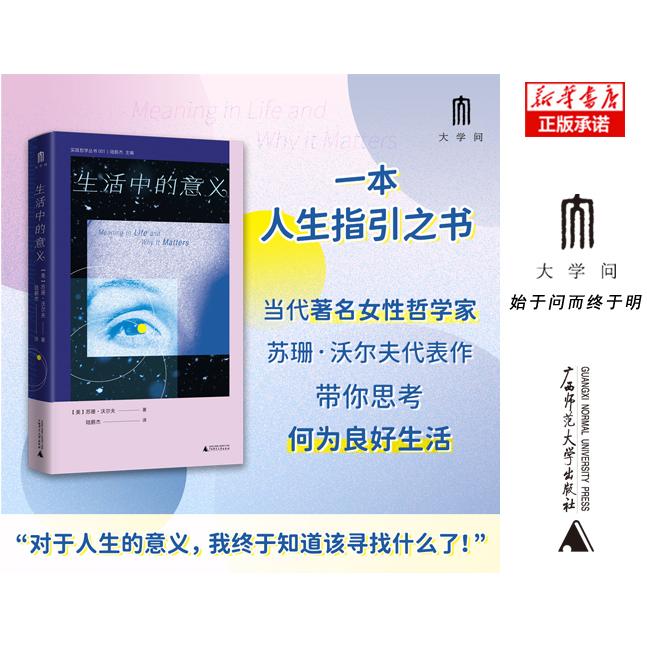
作者:苏珊·沃尔夫,美国著名哲学家,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哲学讲席教授。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等名校,1999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06年当选为美国哲学学会成员。主要研究道德哲学与心智哲学。她于 1982 年发表的论文《道德圣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道德哲学论文之一,著有《理性内的自由》等。 译者:陆鹏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四川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译有《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等。
编者按:《生活中的意义》是当代著名女性哲学家苏珊?沃尔夫的代表作。该书源自2007年11月作者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发表的演讲。作者以分析哲学的方法,对“人生意义”的内涵做了抽丝剥茧的阐释,为我们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视角。该书为近20年关于“人生意义”这一话题引用率最高的哲学书,曾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新生指定读物。以下与您分享的是作者的“开场白”。在这简短的“开场白”中,作者试图让读者了解,除了自我利益和道德责任,“有意义”是构成美好生活的又一重要维度。 虚假二分 人们通常会用两种哲学模型(philosophical models)来描述人类的心理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会用它们来描述人类的动机。将人类当作利己主义者,认为只有那些被人们视为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才能够驱使或引导他们采取行动,这也许是最古老且最受欢迎的一种模型。然而,长期以来也有人在捍卫一种二元论的动机模型;按照这种模型,除了自身的利益,还有某种“更高级的”东西也能够驱使人们采取行动。例如,康德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人们除了受自身倾向的影响,理性本身也能够对他们产生驱动或引导的作用。 这两种描述性的人类动机模型与某些规约性(prescriptive)或规范性的(normative)实践理性模型具有紧密的联系。心理利己主义持有这样一个描述性的论点,它认为人们只会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理性利己主义则持有这样一个规范性的论点,它主张只有当人们试图让自己的福祉(welfare)水平最大化的时候,他们才是理性的;这两个论点不仅密切相关,而且经常被人们混淆在一起。与二元论的人类动机观念相对应,我们会发现,也有人在支持一种二元论的实践理性观念。这种观念也许在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的著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西季威克认为,以下两种视角为人们提供了同样有效的行动理由:一种是利己主义的视角,它会建议人们去做最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另一种则是非个人化的(impersonal)视角,它会敦促人们去做那些“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最好的事情。 在日常交流和哲学讨论中,当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或策略提供辩护(justi.cations)时,我们似乎就会想到这两种模型中的某一种。通常来说,当别人要求我们为自己的选择提供解释或辩护时,我们会给出某些理由并且这些理由看起来属于自我利益的范畴。比这种情况更常见的是,当我们试图说服其他人做某事时,我们也会诉诸自我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诉诸的是其他人的自我利益。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诉诸自我利益根本无法令人信服;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诉诸自我利益要么不恰当,要么则没有把握到要点。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很可能就会诉诸义务(duty),从而说出诸如此类的话:正义、同情心或道德会要求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动,不管那样做是否有助于促进我们自身的利益。 然而,我认为,还有很多动机和理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它们却被上述这些动机模型和实践理性模型忽略了。而且这些被忽略的理由既不是次要的,也不是怪异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些模型所忽略的是我们生活中某些最重要、最核心的理由和动机。正是这些理由和动机促使我们从事某些活动,从而让我们的生活值得一过;它们给了我们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让我们的世界运转起来。这些理由、动机以及它们所引发的活动,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意义。 在本次演讲中,我的目的是阐明这些理由的独特性质,以及它们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具体来说,我认为,“我们容易受这些理由的影响”与“我们有可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会将“有意义”理解为生活能够具有的一种属性,并且这种属性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可以还原成幸福或归入“幸福”这一范畴;不仅如此,我认为它也无法还原成道德或归入“道德”这一范畴。接下来,我将重点解释我所说的“有意义的生活”(meaningfulness in life)具有哪些特征,并且将通过某种阐述方式来表明,对我们自己和我们在乎的人而言,有意义的生活似乎是值得向往的。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的演讲内容在实践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用处。虽然我会提出某种观点来解释有意义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但关于我们如何拥有这样的生活或如何过上这样的生活,我只能提供某些最抽象的建议。因此,在我的第二次演讲中,我会通过回应一组特别重要的反对意见来捍卫我的观点;之后,我将转向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在思考应当去做哪些事情以及应该如何生活的时候,更习惯于使用“幸福”和“道德”这两个范畴,而“有意义”这一范畴又与它们有所不同,那么为什么“有意义”这样一个范畴有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会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呢?正如我将论证的那样,意识到“有意义”是生活能够具有的第三种价值会影响我们对前两种价值的理解。也就是说,采用某些对“有意义”有所关注的人类动机模型和理性模型会影响我们对幸福和道德—以及对自我利益—的思考方式。此外,如果我在这些演讲中所提出来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除非我们认为价值判断具有某种客观性,否则意义就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继续谈论、关注并鼓励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中获得意义,那么在有关价值的讨论中,我们就需要承认这种客观性。 让我先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正在思考的那些理由和动机—要恰当地理解这些理由和动机,我们不能只关注它们是否有利于提高我们的幸福水平,或者是否有利于促进非个人化的理由(或道德)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我能想到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对某些人非常在乎、特别在乎,出于对他们的爱,我们采取了行动。当我去医院看望我的兄弟,或者帮我的朋友搬家,或者彻夜不眠为我的女儿缝制万圣节服装的时候,我的行为既不是出于自利的理由,也不是出于道德的理由。我并不认为,做以下这些事情会让我过得更好:在一个单调乏味的狭窄房间里,我沮丧地度过一小时的时间,只能看着我的兄弟烦躁、痛苦;或者我冒着背部受伤的危险,试图把我朋友的沙发安全地搬下两层楼;或者为了确保在明天的节日游行中,我的女儿想要穿的那套蝴蝶服装会有一双姿态优美的翅膀,我放弃了自己非常渴望的好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我同样不认为我有义务去做这些事情,也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我这么做了,那我就做了对这个世界最有益的事情。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既不是为了促进个人利益,也不是因为我有义务或者有其他非个人化的理由(或不偏不倚的理由)要这么做。恰恰相反,我是因为爱才去做这些事情的。 由于利己主义和二元论的实践理性模型忽略了上述这些理由—这些理由或许可以被称为“爱的理由”(reasons of love),因此我认为,这两种模型同样也忽略了另外一些理由:这些理由会促使我们去追求某些与人无关但却让我们充满激情的兴趣爱好。写哲学论文、练习大提琴,以及除掉自己花园里的杂草,这些事情可能会要求我们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从自身福祉的角度来看,它们可能并不是最优的行为。而且在这些情况下,非个人化的视角显然并没有要求我们采取任何行动—比起那些涉及我们所爱之人的情形,这一点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更加明显。当我们为了所爱之人而采取行动时,是那个人的利益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理由;同样地,在我设想的这些情况下,当我们追求一些与人无关的兴趣爱好时,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的是一种在我们自身以外的价值,无论我们是通过认知还是通过想象而相信这样一种价值的存在。我之所以为我正在努力撰写的哲学论文感到痛苦,是因为我想把这篇论文写好;也就是说,是因为我希望我的论证可靠、观点正确、文笔清晰优美。我如此艰辛地完成我的作品,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至少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当我努力改善我的作品,使其符合某个标准的时候,我既不知道、也不在乎这么做对我来说是不是最好的(即从我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最好的),就像我为了让我的女儿过得幸福而投入那么多的精力,但我并不关心这对我来说是不是最好的。我们可能会说,我是“为哲学”而奋斗,而不是为自己而奋斗,但这么说不仅会产生误导作用,而且既晦涩难懂,又显得自命不凡。尽管如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优秀的哲学作品所具有的价值在驱动和引导我的行为,就像可能是音乐的美或尚待开发的花园有可能展现出来的美,促使大提琴演奏者或园艺爱好者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会牺牲安逸,并且会约束自己。 将这些例子中的人说成是一些爱哲学、爱音乐或爱花的人,这么说似乎不会显得不自然,也不会显得牵强附会;比起说他们爱的是自己、道德或其他非个人化的公共利益,说他们爱的是这些东西(即哲学、音乐或者花)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他们的选择和行为,而且也能够更好地为他们的选择和行为提供辩护(或者更严谨地说,能够为这种辩护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这些人的动机和深思熟虑的结果与那些出于对个体的爱而采取行动的人是相似的,所以我将使用“爱的理由”这个短语来涵盖这两类情形。因此,我的主张是,爱的理由——无论是爱人类个体或其他生物,还是爱某些活动、理念或其他类型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些理由并不等同于自利的理由或道德的理由。如果我们既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去理解这些理由的正当性(legitimacy)和价值,那么我们就会对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自己产生误解,并且不会去关注那些真正值得关注的事物。 然而,不是所有由爱的理由所驱动和指引的行为都有合理的依据(justi.ed)。并非所有爱的理由都是好的理由。首先,你爱某个东西或某个人并不意味着你就知道哪些事物真的对他们有好处。虽然你可能想要去帮助你所爱的对象,但你的行为却有可能不会使其受益。比如说,你可能会宠坏你的孩子,给你的植物浇水过多,或者对你的哲学风格施加不必要的限制。 更有趣的是,你可能会把爱给予错误的对象,或者你的爱可能会受到别人的误导;你对爱的对象所付出的精力或所给予的关注可能与该对象的价值不匹配。[2]一个出色的女人可能会放弃自己的事业、家庭和友谊,去跟一个其他人都认为“配不上她的”男人在一起,而且还要照顾这个男人。一个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的青少年可能会将 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给他解释,却茫然不解了。”许多哲学家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切哲学中最深刻、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哲学中最为含糊不清的问题之一。本书以分析哲学的方法,对“人生意义”的内涵做了抽丝剥茧的阐释,提出了诸多洞见,论证清晰、精妙而严谨。通过阅读此书,相信读者既能在人生意义方面得到指引,也能近距离感受和领略哲学思考的乐趣。 我们很多人会在生活的某个阶段或某些时刻对人生的意义而感到迷茫,比如在生活发生巨变的时候,在郁郁不得志之时,甚至在某个稀疏平常的夜晚。这是一种古老而经久不衰的迷茫,也是一种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面对的困境。这本书为我们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视角。作者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告诉我们:在个体的生活中,依然有某些东西可以使得人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一位70岁的美国读者这样评论此书:“这本书非常值得阅读。普林斯顿大学的新生被要求阅读这本书,以便他们在选择职业之前思考一个人的选择是如何塑造其人生轨迹的。至于我,一个70岁的老人,我发现这本书对我反思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深刻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