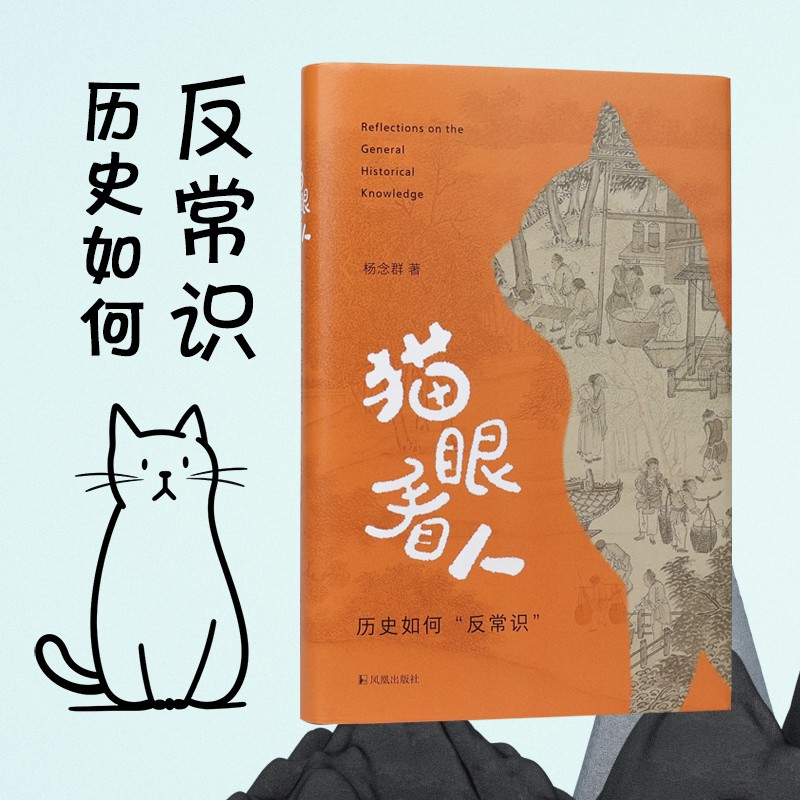
出版社: 凤凰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8.40
折扣购买: 猫眼看人:历史如何“反常识”
ISBN: 97875506388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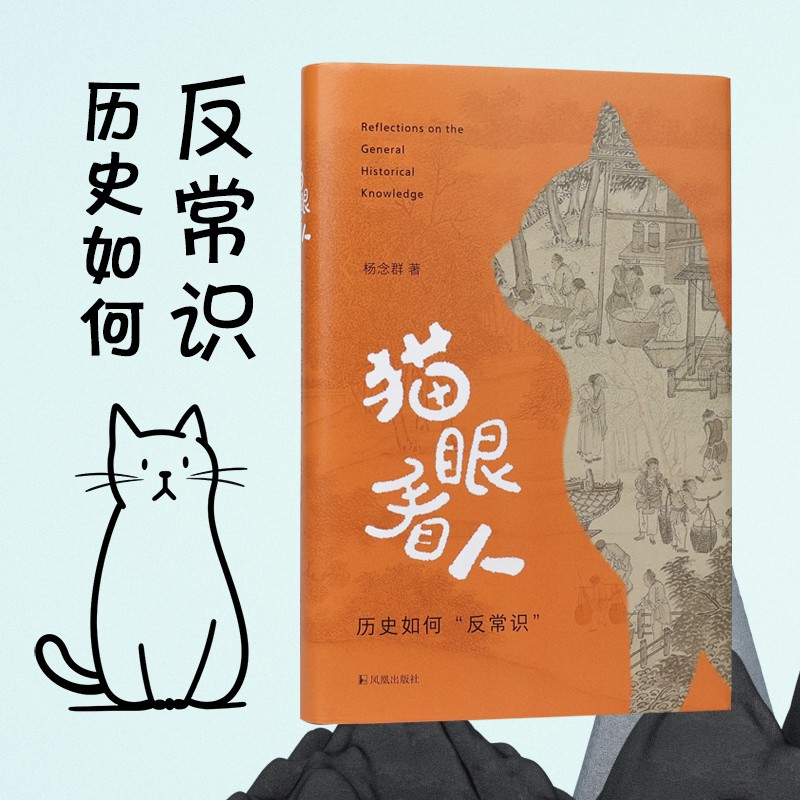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 生》《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等。
我觉得我们常常不知不觉陷入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常识之中。这些历史常识本身应当是被怀疑的,却一直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谈“反常识”,不是说要事事都拧着干,非要彻底把一切 “常识”打趴下不可——事实上也做不到。我们只是想在各类“常识”的巨无霸叙事之笼罩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更为合理的历史观作为补充。也就是说,对已构成我们生活常识的那部分历史观提出商榷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一些鲜灵的思想。事实上,“反常识”的历史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会变成一种僵化的 “常识”,受到批判和摒弃,这正是我所期许的。历史学之所以丰富和有趣,正在于它可以在相互替代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在人文科学领域里,任何有益的观点都应该并行不悖,不存在最终的权威。(前言) 大多数能臣循吏,都是在上任后经过多年摸爬滚打的历练,才提升了自己的治世能力。当年科举的训导只是为获取一种入官资格,与治世的阅历经验和见解并无直接关联。更夸张点说,从科举生产线中脱颖而出的官员,其成就大小恰恰可能与科举训练的程度成反比。同样是科班出身,流品却有高下之别。陈宏谋有一句话说得贴切: “自古流品,诚不足以限人也……有志者,正可乘时自奋矣。”流品的高低实在于能否真正冲破应试规定的束缚,给自己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明清为官功绩的大小确也证明,谁对应试八股规定的阅读范围超越得越彻底,谁就越有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创造一个新世界,这就是 “流品不足以限人”这句话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呆子治国论”错在哪儿?》) 绅士不愿待在城里,老往乡镇跑,意味着城市的人群向下流动,不断给底层社会注入活力,这是科举制的功劳。这些人生活太闲适了难免招人妒忌,近代革命的一个目标就是造这帮人的反,最后结果是绅士滚出了乡村。……绅士滚到了城里,尽管他们西装革履,成为疑似的“小资”,却使乡间失去了作为文化源头的活水,一路萧索下去,自然变成了文化空巢。小镇风情的记忆犹如老照片里模糊的影像资料,中产阶级的覆灭也就随着革命的进程开始了。这段故事的发生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促成中产阶级诞生的历史演变过程恰好相反。(《中国有中产阶级吗?》) 衡量忠奸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能否死心塌地效忠当家皇帝。所以拼死抵抗的史可法被捧上天,开门纳降又密谋反清的钱谦益则被看作首鼠两端而列入历史的污名册。可见,在乾隆爷的脑子里也有一个两极的人性光谱,那就是忠和不忠。臣子们脑袋上都贴了标签,分处两极,各自站队,泾渭分明。可是如果我们也把这枚金箍当成桂冠,洋洋得意地戴在自己头上,或者自作多情,拿着这顶帽子四处找人,强行试用,则大可不必。在我看来,大街上还是少点戴这类帽子的人,日常生活才显得正常、多样和有趣。(《人性光谱的灰色地带》) 一部中国近世史,也是一段家族撕裂的悲怆历史,同时也是 “老人权威”崩解的历史。家族以祖先为中心搭设生活舞台,努力依靠旧秩序维系和谐与平衡的时代已经结束。叶崇质作为家长虽已弃官从商,仍始终保持着每天到老太太房中请安的习惯;到了叶笃庄辈则个个奔走无常、风流云散,礼仪的持守即便在形式上也已消失殆尽。个体选择的多样性确是以摧毁庞大家族的延续为代价的,个中滋味真是一言难尽。(《“叶”的隐喻》) 按立宪派的设计,在皇帝这顶大帽子底下正好能开开小差,完全可以拿皇帝当幌子,名正言顺地干出惊世骇俗的大事,既可以促民主,也可以搞宪政,最后把皇帝架空就是了。这个“君主立宪”的顶层设计现在看来并非不切实际,说明立宪派比革命党对大清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大清立国,满洲皇帝不是如以往那样只是汉人的主子,大清的特色是以异族身份总揽寰宇、一统疆域,皇位起的是多民族黏合剂的作用,这与仅由汉人当皇帝的王朝明显不同。(《皇帝的影子有多长?》) 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多重思想资源同时起着作用,如最初流行的是会党反清复明的旧说,复兴明朝的欲念一旦与近代民族主义接榫,就成了直接助燃反满烈焰的催化剂。明末江南屠杀与文字狱记忆通过现代媒介转输,为科举制崩毁后的新式学生提供了反叛的精神资源。晚清的“发妖风”现象也随之被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终于把革命风潮推向了不可逆转的激进境地。(《“创伤记忆”唤醒辛亥浪潮》) 在我看来,国民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洋人揶揄挖苦国人的陈旧习气,难道从来都是编造谎言的无聊举动吗? 如果我们把外来的警告统统揣摩成是对中国的不怀好意,那么我们离阿Q遍地复活的日子也就不远了。道理并不复杂:有些习惯是在文明的新标准下渐渐滋养而成的,也许这个文明的标准是由西方制定,再向全世界推广,但它在不同人群承认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不能因为它是洋货就随手贴上 “殖民主义”的标签——不但要声讨,还得冲过去踹上几脚才算过瘾。如果我们还是像过去那样习惯二元思维,不是献媚西方就是把西人的批判视作帝国主义的阴谋,那么,要想令人尊敬地在现代文明中前行实在是步履维艰。(《国民性是如何炼成的?》) 拨弄 “琴声”、搞文化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建设过程,聚拢人心靠的是高超的分寸感,靠的是对当地习俗与文化的真正理解与尊重,并非一味灌输即能起效,否则定会造成水土不服。不能以为 “琴声”悠扬,就一定能让所有人都竖起耳朵、面露欣喜地倾听;若是强加于人,即使听者脸上勉强挤出陶醉的表情,看上去也会让人直起鸡皮疙瘩。(《“琴声”的滥用》) 以“反常识”的历史观关怀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