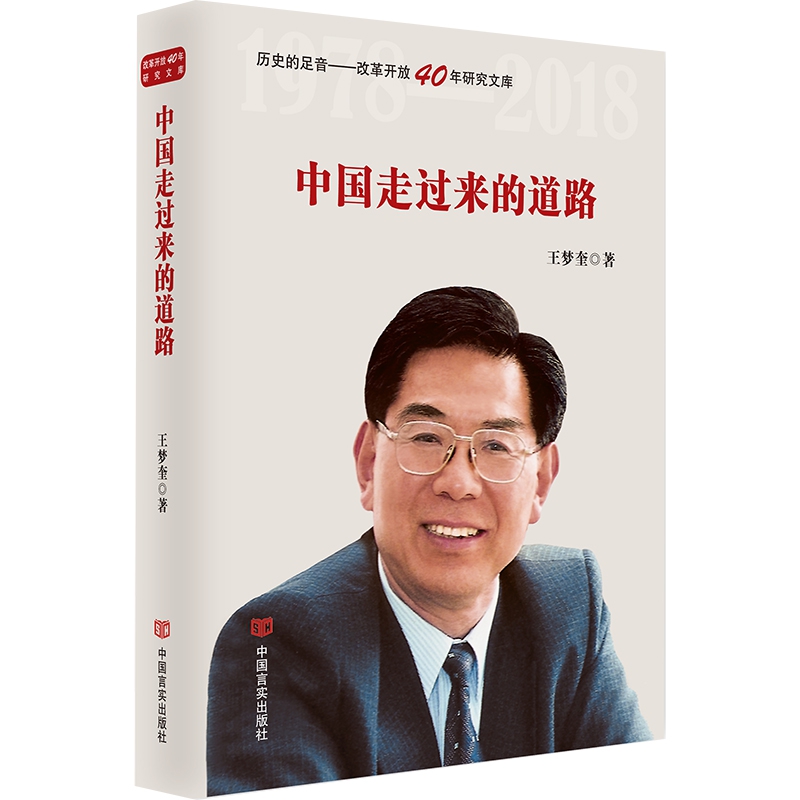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言实
原售价: 268.00
折扣价: 168.90
折扣购买: 中国走过来的道路(精)/历史的足音改革开放40年研究文库
ISBN: 9787517129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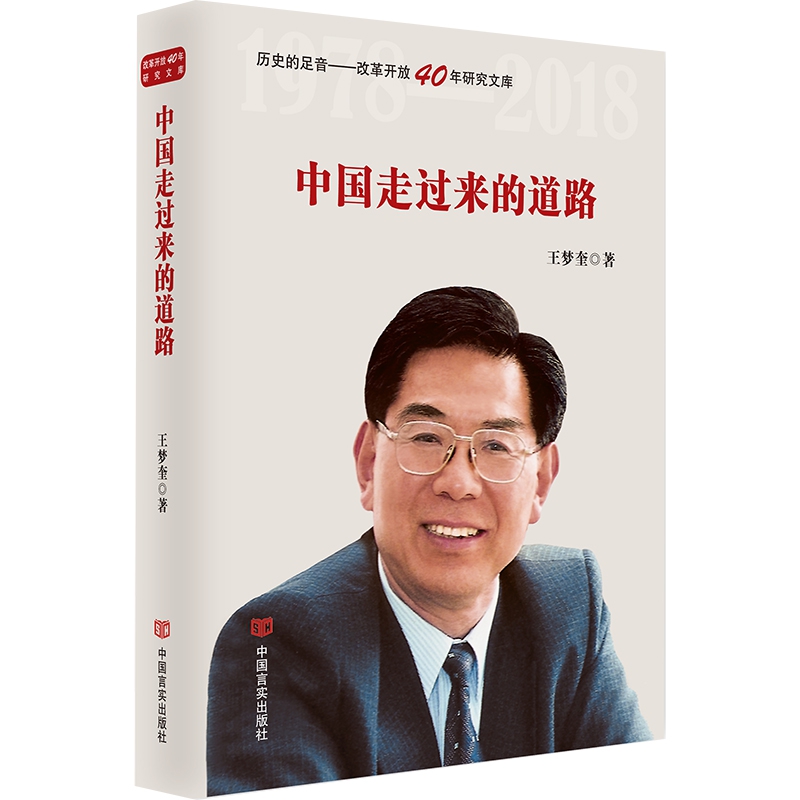
王梦奎(1938—),河南温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供职于《红旗》杂志和第yi 机械工业部。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国家计委委员和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参加过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主持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许多重要课题的研究。多年主持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等国际交流活动。出版有《王梦奎文集》(8 卷)以及经济学和其他方面的著作多部。编有《怎样写文章》等图书多种。
论工业生产专业化协作 (1979 年 10 月) 一 分工是劳动社会化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的 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 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b 生产专业化是社会分工的 一种形式,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越发展,社会分工 越深化,生产专业化程度也就越高。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最初的社会分工到现代的生产专业化,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社会分工有很大的局 限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交换处于微弱状态, 严格来说,这时还不存在生产专业化。工业生产专业化是近代机器大 工业的产物。机器大工业使社会分工获得了无比广阔的发展,使特殊 的生产部门和独立的生产领域的数量空前迅速地增加,生产专业化随 之日益发展起来。 马克思在谈到分工时指出:“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作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 和亚种,叫作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作个别的分工。” 马克思又把“一般的分工”和“特殊的分工”称之为“社会内部的分 工”;把“个别的分工”称之为“企业内部的分工”。我们通常所说的 工业生产专业化,就是指“特殊的分工”,即工业部门与部门之间、企 业与企业之间所进行的分工。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企业内部的 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某个工序就可以独立化为一个企业,甚至发展 成为独立的工业部门。比如一个工厂的铸造车间发展为专业铸造厂, 许多专业铸造厂组成独立的铸造行业,“个别的分工”就转化成了“社 会内部的分工”。 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过程,也就是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从社会分 工的角度来看,实质上就是把产品的各种加工过程彼此分离开来, 划分并独立化为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和企业的过程。列宁揭示了这 种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趋势,指出,社会分工“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 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 — 不 仅把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制成真正消费品的各个操作都变成专 门的工业部门。” 生产专业化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列宁说:“技 术进步必然引起生产的各部分的专业化、社会化。” 一方面,现代科 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劳动工具、新的加工工艺和新的原材料 不断地涌现出来,产品日益多样化,这必然伴随着原有工业部门的日 益分解和新兴工业部门的不断产生;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结构极其复杂的工业品的生产,只有在专业化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专业化生产也要求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如果说,结构简单的木帆船和 独轮车可以在一个手工作坊里完成生产全过程的话,那么,由上万个 零件组成的汽车,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零件组成的巨轮,在一个企业里完成生产全过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必须进行合理的社会分工, 组织专业化生产,每个企业只生产极其复杂的产品的某些部分,或只 完成某个工艺过程。 社会生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愈益发展的分工把社会生产分解 成各个独立的专业化生产部门和企业;协作则把这些专业化生产部 门和企业联结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生产体系。专业化和协作是相辅相 成的,是以同样的深度和广度相伴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专业化 生产是协作的基础,没有专业化就无所谓协作;协作是专业化生产 的条件,没有协作就不可能进行专业化生产。社会生产力越发展, 科学技术越进步,社会分工越细致,生产专业化程度越高,协作的 范围也就越广泛。 近代工业史表明,生产专业化协作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 发展过程。试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例。机械制造工业是近代工业的典型 代表,在历史上,产业革命就是由各种纺纱机、机器织布机和一系列 其他机械设备的发明而引起的。机械产品一般是由许多零部件组装而 成,具有可分性,不少零部件可以通用互换,在制造上又有大体相同 的工艺过程。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纯机械性质的行业同那些要经 历某种化学和物理过程的行业相比,生产结果比较容易得到保证,劳 动的中断也比较容易做到。 所有这些,使得机械产品的专业化协作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比较便利的条件。但是,在近代工业发展的初 期,并没有独立的机械制造工业部门。它从一般的加工工业中独立出 来形成专业化生产部门的初期,是在一个机器制造厂里生产各种机器, 这可以称之为部类专业化。尔后发展为种类专业化,即一个机器制造 厂只生产一定种类的机器,如机床厂生产各种机床,纺织机器厂生产 各种纺织机器,等等。再后发展为产品专业化,即由于生产规模的扩 大,种类专业化工厂不断分化,一个工厂只生产一定品种的产品,如 生产机床的工厂,有的生产车床,有的生产铣床,有的生产磨床,等 等。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发达的国家很快就由产品专业化发展到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 这时,一台机器不再是由毛坯、零部件加工到总装都由一个工厂来完 成,而是由若干工厂协作,有的生产一部分零部件,有的专门承担一 部分工艺过程,如铸造、锻压、热处理等等,都变成了专业生产厂。 不仅生产过程愈益专业化,技术后方也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如工具、 模具专业化,设备维修专业化等等。不同的专业化协作的形式,标志 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今,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机 械工业专业化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全能厂已经成为历史。以美国为例, 机械工业专业化程度达 90% 左右,其中汽车工业为 96%,农机工业为 92%,机床工业为 85%。 某些产品专业化协作的范围已经超出国界, 在若干国家间进行。列宁说:“专业化,按其实质来说,正像技术的发 展一样没有止境。” 可以预料,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专业化协作还会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建设了一 批“大而全”的“全能厂”,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难免的。当时工 厂很少,差不多是在“空地上”建设第一批大企业,广泛实行专业化 协作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当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应当而且 能够组织专业化协作的时候,没有及时实行这种转变,而是继续搞了 一些“大而全”和更多的“小而全”的“全能厂”。虽然也搞了一些零 部件和工艺专业化生产,但为数不多,整个说来,目前基本上还是处 于产品专业化的阶段。据对 1976 年的统计,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县以 上全民所有制企业 6100 多个,其中主机厂 1400 多个,有 1100 多个是 “全能厂”;4000 多个辅机、配套和配件厂,大多数也是“中而全”或 “小而全”。总的来说,“全能厂”大约占 80% 左右。一个工厂,一般 都生产着一种产品的绝大部分零部件,具有铸、锻、金加工、热处理 等基本工艺。这种“全能厂”,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组织形式。我国汽车和拖拉机制造工业,工厂数量、职工人数和机器设备 不算少,但产量低,质量差,成本高,型号杂,发展速度缓慢,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按专业化协作原则组织生产,吃了“大而全”和 “小而全”的亏。 专业化协作的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从世界范围来说,工 业生产专业化已经有了长久的历史。我国也早在 1964 年就提出了按专 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的问题。但是,改组伊始,就遇到了“文化大 革命”为时十年之久的破坏,致使这项工作被迫中止。加之闭关自守、 自给自足思想的泛滥,正常的协作关系被打乱,使得“全能厂”不仅 没有减少,反而更增多了,有些专业化厂也倒退为“全能厂”。“文化 大革命”中把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批判为“复辟倒退”和“资 本主义托拉斯”。其实,专业化协作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先进的组 织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大生产 为其物质基础的。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可以用有计划的分工代替资本 主义自发形成的分工,专业化协作应该而且也有可能比资本主义搞得 更好。如果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 家取得了胜利,那么,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向资 本主义学习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其中包括搞专业化协作的经验。 列宁说得好:“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 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 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 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 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么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 今天, 当我们重新提出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的时候,认真学习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专业化协作的理论,认真总结我们自己正反两 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和借鉴工业发达国家搞专业化协作的正反两个方 面的经验,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中国走过来的道路》作者系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同志。王梦奎同志曾先后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高层政策研究部门工作,参与或主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研究,以及重要文件的起草,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这种经历,为作者提供了独特的观察问题的立足点和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