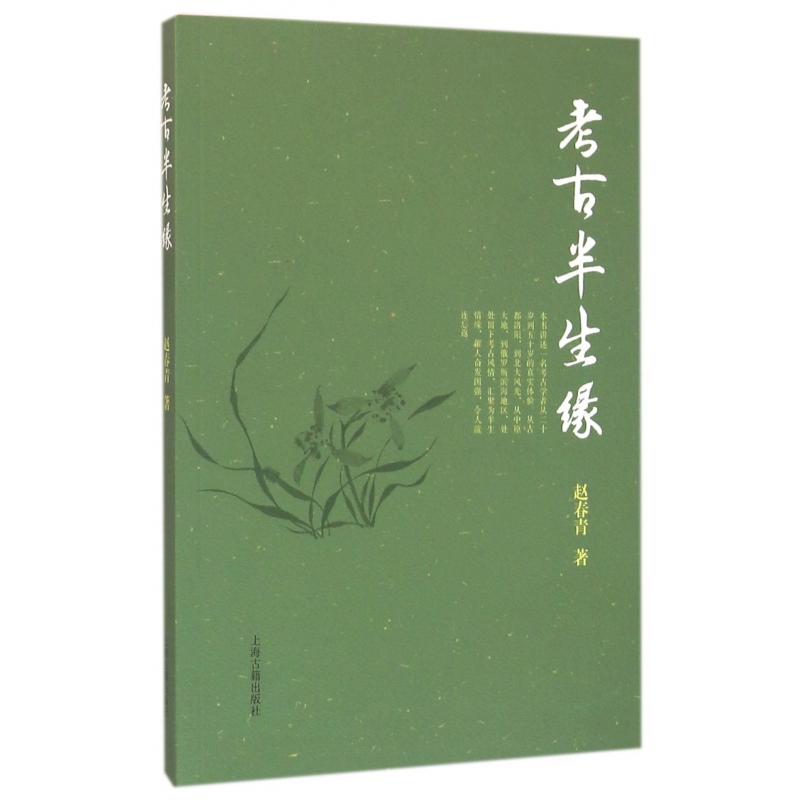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古籍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3.30
折扣购买: 考古半生缘
ISBN: 9787532579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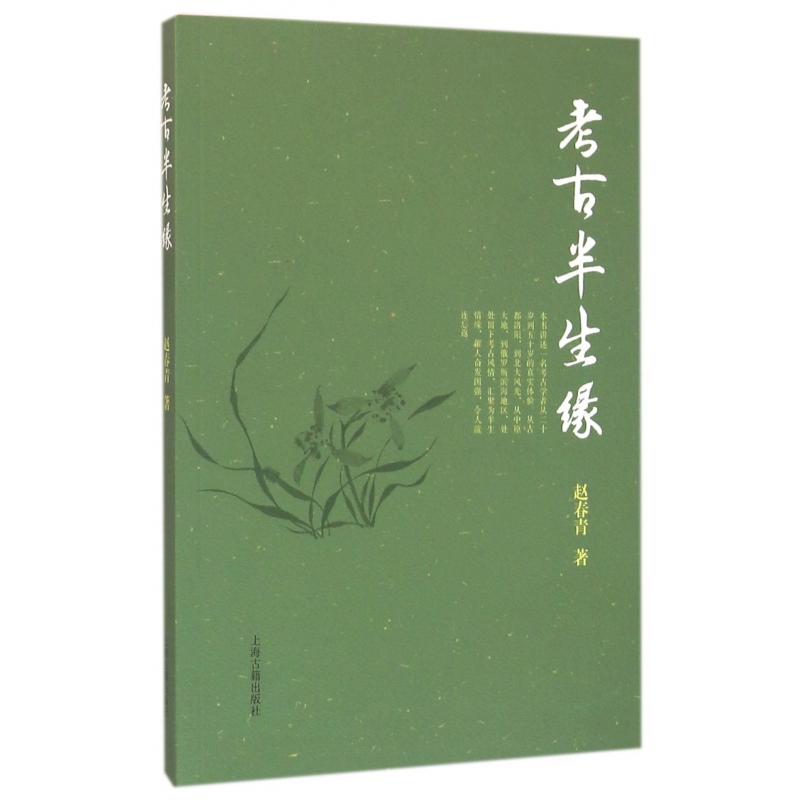
赵青春,19**年生,河南驻马店人,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夏商周考古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史前考古与民族考古学。
我的“豆*块” 1984年秋,我刚满20岁,已经大学毕业了。回忆 大学四年,没有穿过一双皮鞋,没有乱花过一分钱, 也没有慢待过任何**。整天价乐呵呵、笑嘻嘻地面 对每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现在,四年的大学生活匆 匆结束,我带着满满期待来到新的工作岗位——洛阳 市文物工作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我随年轻的技工一起投入到工作当中。我的** 个配合基建的考古工地是洛阳市钢管厂建筑工地,发 掘对象是汉代的几座墓葬。我跟随技工师傅,学会了 考古绘图,学会了怎样处理遗迹现象。但是,这只是 我在漫长的考古道路上迈开的**步,我今后必须学 会如何把这些气力活转变为“笔墨官司”,即转变为 文字。于是,我想,必须尽快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文 章。 机会来了。我在洛阳关林工地上挖到一座保存较 好的唐代墓葬。重要的是,墓葬中出土了威风凛凛的 唐三彩马,它们好像是故意躲藏了许多年的朋友们, 终于赶来见面似的,集中出土。于是,我向《洛阳* 报》写下通讯一则,发布手中的重要发现。 这是我的**作,虽然只有区区几十个字,刊登 在报纸不甚显眼的位置,介绍的仅仅是我的工作内容 ,但这毕竟是我**份见诸报端的文字稿。自此以后 ,我的名字将会不断出现在报刊上,而这一切以此为 始点。 以前,我念初中时,曾经编写过一本短篇小说集 ,当时恭恭敬敬地抄写在作业本上,取名为某某小说 集。可是,我始终没有拿出去公开发表,心想直到修 改工作完成以后再正式投送出去不迟。后来,几经折 腾,本子*终不明去向,十几篇短篇小说,*终化为 乌有。伴随着青年人对文艺的满腔热情,我慢慢地长 大了。**,我终于从实际工作中,生发出对考古的 热爱。我一边辛苦地工作,一边勤奋地写作。这篇“ 豆*块”,将会是我公开发表文章的开端。 我做了一连串的美梦。我又被一连串的美梦鼓舞 着。我先后为《洛阳*报》写出一篇又一篇“豆*块 ”,报告我的重要考古发现。这些也奠定了我写作的 基础。不知道的人们,还以为我是一位年长的老同志 呢,实际上,我只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时不时 地报导我所主持的考古工地的零星发现而已。至于对 未来*多的设想,我每*都在憧憬着,盼望着,并且 相信这样的好*子一定会到来,只是需要我张开双臂 ,迎接他的出现。 这种的机遇很快就来到了我的面前。我不禁感叹 :这样的好*子来得太快了。我感到太阳每天都是新 的,机遇每天都在向我招手,我没有理由不拥抱她! 蹒跚学步 我干考古属于那种“先结婚、后谈恋爱”的类型 ,考古不是我的初恋,我的初恋对象是法律。就像许 多电视剧套路那样,初恋注定失败,而婚姻不浪漫, 却来得实在,经得起风吹浪打。 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想转行干法律,我甚至给 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写过一封信,表示我想 报考他的民法专业研究生。大名鼎鼎的江教授居然给 我回信,说愿意收我为徒。我将法律专业书背得滚瓜 烂熟,自信肯定能如愿以偿,考上法律专业研究生。 拜拜吧您,味同嚼蜡的考古学。 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论是学校领导还是 单位领导,还没有**地做到思想解放,只要我一向 他们提起考法律系的研究生,一律遭到拒*。像跟事 先约好一样,他们一律劝我巩固专业思想,一律开导 我要干一行爱一行,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于是,万 般无奈之下,我不得不从事一点也不喜欢的考古专业 ,与挚爱的法律专业渐行渐远。 如今,30个年头过去了,如果说自己在考古圈里 好歹也混出点名堂的话,回头看看,在洛阳的*初几 年,是我从事考古事业蹒跚学步的阶段。此事,一方 面得益于田野考古,另一方面,应当感谢鼓励我搞学 术研究的地方学者蔡运章先生和余扶危先生等。 记得我在洛阳写的**篇稿子,是在《洛阳*报 》上刊登的一个“豆*块”,报导了我亲手发掘出来 的一座随葬有唐三彩的唐代墓葬。稿件标题就是:“ 三彩马威风凛凛,隋唐墓重见天*”。稿件很快就被 《洛阳*报》副刊刊登出来了。面对着散发出油墨香 的“豆*块”,我喜不自禁,**次对考古学有了感 觉。 除了田野考古,时任队长的余扶危先生,热心地 把我往新成立的洛阳钱币学会拉。那时,洛阳钱币界 有一位老干部,**热心组织学会活动。他本人是钱 币学的外行,但对钱币学一往情深,他对像我这样初 出茅庐的年轻小伙,也给予了充分的热情和鼓励。之 后,我在蔡运章先生的鼓励下,选择汉代五铢钱作为 研习对象,写了一篇关于五铢钱废止年代的论文,发 表在《洛阳钱币》创刊号上,这是我的**篇考古论 文,是考古学研究的**作。论文,原来可以这样写 呀!我可以写考古学论文了。这次经历让我对考古学 *加亲近了几分,尝到了做考古研究的甜头。在接下 来不久,我先后写了关于北魏和晋代墓葬的发掘简报 ,并依据这些新材料,*成《洛阳北魏墓略说》,大 胆投给了《中国文物报》。不想,竟也发表了。此外 ,我把北魏墓中出土的墓志单独提出来,就墓志上的 汉字书法艺术进行一番研习,习作被《中国书法》接 纳,稿子也变成了铅字。就这样,一篇篇考古学稿件 ,接二连三地被刊登、发表,一时间我成了考古学的 希望之星。这突如其来而又轻而易举地成功,使我对 考古学渐渐地不再厌恶,甚至产生几多喜欢的情绪来 ,考古成为我明媒正娶的“发妻”了。 想到这些,如果当初没有遇到余扶危、蔡运章等 先生,没有他们的积极引导,我说不定还会心猿意马 ,还会对法律学割舍不断,搞不好还会变成考古学界 的“剩男剩女”呢。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