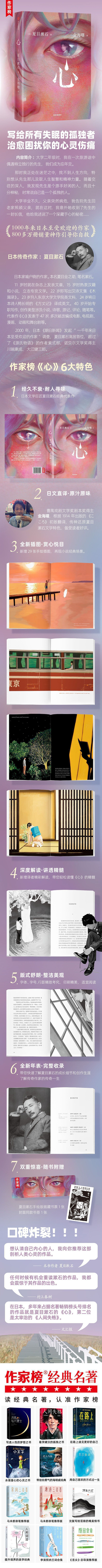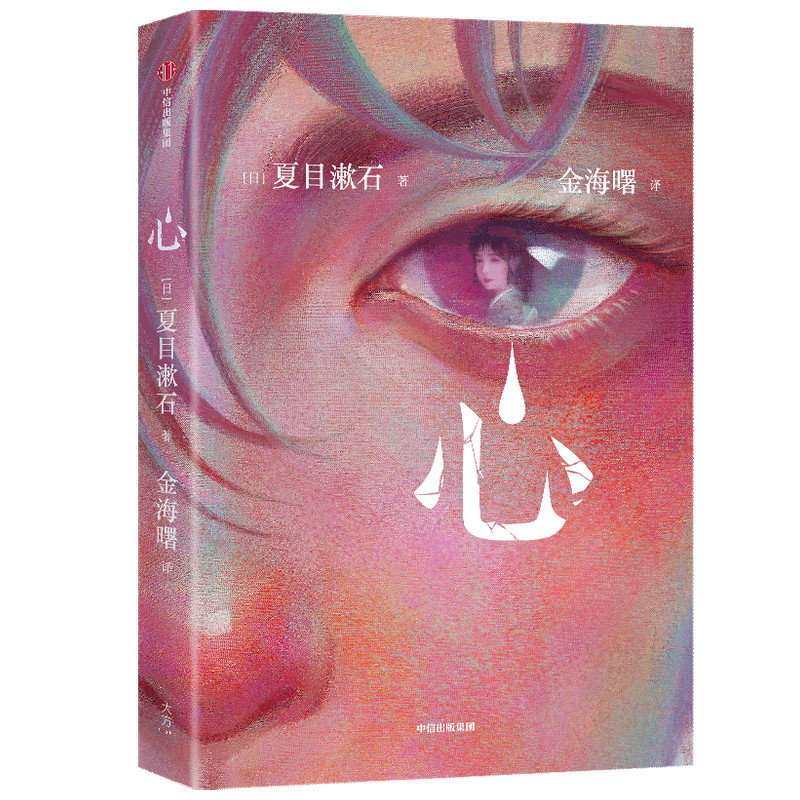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8.80
折扣购买: 心
ISBN: 9787521727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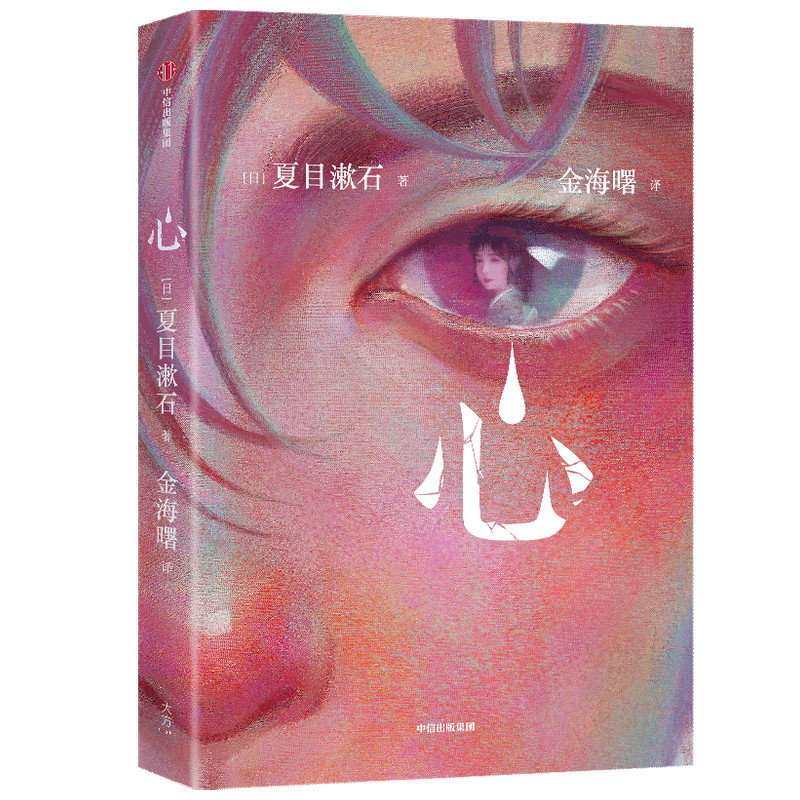
\\\\\\\"日本家喻户晓的作家。本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 出生于江户的牛込马场下横町(现为东京都新宿区的喜久井町),水瓶座人。 父亲是个小吏,生了八个孩子。夏目漱石最小,自幼被送给一个叫盐原昌之助的做养子。8岁时,夏目漱石随养母搬回自己亲生父母家住,后来一度与养母单独生活。 11岁时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15岁时热衷汉籍和小说,立志专攻文学。夏目漱石的亲生父亲和几个哥哥都与他关系平平,并对他的文学志向有鄙夷之意,而亲生母亲在他14岁那年便因病去世。直到21岁,夏目漱石才回归原籍,恢复了夏目的姓氏。 22岁即写出汉诗文集《木屑录》。23岁升入东京大学文学院英文科,24岁将日本诗人鸭长明的《方丈记》译成英文。33岁时被选为公派留学生赴伦敦,35岁回国后任第一高中讲师、东京大学英文科讲师,执教的同时笔耕不辍,常为杂志撰文。 40岁开始专职写作,创作类型涉及小说、诗歌、游记、评论、随笔等。代表作《心》发表于47岁,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漫画、动画和舞台剧等。 49岁的夏目漱石因病逝世,死后他的大脑和胃捐给了东京帝大医学部,大脑迄今仍保存在东京大学。 2000年,日本《朝日新闻》发起“一千年来日本至受欢迎的作家”调查,夏目漱石高居首位;超过了《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 \\\\\\\"
\\\\\\\"先生和我 一 我总是叫他先生。所以这里我也只称他为先生,真实姓名不予公开。与其说这是怕惹人物议,不如说这样对我更为自然。每当我想起他,“先生”二字就几欲脱口而出,拿起笔时心情也同样如此。我特别不愿用冷漠疏离的首字母缩写来指代他。 我和先生相识于镰仓,当时我还是个年轻学生。暑假去海水浴的朋友发来了张明信片,要我也一定过去玩,我就筹了点钱出门。我筹钱花了两三天,可到镰仓还没三天,叫我过去的朋友却突然接到家里电报,命他速归。电报说他母亲病了,朋友却并不相信。家乡的父母一直逼着他结婚,而他觉得如今社会这岁数结婚未免太年轻了,更重要的是他没看上那姑娘。他本该暑假回家,却故意逃避来东京周边游玩。朋友给我看电报商量怎么办,我也不知该怎么办。他母亲要真是病了,那他肯定是应该回去。他终于还是回去了,好不容易来到这儿的我,却被孤零零地留了下来。 离开学还有些日子,我的情况是或留或回皆可,暂时决定还是先留在这儿的民宿里。我那位朋友是中国有钱人家的儿子,经济上很宽裕。可他毕竟还在上学,又还年轻,生活消费和我也相差无几。我虽是一人留下,却也没必要再费功夫去另找合适的住处。 我住的地方就算在镰仓也是够偏僻的。台球、冰激凌之类的时髦货,必须翻过一条长长的田埂才能够得着,坐车过去要收两角钱。不过这一带也建了些私人别墅,而且离海非常近,占据了海水浴极为有利的位置。 我每天去海边,穿过烟熏火燎、屋顶铺着稻草的老房子下到海滩。没想到这儿竟住着这么多城里人,来避暑的男男女女在沙滩上活动。有时就像大海上的澡堂,人头凌乱地堆在一起。被围裹在这片喧闹的景色里,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就这样躺在沙滩上看着,或者在海水里跳来跳去,让海浪拍打膝头,我觉得很愉快。 正是在这喧嚣嘈杂之处我邂逅了先生。那时海边有两家茶铺,很偶然我习惯于去其中一家。和长谷那边造起大别墅的人不同,来这儿避暑的游客并没有各自专用的更衣室,必须利用这种公共场所换衣服。他们在这儿喝茶、歇息,还在这儿清洗泳衣,冲洗他们带盐分的身体,也有把帽子和伞寄存在这儿的。我虽然没有泳衣也担心随身之物被人偷走,每次下海前都脱光,把所有东西撂在这家茶铺里。 二 我在茶铺见到先生时,他正脱了衣服准备下海,相反我从海里上来,海风吹着湿漉漉的身子。两人之间人头攒动遮挡住了视线,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也许就和先生错过了。虽然海边很混乱,我又有点漫不经心,但我仍然一眼就注意到了先生,因为他当时正陪着一个外国人。 刚要走进茶铺,那外国人白得过分的肤色立刻吸引住了我目光。他穿着传统日本浴衣,脱下后随手搁在长凳上,环抱胳膊面向大海站着。这外国人只穿着条跟我们一样的猴兜裤衩,其余一丝不挂,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两天前我去了由井滨,海滩上到处是外国人。我蹲在略略隆起的沙丘上,在那儿我看了很久,旁边就是旅馆后门。很多外国男人洗完海水浴上来,并没一个露出腰身、胳膊和大腿的,外国女人更是把肉体都遮盖住。他们中大多戴着橡胶头套,海面上漂浮着一片虾红、绛褐和青蓝色。我刚见识过那番景象,再看这个只穿着一条猴兜就站在众人面前的老外,就觉得很新鲜。 他回头看自己身边的日本人,说了一两句什么。这日本人当时正弯腰捡拾落在沙上的毛巾,那一刻正是将捡未捡之际。他捡起毛巾后马上包住了头向大海走去,这人就是先生了。 纯粹出于好奇,我目送着两人的背影肩并肩走向海滩。他们直接走进了大海,穿过远处浅滩上呜哩呜哩喧哗的人群,到了比较开阔的地方,两人一起纵身向前游去。向着远处海岬,两人的头越来越小,然后又翻身折回,笔直向岸边游来。两人回到茶铺,也不用井水冲洗,马上擦干身体穿上衣服,快速向什么地方去了。 他们走后我还坐在长凳上抽烟。我有点走神,心里想着先生的事,总觉得在哪见过这张脸。可怎么也想不起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这人了。 那段日子里我与其说无忧无虑,不如说苦于无聊久矣。第二天,算好能和先生相遇的时间,特意去了茶铺。这次那个外国人没来,先生一个人戴着草帽来了。他摘下眼镜放在柜台上,用毛巾包好头,匆匆忙忙向海边走。像昨天一样,他穿过喧哗的游客,独自向远方游去。我立即起身一头扎进水里,抄近道向先生追了上去,浪花在额头飞溅,直到海水相当深的地方。先生跟昨天不同,他拉了条弧线,从我意想不到的方向返回岸边。目标落空了,我甩着手上的水上了岸。刚一跨进茶铺,先生已然穿戴齐整,同我擦肩而过,出门走了。 三 第三天同一时间我来海边看见了先生,第四天同样情况又发生了一遍。但我一直都没找到跟他搭讪的机会,两人间连打个招呼之类的事也没发生。先生的性格显然是非社交性的,在规定时间超然而来,又在规定时间超然离去。无论周围怎样热闹,他似乎都从未稍加留意。最初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外国人之后再没见过,先生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先生有次和往常一样从海里快速上来,拿起了放在老地方的浴衣正要穿上。不知怎么回事浴衣上沾了不少沙子,他拿着浴衣向后抖了两三下。这一来放在浴衣下的眼镜就从板缝间掉了下去。先生系好白底碎花浴衣上的宽幅腰带后,这才发现他眼镜掉了,急忙上下摸索着寻找起来。我把头钻进长凳下,伸手捡起了眼镜。先生说了声谢谢,就从我手里接了过去。 次日我跟着先生跃入海中,向先生同样的方向向前游去。游出二百米左右,先生回头跟我说话了。漂浮在广阔、苍茫的海面上,附近除了我俩外并无他人。目光所及,透彻的阳光照耀着山山水水,我的肌肉里涌动着自由和欢喜,情不自禁在大海中雀跃。先生突然停止了划动,仰身躺在了波浪上。我也学着他的样子翻过身来,天空之光强烈地投射在我脸上。“太愉快了!”我大声叫喊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先生换了个姿势,好像要在海里站起来。“还不回去吗?”他问我。我体质还算强壮,原来还想再游会儿。可先生这么一问,我应声而答:“哎,回去吧。”我们原路游回了岸边。 从此我跟先生有了交往,可我依然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此后又过两天,记得刚好是第三天下午。在茶馆同先生相遇时,先生突然转向我:“你还打算在这待很久吗?”我没想过这事,有些猝不及防,就顺口答道:“我也说不上。”看着先生微微笑容,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情不自禁反问道:“先生呢?”这是从我嘴里第一次说出“先生”这个词。 那天晚上我去了先生的住处。和普通客栈不同,它像是坐落在宽阔寺院里的一幢别墅,我也搞清楚了住这儿的其他人并非先生家眷。见我称他先生,先生不禁苦笑,我辩解说这是我称呼长辈的习惯。我问起前些天的那个外国人,先生说那人有点特立独行,已经不在镰仓了。先生说了外国人的各种事,最后感慨说他连日本人也不大交往,居然和这样一个外国人成了朋友,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我最后问先生,似乎在哪儿见过他,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先生也许会有一样的感觉吧,当时年轻的我心里暗暗期待着先生的回答。先生沉吟片刻说:“怎么也想不起来见过呀,认错人了吧。”我心里不由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失落。 四 我月底回东京,比先生离开避暑地要早得多。同先生分手时我问他:“以后可以常到府上拜访吗?”先生只是简单地应了句:“行,来吧。”我很想同先生交往,期待先生能说点贴心话,这样敷衍的应对稍稍挫伤了我的自信心。 令我失望的情况屡屡发生,先生似乎也感觉到了,但他根本不予理会。我反复感受着轻微的失望,却从未因此产生过不再交往的念头。每当我为不安所动摇,反而想着要更进一步地深入他。如果再向前走一步,我所期待的也许总有一天会圆满呈现在眼前吧。我很年轻,可我年轻的血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会这样温顺地涌动。为何仅仅对先生产生了这样的心情?我也说不清楚。直到先生已过世了的今天,我才明白先生从开始起就没有不喜欢我。他常常看似不经意的寒暄和冷淡举止,并非是想要回避我而表现出的不快。那只是内心凄凉的先生对想要接近自己的人发出的一个警告,表示自己并无亲近的价值。不愿响应他人眷恋的先生,似乎在他人看轻他之前,已先行将自己置身于低处。 当然要去拜访先生—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回到了东京。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其间原本打算去拜访一次。可回来后过了两三天,在镰仓时的心情就渐渐淡漠了下来。大都会五光十色的氛围复活了我以往生活的记忆,伴随着它强有力的刺激,在我心上渲染出一片浓墨重彩。看着来来往往学生的脸,我感受到了新学年的紧张和渴望。有段时间里我把先生给忘了。 开学了。刚过了一个月,一种松弛感袭上心头。我在自己房间里脸色郁闷地走来走去,充斥着物欲的目光来回逡巡,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先生的脸。我又想见先生了。 第一次拜访先生,他不在家。第二次去,记得是接下来的星期天。那是个天空晴朗得沁人心脾的好日子,先生依然不在家。在镰仓时我曾听先生亲口说过他平时大多在家的,还说他讨厌外出。两次来两次扑空,我想起了他的这番话,顿时冒出一股无明之火。我没有马上离开,站在玄关前有些踌躇地看着女佣的脸。女佣还记得我上次递过名片,她让我稍等,然后回到了内。一会儿,换了个女主人模样的人走了出来,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主人。 女主人彬彬有礼地告诉了我先生的去向。先生在每月的这一天里,都有去杂司谷墓地为某个逝者祭扫的习惯。“刚出门,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她歉意地说。我向她点头致意,走出了先生家。在喧闹的大街上走了差不多一个街区,我忽然心生一念。何不也顺便散步到杂司谷去走一趟,说不定会邂逅先生呢?我随即掉转了脚步。 五 我从墓地前的苗圃左侧进去。宽敞的通道两边种植着枫树,我沿通道走向墓地深处。路边茶馆里忽然走出一个很像是先生的人,他的眼镜片反射着阳光。我凑到跟前冷不丁大叫了一声:“先生!”先生突然停下脚步,看到了我的脸。 “怎么……怎么回事?” 同样的话他重复了两遍,声音在光天化日的寂静中回荡着,显得相当怪异,我一时什么都说不上来。 “你跟在我后面来的吗?为什么……” 先生镇定了下来,声音也随之变得低沉,表情中闪过一道难以准确描述的阴影。 我向先生说了我是怎么来这里的。 “给谁来扫墓,我妻子说了那人名字吗?” “没有,其他什么都没说。” “是吗?—当然了,这些是不会说的。她第一次见你,也没必要说这些。” 先生终于安下心来,但我却完全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和我穿过墓地走向外面的马路。在伊莎贝拉什么什么之墓、神父拉金什么什么之墓的旁边,立着一座塔型墓碑,上书“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还有的刻着“全权公使某某”。在一座刻着“Andrea”字样的很小墓碑前,我问先生这该怎么念,先生苦笑着回答:“应该念作安德烈吧?” 对形形色色的墓碑款式我觉得滑稽和讽刺,先生似乎并不认同。我指点着那些圆形墓石和细长的花岗岩墓碑,不停地说长道短。起初他默默听着,最后终于开口说:“死这件事你还没认真想过吧。”我沉默了下来,先生也没再说什么。 墓地尽头矗立着一株遮天蔽日的巨大银杏。走到树下,先生抬头看着高高的树梢。“再过些时候这里会变得很漂亮。树上的叶子全都黄了,地面也会被金色落叶都埋起来。”先生每月一次,必定会在这棵树下走过。 对面一个男人平整着凹凸的地面,在开辟新的墓地,那人放下手中的铁锹,看向我们。我们左拐,出了墓园走到了马路上。 我此行并无目的,只是跟着先生的脚步往前走。先生的话比平时更少了,我并未因此感到不安,仍然跟在先生后面信步走着。 “你这就回家吗?” “哎,也没什么别的地方要去。” 我们默默地向南下了坡道。 我开口问道:“先生的父母葬在那儿吗?” “不。” “谁的墓——亲戚的吗?” “不。” 此外先生什么都没说,我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 又走了差不多一个街区,先生却忽然重提话头。 “是个朋友的墓。” “您每月都来给这朋友扫墓?” “是的。” 这天先生除此之外没说过别的话。 \\\\\\\" \"★ 畅销书《心》:写给所有失眠的孤独者!治愈困扰你的心灵伤痛! ★ 不容错过!1000年来日本至受欢迎的作家!800多万册销量神作引导你自救! ★ 日本文学巨匠夏目漱石经典代表作,作家榜经典文库版八大特色: ★ 日语直译,原汁原味:曹禺戏剧文学奖剧本奖得主金海曙,根据1914年岩波书店出版的《こころ》初版翻译,传神还原夏目漱石文学特色,一字未删完整典藏。 ★ 全新封面,颜值爆表:新锐设计师联合作家榜设计团队打造全新封面,典雅独特,值得收藏。 ★ 原创彩插,图文并茂:新增29张全新手绘插图,再现小说经典场景。全新视觉感受,丰富阅读。 ★ 深度解读,讲透精髓:新增译者精彩解读,带您轻轻松松读懂《心》的精髓。 ★ 作者年表,完整收录:带您快速了解夏目漱石的成长细节和创作生涯,了解传奇作家的传奇一生。 ★ 双重惊喜,免费赠送:随书附赠夏目漱石手绘版画藏书票1张。 ★ 版式疏朗,整洁美观:字体、字号、行距精致考究,印刷精美,适宜阅读,不费眼睛。 ★ 经久不衰,耐人寻味:2000年,日本《朝日新闻》发起“一千年来日本至受欢迎的作家”调查,夏目漱石高居首位;超过了《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 ★ “本书献给所有追寻自我内心的人,你们终将如愿以偿。”——《心》作者 夏目漱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