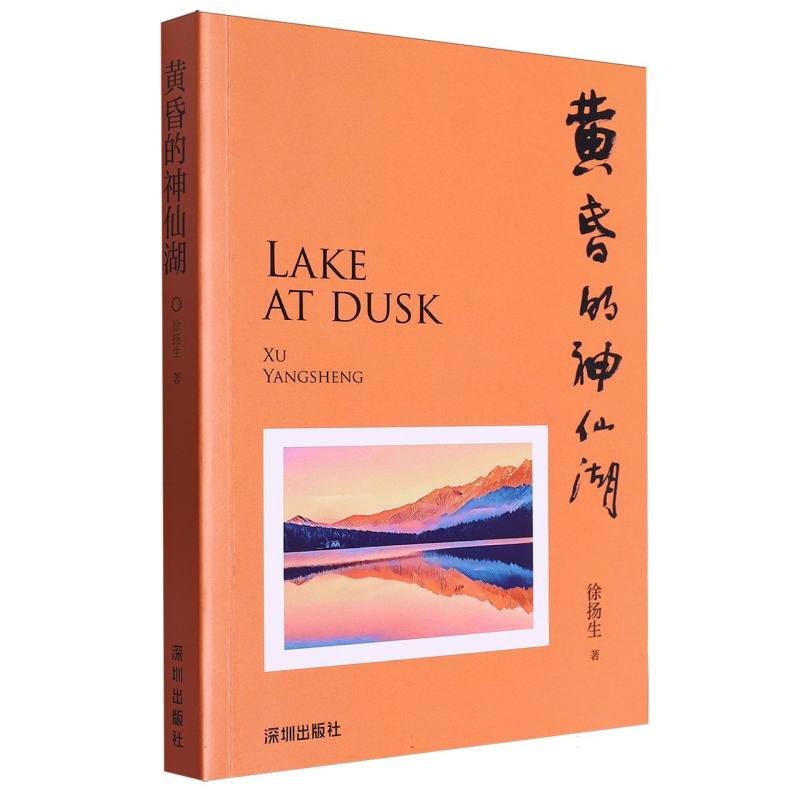
出版社: 深圳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4.30
折扣购买: 黄昏的神仙湖
ISBN: 9787550739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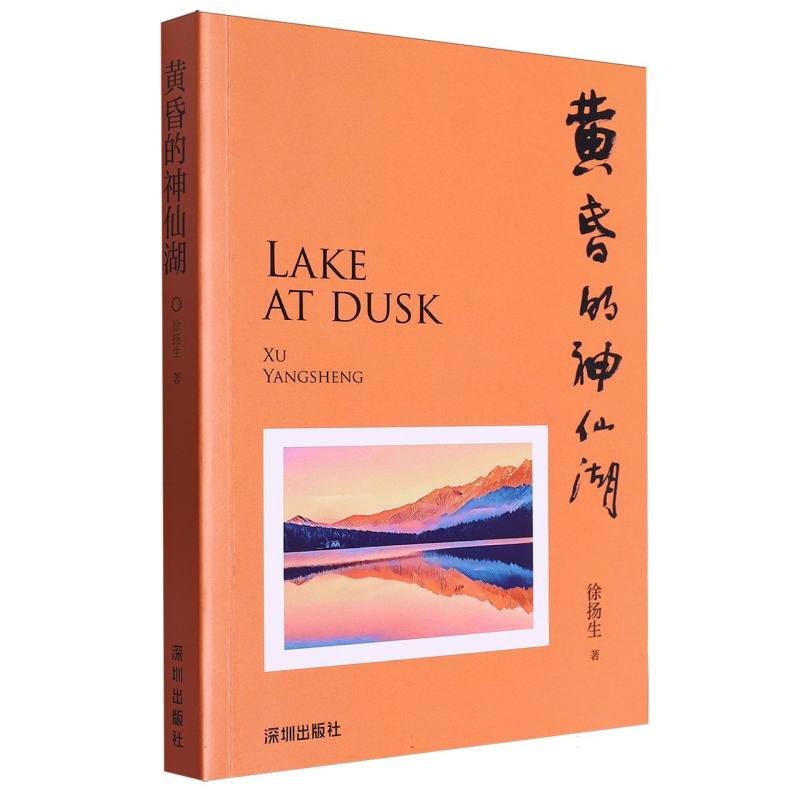
徐扬生 浙江绍兴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以及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为表彰徐扬生教授在科学与教育方面的贡献,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国际永久编号第 59425 号小行星 1999 GJ5 命名为——“徐扬生星”。
孟先生 有些人,曾经在我们的人生中,安静地出现过,陪我们走了一段路后,又安静地消失了。多少年后,每当我们回想起他们的时候,哪怕是在风雪交加的晚上,都会感到那种久违的宁静与温暖! 孟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孟先生是我下乡的那个村里的生产队会计,他和我是村里少数两个异姓人。这个村有百来户人家,以两个大姓为主,分居在小河的两岸。我不知道孟先生是从哪里来的,缘何落脚在这里,只知道他来得比我早得多。孟先生当时已有五十来岁,身子佝偻得厉害,总是穿着一身淡灰色的中式布衣,干干净净。有时候大家会调侃他,问他怎么总是穿得这样清爽(干净的意思),他总是说是老母亲给洗的。是的,他有个老母亲,但从未听说过他有妻子。至于他为何没有结婚,我没有打听过,大家对此都讳莫如深,可能是有点历史问题吧。看他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应该是个读书人出身,大家很少谈论他的过去,我也不去问。 孟先生面目清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有静气,平和理性。他是那种慢热的人,不会主动过来打招呼,甚至很少有笑容,但也从未见他发怒。他说话不多,慢条斯理,从不教诲人,行事极为低调,说话办事实在,用现在的话来说,不作,不虚,所以大家都很尊重他。那个时候在村里,吵架是常事,也常常听见人们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但我从来没有听谁讲过孟先生的坏话。如果有谁碰到了难事,人们也都会说,让他去问问孟先生。大家对他的尊重,由此可见。村里老老少少见到他,都会叫一声“孟先生”。注意,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可以被公开称为“先生”的,人们都互称“同志”。像我这样最底层的年轻人,一般都称呼人家“师傅”。能被称为“先生”的人极少,我记得当时好像只有鲁迅,大家是称为“鲁迅先生”的,不是“鲁迅同志”,可见孟先生在村里是有江湖地位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地位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 由于孟先生和我是村里两位“有点文化”的外姓人,村民对我俩做事比较放心。孟先生是会计,忙的时候就会叫我帮忙。我也很乐意帮他,主要是两样事务。一个是记账,村里要记账的事情很多,最主要的是记工分,要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候还要村民按指纹或打章,以示公正,其余的还有很多账目,一般是需要我帮他核校一下是否正确。孟先生打算盘很厉害,十几分钟打下来,很复杂的一个账已经算清楚了。他从老花眼镜后面瞧我一眼:“小徐,你核一下,看有没有错。”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有什么计算错误。打算盘是一项绝活,我母亲是个高手,手在算盘上像飞一样,四位数的乘法一两秒钟就算完了。每次看她打算盘,我总想我大概一辈子也学不成这样。帮孟先生做账,是我唯一一段有机会练珠算的时光,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难得。 孟先生需要我帮忙的第二项事务是每晚生产队要学习,读报纸,读文件,常常孟先生读一两页后,就会叫我继续往下念。孟先生读报是典型的“绍兴官话”,蛮好听的。“绍兴官话”是一种特别有趣的语言,外地人觉得是绍兴话,绍兴人觉得是普通话。有一次一位外地的公社干部听到孟先生读文件,夸他说:“孟先生,你的绍兴话很好懂。”孟先生说:“领导,我说的是普通话。” 孟先生是位很有智慧的人,我在他身边看他处理过大大小小不少很难办的事。有一年早春,天气极为寒冷,青黄不接,大家吃了上顿没下顿。饿过肚子的人都知道,那个难受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起初两三天还可以忍,到了第四天真的比死还难受。以往到了晚上,吃过饭后人们会到村里小桥边上闲聊,但是那一天,没有人来,只有我和孟先生两个人,不远的地方站着S叔。S叔是个复员军人,总是穿着一件军大衣。他个子很高,背对着我们,在桥上站着,看上去很有“将军”的风度。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他家最难熬的日子。他家只有他一个劳动力,妻子长期卧病在床,五六个小孩都还小,全家根本吃不上饭。那天,孟先生和我讲,明天会有一船红薯,是队里从公社拉过来的,救救急。他说:“不知道上头的意思是怎么分?”我说:“大概还是按劳分配吧。”也就是按每个人的工分来分红薯。孟先生没有说话,眼光望向桥上的S叔,叹了一口气就走开了。 第二天一早,小河两岸就热闹了起来,满载红薯的大船撑过来了,孟先生和我连忙去仓库。队长指挥着大家,一担担把红薯运到了仓库,先称重记下来,再放好。一两个钟头后,我俩就把整船的红薯总数算出来了,然后再把总数除以村里劳动力的总数,定下来每个家庭可以分到的量。只不过,问题来了!等所有家庭把红薯取走后,我俩发现仓库的角落里还剩不少红薯。你想,卸船时是一担担加起来的总数,分配时是大家一担担取走的,其中肯定有积累误差,这完全正常。只是剩下的这些是不够再均分给所有村民的了,怎么办呢? 孟先生看了我一眼,问我怎么办,我也没有主意。他说不如把这些红薯给S叔家送去吧,他家那么多小孩,按劳分配最吃亏的是他家,搞得不好,是要出人命的。我表示赞同,于是就把所有剩下的红薯装上箩筐,两个人抬着往S叔家送去。路过小桥,遇见了队长,孟先生同他讲了一声,他也很赞同。孟先生在桥上叉着两手和队长讲话的样子,我觉得很威武,比S叔更像将军。 后来还碰到很多事,孟先生都妥帖地把事办了,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如果要把他的处事原则用现在的话总结一下的话,大概有三条:一是没有私心,他老是同我们讲,取之于公,用之于公的事,错不到哪里,关键是不能有私心;二是集体决定,他办事总是和几个人商量而定,哪怕只有一个伙计,哪怕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也充分尊重我的意见;三是沟通,与上与下都要充分地沟通。这三条我觉得是任何一位管理者都应该明白的道理,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不可能不犯错,但只要他能记住这三条,就不会错到哪里去。 社会是道场,淤泥出莲花,孟先生就是一朵莲花!我与孟先生交流最多的时候是在放工回村的路上。当队长的哨子一吹,宣布“放工了”,所有农友就立刻着急往家赶。有的是回去烧饭,尤其是妇女们;有的是着急回家上厕所,因为那个时候肥料是大事,“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每次走在最后的只有我和孟先生。回村的路要走半个多小时,我们就会聊很多事情。他同我讲得最多的还是鼓励我,他总说:“你是有前途的,要往远处看,世界是变化的,机会是会有的……”这些话来来回回反复地说。他又说,最怕的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自己不想要了!有的鸟就是这样,在笼子里关久了,习惯了笼子里的生活,放出来之后,也只会在笼子周围转来转去,而有的鸟却是关不住的,总是向往自由! 那个时候,我前面的路一片黑暗,看不到一丝希望。他的话就像透过阴云的阳光,让我少了许多孤独和寂寞。 孟先生是个善人。我从小喜食小鱼小虾,祖母总会买来简单蒸一下,很是可口。到了乡下,我们村临江,对面是集市,很多小船会经过我们村去集市买卖,等集市结束后,又会路过我们村。有时候我正好看见他们船里有许多尚未卖掉的鱼虾,一般都是杂的,有大有小。我会去买下来,叫作“倒担”,很便宜,从来不会超过一毛钱。但是,买下来小鱼小虾后,清理是个大问题,很花时间。我挑了几条大一点的鱼清理后,对那些很小的鱼,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我犹豫时,孟先生路过说,花这么多时间清理这些小鱼,到嘴里只有两口,没多少肉,不如放了它们,等到明年就是大鱼了,也算是积德。我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去河埠头把这些小鱼都放生了。 几次下来,在田间做农活的时候,就听见人们在背后议论我,特别是那些老年妇女们,说我这位城里来的知识青年真是个善良的人,德性好得很,把小鱼倒在河里放生。我听了之后,很是惭愧,即便这算一个善举,其中至少一半的动机是因为我清洗不了,或者说懒得清洗那些小鱼小虾,而另一半则是孟先生叫我这样做的,并不是我自发的。 几十年后,有一年春节,我终于有机会重访我当年下乡的村庄。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当年宿舍的位置,以那间小屋作为参照,再去找那个临着大江的河埠,竟然还在,而且在那里还遇到了当年经常一起玩的农友和他的妻子。多年不见,大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他低着头,我也低着头。我看到他脚下的江水,浅浅的,清清的,连水草和成群成群的小鱼都看得很清楚。 啊!我忽然想到了那些我放生的小鱼,就是在这个河埠。这一级级的台阶下面,这清清的水中的小鱼,或许就是我当年放生的那些小鱼的子子孙孙吧!于是,我想起了孟先生,我都不敢问,怕是很久以前就过世了吧!他的身后没有子孙,不像那些小鱼……孟先生那清癯、平和、充满智慧的面容,一闪一闪,浮现在这浅浅的江水上面…… 1. 沉沉浮浮数十载人生,千帆阅过、冷暖尝遍,作者以简雅隽永的文字回忆过往,提炼俯仰之间沉淀下来的人生感悟,凝结成这本小书,邀请年轻的朋友们,于黄昏的神仙湖畔共赴一场赤诚的神思交流。 2. 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邂逅的人、经历的事,都是人生的馈赠;关于学习,关于工作,关于人生选择,关于自我的成长,这本书是一位资深教育工作者、“精神摆渡人”送给年轻人最好的礼物。 3. 书中彩色插图60余幅,皆为作者摄影作品的再创作,艺术与科技的碰撞和交融,展现了作者独具一格的审美视角。 4. 工作之外,徐扬生还是一位风格独特、颇有建树的书法家,书名由其亲自题写。 5.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创校校长,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为表彰徐扬生教授在科学与教育方面的贡献,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国际永久编号第 59425 号小行星 1999 GJ5 命名为——“徐扬生星”。 6. 作者前作《摆渡人》重印10次,销量近10万册,豆瓣评分7.9分,广受年轻读者喜爱。《黄昏的神仙湖》是作者继《摆渡人》之后的又一全新散文集,延续了前作的风格,又添许多耐人寻味的新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