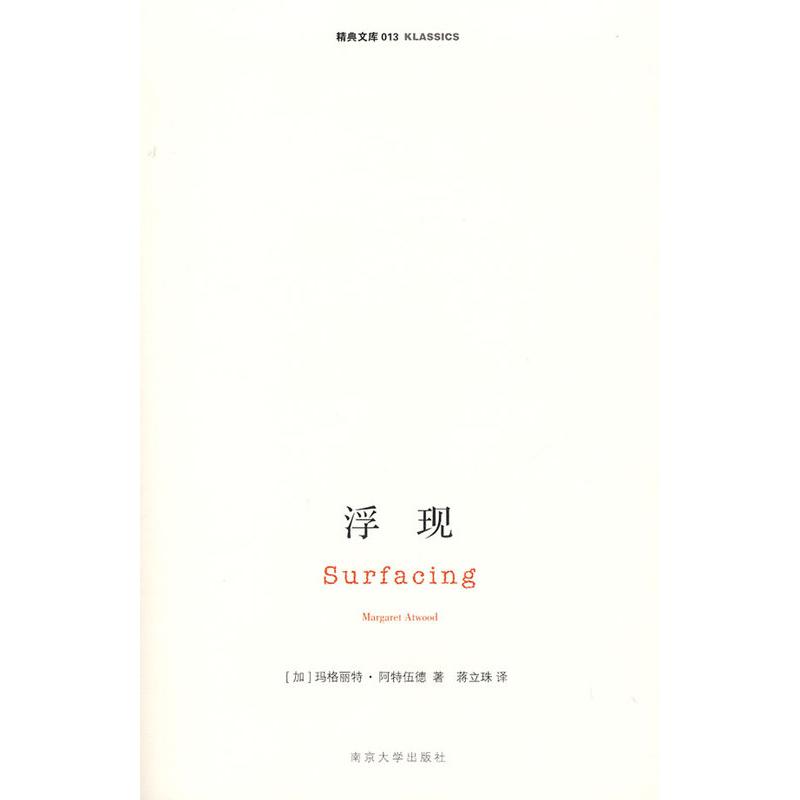
出版社: 南京大学
原售价: 18.00
折扣价: 11.00
折扣购买: 浮现/精典文库
ISBN: 97873050555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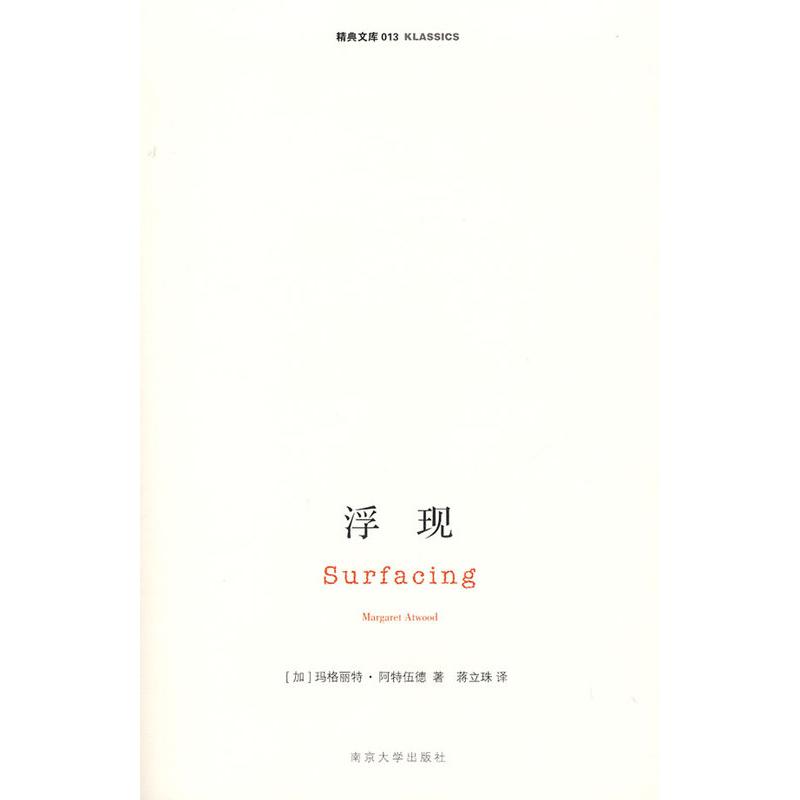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年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早年在安大略北部和魁北克度过,1962年获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曾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她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其作品迄今已在全球35个国家出版。她曾推出3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小说、诗歌与批评散文。她的小说《女仆的故事》、《猫眼》与《别名格雷斯》曾获得加拿大的吉勒尔奖与意大利的普雷米欧·蒙德罗奖;《瞎眼刺客》曾获2000年英国布克小说奖。
此时此刻,我却坐在另一辆车上,坐在大卫和安娜的车上。车的尾部向 上凸起,车身贴有条纹的铬条,十年前就淘汰了的车型,看起来像个笨拙的 怪物,大卫得把手伸到仪表盘下才能把车灯打开。大卫说他们买不起新车, 这话倒未必尽然。我发现大卫车开的好极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外侧的手 握在车把手上,一是为了撑牢自己的身子,再就是发生紧急情况时我可以立 刻从车上跳出去。以前我和他们。一起乘坐过这辆车,但行驶在这条路上, 情形好像有些不对头,不是他们三个有问题,就是我出了毛病。 行李和我都在后座上。乔,就像一件行李,坐在我身旁,他嘴里嚼着口 香糖,还握着我的手,这样他就很容易打发掉时光。我注视着他的手:手掌 宽大,手指短小但张弛有度。他正摆弄着我的金戒指,转过来转过去,这是 他的习惯性动作。他的手是地地道道农民的手,而我却长着一双种田人的脚 ,这是安娜告诉我们的。眼下每个人都喜欢卖弄小魔术,安娜就常常在聚会 上给人看手相,她说这样可以替代言语交流。在给我看手相时,她问我:“ 你是双胞胎吧?”我说不是。“你肯定?”她接着说,“因为你的一些手纹 是双重的。”她用食指触摸着我的手纹,“你有个美好的童年,可后来竞长 出了这条莫名其妙的断纹。”她皱了皱眉头,所以我只好对她说我就是想知 道我能活多久,不必泄露其他的什么天机。她说乔的手表明他是一个值得依 赖的人,只是不太敏感。对此我置之一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从侧面看,乔简直就是美国五分硬币上的水牛像,毛发浓密,鼻_子塌 矮,一双眯缝眼流露出愤愤不平和极其愚蠢的神态,就好像什么动物一样, 曾经统治过地球而如今又面临灭顶之灾。他恰好也是这么看自己的:备受欺 辱,怀才不遇,可暗自里,他奢望人们为他建造一座公园,比如一座鸟类禁 猎区公园。两面的乔。 意识到我在注视他,乔松开我的手,吐出口香糖,用口香糖纸把它包好 塞进烟灰缸里,然后双手抱起肩膀。这意味着我不该看他,于是我把头转过 来注视前方。 行程的头几个小时,我们翻过牛群点缀的平缓山坡,穿过叶林和已经枯 死的榆树林,又进人针叶林,驶过炸药炸开的路段——这里的石头都是粉红 色和灰白色的花岗岩,路过那些看起来很容易坍塌的供旅行者憩息的小屋, 上面挂着“通往北方”的木牌,至少四个小镇都挂有同样的牌子。“未来在 北方”曾经是一句政治口号。我父亲听到这句话时,曾说道:北方,除了过 去,什么都没有;即便有,也不值一提。现在,无论他在哪里,是死是活, 没人知道,可他不再说那些警句格言了。我们的父辈不应该变老。我羡慕那 些年幼就失去父母的人,他们的父母很容易被记起,他们的形象永久地存在 人们的心中。我想我的情形也不会例外,即使我迟一些动身返回,我对父母 的记忆还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父辈是生活在另一时代的人群,他们只为自 己的事情而忙碌,他们安全地躲在果冻一样半透明的墙壁后面,好似冰冻在 冰川里的猛犸象。我应当做的就是一旦准备好就立刻返回,可我推迟了行期 ,事情总是太多。 我们驱车驶过岔道,朝着美国人曾经挖的掩体方向开去。从这里看,那 座掩体好似一座平静的山丘,上面覆盖着云杉原木,可树林中又粗又重的电 线却泄露了它的秘密。我听说美国人早已离去,但这也许是个骗局,如此一 来他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长期住下去了。将军们住在混凝土筑起的掩体内, 普通士兵住在地下房屋里,那儿的灯光昼夜通明。我们无法走进去亲眼看一 看,因为我们没有被邀请,但这座城市邀请了他们,他们滞留此地对当地的 生意大有好处。他们很能喝酒。 “那地方是放火箭的地方,”我说。我本该说“曾经是”,但我并没有 纠正。 大卫愤愤地骂道,“该死的法西斯蠢猪美国佬”,可他的口气听起来好 似在评论天气。 安娜倒是一言小发。她把头靠在座位靠背上,车窗没有关严,钻进来的 微风轻轻地将她的发梢吹起。刚开始她一直唱着《旭日之屋》和《丽丽·玛 莲》这两首歌,一连唱了好几遍。她尽量把嗓音控制得低哑、深沉,可挤出 来的声音却是沙沙的童音。大卫扭开收音机,什么也收不到,我们的位置正 处在两家电台之问的盲区。这时,安娜哼唱起《圣路易的布鲁斯》,唱到一 半,大卫吹起口哨来,于是她把嘴闭上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最要好的 女性朋友,我认识她有两个月了。 我向前倾了倾身子,对大卫说:“那个‘瓶屋’就在附近,再向前左转 弯就到了。”他点了点头,放慢了车速。我对他们提到过这家“瓶屋”,我 想他们会有兴趣的。他们正拍摄一部片子,乔负责摄影;虽说他从未干过这 行,可大卫说他们是新潮的文艺复兴多面手,一边干一边学,自己教会自己 。拍电影大概是大卫的主意,他自称导演,花光了他们所有的存款。他要把 他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拍下来,并把这一创意称作随意取样,这也是他们这部 影片的名字:《随意样片》。他们拍完胶片后(胶片是他们唯一能够买得起 的东西,摄影机是租来的),还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然后再剪接这些镜头 。 在大卫描述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时,我曾经问过他:“要是你不知道那 是关于什么的主题,你怎么知道该拍些什么呢?”他用教导新手入门的眼神 撇了撇我。“如果你事先就否定了你的想法,就像你现在这样,那你就什么 也做不成。你需要做的,就是一往无前。”安娜正在炉灶旁往外舀着咖啡, 说她所认识的人都在制作电影。大卫接着说没什么他妈的理由认定他就不能 拍电影。安娜回答说:“对不起,你当然可以。”可背地里,她却对他们的 做法大大地嘲弄了一番,说那是“任性的粉刺”。 那家“瓶屋”很特别,是用混凝土把饮料瓶子粘在一起建成的。它们瓶 底朝外,绿色和褐色的瓶子锯齿状交错排列,就像学校老师教我们画的圆锥 状帐篷上才有的图案。不仅如此,围绕房屋的围墙也是用瓶子砌成的,瓶子 按字母顺序排列,于是褐色的瓶子就拼成了“瓶屋”。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