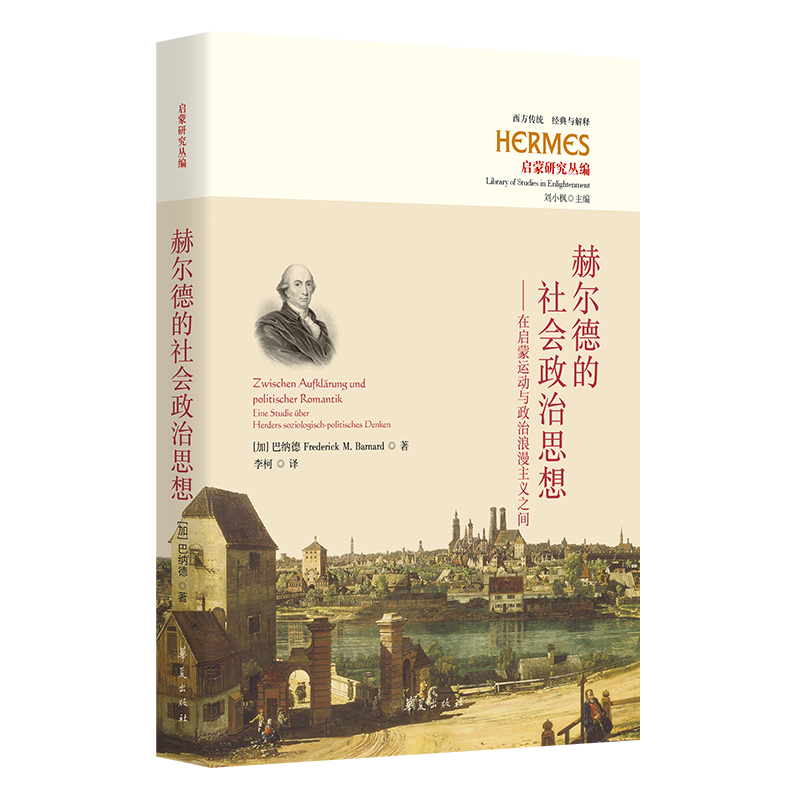
出版社: 华夏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42.90
折扣购买: 赫尔德的社会政治思想:在启蒙运动与政治浪漫主义之间
ISBN: 97875222048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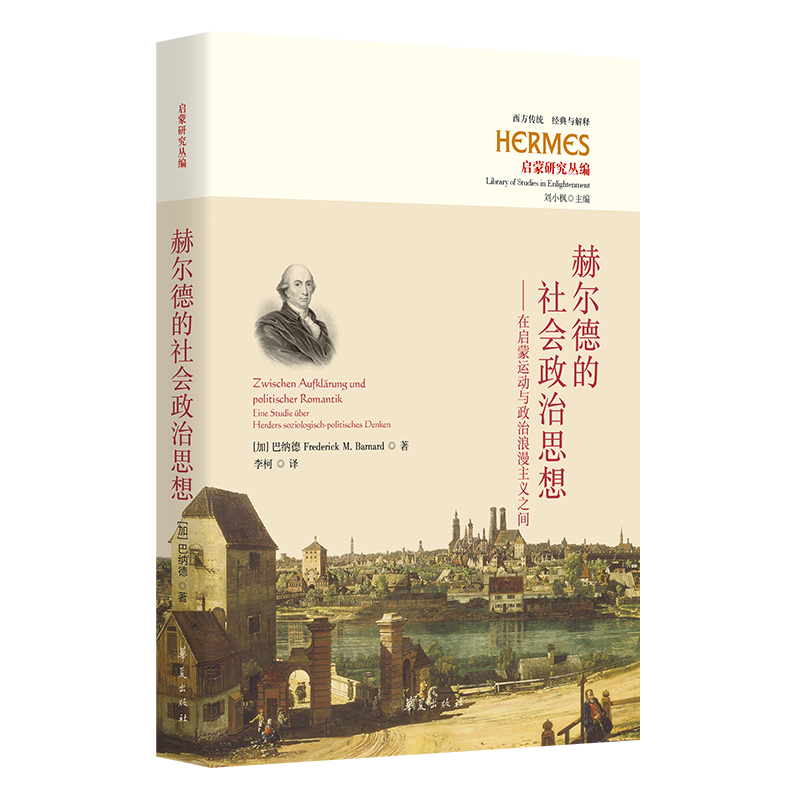
赫尔德如何看待中央权力 (摘自“有机主义国家”一章,标题为自拟) 赫尔德反感把最高政治使命委以中央权力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他对事物的天赋差异性的深刻信念。他担心,对于不同角度起作用的力量,中央权力只懂得压制其发育,阻止其展开协作。他认为总体中的多样性是彼此相连的,很显然,如果尽可能给予这种多样性更多的活动空间,一项主权性的中央权力必将不可避免地对一些个体和团体带来负面冲击,因此它迟早必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威而采取强制措施。一旦有志于此,它就会意图牺牲差异性来促成统一,摧毁自然自生力量,而这些力量在保持着多样性的健康社会秩序中本会以共同性为鹄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整齐划一和虚假统一,因为共同性只能繁茂在差异性的土壤上。 赫尔德坚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命令权与个体尊严不可兼容,这也是他拒绝给政治权力以某种组织化的第二个理由。个人或团体行使国家权力,乃以公民情愿服从该权威为前提。不过在赫尔德看来,即便如此也意味着不必要的贬抑。总之,他的法权学说反对设立任何此类机构,因为法律和条例由权威制定,但权威自己却不服从法律。所以,赫尔德担心它会蜕变成专断。 赫尔德的法权观念与中世纪思想走得很近。法以风俗为基础,并通过习惯而神圣化,人们更多地是发现法而不是创造法。法内在于自然社会中由人所传承的生活方式,就如同一个民族所传承的生活方式那样。因此,正确的理解是,立法不需要表现为一种强制措施。立法是民族道德觉悟的表达,并拥有内在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一部法律如果不是从共同体的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而仅仅依靠权威的强迫推动来设定秩序,那它不过是一片死寂的阴影罢了(IV,466-469)。 赫尔德反对中央权力的主要观点有待商榷,自不待言。他相信差异性是和谐的社会共同作用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他信赖民族法权,这些在经验和逻辑上都可能成问题。差异性可以是事物的自然秩序,它有倾向于统一的本质特征,但同时也有倾向于分离的本质特征。民族法权可以被岁月神圣化,也可在岁月中遭到废弃或变得含混。建基于“健康的民族感悟”之上的法律可以是良法,但也有可能包含缺陷和危险。并不是差异性本身,也不是以习俗为基础的法律,构建了针对社会和政治之恶的可靠屏障,因为在差异性与共同作用之间、在民族法及绝对正义之间,本质上并没有既定关联。 然而,赫尔德的基本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他希望通过强调社会政治关系的内在力量,以界定自然和个体自由,同时证明外在强制纯属多余。同康德相似,他已然确信,人只有在服从自己内在的法则时才是自由的。按照这一观点,自决是最高的道德善和政治善,对一个病态的社会来说亦是最好的救济手段。今天的人们可以轻易地说,这种要求所造成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还要多;但是在当时,它不仅相当全面地改变了政治思维方式,更明显地影响了政治实践的趋势。
赫尔德如何看待中央权力 (摘自“有机主义国家”一章,标题为自拟) 赫尔德反感把最高政治使命委以中央权力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他对事物的天赋差异性的深刻信念。他担心,对于不同角度起作用的力量,中央权力只懂得压制其发育,阻止其展开协作。他认为总体中的多样性是彼此相连的,很显然,如果尽可能给予这种多样性更多的活动空间,一项主权性的中央权力必将不可避免地对一些个体和团体带来负面冲击,因此它迟早必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威而采取强制措施。一旦有志于此,它就会意图牺牲差异性来促成统一,摧毁自然自生力量,而这些力量在保持着多样性的健康社会秩序中本会以共同性为鹄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整齐划一和虚假统一,因为共同性只能繁茂在差异性的土壤上。 赫尔德坚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命令权与个体尊严不可兼容,这也是他拒绝给政治权力以某种组织化的第二个理由。个人或团体行使国家权力,乃以公民情愿服从该权威为前提。不过在赫尔德看来,即便如此也意味着不必要的贬抑。总之,他的法权学说反对设立任何此类机构,因为法律和条例由权威制定,但权威自己却不服从法律。所以,赫尔德担心它会蜕变成专断。 赫尔德的法权观念与中世纪思想走得很近。法以风俗为基础,并通过习惯而神圣化,人们更多地是发现法而不是创造法。法内在于自然社会中由人所传承的生活方式,就如同一个民族所传承的生活方式那样。因此,正确的理解是,立法不需要表现为一种强制措施。立法是民族道德觉悟的表达,并拥有内在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一部法律如果不是从共同体的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而仅仅依靠权威的强迫推动来设定秩序,那它不过是一片死寂的阴影罢了(IV,466-469)。 赫尔德反对中央权力的主要观点有待商榷,自不待言。他相信差异性是和谐的社会共同作用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他信赖民族法权,这些在经验和逻辑上都可能成问题。差异性可以是事物的自然秩序,它有倾向于统一的本质特征,但同时也有倾向于分离的本质特征。民族法权可以被岁月神圣化,也可在岁月中遭到废弃或变得含混。建基于“健康的民族感悟”之上的法律可以是良法,但也有可能包含缺陷和危险。并不是差异性本身,也不是以习俗为基础的法律,构建了针对社会和政治之恶的可靠屏障,因为在差异性与共同作用之间、在民族法及绝对正义之间,本质上并没有既定关联。 然而,赫尔德的基本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他希望通过强调社会政治关系的内在力量,以界定自然和个体自由,同时证明外在强制纯属多余。同康德相似,他已然确信,人只有在服从自己内在的法则时才是自由的。按照这一观点,自决是最高的道德善和政治善,对一个病态的社会来说亦是最好的救济手段。今天的人们可以轻易地说,这种要求所造成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还要多;但是在当时,它不仅相当全面地改变了政治思维方式,更明显地影响了政治实践的趋势。 赫尔德如何看待中央权力 (摘自“有机主义国家”一章,标题为自拟) 赫尔德反感把最高政治使命委以中央权力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他对事物的天赋差异性的深刻信念。他担心,对于不同角度起作用的力量,中央权力只懂得压制其发育,阻止其展开协作。他认为总体中的多样性是彼此相连的,很显然,如果尽可能给予这种多样性更多的活动空间,一项主权性的中央权力必将不可避免地对一些个体和团体带来负面冲击,因此它迟早必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威而采取强制措施。一旦有志于此,它就会意图牺牲差异性来促成统一,摧毁自然自生力量,而这些力量在保持着多样性的健康社会秩序中本会以共同性为鹄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整齐划一和虚假统一,因为共同性只能繁茂在差异性的土壤上。 赫尔德坚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命令权与个体尊严不可兼容,这也是他拒绝给政治权力以某种组织化的第二个理由。个人或团体行使国家权力,乃以公民情愿服从该权威为前提。不过在赫尔德看来,即便如此也意味着不必要的贬抑。总之,他的法权学说反对设立任何此类机构,因为法律和条例由权威制定,但权威自己却不服从法律。所以,赫尔德担心它会蜕变成专断。 赫尔德的法权观念与中世纪思想走得很近。法以风俗为基础,并通过习惯而神圣化,人们更多地是发现法而不是创造法。法内在于自然社会中由人所传承的生活方式,就如同一个民族所传承的生活方式那样。因此,正确的理解是,立法不需要表现为一种强制措施。立法是民族道德觉悟的表达,并拥有内在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一部法律如果不是从共同体的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而仅仅依靠权威的强迫推动来设定秩序,那它不过是一片死寂的阴影罢了(IV,466-469)。 赫尔德反对中央权力的主要观点有待商榷,自不待言。他相信差异性是和谐的社会共同作用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他信赖民族法权,这些在经验和逻辑上都可能成问题。差异性可以是事物的自然秩序,它有倾向于统一的本质特征,但同时也有倾向于分离的本质特征。民族法权可以被岁月神圣化,也可在岁月中遭到废弃或变得含混。建基于“健康的民族感悟”之上的法律可以是良法,但也有可能包含缺陷和危险。并不是差异性本身,也不是以习俗为基础的法律,构建了针对社会和政治之恶的可靠屏障,因为在差异性与共同作用之间、在民族法及绝对正义之间,本质上并没有既定关联。 然而,赫尔德的基本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他希望通过强调社会政治关系的内在力量,以界定自然和个体自由,同时证明外在强制纯属多余。同康德相似,他已然确信,人只有在服从自己内在的法则时才是自由的。按照这一观点,自决是最高的道德善和政治善,对一个病态的社会来说亦是最好的救济手段。今天的人们可以轻易地说,这种要求所造成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还要多;但是在当时,它不仅相当全面地改变了政治思维方式,更明显地影响了政治实践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