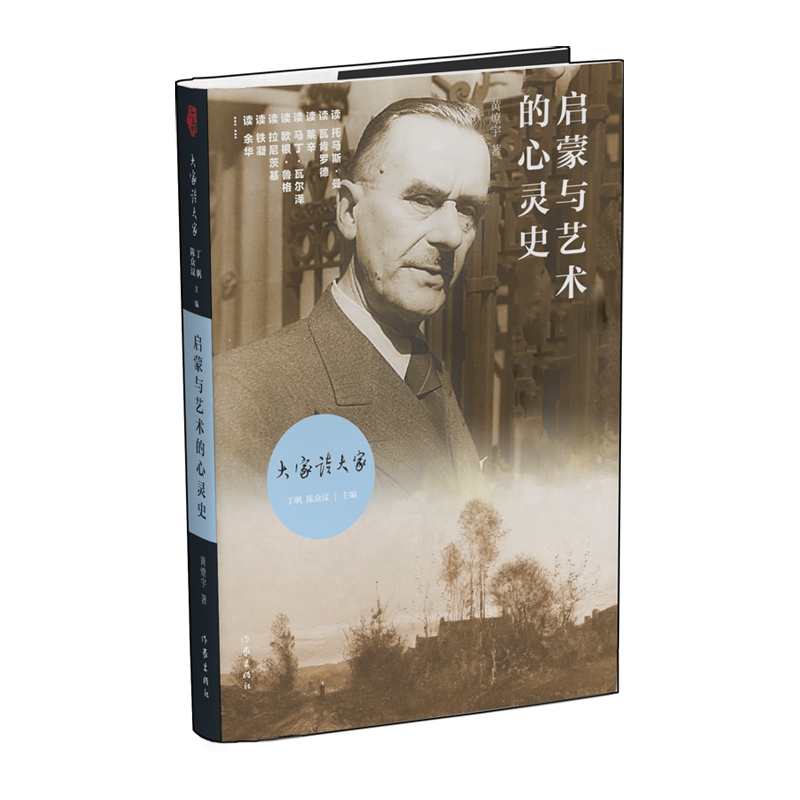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3.00
折扣价: 28.00
折扣购买: 启蒙与艺术的心灵史(精)/大家读大家
ISBN: 9787521207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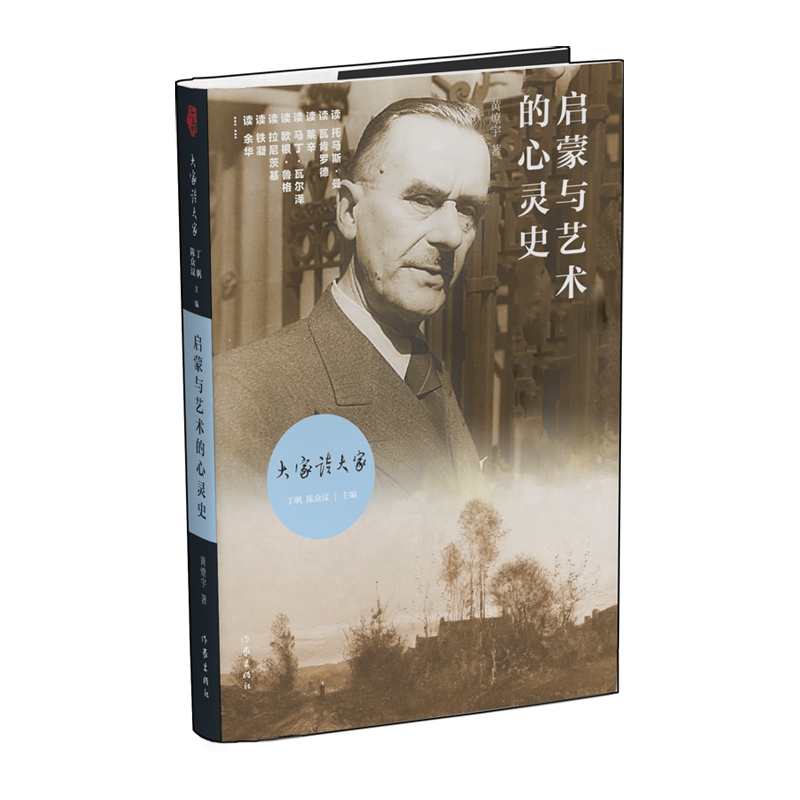
黄燎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德语现当代文学和德国问题研究。著有《思想者的语言》《托马斯·曼》等;译有《死于威尼斯》《雷曼先生》《批评家之死》《恋爱中的男人》《艺术社会史》等。获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鲁迅文学翻译奖以及“2016 书业年度评选社科翻译奖”。
“伟人乃公众之不幸” ——从 《绿蒂在魏玛》看托马斯·曼的艺术观 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第八章,写歌德设宴款待远道而来、阔别四十四年的夏绿蒂。席间,他冷不丁地引用了一句据说来自中国的格言,“伟人乃公众之不幸”。话音刚落,听众中间爆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对于冷眼旁观的夏绿蒂来说,这分明是欲盖弥彰,是要防止有人“跳起来掀翻桌子再吼上一声‘中国人说得对!’”。 既然如此,那么歌德信手拈来的“中国格言”到底点破了什么秘密?或者说,伟人歌德为什么成为公众之不幸?他使谁遭受了不幸?对此,小说至少提供了如下事例:歌德是大众的不幸,因为他是不可救药的精神贵族,声称“群众和文化不合拍”。歌德是进步人士的不幸,因为他主张新闻检查,反对出版自由。歌德是歌德信徒们的不幸,因为他永远保持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歌德是亲人的不幸,因为他对亲戚——无论长辈、晚辈或者平辈——都漠不关心,甚至可以整整十一年不探望母亲;他的独生儿子奥古斯特慑于父亲的精神光环,死心塌地当父亲的管家,而且在婚姻大事上也遵从父言。歌德是助手的不幸,因为尽管秘书里默尔学识渊博,而且已过不惑之年,尽管他始终默默无闻地充当大师的活词典,甚至在标点语法方面为他出谋划策,可到头来也只被大师唤作“好孩子”。至于夏绿蒂,歌德也给她造成了多重不幸。年轻时,歌德插足其爱情生活,给她带来了痛苦和迷惑。《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发表,又使她和丈夫尴尬不已。六十三岁的她,带着重温旧情的愿望来到歌德的魏玛,而六十七岁的歌德当面只是敷衍和客套,背后则嗤之以鼻。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这是歌德吗?当初是这种情形吗?纠缠于此类问题的人,多半是一个无法和文学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且和小说中的夏绿蒂处于同样认识水平的人(夏绿蒂就不理解歌德为什么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把她的蓝眼睛变成了黑眼睛,还对此耿耿于怀)。他极有可能把《绿蒂在魏玛》和某些通过揭示人性弱点或者暧昧逸事来“颠覆”伟人,进而哗众取宠的名人传记相混淆。但是,我们没有这种“忧患意识”,我们也并不关心《绿蒂在魏玛》是否塑造了一个“真实”的歌德形象。我们感兴趣的是,托马斯·曼通过歌德这一形象究竟想说明什么。当歌德宣布“伟人乃公众之不幸”的时候,托马斯·曼当然不希望读者单纯从字面、从社会学层面去加以理解,也无意把伟人的形象定格于自私、冷漠、傲慢。歌德是文学家,文学正是其生命的符码。他的伟大、他的“祸害”,都源于文学。用文学来演绎歌德其人其事,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蒂在魏玛》叙述的是一场有关文学的道德官司。惯于而且善于夫子自道的托马斯·曼就此轻而易举地把这部“歌德小说”变成了艺术家小说。声讨也罢,辩护也罢,指控也罢,开脱也罢,歌德的话以及围绕歌德的谈话,都自然而然地具有托马斯·曼的话语特征。 为了澄清这场关系到歌德、关系到托马斯·曼乃至整个文学界的道德官司,我们有必要对歌德给夏绿蒂造成的几重“不幸”做一番分析和演绎。绿蒂的第一桩“不幸”,是歌德插足她和凯斯特纳的情感生活之后给她带来的诱惑与困惑。由于夏绿蒂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没想通歌德为什么“爱别人的未婚妻”,所以和里默尔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两人说得有些玄乎。夏绿蒂说歌德“把感情的布谷鸟蛋放进一个筑好的巢穴”,说他“在寻觅和恋爱方面缺乏自立精神”,说他有“寄生性”。里默尔则总结说“有一种天神寄生、天神下凡的现象,我们的想象对此毫不陌生,天神在漫游途中参与凡人的幸福,对一个被此间选中的女子做更高级的选择,这个众神之王对一个凡夫俗子的女人产生爱的激情,这个凡夫俗子十分虔诚虔敬,对天神的参与并不感到损失和屈辱,反倒感觉被抬举,感觉很光彩……”里默尔所讲的,就是希腊神话中有关安菲特律翁的故事:宙斯借安菲特律翁出征之机,化装成后者的形象去他家,跟他妻子阿尔克墨涅享受床笫之欢。安菲特律翁回家之后,自然也和妻子云雨一番。结果,阿尔克墨涅生下双胞胎。伊菲克勒斯属于安菲特律翁,赫拉克勒斯属于宙斯。由于这个故事意味深长,解释起来极富弹性,所以从古罗马的普劳图斯到法国的莫里哀再到德国的克莱斯特,许多文学家都钟爱这个题材。托马斯·曼也不例外。虽然他只写过一篇评论克莱斯特剧本的文章,没有用这个故事来创作小说,但他还是把歌德、绿蒂、凯斯特纳三者的关系镶进了这一神话框架。他当然是别有用心的。他不仅把作为第三者的歌德变成了宙斯,变成了神仙,而且还不露声色地把一顶艺术家的帽子塞给了宙斯。歌德是一个无所事事、风流倜傥的闲人,凯斯特纳是一个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的职员。光是这种对比,就足以引出托马斯·曼的艺术家主题。 众所周知,托马斯·曼从创作伊始便反复述说艺术与生活的对立,而对立的根源又在于艺术活动的非功利性,在于艺术家从七十二行中找不出适合自己的一行。这种对立使艺术家成为世人眼中的“闲人”“局外人”“多余人”“无用之人”。《布登勃洛克一家》中那个断送了辉煌家业的汉诺便是这种典型。但是,受过叔本华艺术哲学熏陶的托马斯·曼,脸上是“天生我材有何用”的困惑,心里却是“天生我材另有用”的自信,骨子里把艺术看作一项超凡脱俗、以特殊的方式服务于人类的事业,把艺术家看作一种道德可疑但拥有精神优越性的特殊人种。和忙人凯斯特纳相比,闲人歌德是可疑的。但是,他使凯斯特纳相形见绌,就像宙斯让安菲特律翁自惭形秽一样。已经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占有绿蒂的凯斯特纳只好以如下方式为自己开脱:“一个人要是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上无所事事,享受着充分的自由,他就很容易潇洒起来,他会显得大方,活泼,出众,机智,很让女人喜欢,别人却因为忙碌了一天,被工作问题搞得疲惫不堪,回到爱人身边后已不能按照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来表现自己了。”换言之,歌德的优越,在于他闲世人之所忙:工作/生计,忙世人之所闲:感情/精神。绿蒂称这种现象“不公正”,但是她不认为谁都能闲出歌德的水平,而且她也感受到歌德的特殊诱惑。在此,我们触及一个通俗然而重大的话题:情人与丈夫的分离。事实上,在克莱斯特的剧本中,虚荣的宙斯就不断暗示阿尔克墨涅情人与丈夫,也就是他和安菲特律翁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阿尔克墨涅听不懂宙斯的意思,天真地回答宙斯:“情人和丈夫!你在说什么?”那么绿蒂心中却是明亮的。只是她作为谨慎务实的市民女子,对于“王子和流浪汉的吻”不免有几分畏惧。否则,她会选择情人,背弃丈夫,成为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以及艾菲·布利斯特那种叛逆女性。同样有趣的是,托马斯·曼在一个艺术家的沾沾自喜之中不知不觉地让宙斯、让歌德、让艺术家与花花公子有了牵连,同时又让罗多尔夫们、伏伦斯基们、克朗帕斯们多少沾上一些神气、灵气、才子气。倘若福楼拜、托尔斯泰、冯塔纳在天有灵,不知会做何感想。 在启蒙与艺术的天地里,陪你畅聊说不尽的德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