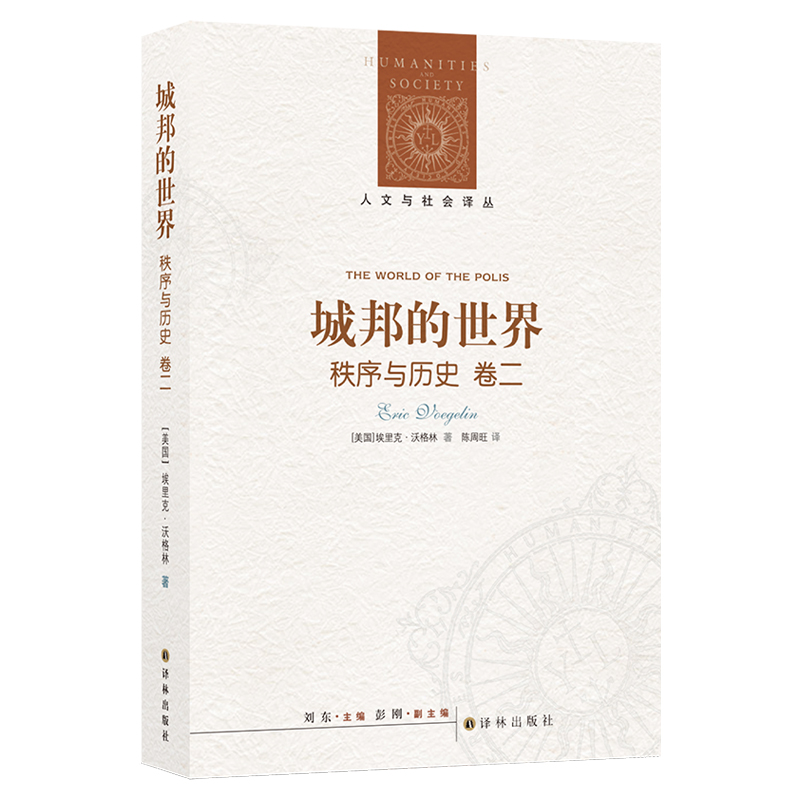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85.00
折扣价: 56.10
折扣购买: 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2)/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268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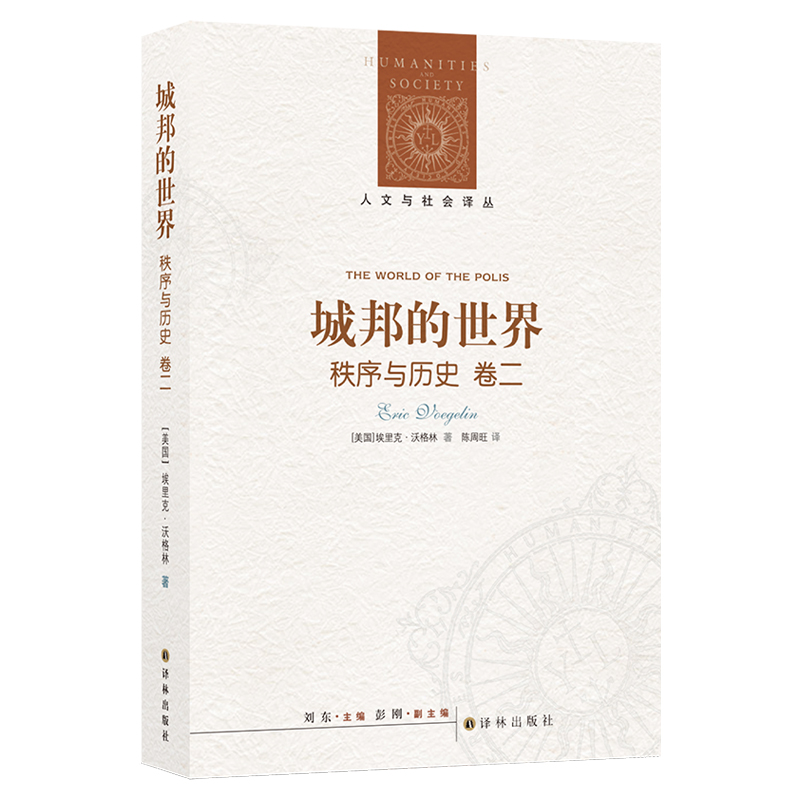
埃里克·沃格林(1901—1985),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生于德国科隆,求学于维也纳大学,并成为该校法学院的政治科学教授。为躲避希特勒的迫害,1938年和妻子移民美国,并于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沃格林的大部分学术生涯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度过。主要著作包括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和五卷本《秩序与历史》。
编者导言 3.人与历史 在导论“人与历史”中,沃格林扼要说明了他的《秩序与历史》研究所仰赖的原则,这些原则奠定于1956年。正如我们所见,沃格林将政治社会设想为“心灵形式”。相应地,对它们的研究,也就不能拘泥于“理想类型”的分类,而要对激发它的召唤中心(evocative centre)进行理解和评判。一切人类社会都是为了存活和共同行动而组织起来的,相应地就要装备权力的规则和工具。然而,与昆虫社会不一样的是,后者是千篇一律的本能模式,而人类社会,与人类的自由相一致,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然而,形式之多样,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社会的秩序也不是一种发明,不是将自主理性应用于一个既定问题的结果。毋宁说,它是将意义赋予在社会中存在的事实的一种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常常是,而且必然是不完美的,但它多少也算尽力而为了。从一个被认识到,但从根本上说是无法真正理解的整体来说,它表明人们在走向更大程度的团结。对于涌上人类意识的秩序的暗示,它给予符号化的表达。在一个催生、命名和固定的过程中,秩序的要素和模式产生了。在此意义上,社会是召唤,是精神的客体化。 一切从政治上言说的召唤,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等的,因为精神泽被天下;社会现实只是存在那包罗万象的现实中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现实,对于人类经验来说总是一视同仁、大家都有的。只不过,言传的程度、符号解释系统高度发达的程度、符号分殊化的水平,差异很大。正是这种差异性,让人们在回顾时可以将社会及其各自相应的“心灵形式”进行排序。 历史中出现的大多数社会,既非仅仅说明只存在一种可能性,亦即由生物来决定的可能性,也不是一个随机的大杂烩。不存在什么简单的线性发展,因为有好几条独立的平行线展现出来,例如,除了在西方历史中的发展,还有在印度和中国历史中的发展。许多虚假的出发点、片面的进步,模糊了其他方面的真实成就,确实全都是意识形态的歪曲。不过,沃格林争辩道,抛却一切复杂性和必要的审查不管,这里存在“一个秩序的先后次序,环环相扣,要么向真理充分的符号化前进,要么倒退”。本身就自有其意义的社会,由于参与了长远的精神演化,又具有了一种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产生的“心灵形式”,反映出越来越分殊化和全面化地接近于生存的真理,奔向普遍之人类。 沃格林煞费苦心地指出,一个社会对于“人类共同奋斗”的意义,如它向回顾过去的历史学家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并没有囊括生活在该社会中的人的生存意义。换言之,那些活着的人,没有为了目的论的历史思辨而被工具化。每一种生命本身都是有意义的。然而,对于这位秩序历史学家来说,整体的社会和文明都跌倒在路边,因为,他已经在他论美国的书中写道:“资料的取舍,必须取决于历史本身的取舍。历史意义之脉络,就像一根横穿在深渊之中的绳索,一切都掉入了深渊,而不在绳上稍作停留。”与之相似,在本卷之中,希腊文明其他许多显著特征,都被忽略不计。在此,历史意味着“精神”(Geist)的历史,是它相继的言说和体现。 然而,沃格林要与宰制这样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企图划清界限,比如黑格尔的。历史不是人的行动所能掌控的一个筹划。历史学家不可以站在历史之外对这个进程指手画脚。他既无法知道历史的开端,也不知道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非有限的人类认知所能企及。所有可以知道的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被活着的当下所经验,并借由这一进程本身生产的证据和理解的工具,而成为可以理解的。 心灵或精神走向分殊化的宏大历史进程,是以一种挑战和应战的模式来进行的。符号表达的内部结构一旦稳定和固化,便有物化之虞。符号和制度之所以不完美,是因为它们有局限性。任何完成了的形式,都蕴藏毁灭自身的种子。符号形式收敛起自己,不再向产生这些符号形式的激发性经验(motivating experience)敞开,这种不透明性将遮蔽而不是揭示意义之源,本身就成了一种无秩序的因素,妨碍在真理中生活。无序,表现为暴力、非正义和其他社会解体的征候,激起人对秩序深层根源的敏感,带来一场新的突破。 社会动荡、战败、道德危机和其他现象,是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称之为“乱世”(trouble times)的特征,它们似乎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尽管明显不充分的刺激,让人试图去重建与秩序的超验本质之间的联系。对沃格林来说,这些努力统统都是个人的工作。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集体意识这样的东西。心灵的形式,一国一民的mentalité,只不过是具体到某些人的态度、观念和感觉。因此,一定的心灵结构的盛行,与一定的品性和心智之主导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公共体系的德性和恶习,就是它的人民的德性和恶习。 个人意识影响、塑造或者改变重要的社会领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或许又可以通过亨利?柏格森更容易理解的语言来加以说明。沃格林深受柏格森著作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柏格森写道,“道德先锋”打破了社会习惯和社会团结的框框,这来自于他的名著标题“两个起源”中的另一种。他们的影响与卢梭的相似,后者改变了欧洲人回应自然的方式: 从开天辟地以来,山就有一种功能,在那些仰望高山的人心中引起某些情感,这些情感可比感觉,确实与山不可分割。但是,卢梭在这种联系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本源的感情。卢梭让它开始流通,这种情感便成为通货。甚至今天,也还是卢梭,让我们更多地感受着这种感情,远胜于感受山。诚然,这种源于让—雅克内心的感情,为什么要与山而不是其他物体维系在一起是有理由的;那些类似于感觉的基本情感,是直接由山所引起的,一定要能够跟这种新的情感相融和。但是卢梭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让它们各安其位,从此成为一部旋律中单纯的和音,而卢梭通过一次真正的创作,为这部旋律提供了一个基调。 通过言说他自己深刻的经验,卢梭在一定意义上,让那些一直都在的东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被人所感受。卢梭通过一种分殊之举,即又是挖掘内心,又是创造词汇去改变和丰富欧洲人的感受力,而超越了此前在这方面乏善可陈的主流审美。这样一来,他就创造了一个文化领域,这个领域属于一切对这种已经升华的感受力分有一杯羹的人,属于他的追随者中被他拷问灵魂的新思想所唤醒的人。 柏格森的道德先锋以此为楷模。“他们无欲无求却有所得。他们毋庸劝导;他们只要生存着,就足矣。”一个“封闭社会”仰赖于约定俗成的团结,这与昆虫社会普遍奉行的本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封闭社会的法则非人化,并且化约为命题公式,它们就愈发灵验。它们似乎是通过强制来运作的,通过宣扬与闭塞的政治体休戚与共的重要性,将封闭社会的影响加诸自身。反观另一种道德,如果“化身为一位堪称楷模的特权人物”,则圆满了。作为一种志向,它扎根于人的自由,符合人的精神尊严,而不是处于功能和必需性压力之下来运作的。相应地,它就趋向于统一的人性,而不是闭塞的国家,并效忠于这种统一的人性,这样做,就产生了一个“开放社会”,“驱使人性前进”。 柏格森的开放社会,尽管很难说是生物进化的自动产物,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有一种理想化了的历史向度,是一种道德的隐德来希(entelechy),而不是生命力(élanvital)的决定性终结。柏格森的先锋,产生于社会习惯之外的源泉,但是他们并不必然对一场危机做出回应,而所谓危机,就是剧烈阵痛意义上的,社会解体的生死存亡之秋。柏格森的“封闭社会”是有缺陷的,在道德上是不完整的,但并不必然是功能不良和无序的。相反,对于沃格林来说,似乎只有一种秩序来源,只是被承认或否认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历史对他而言是人类向更高水平的真理前进的进程,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而认识和构建它自身。精神突破创造出这一进程中的一个个划时代阶段,这些突破受到特权人物的影响,他们不仅仅是楷模,就像柏格森所认为的那样,而且他们肩负一种责任,要传播他们的真知灼见,正如大众也有义务要倾听一样。沃格林的精神先锋,身为他的人类同胞的代表,获得并言说分殊化真理的信息。向人们传达分殊化真理的信息,既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权利。对于沃格林来说,这种权威的,因而也常常是血气方刚、不屈不挠的召唤,构造了人类历史。因此,历史研究岂能是“不温不火的纪事”,它必须与一个接一个随着真理的依次涌现而产生的先知权威进行殊死搏斗。 就此而言,一部完整的作为秩序历史的人类史,必须考虑思想王国中的各种表现形式———符号形式,同时还有制度化的政治结构模式———秩序类型。从原始部落社会中崛起的最早的秩序类型,是宇宙论王国,它被构建为宇宙的同类物。这个王国是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因为它反映了令人敬畏的天体运动和季节转换规律。然而,对实际存在的无序的经验,削弱了宇宙作为一个楷模表面上所具有的那种可靠性。相对于人生存的变化无常,与物理宇宙的伙伴关系被证明不是一根足够牢固的支柱。在已有的条件下,人,害怕面对与生存失去了联系的深渊,转向了比宇宙更持久的东西,发现了超越现象世界的、无形的存在的根基,这成为他依恋的对象。既然人只有在他的灵魂活动中才可以经验神圣存在,那么,正是在有序的灵魂的结构中,他才找到一个合理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的典范。社会,被构建为一个小宇宙,现在也被正确地理解和言说为大写的人。沃格林称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为“存在的飞跃”。这是他历史哲学的关键事件。它以两种判然有别、相互独立而对应的模式发生:以以色列的启示的形式,以希腊人哲学的形式。本卷关注的是后者。更确切地说,本卷探讨的是希腊心灵从它自己的宇宙论神话走向柏拉图的漫漫征程。至于柏拉图居高临下的召唤,冀望具有哲学形式的秩序经验,能够产生出秩序化的影响,沃格林将在下一卷加以讨论。 从圣奥古斯丁到波舒哀、布丹、伏尔泰和黑格尔,再到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这些人都在努力建构一种包罗万象的人类历史。讨论完自己的著作与这些努力之间的关系,沃格林对统领眼前这些历史资料的东西,用寥寥数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无所不包的计划,在同一时期的《政治的新科学》中讲得更为充分些。根据沃格林当时的概念,启示和哲学是基督教作为西方社会的符号形式而兴起的根基。现代西方的危机,是从全体中世纪基督教徒(Medieval Christendom)所达到的意识高度堕落的标志。异化,也就是从与存在秩序相谐和的自我中倒退的现象,由于工具理性的运用而被加剧,为反真理的生存状态正名,尽管这种东西在人类社会中可谓屡见不鲜,但是在现代显得尤为猖獗和败坏,产生了意识形态这种东西,沃格林将它划归灵知主义门下。这场危机的毒害性,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分殊化的程度,意识形态歪曲正是从这里倒退的。因为,神话的浑然一体,纵使在其他方面有千般不足,当大家都误入歧途的时候,它比那些更纯正的符号表达,更有可能保留秩序的暗示。 在研究过程中,当沃格林发现哪个方案干净得容不下任何资料的时候,他就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之所以放弃《秩序与历史》最初的方案,是因为他认识到,只要历史被认为是一个“过程”,历史的秩序就不会从秩序的历史中产生。沃格林并没有减缓对现代意识形态的批判,但是他的意识哲学转向了,(可以说)转向内在,产生了他后来岁月中深刻的思辨。 本卷所呈献的希腊城邦研究,属于沃格林思想中可谓最“基督教”的阶段。希腊秩序及其“心灵形式”被放进一个世界历史规模的宏大进程之中。《政治的新科学》勾勒了这一进程,根据尤尔根?戈布哈特的评论,它: 提出了一种政治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与基督教历史哲学遥相呼应。本书可以理解为一位奥古斯丁基督徒的著作,他的用意是重申奥古斯丁意义上的基督教秩序观念,直面灵知主义的异端邪说……超越单个文明循环的更庞大的循环在这里若隐若现。这个循环的顶点,是以基督的出现为标志的;前基督的高度文明将成为它向上的支脉;现代灵知文明将成为它向下的支脉。 精神在几个社会和文明中相继走向分殊化,随之而来的宏大历史叙事的狂飙,让人油然想起黑格尔。不过,沃格林的事业,与黑格尔的具有截然不同的气魄。因为它不寻求调和,而是以思想运动———追寻秩序,来反对思想家当下的政治现实。正如赫尔穆特·科恩所察觉的,沃格林的研究,旨在重拾“救赎的知识(Heilserkenntnis),这种知识之所以被掩埋起来,不是由于偶尔的疏于理解或恶意,而是由于历史运动本身”。换言之,沃格林的研究,是秩序的历史,同样也是谬误的系谱。 《政治的新科学》与在前三卷中所执行的《秩序与历史》的本来目标,其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皈依于一个古老的传统。沃格林与奥古斯丁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秩序与历史》每一卷的卷首语,就是明证(包括后来在他的慕尼黑岁月之后所出现的)。在本卷的导论中,这种联系尤为明显。在此,沃格林利用了奥古斯丁对追溯到柏拉图的三种神学的讨论———这是沃格林反复兜来兜去的重要主题。往大处说,沃格林力求使奥古斯丁那个超越王权(regna)兴衰的“神圣历史”(historia sacra)概念,适应现代科学所提供的辽阔的历史地平线和历史资料财富。在他政治学的新科学中,沃格林加入了基督教的新柏拉图主义传统,据他看来,希腊思想中最深刻的见解,与基督教神学的信条,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沃格林当然不会去做基督教卫道士。哲学与历史不是信仰的婢女,某种意义上,信仰是以另一种不可通约的方式赐予或者达到的。这个研究不是从神学前提出发的。正如沃格林在1956年写给他的朋友罗伯特·海尔曼(Robert B. Heilman)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形而上学不是任何东西的‘前提’……而只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家用理性符号解说他的各经验,特别是对超验性的经验。”在修改了原来的计划之后,随着《秩序与历史》第四卷的付梓出版,有一点十分明显,尤其是在沃格林对圣保罗的论述中,那就是,沃格林认为基督教符号体系,与其他任何符号体系一样都是建立在相同方法论基础上,是对经验的言说,应屈从于批判性分析。事实上,他的一些认为沃格林的著作是在智识上捍卫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的读者,对此难免大失所望。 早期教会的很多神父,都对希腊遗产抱有敌意;但是基督教传统的这一个部分,并不排斥异教徒的过去,倒是不遗余力地从它身上获取论据,去强化它自身的启示,将柏拉图这位“天生的基督徒”(naturaliter christianus)看做是希腊的,其实也是一切前基督教异端的智慧无与伦比的顶峰。它把我们习惯称之为前苏格拉底的东西,视为柏拉图的前奏,而把他之后的视为一种回潮。据此,就像它渊源于圣奥古斯丁一样明显,它无疑也深受希腊和罗马教科书的影响,这些教科书根据“学派”和“嫡系”来对哲学家评头论足。有趣的是,虽然沃格林正确地指出,根据“学派”来划分早期希腊思想家,是一种引人入歧途的古代思想编纂的俗套(doxographic convention),但他却跟奥古斯丁一样,按照“爱奥尼亚派”和“意大利派”来处理他们。不过,决定这种编纂方法的,首先还是在于柏拉图领袖群伦的地位。 对始于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来说,柏拉图的宗教经验与摩西的没有实质区别。确实,奥古斯丁宁可相信柏拉图读过摩西。要假定文献之间具有亲缘关系,先决条件就是坚持说它们是大同小异的。奥古斯丁在《蒂迈欧篇》和《创世记》之间发现了一种对应关系。更根本的是,上帝回答摩西,“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he who is),这一回答所表达的难以言传的存在大全,据奥古斯丁说,正是柏拉图“热烈拥护、不遗余力去传播的”信条。因为,柏拉图坚持“与真正的在者相比,一切顺应变化而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无存在”。哲学家,从词源学上,意思是爱智者,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爱上帝者,这样,对奥古斯丁来说,柏拉图就可以跟摩西相提并论了。同样,沃格林写对应的“存在的飞跃”,力图将希伯来和希腊对存在秩序的见识画上等号。沃格林引述亚历山大的圣克莱门的话,将他的导论归结为:“以色列和希腊的《圣经》,都是基督教的《旧约》。” 虽然沃格林不是旨在复归,也就是纯粹返回到一种古老的理论中去,但他的著作具有很多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特点:专以复兴柏拉图的智慧为己任的哲学和哲学史,被理解为一种诊疗手术,是为了解除今天的精神痼疾而实施的。这位思想家认识到有必要诉诸符号,虽然他知道这些符号本身也难免有缺陷,同时也诉诸存放于上天,而经验于内心(in immo cordis)的模式,看到了克服符号缺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相应地,对相关文本做有意义的解读,就要求一种内心的转变。例如,马斯里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建议读者采取柏拉图的心态(frame of mind),来接近《巴门尼德篇》这一“神圣文本”。同样,沃格林邀请他的读者诚心解释(pia interpretatio)重要的文献,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外部的权威或盲目接受的事实,而是一种内部准备,是让大家都有机会去做阐释者。费奇诺划分了上天计划演变的“激发期”和“阐释期”,重现为导致新突破的解体期和相对稳定、智识平静的时期的交替,这构成了沃格林的叙事。费奇诺所期待的,是全基督教不拘泥于教义,考虑多种多样的宗教表达,又能同时给予基督教最高的尊崇,而那时沃格林著作的特色就在于此。这种立场,与柏拉图《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中否定式的开放(apophatic openness)不谋而合。这封信声称,关于作者对圣事的理解,谁都不曾见到过什么系统的教义。这封信对费奇诺十分重要,也是沃格林下一卷分析的出发点。根据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第一卷开头提纲挈领的警句,“历史之秩序产生于秩序之历史”。显然,作者对历史秩序的理解,反过来也塑造了多种秩序研究———包括《城邦的世界》。 《城邦的世界》是沃格林的五卷本巨著《秩序与历史》的第二卷,作者重点考察了“无柏拉图的希腊”这段历史时期,追溯并重估了其背后的秩序理念,并从古希腊城邦的盛衰中,剥析出了现实世界失序的历史源头,这与整个五卷本的宏大哲学努力,也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