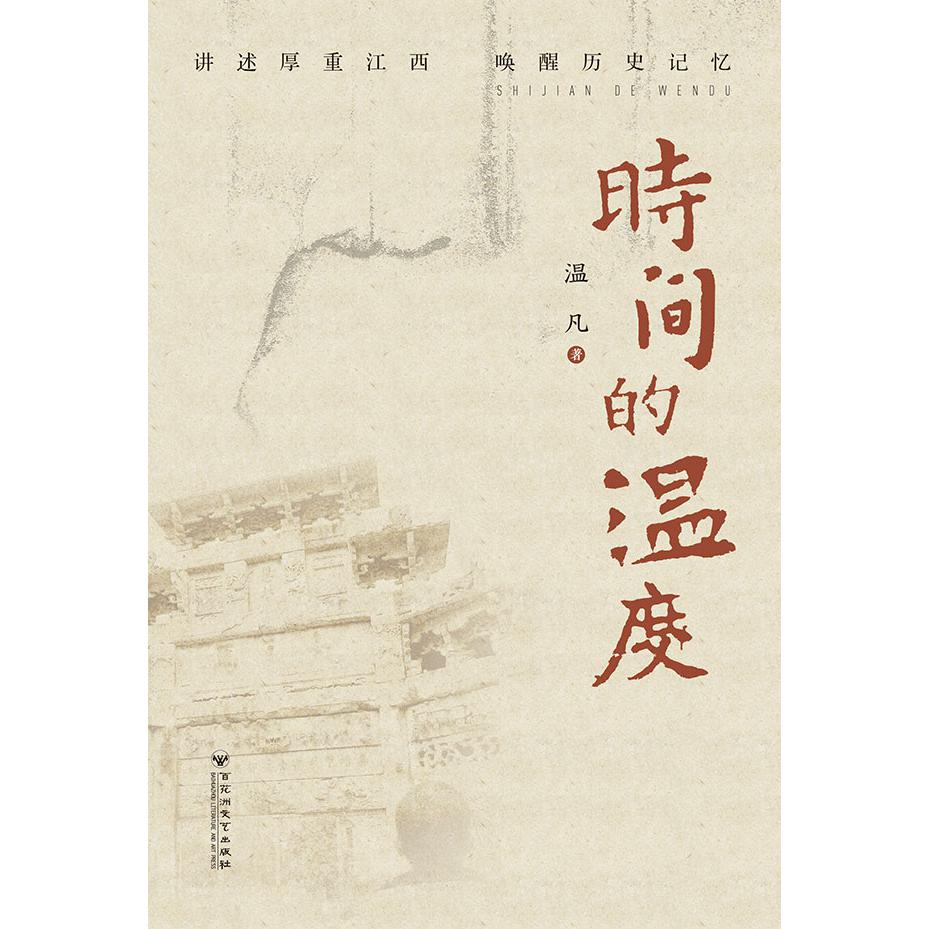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时间的温度
ISBN: 9787550049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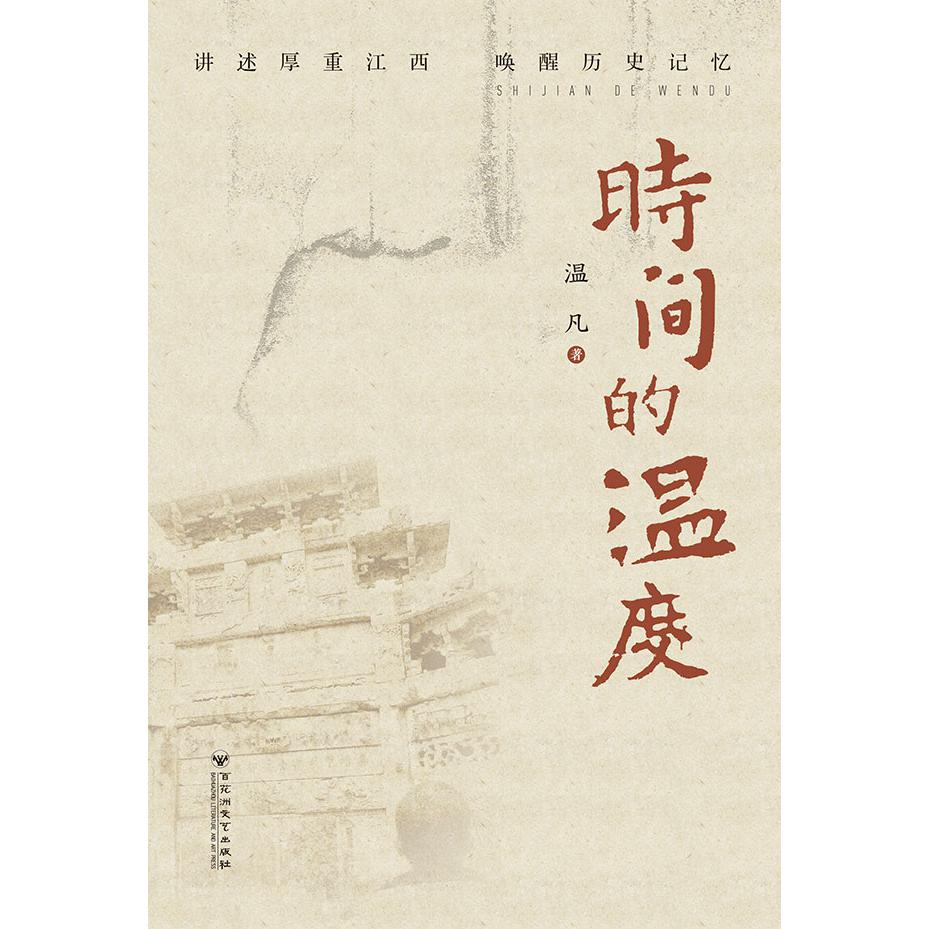
温凡,1973年3月出生于江西省宁都县,现供职于江西日报社。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抚州文学院特聘作家,资深媒体人,从事新闻工作20余年、文学创作30余载。自1990年以来,在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电影评论等。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刊发。参与策划并担任主撰稿人的“当汤显祖遇见莎士比亚”课题被评为全国33个公共外交典型案例之一,入选《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一书。
样章 解码《牡丹亭》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67岁的汤显祖在住地临川玉茗堂溘然辞世的那一刻,他不会想到,自己创作的作品,能够延续数百年之久,依旧传唱不衰。400多年来,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戏曲作品在海内外广泛流传,被誉为世界古典戏曲名著,汤显祖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拂去岁月的尘埃,我们可以窥见,除了《牡丹亭》本身的经典,与这部经世作品相关的种种,竟然也颇具传奇色彩。 一 一部世界级伟大戏剧作品的存世,必定少不了各种相左的看法。关于《牡丹亭》创作地和成稿时间,赣浙两位专家学者针锋相对的意见,以其不唯家乡情的立场赢得了学界的尊重。 按理说,作品的故事由来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因为汤显祖在开篇的《牡丹亭题词》中就已经交代得一清二楚:“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也就是说,《牡丹亭》的故事来自这两个传说。武都守李仲文的故事出自东晋陶潜的《搜神记》卷四,广州守冯孝将的故事出自南朝刘敬叔《异苑》卷八。但是,这两位太守儿女为爱死而复生的故事,似乎只是汤翁卖的一个关子。 20世纪50年代末,有学者根据明代目录学家晁瑮编撰的《宝文堂书目》中的话本《杜丽娘记》和明何大抡辑《重刻增补燕居笔记》中《杜丽娘慕色还魂记》的故事,认定这才是《牡丹亭》故事的源头。 20世纪90年代,江西大余县退休高级讲师谢传梅经过十几年潜心研究,有了新的发现,他在大余搜集到多个版本的类似传说,并查找到南宋大学者洪迈在其著作《夷坚志》和《夷坚志支甲》中记载了两个与《牡丹亭》内容大体相似的故事。所以,谢传梅认为,汤显祖并不只是随意地将《牡丹亭》故事的发生地放在南安府(现今的大余县),其创作的原文也和南安府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这里,有必要重提汤显祖的一段经历。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朝廷发生了一起弹劾案。在那个朝代,弹劾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由于皇权体制,各种纷争只能由天字第一号裁判定夺,所以弹劾作为各方势力博弈的一种方式,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多臣子只是奉命行事,上朝时刀光剑影,退朝了依旧躬迎揖请。 这起弹劾案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历史上只是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件,但在中华戏剧史上,却无意间埋下了影响世界的种子。 弹劾的对象叫申时行,曾在明万历年间任内阁首辅。在他任首辅数年间,弹劾者众多,仅在万历十九年,就有多位大臣单独或联名上疏弹劾,其中就有时任南京礼部主事的汤显祖。 和大多数人的命运相似的是,汤主事的弹劾状没有受到神宗皇上的待见,还被反奏为以己之私假借国事攻击首辅。神宗这回倒是信了,一怒之下将汤主事赶出朝廷,贬至南蛮之地的广东徐闻县当典史。 从南京到徐闻要经过江西的一座小城-南安府(今大余县),南安府境内有一座两省交界的大山:梅岭。唐朝以来,梅岭在商业贸易互通等方面一直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古代陆上的丝绸之路。出了梅岭,就是荒凉的关外。 也正因此,郁郁的汤显祖在南安府磨叽了好几天。也许是有了感情,半年后,升任浙江遂昌县令的他再次途经此地时,即使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汤县令,依旧在此地逗留了好些日子。 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汤显祖呢? 谢传梅考证的当地传奇故事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进入他的视线的。7年后,汤显祖把那段感天动地的爱情传奇发生地放在了南安府,而不是《杜丽娘慕色还魂记》的广东南雄。《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中借杜丽娘念诵的《乌夜啼》词“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以及杜丽娘生前常向梅树倾诉,死后安葬在梅树下面等多个情节,可见这两次大余之行对汤显祖影响至深。 知名学者徐朔方是这样解读的: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古代传说自然容易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而汤显祖认为无论是杜丽娘的故事还是大余当地的传奇,整理者都还年轻,故事不够老,难以令人信服,所以才在题词中抬出年代更久远、传播力更广的另外两个类似故事作为话本的佐证。 《牡丹亭》故事的由来,学者们的研究结果稍显温和。但关于创作时间和地点的争议则有一点火药味。一方认为是万历二十五年完稿于浙江的遂昌,另一方则认为是万历二十六年完稿于江西的临川。 “遂昌说”的主要依据来自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通史》,其中写道:“大约在投劾回家的前一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汤显祖写成杰出的古典名剧《牡丹亭》传奇。”剧作家石凌鹤在《凌鹤剧作选》中《遂昌弃官》一节,描写了汤显祖在遂昌的生活经历,其中就有其创作及指导小红演唱《牡丹亭》等情节。 “临川说”的依据则出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汤显祖条目记录:“万历二十六年……秋天,从临川东郊文昌里迁居城内沙井巷。著名的玉茗堂和清远楼就在这里,传奇《牡丹亭还魂记》也在此时完成。”我国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徐朔方在其编写的《汤显祖年谱》中给予了确认,并在其著作的《汤显祖评传》中提到一个细节:汤显祖“临川四梦”的其他三篇题词所署年份都是创作完成之时,或润色改定的年代。由此推断,《牡丹亭》所题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就是创作及完成的年份。同时,他于《汤显祖全集》中笺注:“《牡丹亭》成于遂昌说,难以自圆其理。” 有意思的是,“遂昌说”的主要传播者石凌鹤是江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主席。而“临川说”的主要研究学者徐朔方是浙江人,一直在浙做学问研究。两位专家学者都没有因为自己的省籍身份而影响研究成果,观点的相左或许只是取材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这点着实令人敬仰。 回到弹劾案。我们可以大胆臆想,正是那次弹劾未遂的遭遇,大明王朝少了一位有思想的官员,多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戏剧大师。 这是汤主事为官生涯的不幸,却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幸事! 二 一座名楼的公演瞬间燃爆了世人对《牡丹亭》的喜爱,旋即在戏曲界引发了一场交锋激烈的“汤沈之争”。几百年后,一位名将后代给作品注入了新的青春活力,也成了这部名作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 在汤显祖的那个年代,南昌还不叫英雄城,但在江畔有一座楼阁,从建成之后一直蜚声大江南北,那就是滕王阁。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几经损毁的滕王阁完成了第五次修建,落成大典选在当年的重阳节。典礼本是一件平常事,但是由于其间的一台戏,让这次庆典在滕王阁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这出戏瞬间传唱。 这台戏就是《牡丹亭》。 汤显祖是南昌的熟客,从第一次乡试题名到后来无数次的过境停留,在南昌,他结交了许多文朋诗友。对于滕王阁,他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多少次对酒当歌,凭江而眺。但是,这次庆典对他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我们无法重现当年公演的盛况,只能通过几条线索来推测演出的效果和影响力。首先是汤显祖本人,很显然他对名伶王有信的表演颇为满意,当场作赋《滕王阁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二首,其中第一首是这样写的:“韵若笙箫气若丝,牡丹魂梦去来时。河移客散江波起,不解消魂不遣知。”再就是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的记录:“《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就这样,名楼滕王阁与名作《牡丹亭》完成了一次堪称完美的和谐之舞,那一年的曲艺史上,它们是绝对的主角。 今天,我们登临滕王阁,在第三层中厅的屏壁上,还能看到一幅壁画,这幅2. 8米*5. 5米的丙烯壁画取名《临川梦》,展示的就是汤显祖在滕王阁排演《牡丹亭》的故事。南昌市社科院特聘研究员、潜心研究“汤显祖与南昌”课题10余年的萧德齐表示,正是在滕王阁的公演,让《牡丹亭》不再限于临川一隅,促其成为传唱天下的名作。而同样是《牡丹亭》,让“江南第一楼”平添了几分文化的厚度。 汤翁在滕王阁迎来了他戏曲人生的一个巅峰,随后则经历了一次纷争,对手是与他同时代的戏曲家沈璟。两位戏曲大师就《牡丹亭》的音律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言辞激烈,被称为“汤沈之争”。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段纷争的来龙去脉:简单地说,就是《牡丹亭》闻名之后,无论在官场还是民间都非常受欢迎。但是,在千里之外的苏州,一贯严谨的昆曲家沈璟认为《牡丹亭》的唱法是昆曲,但其中有些韵律有明显错误,所以他按照昆腔的韵律进行了调整,并修改了一个话本《同梦记》公开演出。那时没有现代的互联网传播媒介,所以汤显祖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这事。直到一位友人给他寄了一本《同梦记》的印本,顿时引发了汤翁的强烈不满。 目前汤学研究者引用最广泛的是两段文字,分别代表两人的观点和态度。沈璟提出修改的理由同时,尖锐地指出《牡丹亭》的问题:“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中之之巧。”汤显祖的回击则非常直接和情绪化:“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大意就是,沈璟认为《牡丹亭》中的昆曲韵律有些低级错误,而汤翁的反击是谁说《牡丹亭》就是昆曲了,你有那么大本事能让昆曲统一天下? 后来众多汤学研究者对于“汤沈之争”有着各种分析和解剖,有的将两者之争上升到了封建思想与反封建思想的政治高度。有的则将两人的争论提升到了“临川派”和“吴江派”之间的交锋。其中,既有学术之争,又有意气之论;既有基本理论的认识不同,又有历史材料的理解差异。因此,对于“汤沈之争”的研究竟然持续了数百年,依旧未有定论。 真实情况或许并没有汤学研究者们所说的那般复杂和高深。因为“汤沈之争”只是一场隔空交锋,两位当事者虽然同时代却素无交往。支撑这段曲艺公案的依据,就是几封写给第三人的书信。回归到作品本身,也许就是这么简单:汤显祖要求格律服从文辞,服从内容;沈璟则强调文辞服从格律,服从观众。 就在“汤沈之争”绵延300余年之后,在中国台湾,一位名将的后代低调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给《牡丹亭》注入了新鲜元素。他叫白先勇,是戎马一生的白崇禧将军的公子。2004年,由他领军打造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被视为不仅唤醒了昆曲的青春,也唤回了《牡丹亭》的青春生命。 白先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是9岁那年随母亲第一次去看戏,看到梅兰芳参演的《牡丹亭》时,瞬间就迷上了,此后再没有放下,从此致力推广昆曲《牡丹亭》。2004年4月,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市台湾大剧院首演,吸引近万名观众,宛如《牡丹亭》滕王阁公演盛况再现。白先生时年67岁。 之后,青春版《牡丹亭》启动了全国巡演、全球巡演。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受到众多年轻观众的热捧。在一系列的巡演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创造了昆曲演出史上前所未有的成绩。滕王阁公演、汤沈之争、全球巡演。纵观《牡丹亭》的一件件往事,就如影视剧的情节,峰回路转、高低起伏,最终结局皆大欢喜。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正是以汤翁为代表的众多艺术家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和《牡丹亭》作品本身不朽的艺术价值。 主要收录作者发表于《江西日报》等报刊上的作品,作者以新闻的视角和文学的叙事方式,对赣地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度的解读,讲述王安石、王阳明、汤显祖、曾巩、颜真卿等历史人物的江西故事,探寻赣州古城墙、抚州文昌里等历史建筑背后的人文意义,探索江西古村落文化、广昌莲文化等赣地独特的文化现象。这是一部有温度的新闻作品集,是一部展现江西形象、讲好江西故事的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