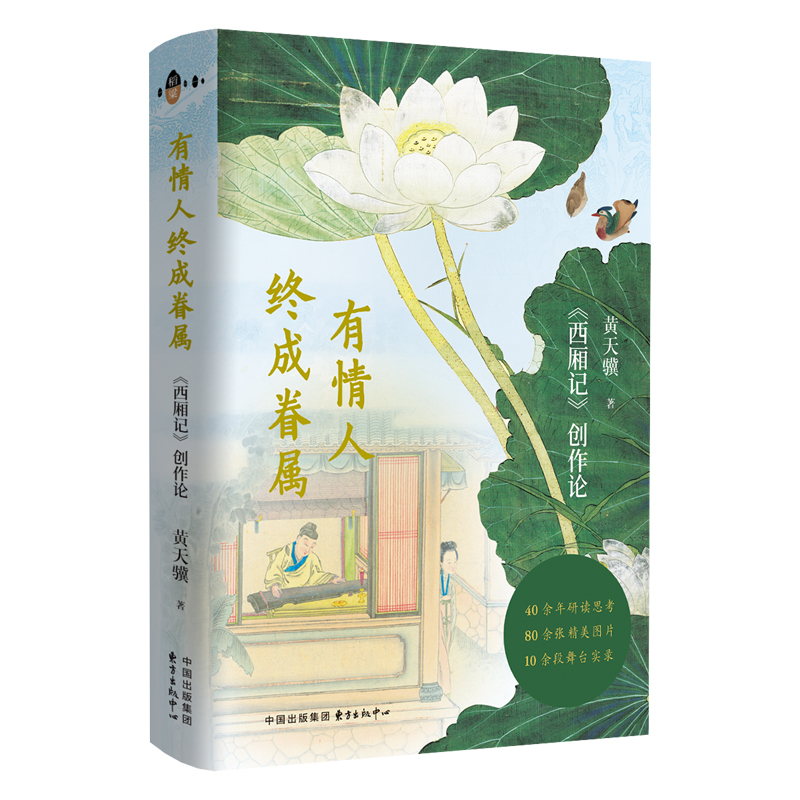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7.20
折扣购买: 有情人终成眷属——《西厢记》创作论
ISBN: 9787547324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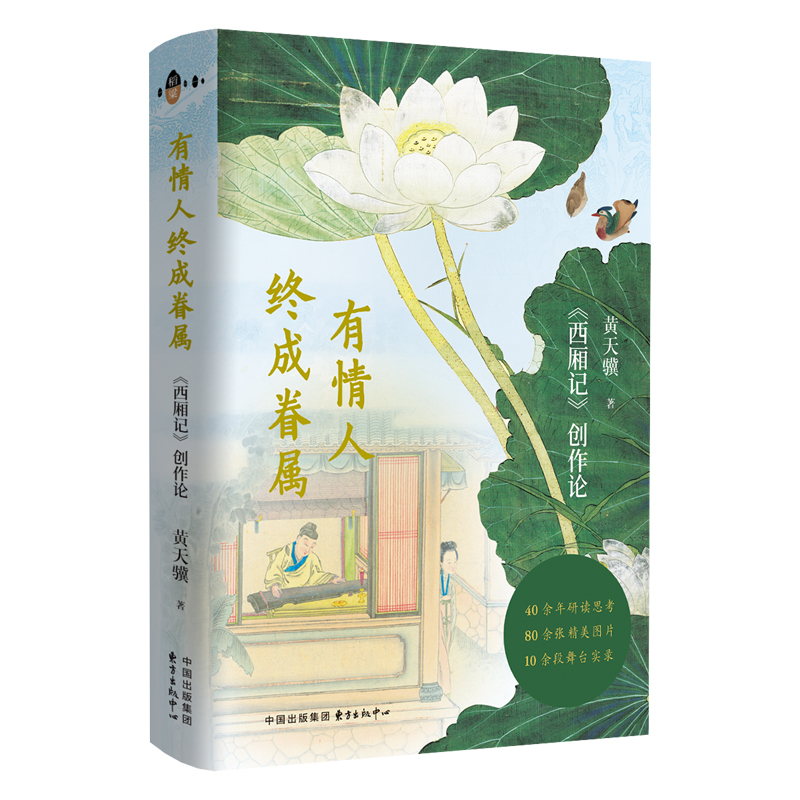
黄天骥,著名古典文学专家,1935 年出生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曾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黄天骥教授治学育人,桃李满天下,为国家级教学名师。出版有《黄天骥文集》(十五卷)及《岭南师友》《唐诗三百年》等。
入元以后,戏曲表演成了艺坛的主流。这包括唱念做打的表演形式,让观众趋之若鹜。那时候,诸宫调、说书、杂耍等伎艺,虽然还在舞台上流行,但以故事情节为主干,把诸般伎艺综合起来进行表演的戏曲,在艺术形态上,明显更能适应时代审美的需要。一时大河上下,塞北江南,艺人们争相把故事编演,我国剧坛也出现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戏曲这一表演形态在艺坛冉冉上升之际,突然冒出万丈光芒,出现了一部震古烁今的剧作,这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 中国人,有谁不知道《西厢记》? 中国人,有谁不晓得那“待月西厢下”的莺莺?不晓得那风流倜傥颇似“银样镴枪头”的张生?不晓得热情地为人牵丝引线的红娘? 贾仲明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其实,《西厢记》的出现,岂止在当时压倒一大片,千百年间,它在剧坛上的成就,又有哪一部作品能够企及?或者说,在同样是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剧作中,只有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差可比肩。不过,就剧本情节结构的完整性而言,《王西厢》优于《牡丹亭》;就其在普罗大众中的影响而言,《王西厢》也大于《牡丹亭》。 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对元代剧作家的创作风格有过很形象的评价,他说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确实,王实甫不像关汉卿那样以豪辣酣畅的笔法描写现实,不会像醉客般发出浪漫主义的遐想。《王西厢》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它确像是在鲜花丛中徘徊的美人,活色生香,悠游顾盼,婉婉动人。而剧作者那细腻优美的笔触,却写出了人的思想感情最细微的律动。 不错,《王西厢》这“新杂剧”,是以元稹的“旧传奇”作为创作的蓝本的。但它在爱情故事中表现人性的萌动,其强烈程度远高于《会真记》与《董西厢》。可以说,它让我国古代剧坛第一次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判断作家和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最重要的是看他能否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王西厢》之所以能称雄于一代,夺魁于文坛,正是由于它有新变。这变,表现于创造了爱情故事的新题旨,让“旧传奇”呈现新格局。 前面说过,入宋以后,在剧坛上,已经出现不少以崔张故事为题材的戏剧,不过,它们都没有流传下来。原因很简单,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登上舞台,就如一轮红日,破晓时喷薄而出,它的光辉,笼罩一切,别的写崔张情事的戏,像是黎明时分的星星,都变得黯淡无光,久而久之,自然也销声匿迹。 不错,《王西厢》所写的崔张故事,其情节进行、人物关系,与《董西厢》没有很大的差异。诸如崔张在佛殿上奇逢,月夜琴挑,隔墙吟和,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等,骤然看去,它似乎是《董西厢》的翻版。更有甚者,《王西厢》在不少地方,还改头换面地搬用《董西厢》的词句。例如: (1)《董西厢》:颠来倒去,全不害心烦。 ——卷一【大石调?·?蓦山溪】 《王西厢》:使别人颠倒恶心烦。 ——第三本第二折【中吕?·?快活三】 (2)《董西厢》:不会看经,不会礼忏。 ——卷二【仙吕调?·?绣带儿】 《王西厢》: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 ——第二本楔子【正宫?·?端正好】 (3)《董西厢》:戒刀举把群贼来斩,送斋时做一顿馒头馅。 ——卷二【仙吕调?·?尾】 《王西厢》:我将这五千人做一顿馒头馅。 ——第二本楔子【正宫?·?叨叨令】 像这样的情况,在《王西厢》里是经常发生的。这也难怪,因为《董西厢》的语言,实在妙不可言。正如吴梅先生说:“董词的文章,实是天下古今第一”,“前人赞他好,是拣他词藻美艳处;我赞他的好,在本色白描处……董词文章,就是平铺直叙,却不全用词藻,方言俗语,随手拈来,另有一种幽爽清朗的风致”。王实甫把董解元用过的词语,顺手牵羊,窃而用之,这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有趣的是,王实甫在偷龙转凤的过程中,有些地方,还会发生点金成铁、张冠李戴的毛病。像在第一本第二折,《王西厢》让张生一上场便唱【中吕?·?粉蝶儿】一曲:“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借与我半间儿客舍僧房,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儿相向。”所谓“不做周方”者,不给予方便之谓也。从《董西厢》的剧情看,张生“惊艳”后,便向法聪问这问那,要求借给他僧房半间,“早晚温习经史”,实则想找寻机会接近莺莺,而法聪,则一一答应了;《王西厢》倒让张生劈头便埋怨他不给予方便,这实在毫无道理。 不过,若把这段情节和《董西厢》作一比较,事情便可清楚。原来,《董西厢》在写张生初遇莺莺时,有这样一段描写:“佳人见生,羞婉而入”,张生便冲了上去,岂知被法聪“一只手把秀才捽住,吃搭搭地拖将柳阴里去”,并且对他鲁莽的行为一再劝阻。对张生来说,这法聪和尚确是不给予他方便的,因此,《董西厢》便有这句“不做周方”的唱词。《王西厢》没有采用《董西厢》的这一细节,或者,有些版本原来有此细节,却被后来的整理者删去了,而在唱词上,又疏于照应,于是就冒出了“不做周方”的话头,让观众感到莫名其妙。 又例如,在第二本第一折,王实甫让崔莺莺唱【油葫芦】一曲: ……这些时坐又不安,睡又不稳,我欲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每日价情思睡昏昏。 对这曲,凌蒙初认为:“‘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数语,乃道张生者,移为莺语,觉非女人本色。”的确,所谓登临,是指登高望远,这话用于莺莺,不合她的身份,女孩子深锁闺中,不可能有什么登临的举动。一查《董西厢》,这原来属于写张生的唱词。它说张生自从遇见莺莺,坐立不安,六神无主,“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坐地又昏沉”(卷一【正宫?·?尾】)。显然,王实甫把这句唱词搬用过来,稍一疏忽,移作莺莺语,便让人觉得不是女人本色。 《王西厢》脱胎于《董西厢》,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从它的总体格局来看,是全新的。这一来,莺莺和张生的故事就有了质的飞跃。在杂剧中,剧中人虽然也叫张生、莺莺,但两者的个性、神韵,绝不是《董西厢》里的张生和莺莺,正如《董西厢》的张生和莺莺,并非《会真记》所写的同名人物一样。 崔张故事人物名字和题材同一,而其实质却有根本的变化,人们把这现象称为“幻”。像明代闵遇五在崇祯年间刻印的本子,称为“六幻《西厢》本”。他所谓“六幻”是说崔张故事经过六次的幻变:元稹《会真记》为“幻因”;董解元《西厢记??弹词》为“??幻”;王实甫《西厢记》为“剧幻”;传说关汉卿续写的《西厢记》第五本为“赓幻”;李日华《南西厢记》为“更幻”;陆采的《南西厢记》为“幻住”。后三幻,可以不论;而前三次的幻变,确是崔张故事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其实,这三次的“幻”,正是不同时代婚恋观变化的产物。社会意识形态的蜃影,折射到文坛上,作者的笔触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导致笔下的同名人物,具有不同的神韵。名同而神异,人物神韵、个性的不同,让人物关系生发出不同的含义,从而使故事的题旨出现实质性的变化,这就是“幻”。 就前三“幻”而言,《王西厢》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它让人们看到,在12世纪的中国大地上,有一个幻影在徘徊。 人问影:你是谁? 影回答:我是“人”! “《西厢记》天下夺魁”,这是古人对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高度赞誉。然而这部杰作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作者的灵心慧性如何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绝妙好辞与生动情节如何得到完美的结合?“始乱终弃”的悲剧故事如何获得脱胎换骨的升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丽主题如何得到提炼?莺莺和张生的心灵交流如何逐步展现?红娘如何成为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婢女形象?凡此种种,本书都作了细致深刻的分析,丝丝入扣,引人入胜。黄天骥先生堪称王实甫的异代知音! ——莫砺锋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被元代人评为“天下夺魁”的《西厢记》,作为公认的经典名作,八百年成为渗透在中华民族情感记忆中的文化典型。黄天骥先生从“张生为什么跳墙”的疑问开始,用至少四十年的研读和思考,从剧作聚焦的“情”中,剖析人性情感,解读关目排场,回应戏理体局。尤其是先生建构的“创作论”,将王季思先生《西厢记校注》通过诗文与戏曲互证、董每戡先生《西厢记论》通过剧史与剧论互释的方法,交融渗透,完成了案头创作规律与场上演剧法则的理论阐释,让“西厢记”的典型价值和青春理想得以绵延增衍。 ——王馗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