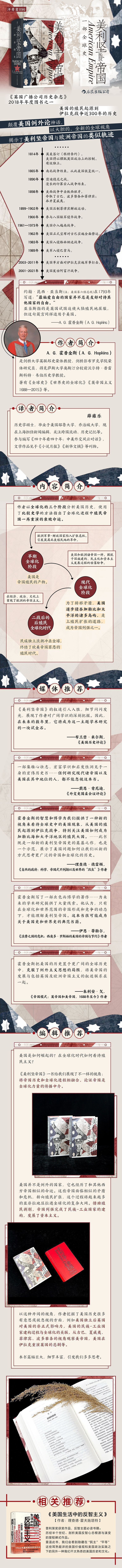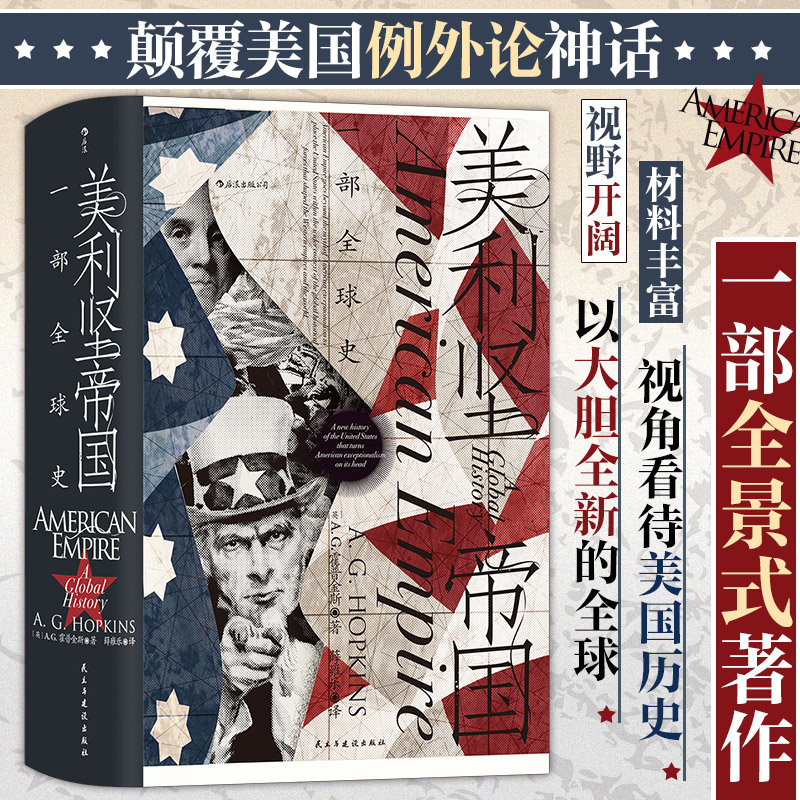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原售价: 160.00
折扣价: 102.50
折扣购买: 汗青堂096:美利坚帝国:一部全球史
ISBN: 97875139367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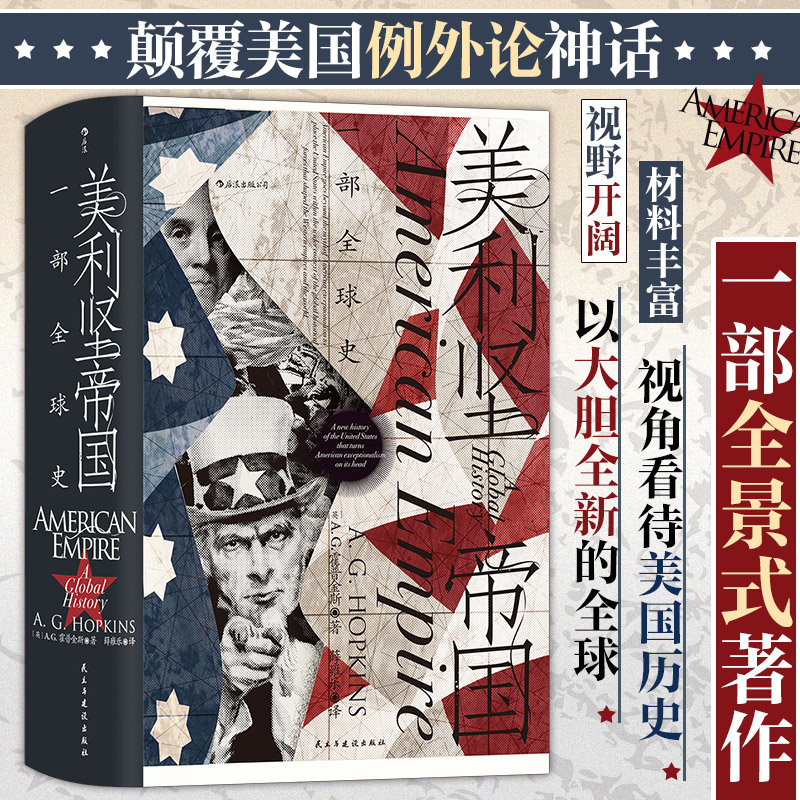
A. G. 霍普金斯(A. G. Hopkins)是剑桥大学英联邦史荣休教授、剑桥彭布罗克学院荣休研究员、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前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伯历史学教授。著有《全球史》《世界史中的全球化》《英帝国主义,1688—2015》等。
尾 声 解放的教训 伊拉克,2003—2011 …… 在1915年开始的库特围城战和2003年经过库特的侵略军之间,显然有一些相同之处。最著名的是,英国和美国都宣称自己是作为解放者而不是作为占领者到来的。接着,它们安顿下来的方式却使它们无法早早撤离。侵略者们毫无疑问地相信自己价值观的优越性,对他们将征服并控制的人民则了解有限。伴随着军事胜利的是对战后秩序规划的欠缺。占领所激起的反抗被人误解,也被错误应对。这两支军队都没有接受过如何应对“叛军”的训练。民事和军事当局之间的沟通常常欠缺,有时还出现失调。这两个大国都没有撤军策略,又都被害怕丢脸的心理所强烈地驱使。大国都自我肯定,感觉自己比其他国家更优越,这点不足为奇。自信和无知混合起来驱动了武断,从而造成了规划的缺陷,汤森德和叶夫宁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明白了这点。战事甚至搅乱了最完善的规划。预测中的短暂战争轻而易举地变成了泥潭。毁灭既简单又迅速,建设则费力、复杂而代价高昂。当地社会远比对它们的刻板形象复杂。每一次发生侵略时,这些事实都会被当成新鲜事被人重新发现。 评论家们援引了这些及其他相似事例,来支持有关英国和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的宏大断言。美国被视为“帝国的继承人”,这两个大国都被拿来和罗马相比。对西方各帝国做全面排序是为了预测。此前的帝国最终都衰落了,有些则突然覆灭。英国从罗马身上学到的东西,美国可能也会从英国身上学到。如果将历史分析和当今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决策者们可能就可以避免衰退,巩固主导地位。 然而,在这里,明智的做法是暂停一下。这种程度的比较需要足够程度的相似性,这样才能识别个别的差异。比较史学最早也最著名的实践者之一伊本·赫勒敦明白,在不同研究对象间建立联系时需要小心。他写于1377年的著名作品《历史绪论》(Muqaddimah)将历史展现为一种系统性研究,关注的是经济及政治力量的互相作用,以及它们对社会和国家兴衰的影响。他认为,比较的好处在于既让人发现相似性,又让人发现区别。他也注意到,意识形态的企图可能会歪曲这一做法,方法的错误也可能会产生误导,导致错误的类比和灾难性的政策。伊本·赫勒敦的规诫强调,在比较对象的不同点可能更重要的时候,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会带来许多危险。 英国和美国都是主要大国,都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特点,其中有些刚刚已经列举。但是,其中许多相似性不仅确实存在,也是老生常谈,除了这两个被选中比较的国家,也适用于一系列其他国家。此外,如果说这些共同特点就能论证英国和美国都是帝国,那就有误导之嫌,除非对“帝国”一词采用非常笼统的解释,用其指代所有控制着种族核心之外地区的国家。然而,这样的说法带来的是蒙昧而不是启迪。罗马、威尼斯和美国的共同点可能不如它们之间的区别那样重要。 甚至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这些比较也不能成立,尽管它们是同时存在的工业民族国家,继承了共同遗产,也被认可为世界大国。正像全书论证的那样,英国和美国身处的全球背景在三个世纪中发生了大幅改变。英式和平所运作的时代要么偏好要么要求领土控制,而在美式和平发生的时代,吞并要么不现实,要么毫无必要。比较研究的潜力存在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那时获取并管理着一个领土帝国,但这一可能性被人忽略了,因为学者们长期以来把岛屿属地扔在默默无闻的幽暗之地。矛盾的是,比较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和潜在霸权国时激增,不过事实是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岛屿帝国已经瓦解,比较的基础已经被深刻地改变了。 在英国占主导地位时,帝国不只是国际舞台常见的一部分,也被视为国际声望的一个衡量标准。美国则在后殖民时代运转,这个时代对帝国主义和帝国都充满敌意。大英帝国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对付原型民族主义抗议,而不是在应对完全成形、组织完备的大众运动。美国不得不在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建立于自决原则之上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道路。1915年对伊拉克的侵略是民族国家间战争的一部分,英国可以通过动员印度军队来保卫帝国领土。美国则是在与超国家的运动组织相战斗,依赖的是由国家公民组成的志愿军。英国人遭遇的抵抗无法超越当地的攻击范围。美国则面对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地球任何地区进行打击的可能性。后殖民发展使毁灭手段民主化的速度,比使生活水平民主化的速度更快。 如果无视或低估历史背景,可疑的论点就会得到可信度。不同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威力方面常常被比较,仿佛可以不顾时间的流逝。如果这样估算,在比较美国和此前的大国时,就会得出美国是超级大国,甚至是“超级帝国”的结论。然而,绝对尺度所忽略的事实是,国际关系中的实力也是相对的。恰当的比较方法是把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它所面临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样算来,美国拥有的庞大军事威力在运用于被标为“叛乱”的运动时是不合适的,通常还适得其反。此外,“9·11”事件显示出,一次小规模行动可以造成大规模后果。如果大卫用弹弓和石头就能打倒你的话,那你就算是歌利亚也没有任何优势。 与其说问题在于集体性健忘,不如说问题在于选择性记忆。就像其他大国一样,所谓的“健忘症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传承了有利于当权者的历史元素,同时抛弃了可能会挑战主流正统的其他元素。因此,“解放的教训”常常不为人知或被人忽略。接着,傲慢就向着天谴发展,这在英国一例中来自过度扩张,在美国一例中则来自过度自信。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可能根本没有解决方案。大国可能无法克服它们过往的胜利所施加的限制。只有在回溯过去时,替代政策才开始受人赞同,但这已经太晚了,无法转为有效行动。正像2009—2010年驻阿富汗联军司令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承认的那样:“我们曾经懂得不够,现在也仍然懂得不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对现状和历史的理解都非常肤浅,而且我们对近年的历史——过去50年的历史——所持有观念简单得令人恐惧。”这些观察很有代表性,可能也格外诚实。麦克里斯特尔是在2011年说出这些话的,那时他已经在两场海湾战争中服过役。但是,在2003年侵略伊拉克之前,他所缺乏的那些知识就已经存在了。研究殖民统治和非殖民化的专家都清楚,一切都会以泪水终结。泪水依然在流淌。 1401年,伊本·赫勒敦作为与埃及政府关系密切的显赫大法官,不得不跟随马穆鲁克王朝苏丹纳西尔·法拉杰(al-Nasir Faraj)领导的军事行动。这场违背伊本·赫勒敦建议的远征规划不足,而当埃及军队的大部分力量从战场中撤下时,已输得无可挽回。此时,69岁的伊本·赫勒敦发现自己被可怕的征服者帖木儿围困在大马士革。此外,和陆军少将汤森德不同的是,他毫无获得增援的希望。绝望的情况需要绝望的解决方案:伊本·赫勒敦安排好别人用绳子将自己沿着城墙降下来,这样便可以和敌人谈判。在七个星期里,他用自己的博学给帖木儿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乃至他得以为自己和手下争取到安全通行权,不过为了达成协议,他不得不向俘获自己的对手提交一份关于北非的详尽情报的报告。 伊拉克泥潭很快就诱人上钩,然后缓慢地淹没了他们,这再次确认了伊本·赫勒敦的智慧,即历史是(或者应该是)一门“取得优秀统治”所需的实用艺术。尽管“历史教训”存在争议,但我们仍然可以争论它们的价值和缺陷,以确保政策至少是在接受证据而不是在不顾证据的情况下制定的。如今,历史学家不用为了自己国家的政府而被迫将自己置于人身危险之中,尤其是因为不同于伊本·赫勒敦,他们现在远离了力的走廊。但是,考虑到知识缺陷和政策缺陷之间的关系,这一行业仍需要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刻用绳子将它的代表们沿着城墙降下来,以确保它的声音能被强权者帐篷里的人听到。 美国是如何崛起的?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殖民主义?《美利坚帝国》一书给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视角:将帝国历史和全球化进程相融合,论证帝国是全球化力量的传播中介。 美国并不是例外的国家,它也经历了和其他西方帝国相似的命运。这些帝国面临相似的矛盾和危机,转向殖民扩张,这个过程将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地区拉进全球化的复杂大网。借助殖民剥削,帝国列强完成了民族-工业国家的建构,发展了资本主义。 以这种开阔的视角,作者挖掘了美国历史很多有意思或被忽视的方面,例如美国独立后英国对美国的非正式影响力,美国的民族-工业国家建构过程与全球化的关联,从古巴、夏威夷、菲律宾、波多黎各的视角观察美帝国,美国在伊拉克重演英国的悲剧等。本书篇幅巨大,细节丰富,引发我们多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