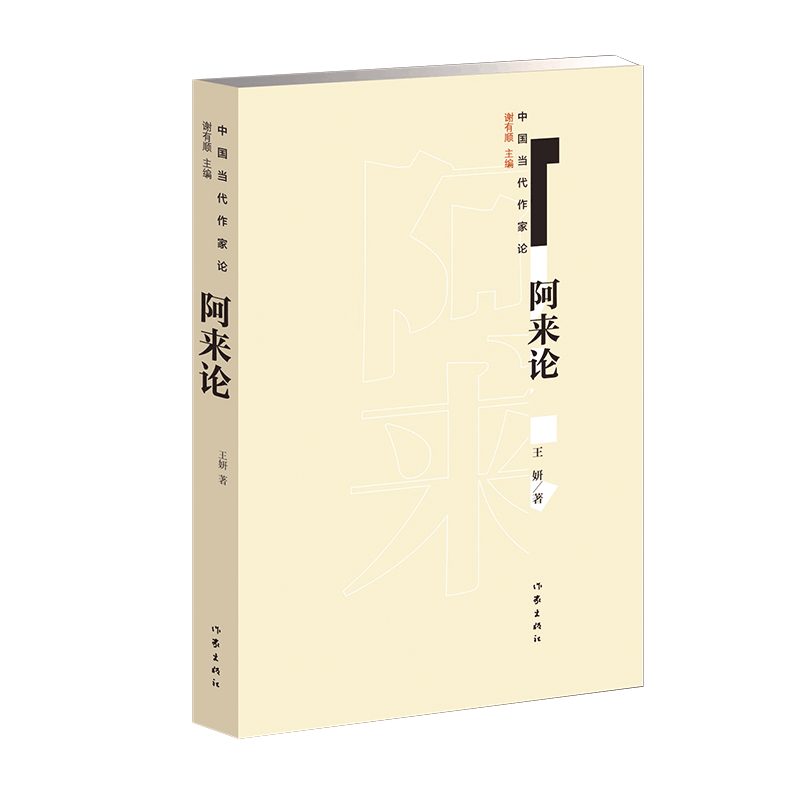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1.90
折扣购买: 阿来论
ISBN: 978752121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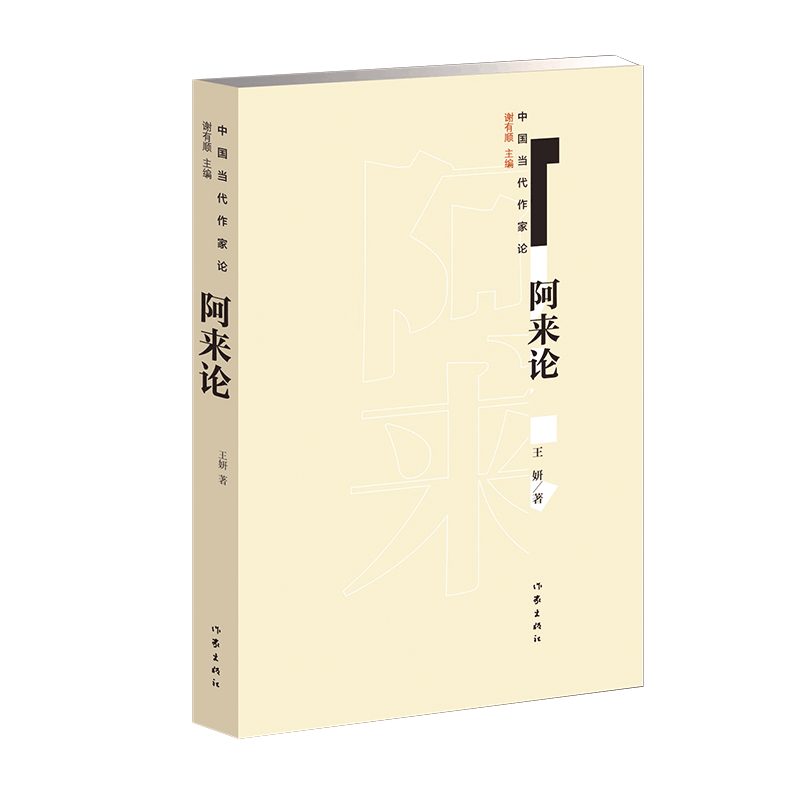
王妍:1981年出生,山东省枣庄市人,东北师范大学本科、硕士,辽宁师范大学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评论文章五十余篇,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等。
引论 消解、建构以及新的可能 我出生在这片构成大地阶梯的群山中间,并在那里生活、成长,直到36岁时,方才离开。……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 ——《大地的阶梯》 一 一个人的诞生蕴含着无数的偶然,一旦这个偶然与血亲、族人相关联,就开始有了不能摆脱的宿命。文学与生命一样都有其诞生的地方,出生的血地、生就的胎记与记忆的灵光都会成为伴其一生的文化土壤,参与绘制其生命的脉络与走向。1959年,阿来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俗称“四土”的马尔康县,具体说来是大渡河上游的“嘉绒藏族”中一个叫马塘的村寨。在藏语中,马尔康意为“火苗旺盛的地方”;而“嘉绒”则是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之间,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嘉’是汉人或者汉区的意思,‘绒’是河谷地带的农作区。两个词根合成一个词,字面的意思当然就是靠近汉地的农耕区。”①?阿来生命的前三十六年几乎都是在这个地方,他“更多的经历与故事,就深藏在这个过渡带上,那些群山深刻的褶皱中间”②。嘉绒这个蕴含特定地域生态空间、民族文化传统、情感思维方式、语言文化基因,甚至是独特“味道”的集体记忆,成为了阿来建构文学世界的基石。 具体说来,阿来出生在“一个在河谷台地上农耕的家族”③,母亲是藏族,父亲是一个偶然把生意做到藏区的回族商人(阿来的爷爷是回族,奶奶是汉族)。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是一群弟弟妹妹。“出身贫寒,经济窘迫,身患痼疾”④,连母亲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出生日期,只能大概给出两个月份以供选择。“阿来”⑤?是他的乳名,在汉语中多译作“阿努”(Anu)⑤,这是藏语中比较常见的名字,是“小孩”的意思。此处,我无意于探讨名字对人物的影响,但阿来在作品中一直秉承着孩童的纯真与本心,并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存在体验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童年,阿来曾这样回忆:“我也有过一个那样面孔脏污,眼光却泉水般清洁明亮的童年!想起日益远去的童年时光,内心总有一种隐隐的痛楚与莫名的忧伤!”⑥?他“从小长大的那个村子非常小,村庄住着大概有两百多口子人,每一户人家之间却隔着好几里地。到今天为止,我父母所居住的地方仍是孤零零的一家人。但这个村子在地域上又非常大,村子的东西向有一条公路穿过,大概二十多公里,南北向大致和东西向的距离差不多。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除了感觉到人跟人的关系之外,你还会意识到周围的世界当中有一个更强大的存在,这个存在就叫做自然界,河流、山脉、森林……”①。偏僻的地域、困窘的生活、浩瀚莫测的自然涤荡着他的灵魂、锤炼他的品格,也使幼小的阿来体味“无所归依的孤独与迷惘”②。同时,辽阔的自然是他“精神一片荒芜”的青少年时代的伙伴和老师,他跟草木对话,倾听群山的声音,对自然的感受和触摸延续至今。自然是他作品永恒的背景甚至书写的中心,但阿来却拒绝任何关于故乡大地的诗意伪饰,他带着庄严的责任感直面这片雄奇的大地。 归结来说阿来的成长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因子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 其一,汉藏之间的语言“穿行”以及藏族民间文化的滋养。阿来曾坦言“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③。而藏族民间文化对阿来的影响不仅止于故事、传说层面,更多是精神、气质性方面的影响,阿来正是努力对族群和民族文化进行朴拙的传达。张学昕在《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的民族身份》一文中指出“回到民族生活的内心,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获得更大发展的关键”,他认为一个作家无法摆脱民族文化的影响,故而民族作家如何准确地为自己书写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民族作家应表达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碰撞与历史发展也给民族作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④?民族性和地域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复杂的文化心理及传统资源是阿来创作的潜在质素,而阿来自己对藏民族的文化滋养也有着独特的论述和阐释。在他的很多散文和访谈之中,阿来不仅梳理了自己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关系,也对自己的创作内容及主旨做了清晰的阐释。 实际上,阿来的小学、初中是在“文革”中度过的,但在当时只有两三间教室的校舍内也进行着藏地普及汉语的教育,这对上学前仅懂得非常简单汉语的阿来而言,显然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开始时,他根本反应不过来老师在说些什么,惶惑到三年级某一天,突然听懂了老师说的一句汉话,这个“顿悟”使小小的阿来幸福无比。其中,所谓“悟”就是包含了感性和理性混合的一种藏民族思维方式,阿来曾坦言他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在“两种语言间‘流浪’”,“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他时常感到在“两种语言笼罩下”不同的“心灵景观”,并认为是“一种奇异的经验”①。我们发现,阿来作品中所包含的母语(藏语)思维也拓展了当代汉语的表现空间,“我是讲藏语中的一种方言,我用汉语写不下去了,或者是这种写法没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就用我懂的语言想。我可以用两个语言想一想,一下子又有了新鲜的表达”②。比如他在《尘埃落定》中用“骨头里冒泡泡”来形容爱情到来时的幸福感受,在《遥远的温泉》中用“整个草原都被呛住了”来比喻现代文明的入侵以及人心的堕落。阿来把一种非汉语的文化经验成功地融入到汉语表述之中,并把二者结合寻找到一种契合藏民族历史文化语境的话语方式,这种朴拙浑厚、自然直接、诗性透明而又沉郁飘逸的表达渐渐成为一种审美经验被复制和传播,丰富了当代汉语的表现经验和感受空间。 而藏族民间口耳相传的部族传说、家族故事、人物传奇和神话寓言,以及其中蕴含的民间立场与佛学因子都为阿来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在他的书写中我们不难体味到那种蕴含着藏族朴素思维和审美特征的表达。不仅如此,藏族传统故事、民歌,使得阿来“学会了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他的叙述自由穿行于现实与梦幻、理性与感性、过去与当下之间,有效地扩大了作品意义与情感空间,展现了“命运与激情”的痴缠。①?对阿来而言,文学言说本身就具有庄严的力量,他一直努力对族群和民族文化进行朴拙的传达,用质朴、直接的力量建构与世界更广阔的联系。读阿来的作品时,就像是围坐在藏族传统的火塘边,一面喝着酥油茶,一面涌动着创造与想象之翼。在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时间与空间、人界与神界的自由挪移中,历史已经隐遁为遥远的回声,现实也只剩下隐约的倒影,只有文学的书写、文学的可能真实地存在。 其二,藏回汉混血的民族身份、汉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多元文化的动态融通。②?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段难以释怀的经历的反刍。“我的母亲是藏族人,我的父亲是回族和汉族的混血,那么,我身上就是二分之一藏族,四分之一回族,四分之一汉族”③,藏回汉混血这种并不纯正的民族血统,“双族别”④?的多重文化身份一度给敏感的孩子阿来带来了困扰,“一些人对我这种血统不纯正的人的加入,很多时候是不屑,更有时候是相当愤怒的”①。在他很多早期作品中都有一个叫做阿来的懦弱孩子的影?子。②?阿来的很多作品中有着混血的人物,如《远方地平线》中的桑蒂(父亲藏族、母亲汉族)、《芙美,通向城市的道路》中的芙美(混血儿)、《蘑菇》中的嘉措(父亲汉族、母亲藏族)、《狩猎》中的“我”(汉藏混血)、《尘埃落定》中的二少爷(父亲藏族、母亲汉族)、《宝刀》中的刘晋藏(汉藏混血)、《蘑菇圈》中的胆巴(父亲汉族、母亲藏族)、《河上柏影》中的王泽周(父亲汉族、母亲藏族),还有因为父亲未知的缘故而血统不详的格拉(《格拉长大》)、斯炯和她的哥哥(《蘑菇圈》)等。《遥远的温泉》中写到“藏蛮子是外部世界的异族人对我们普遍的称呼。这是一种令我们气恼却又无可奈何的称呼”③。在《血脉》中阿来写道:“我是这个汉族爷爷的藏族孙子”,“一个杂种家庭以一种非常纯种的方式在时间尽头聚集在一起。”④?这种感受并非是源自少年内心的敏感,更多是由于周围人的排斥态度和异样眼光。同时,这也使他少有民族主义的狭隘与张扬,用人文的情怀和人类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审视人性。 不仅如此,由于历史进程的突然加速以及现代文明的涌入,使得藏边乡村少年在成长和书写中有着更为真切而痛楚的感受,“我们讲汉语的时候,是聆听,是学习,汉语所代表的是文件、是报纸、是课本、是电视、是城镇、是官方、是科学,是一切新奇而强大的东西;而藏语里头的那些东西,则是与生俱来的,是宗教、是游牧、是农耕、是老百姓、是家长里短、是民间传说、是回忆、是情感。就是这种语言景观本身,在客观上形成了原始与现代、官方与民间、科学与迷信、进步与停滞的鲜明对照”⑤。 阿来在2 0 世纪8 0 年代的文学喧嚣中初登文坛, 以诗歌创作发端, 始终保持自持与自醒, 不仅没有盲从于任何思潮和流派, 甚至采取了一种主动“ 逃离” 的姿态。在《尘埃落定》出版乃至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后, 阿来开始赢得文坛的普遍注意。阿来如苦行僧般地行走在业已斑驳、躁动的旷野之上,他以宽容和豁达坦然面对个体的苦痛、存在的孤独, 并由此建立起个体对世界的关怀与想象, 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内省与包容, 渗透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和东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