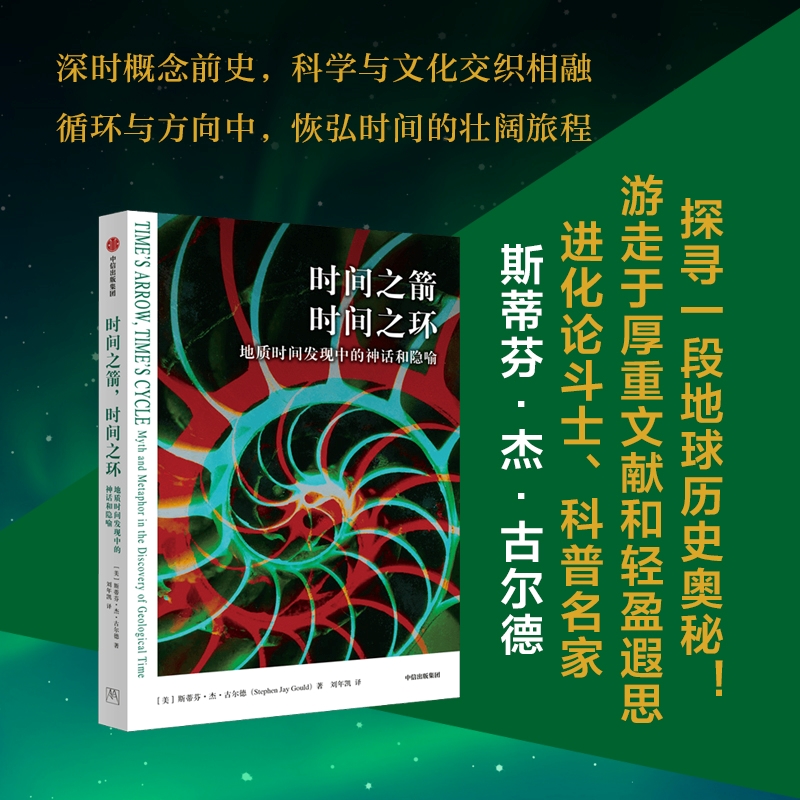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时间之箭,时间之环
ISBN: 9787521762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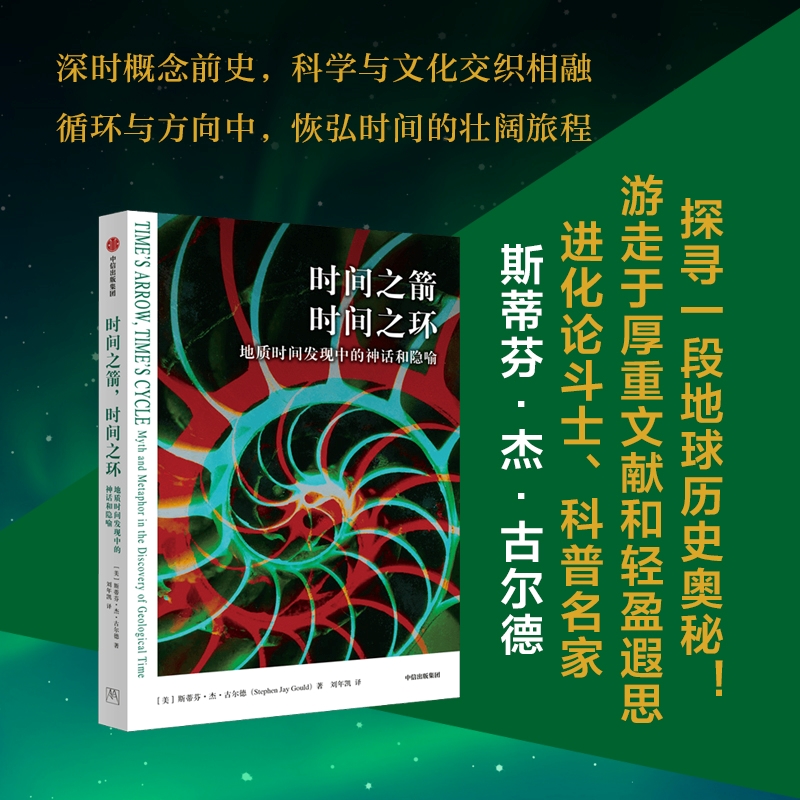
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 美国古生物学家、演化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与科普作家,是享誉世界的反伪科学斗士。美国国会图书馆曾命名他为美国“活传奇人物”。《科学》杂志称古尔德是极少数可以被称为“文艺复兴式人物”的科学知识分子之一,评价他文理双全,博学多才,是百科全书式的真正大师。 自1997年至今,古尔德的著作已有10本书翻译成简体或繁体中文。其中多本已数次再版或重译,如《熊猫的拇指》《自达尔文以来》《生命的壮阔》《奇妙的生命》《干草堆中的恐龙》等。 ?刘年凯,山东泰安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仪器史、科学博物馆学、计量史。
深 时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每一门重大科学都为人类思想的重建做出了显著贡献,而每一次痛苦的进步都打破了人类在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原初希望的某一方面。 在时间的长河里,人类不得不承受科学对其天真自负的两次重击。第一次是人类意识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尺度难以想象的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尘埃。第二次是生物学褫夺了人是被特别创造的这一殊荣,而贬之为动物世界的普通一员。(作为历史上最不谦虚的声明之一,弗洛伊德随后表示,他自己的工作推翻了这种令人不悦的退却的下一个或许是最后一个基座,即虽然人类从低等猿类进化而来但我们至少拥有理性头脑这种自我慰藉。) 然而,弗洛伊德的列表忽略了最伟大的一步,即人类统治的空间限制(伽利略革命)和我们与所有“更低级” 生物的物理联系(达尔文革命)之间的桥梁。他忽略了地质学对人类重要性施加的巨大时间限制,即“深时”(deep time)的发现—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非常恰当地用“深时”一词表达了地质尺度的时间。如果按照传统观念,年轻的地球在诞生后数天便被人类统治,人类必将备感欣慰,其统治也再合适不过。相反,如果人类的存在仅限于难以想象的浩瀚尺度的最后一毫微秒,那么这将是多大的威胁!马克·吐温注意到在如此短暂的存在中寻求慰藉的困难: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32 000 年,而在此之前,地球已经存在了上亿年,因此地球这上亿年就是在为人类的出现做准备。我猜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如果埃菲尔铁塔的高度代表地球的年龄,那塔尖旋钮上漆皮的厚度就是人类历史的长度,任何人都会怀疑那层漆皮是建造这座塔的目的。我猜他们会的,我不知道。 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在描述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既没有开始的痕迹,也没有结束的前景”的世界时,用更忧郁的语气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因此,这个表述将地质学深时的两位传统英雄联系起来,也表达了时间新的深度与牛顿宇宙的空间广度之间的隐喻联系: 这种关于漫长的过去时期的见解,如同牛顿哲学打开的空间一样,实在过于渺茫,很难唤醒崇高的观念而不夹杂一种痛苦的感觉,对于我们还无力想象一个如此无限规模的计划。在许多世界之外还有许多世界,彼此之间的距离遥不可测,而在所有这些世界之外,在可见宇宙的范围内,还可以隐约地看到无数其他世界。(Lyell, 1830, p.63) 深时如此难以理解,超出我们的日常经验,仍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大障碍。即便某些理论只是描述了普通事件在浩瀚时间尺度上的积累效应以替代之前错误的推断,也会被认为是创新性的。奈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和我提出的点断平衡理论(theory of punctuated equilibrium)并不像经常被误解的那样,激进地主张演化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认为普通物种的形成过程若按我们的寿命标准来看应理解为非常缓慢,它不是转化为地质时间里一连串渐次细分层级的中间体序列(传统的或渐进的观点),而是在单个层理平面中地质上的突然出现。 对深时的抽象理解不难,我知道在10 后面加多少个0 来表示1 000 000 000,但真正理解和感受这种尺度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深时对我们来说太过陌生,我们真的只能用隐喻来帮助自己理解。我们在教学中也都是这样做的。如果用一英里来代表深时,那人类历史就只有最后几英寸;或者我们用一年来代表宇宙年龄,那智人出现在《友谊地久天长》唱响前的片刻。一位瑞典记者告诉我,她设想在寒武纪时期把她的宠物蜗牛放在南极点,让它缓慢地向马尔默(瑞典城市)前进,从而把时间形象地表现为地理。约翰·麦克菲在其所著《盆地和山脉》(Basinand Range, 1980)中做了最形象的比喻:把地球历史看作老式英码的一码,差不多就是国王伸出手时鼻尖到指尖的距离,那么用指甲锉在指尖一抹,就抹去了人类历史。 那么,学习地球科学的学生如何完成从数千年到数十亿年的基本跨越呢?在我们寻求了解地质思想史的过程中,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了。 深时的神话 狭隘的分类法是对智识生活的诅咒。学者接受深时并将其作为共识,经历了从17 世纪中叶到19 世纪初的漫长过程。正如保罗·罗西(Paolo Rossi, 1984, p.ix)所言:“胡克时代的人有6 000年的过去,而康德时代的人意识到了数百万年的过去。”在这关键的几十年里,地质学并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和公认的学科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将思想史上这一重大事件归因于一小群地球科学家的岩石研究。事实上,罗西用有力的证据表明,除了地质学家的贡献,深时的发现也结合了当时的神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洞见。在那个博学多才的时代,一些学者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建树。 我将自己的讨论限制在被后世专业地质学家视为前辈的几位学者,是有意识地在我试图推翻(或扩大)的框架内进行的。换句话说,我将处理地质学家所接受的发现深时的标准故事。专业的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这种自利神话(self-servingmythology)的虚假和做作,在这方面我不要求原创性,但他们的观点并没有渗透到一线科学家或学生身上。 我的狭隘性甚至延伸到地域和学科,因为我只选择了英国地质学舞台上的三个主要人物—一个主要反派和两个标准英雄来深入讨论。 他们的时间顺序也代表了关于时间发现的标准神话。带有神学教条主义色彩的反派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在17 世纪80 年代撰写了他的《地球的神圣理论》(Telluris theoriasacra / Sacred Theory of the Earth, 1691)。第一个英雄詹姆斯·赫顿在一个世纪后的18 世纪80 年代编写了他最初版本的《地球理论》(Theory of the Earth, 1788)。查尔斯·莱尔,作为第二位英雄和现代性的编码者,仅仅在50 年后,也即19 世纪30 年代,就撰写了他的开创性著作《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1830—1833)。(毕竟,科学确实会加速进步,正如这次接近真理所花的时间相比上次缩短了一半。) 标准神话被历史学家贴上了他们最嗤之以鼻的标签—“辉格式”(whiggish),即将历史视为一个进步的故事。它使我们能够根据历史人物在启蒙方面的作用来评价他们,但这些评价完全基于后人的观点。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 eld)在其《历史的辉格解释》(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931)一书中谴责英国历史学家与辉格党结盟,将他们国家的历史写成其政治理想逐步实现的做法: 真正有罪过的,是那种在历史编纂中让人无法辨识其偏见的历史写作。……这种方式把事件从情境中抽离出来,并且含蓄地与今日做对比,然后妄称因此就可以让“事实”本身“说话”。这种方式实际上假设,这样的历史……能给我们提供价值判断;也就是假设,仅仅通过时间的流逝,就可以证明某个理想或某个人是错误的。(Butterfi eld, 1931,pp.105-106) 辉格式历史对科学有特别执着的坚持,原因很明显:它与主要的科学传奇相吻合。这个神话认为,科学在其探索和记录自然事实方面的初步研究与所有其他智力活动有着根本不同。这些事实,当收集和提炼到足够数量时,会在一种有力的归纳主义的引导下形成统一和解释自然世界的宏大理论。因此,科学是进步的终极故事,而进步的动力是实证发现。 我们的地质教科书以这种辉格模式讲述深时的发现,它被视为最终摆脱迷信束缚的卓越观察的胜利。(随后的每一章都包含一节对这种“ 教科书纸板”的讨论。)过去糟糕的时代,在人们从扶手椅上站起来去野外观察岩石之前,“摩西五经”中的大事年表限制了我们对地球历史的任何了解。伯内特代表了这种反科学的非理性主义,他对我们行星历史名义上的描述中不恰当地包含了“神圣”一词,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也因将《创世记》的“日”寓言式地解释为可能很长的时间而陷入了相当大的麻烦,但这不重要。)因此,伯内特代表了教会和学会对观察科学之新方法的强烈反对。 赫顿打破了《圣经》的这些限制,因为他愿意野外观察而不是接受先入为主的观念—与地球对话,它会告诉你真相。赫顿的两个关键观察结果推动了深时的发现:首先,他认识到花岗岩是一种火成岩,代表了一种恢复性隆升的力量(因此地球可以无休止地循环,而不是逐渐被侵蚀成废墟); 其次,他正确地把不整合(unconformity)解释为隆升和侵蚀循环之间的分界(为周期性更新提供直接证据,而不是短暂和单线的衰老)。 但当时的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赫顿的观点(而且他的文笔太糟糕,无法说服任何人)。因此,深时的编码还要等到查尔斯·莱尔的伟大教科书《地质学原理》。莱尔以他关于当前地质过程速率和模式的权威汇编获得了胜利:他证明了普通原因的缓慢、稳定运行,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就能产生所有的地质事件(从大峡谷到大灭绝)。地质学学生现在可以拒绝用《圣经》年表来理解世界了。在这个版本中,深时的发现成为历史上观察和客观性战胜成见和非理性的最大胜利之一。 就像英雄史观中的许多故事一样,这种对深时的描述在灵感方面是贴切的,但在准确性方面却严重不足。诺伍德·汉森(Norwood Hanson)、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以及许多其他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开始整理事实与理论、科学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25 年后,这种从观察到理论的简单、单向流动的基本理论彻底破产。相比其他智识活动,科学可能在其对自然物的构造和运作的关注方面有所不同。但科学家并不是推导机器,只会基于自然现象中观察到的规律推测其原因(假设这种推理方式原则上可能取得成功,但我对此表示怀疑)。科学家也是沉浸在文化中的人,挣扎于头脑中所有奇怪的推理工具,从隐喻、类比到富有成效而天马行空的想象,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称科学家被这些工具“绑架”了。主流文化并不总是辉格式历史所认定的敌人,比如,神学对时间的限制使早期地质学家化身贩卖奇迹的灾难论者。文化可以增强也可以限制科学,就像达尔文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模型引入生物学,从而成为自然选择理论一样。(Schweber, 1977)无论如何,客观思想不存在于文化之外,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我们无可逃避的文化背景。 作为一线科学家,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与这些关于我们专业的神话做斗争,拒绝将其视为某种优越而与众不同的东西。神话可能作为游说策略的理由,在短期内服务于我们—给钱就好,其他的别管,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搞不明白。但从长远来看,自我区隔为守护科学方法的神圣仪式的牧师,只会伤害科学。所有思考者都可以走近科学,因为它只是将通用的智识工具应用于特定的材料。无须赘言,在这个生物技术、计算机和炸弹的世界中,对科学的理解变得越来越重要。 纸板神话将科学视为纯粹的观察和应用逻辑,脱离了人类创造力和社会背景的现实。除了以积极的方式揭穿剩余的纸板科学神话,我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创造性思想的普适性。围绕深时发现的地质学神话,可能是残余传说中最为持久的。 这本书考虑从神话被定义的边界内部瓦解它。我详细分析了三位主要人物(一个反派和两个英雄)的主要文本,试图找到一把钥匙,可以解锁这些人的根本构想(visions),它们在将它们描绘成观察中的进步敌人或化身这一传统里早已丢失。我在二分法的隐喻中找到了这把钥匙,这些隐喻表达了对时间本质的相互矛盾的见解。伯内特、赫顿和莱尔都在与这些古老的隐喻做斗争,尽力应对并相互比较,直到他们对时间和变化的本质形成了独特的见解。正如任何对岩石和露头(outcrops)的观察一样,这些构想必然推动了深时的发现。内部和外部资源,即以隐喻为依据的理论和受理论约束的观察,二者的相互作用标志着科学的任何一次重大运动。我们认识到几个世纪争论背后的隐喻时,就能更好地理解深时的发现,它是所有曾与方向性和内在性等基本谜题斗争过的人们的共同遗产。 (1)关于作者:古尔德在《自然史》杂志的“这种生命观”专栏上,用散文体形式,向我们讲述了由自然现象引出的种种思考,包括对自然现象的遐想,对科学的反思,既有对社会偏见的尖锐批判,又充满了对于自然、人类、文学、艺术和哲学的深爱。这些文章的中心是生物的进化和进化的理论,但是由于作者联想的丰富、思考的独特、文笔的流畅和学识的广博,所以我们读来不仅感到惬意,而且还会跟随作者的引导,去思考周边事物及现象的背后所蕴含的深刻而具普遍性的道理。因此,不仅普通读者爱读古尔德的作品,甚至一些严肃的学术论著中也常引述他在这类作品中的见解。 (2)关于本书:本书从科学家发现“深时”这个地质尺度的时间观念,到通过三位科学家的三部专著中关于地球和地质学理论的探讨,引出了西方思想中关于时间这一中心主题的最深刻、最古老的设定,即线性和循环的构想,或者说是时间之箭和时间之环,而时间之箭正是《圣经》中历史的主要隐喻。本书深刻地反映了西方世界的科学家与神学、与宗教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历史渊源,并围绕达尔文的进化论展开了“进化和神创”的一系列思辨,涉及了许多科学与宗教的较量和融合。 (3)关于深时:在地球科学领域,这些地质学思想仍或隐或现地影响着当前的研究。如今“深时”越来越引起学界,尤其是古气候学和沉积学领域的关注。“深时”被定义为前第四纪的地质记录。“深时”气候变化的极限、速率及反馈作用已远远超出第四纪同类变化的规模和范围。学界也逐渐认识到时间尺度对地质过程的重要性,在该时间尺度上,以热年代学等为手段的沉积物“从源到汇”研究、抬升速率研究正在展开。而且,在很多研究背后都可见均变/灾变、时间之箭/时间之环等二分法的影子——这也展示了地质学思想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