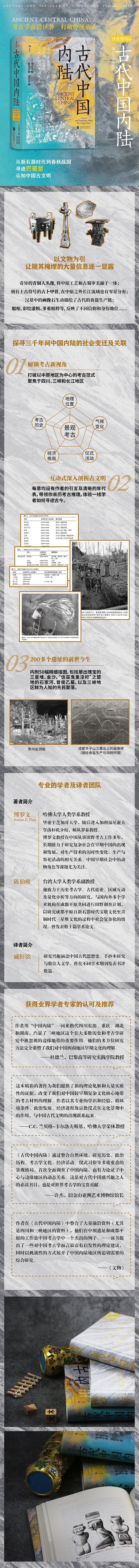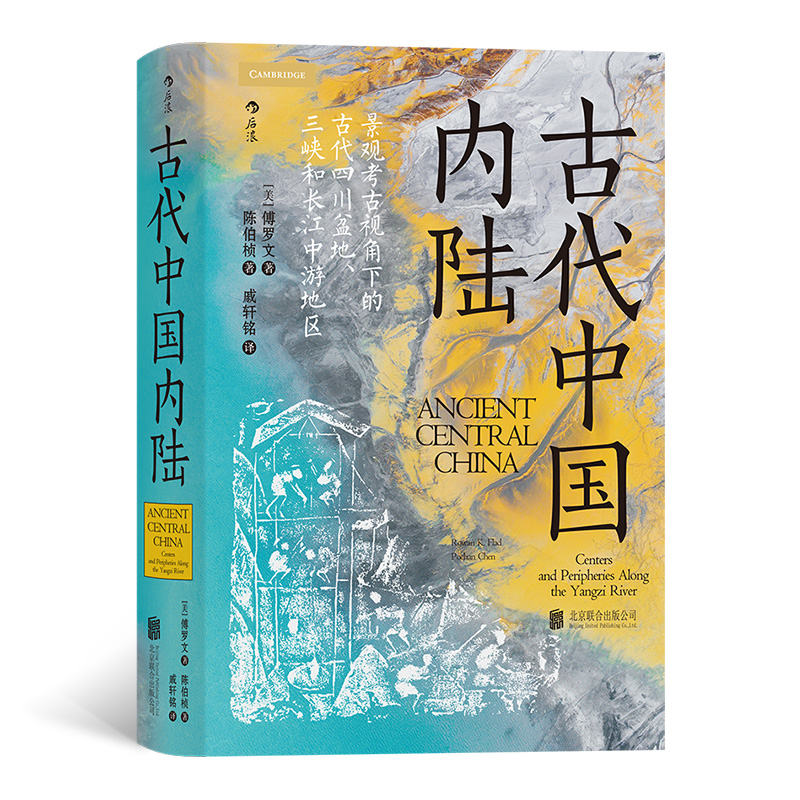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社
原售价: 82.00
折扣价: 52.50
折扣购买: 汗青堂083:古代中国内陆 景观考古视角下的古代四川盆地、三峡和长江中游地区
ISBN: 9787559649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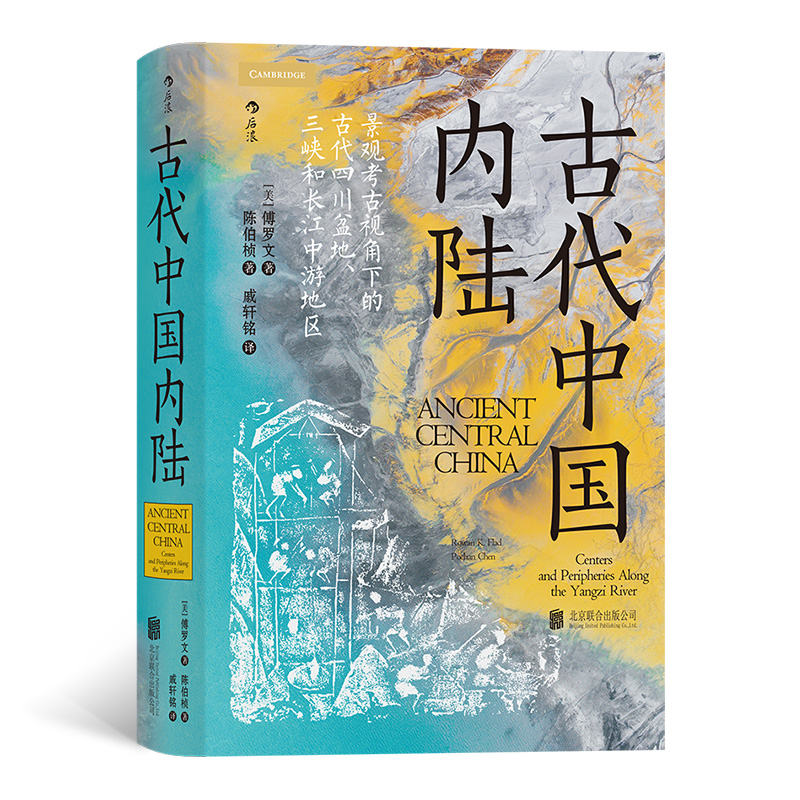
作者 [美]傅罗文(Rowan K. Flad),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师从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傅罗文教授在中国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多年,长期致力于研究复杂社会在早期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对生产技术的历时性变化、生产与祭祀活动的相互关系、中国早期社会中的动物角色等课题尤为关注。曾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 陈伯桢,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博士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他致力于历史考古学、古代盐业、区域互动及量化分析等方向的研究,与国内外多个学术机构在成都平原共同进行一项长时段的田野调查计划,以研究成都平原自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至青铜时代三星堆文化的过程中社会复杂化的情况。曾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 译者 戚轩铭,现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涵盖中国古代思想史、手抄本研究与数位人文学。曾在不同学术期刊发表书评数篇。
第4章 四川盆地 (蜀及其前身) 文献中的蜀 正如我们在第3章表明的,四川盆地被人们,甚至是那些以这个地区为其研究中心的人视为一个在历史重要性上属于次要的地区。例如,郑德坤在其1957年出版的对四川考古学做综合研究的著作中(1957:xix)指出,“四川完全是一个边缘地区,这个省的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发展的结果,它经常受到一些邻近文化的影响”。 我们认为,文化的发展总是要受到周边影响的。但如果人们将这个议题搁置在一边的话,四川近年的研究使考古学界更愿意去接受四川本土社群在地方社会发展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四川最终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边缘地区”。 我们这里的注意力将集中在先秦时期的成都平原上。这里有关政治和文化格局的考古证据相对四川盆地其他地方要更扎实,而历史记载也以蜀为中心。在不同时期里,以“蜀”为名的国家均位于四川地区:前蜀(907—925)和后蜀(934—965)是五代十国时期(907—979)十国中的两国,它们以三国时期(220—280)的蜀汉(221—263)为国号。这个国家的名字又转而用来指代被秦在公元前316年所攻占的四川盆地的蜀国(Sage1992)。 我们只有从在其他地区撰写的历史文献中才得知这个最早的蜀国,而且这些有限的历史资料是由在四川盆地之外的都市化国家以外部的观点撰写的。根据这些材料,蜀据说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过去数十年的考古证据表明,成都平原附近的遗址为其政治中心,这为我们对中国内陆景观的讨论提供了基础。 与蜀有关的较次要的历史文献包括一些从商代后期首都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林向1989;董作宾1942),以及从陕西周原出土的先周和西周早期的甲骨资料(Sage1992:31—34)。但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为数甚少的例子实际上是否真的在指四川盆地的政治组织或人民[顾颉刚1981(1941)]。历史学家更加信任《史记》所提及的蜀国与四川之间的关联(《史记》,卷4)。这个名为“蜀”的政治组织是在标志着由商代过渡到周代的牧野之战中参与对抗商政权的联盟国之一。大量研究集中讨论了这场战争的年代,而这些研究将周代征服商代的时间定于公元前11世纪40年代(与具体的年代有关的讨论和材料,见Falkenhausen2006b:7;Shaughnessy1999:23;有关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尝试巩固这个年代的讨论,又见Lee2002a,2002b)。在本书中,我们采纳公元前1050年作为这场战争和与之相关的过渡期发生的大约时间。 对于汉代以前有关成都平原的历史记载中,以公元前316年秦征服四川以后的记载对本书帮助最大。例如,《史记》讨论了李冰对蜀地的管治权。李冰据说负责了多个成都平原的工程项目,其中包括第2章讨论到的都江堰。诸如常璩(约291—361年)的《华阳国志》这类夹杂历史和神话的传统典籍中记录了蜀国在先秦时期对成都平原的控制,并将蜀人与“黄帝”的后代联系在一起(Chang1987;李学勤1985:204)。正如王明珂(2010:7396)指出的,这篇文献的标题“显示了作者将蜀视为华夏边陲的地理意识”。王明珂认为,蜀和黄帝之间的联系再现了一个共有“结构化情节”,通过对去到边疆并建立文明的英雄的身份认同,将所有对中原来说是边缘地区的历史与中原历史本身对接起来。 《华阳国志》和传统以来被认为是由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所撰的汉代文献《蜀王本纪》零星罗列了传说和虚构的历史记载中蜀国领袖的次序。第一位领袖是蚕丛,紧随其后者则为柏灌、鱼凫、杜宇和最后的开明。这些名字可能是指不同的氏族,它们在不同时代里相继登上权力中心(彭邦本2002)。这种含糊的历史材料表明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有过脆弱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在不同地点相继或周期性地出现过最高统治者。我们在其他文献中也找到了关于蜀的零星资料,这些文献包括《逸周书》和《竹书纪年》,但没有一部文献能无可辩驳地与成都平原的蜀国政治组织有关(Sage1992:40—41)。部分学者曾尝试将这些记载和下文将会讨论到的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的遗物联系起来。首位将从四川得来的青铜时代遗物判定属于巴蜀文化的学者似乎是卫聚贤(1898—1989),他断定这些青铜器中的罍、壶、戈、钺和剑的时代为晚商至战国时期(卫聚贤1941,1942)。冯汉骥通过将成都平原附近巨石遗址古文献联系起来,认为这些遗物是属于古蜀国的(冯汉骥1985a)。后来的学者亦继续将考古发现与这个地区模糊的历史相联系(有关这个地区的考古学和与蜀有关的历史记载的联系的进一步讨论,又见:李绍明主编1991;四川省主编1992a;宋治民1998a;孙华2000;童恩正1979;徐世群1998;徐中舒1987),然而,文献资料的历史真实性及上述领袖与考古发现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得到证实的。 对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概观 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得到的资料已经开始超过零星的历史文献记录,成为我们了解成都平原政治和文化格局的时间透镜。新资料不断地出现,但人们对这个地区文化发展的个别阶段的年代仍然有着不同意见。尽管如此,一个大体框架已经逐渐清晰。我们在这里将主要关注成都平原,也会简单地考察邻近地区。在本章脉络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与这个地区政治格局有关的证据,如精英结构、大规模的人口动员迹象和区域性的阶层结构。虽然资料是很零碎的,但我们仍可以做出一些可供将来研究考察的初步陈述。先秦考古编年可粗略分成五个阶段(表4.1):宝墩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700—公元前1700年)、三星堆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700—公元前1150年)、十二桥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200—公元前800年)、新一村文化时期(约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和青羊宫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公元前300年)。在介绍每个阶段时,我们会先描述与之相关的考古学文化的整体特征,并在随后讨论那些能够说明政治权威和整体制度的证据。 宝墩文化 位于新津县的宝墩文化遗址于1950年被发现(图4.1),年代被推定为约公元前2700—公元前1700年。在没有得到明确定义的情况下,这个文化又被分成四个年代学阶段(I—IV;王毅2003)。这一年表主要基于19个放射性碳测年数据,由于对报告的年代是否经过校准的不同意见,关于其起始阶段的年代的争论聚焦在公元前2850年(2000:295)、公元前2450年(成都主编2000:97),甚至更晚(王毅2003)。 宝墩本身是这段时期得到最全面公布的遗址(成都与新津2011;成都1997,2000;江章华主编1997,2000;宋治民2000;孙华2000:321;王毅2003;王毅与孙华1999;中日1998)。人们报告有2座平面为长方形的木骨泥墙房址(成都2000:70),其他遗迹包括24个灰坑和5座保存得很差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没有发现随葬品。有一个平面近乎正方形的土墙围绕着这个遗址,所包围的范围约为66公顷(成都2000:74)。在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调查中,确认了第二座包围约220公顷土地的墙体,具体情况才刚刚开始公布(成都与新津2011),而这会使宝墩成为东亚规模最大的一处有墙包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迄今为止,我们仍不清楚外墙和内墙中间的区域是用作居住、农耕或是存在其他功能。这面墙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遗址的理解,但我们现在先将我们的讨论集中在已经出版的研究上。 宝墩的陶器主要是泥质陶,表面饰有绳纹,某些器物的底部有圈足。精美的陶器包括没有装饰的宽沿平底尊(图4.2a1)和壶,以及饰有刻划纹、戳印纹、附加泥条戳印纹装饰和黑色泥釉的喇叭口高领罐(图4.2a3—4)。其他种类的陶器包括敞口平底壶(图4.2a5)、宽沿盆(图4.2a2)和浅盘豆(图4.2a6)。夹砂陶器主要是绳纹壶(图4.2b1—4)和敞口圈足尊(图4.2b5)以及盘口圈足尊(图4.2b6—8)。石制工具为小型的斧、锛、凿、铲、箭镞、杵和磨石。 其他几个宝墩文化的遗址也经过了考古调查。都江堰市芒城带墙的遗址与第二阶段有关(成都与都江堰1999;王毅2003;中日2001a,2001b)。这个遗址被内外两层高度为1—2米的土墙包围:内墙围绕的区域面积约为7.2公顷,外墙围绕面积约10.5公顷。两者都是用遗址周围壕沟的泥土和石质土堆建的。另外,内墙的建造工艺包括系统地使用名为“夯土”的土壤处理技术来夯实8—10厘米厚的土层,某些地方仍然保留了一些工具撞击的痕迹。很明显,内墙是分两次建成的,但外墙是一次性建成的。内墙的外层以及整个外墙都分散覆盖着中型鹅卵石。 我们已经知道芒城遗址中有若干房屋遗迹,包括一处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保存得最好的木骨泥墙建筑物。这座房屋(F5)是在遗址东南角的内墙附近发现的(图4.3),它包括两个有门连接的独立房间。一部分墙体被烧毁并倒塌进更大的房间,从而保存了有关建筑方法的证据:先挖一个宽16—23厘米的基槽,然后将一个由竹竿或木头搭成的骨架放置基槽中,再用淤泥包裹住这个骨架,最后用火将这个木裹泥的骨架烘干变硬,这样就制成了一个木骨泥墙结构的墙。不幸的是,其他房屋并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而且我们也不清楚整个遗址的布局。大量灰坑和灰沟出土了陶片、石器、炭灰、烧土和丰富的植物岩化石。 陶器既有夹砂器也有细泥陶,有60%以上的精美陶器由手工制作并经快轮修整。人们发现了许多石器,种类有斧、锛、凿矛和锤,它们全都细致小巧而表面光滑文化第三个重要的带墙遗址是郫县的古城遗址(成都与郫县1999,2001a,2001b;江章华主编2000)。与鱼凫(后文将述)早期的地层一样,郫县古城早期的遗物代表了宝墩文化的第三阶段;古城后期的遗物被推断属于第四阶段,即公元前1900—前1700年。古城遗址的城墙是所有宝墩文化遗址中保存得最好的,它的形状是长方形的,方向120度,墙内面积约30.4公顷。发掘工作揭露了超过10座房屋的地基遗迹,当中一些房屋是木骨泥墙结构并呈长方形。我们在其中发现了一些叠压关系,这表示这里有着连续的使用年代(图4.4)。其他房屋则是有中型的鹅卵石长方形覆盖的长方形区域。另外,发掘人员还在遗址中心发现一个由鹅卵石系统排列而成的大型地基(F5;见后文讨论)。郫县古城的陶器主要有夹砂陶和细泥陶,但与宝墩和芒城不同的是,这里泥质陶的数量似乎随着时间而减少。这里的石器则有体积较小而表面光亮的石斧、锛、矛和凿。 鱼凫较早时期的地层年代同样为宝墩文化的第三期,它位于成都平原中部温江区的岷江冲积扇上(成都主编1998;李明斌与陈云洪2001;宋治民2000)。这个遗址保存了围墙环绕的四个片区。围墙的形状不规则,包围着大约25至40公顷的土地。除了可能是古代河床的一个下陷地带,遗址围墙内的地势要比周围高。 人们在围墙内发现了14间房屋的地基遗迹。这些房屋分为三类:一类有为了插上木制或竹的篱笆墙而设的基槽;一类为存在桩孔线的干栏式房屋;一类拥有由中型鹅卵石排列而成的长方形区域。人们发掘出155个灰坑、1条壕沟和4座墓葬。所有墓葬都是仰身直肢葬,没有任何随葬品。 发掘人员将鱼凫的遗址分作三期。第一期在围墙建成之前,第二期是围墙被使用的时间,第三期是围墙被废弃之后。初步的报告推测鱼凫的第一、第二期与宝墩、月亮湾下层和三星堆第一期同期。但在最近,同一位作者在作为其贡献之一的宝墩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鱼凫遗址的年代上限比三星堆第一期要晚(江章华主编2000:106—107)。主流的意见认为这个遗址早期年代在公元前2550—公元前2250年之间,而它晚期的年代则与宝墩第四阶段同时,在公元前2050—公元前1750年(李明斌与陈云洪2001)。成都平原还发现了一些与宝墩文化有关的城墙遗址,一些同时期的无城墙遗址也得到了调查。在后者中,有少量遗址已被详细发掘,但有关报道很少。例如,绵阳市边堆山虽然是该地区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但有关它的报道都很简短(何志国1990,1993;马幸辛1993;宋治民1998b;西南博物院筹备处1954;中国1990a),一些人甚至认为边堆山遗址是这个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孙华1992:23)。在遗址的清理工作中发现了30件石器,包括斧、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凿、刀和石镰,以及超过400块陶片。陶片中占大多数者,装饰有绳纹、刻划纹、粗凹弦纹、贴花和戳印纹,只有一个盘能被完整地复原。尽管有关资料有限,但这个遗址却极为重要,这可从它在讨论其他遗址的报道被频繁地提及一事看出来(尤其见刘磐石与魏达议1974;礼州1980;四川2006b;王仁湘与叶茂林1993;吴耀利与丛德新1996;徐学书1995;中国与四川1991;中国1991a)。人们公布了两个放射性碳测年数据:距今3960±250年(ZK—2346;本书使用CalPal_2007_HULU校正,标准的碳年代为公元前2467±347年)和距今3590±255年(ZK—2349;碳年代为公元前1993±335年)。通过使用较近期的校准曲线(Stuiveretal.1998)来产生一个比原本的报告范围更广阔的校准年代(中国1991d),原始报告中校准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883—公元前2050年和公元前2330—公元前1630年。奇怪的是,在江章华主编的著作(2000:115)中将这两个例子列为距今4505±270年和距今4020±260年。虽然我们无法解释这种矛盾,但这个遗址的年代理应为公元前3千纪后期。 近年,人们日益频繁地在成都市附近发现小规模遗址。但我们并不清楚哪些遗址代表了整个聚落和与之相关的特点,哪些又是更大型遗迹现象的一部分。成都平原没有围墙的宝墩时期遗址有成都市西部的十街坊(朱章义2001)、格威药业一期(成都2005c)、航空港(成都与郫县2005a)、摩甫(成都2006b)、高新西区方源中科(成都2006c)。还有邻近的地点:中海国际社区毗邻的遗址(成都2007b);黄忠村的一条壕沟和放满宝墩文化陶器的灰坑(成都2004c,2005a,2005b);康家村精品房分散的遗物(成都2006e);出土了墓葬、灰坑和几座房屋地基的化成村(刘雨茂与荣远大2001)和置信金沙苑一期的建筑物地基、10座墓葬以及21座灰坑(成都2004)。后面的这些地点全都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北部。人们在置信金沙苑发现了三个长方形基槽,基槽里有作为支撑墙的木和竹的柱洞,它们与墙的相对位置相同。这显示在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 在宝墩文化之前的时期里,居住在成都平原的人口似乎很稀少,但我们知道附近的高原上有着一些较早时期的遗址。例如,在过去多年沿着岷江进行的调查确认了超过10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陈剑2007;陈卫东与王天佑2004;江章华2004a;蒋成与陈剑2001;四川2007;孙吉与邓文2006;徐学书1995)。最著名的是营盘山遗址(陈剑2007;成都与其他2002),挖掘人员在其中发现了与在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公元前2700年)有关的彩陶。这些遗物记录了遗址与北方的联系,并显示公元前4千纪晚期,相对较接近成都平原的前宝墩文化人群的存在(洪玲玉与其他2011)。诸如绵阳附近的大水洞(四川2006b)和白水寨(成都2007a、2007b)这些平原北部边缘的其他遗址证明了岷江流域和边堆山的联系。它们表明,北方是成都平原早期接受域外文化影响的主要方向。 就东北部而言,广元市中子铺的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公元前3500年,并与汉水流域的遗址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李永宪1996;叶茂林1991a;中国1991a)。我们也知道在四川盆地东北部也存在其他几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重庆1983b;李永宪1996;马幸辛1989,1993),这些遗址中,张家坡可能像中子铺后期的遗物一样早(江章华主编2000:116;吴耀利与丛德新1996;中国与四川1991)。另外,广汉西北方的什邡近年也发现了一个名为“桂圆桥”的遗址,这个遗址有着与营盘山和三峡哨棚嘴类似的小型石器和陶器。对这个遗址以后的研究可能会确定成都平原在宝墩时期之前的聚落。 人们在其他邻近的地区也找到了与宝墩文化同时的遗址。例如,狮子山遗址(刘磐石与魏达议1974;马继贤1991;中国1991b),位于汉源县西南部的山地中,它的年代约为距今4500—4000年(江章华主编2000:119)。近年在大渡河和安宁河地区进行的调查确定了其他诸如麦坪村的早期遗址(大渡河2003;中国主编2006)。在东北部嘉陵江流域的遗址,如邓家坪(叶茂林1991b;吴耀利与丛德新1996)和擂鼓寨(孙智彬1992;雷雨与陈德安1991;四川与通江1998),则与边堆山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而其年代也与早期宝墩文化相一致。人们根据四种放射性碳测年数据和公元前3千纪中期之前的一些最早的遗物推断邓家坪的年代在公元前3634至公元前1647年之间[这些见于江章华主编(2000:121n28)的著作之中的年份与它们大概来自中国(1991d:229)所载的年份并不相符。我们将依据后者的材料]。就擂鼓寨而言,最早地层(第9层)的校准年代为距今4995±159年(校准年代为公元前4221—公元前3377年),这表明人们在该地区进行活动的时间要早于成都平原聚落的出现。 遗憾的是,上述资料存在多种不足。这种情况即使在诸如宝墩这类得到详尽发掘的遗址也是存在的,在成都平原及其周围地区规模较小的遗址情况更糟。尽管如此,已出版的资料和总结性的论述因为本着极度的谨慎,还是包括了一些容许人们对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制陶业方面的一些特点做整体性总结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这个总结对远离这个区域的遗址来说缺乏足够的准确性,而且是不适用的。 有着花边口沿的壶,不同种类的大口尊,长颈瓶或类似的有着喇叭形口、带网状小孔圈足的容器是在成都平原众多宝墩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典型器型。江章华和他的同僚已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种类与器型的变化来将这个地区的陶器仔细地分成四个年代学时期(2000:106—113;成都主编2000:122—134;江章华主编1997,2002;孙华2000:309—314)。尽管我们对仅仅完全依赖陶器的地层关系及其器型变化作为文化变化标志的普遍做法存疑,但从陶器制品方面来探究这些共同种类的容器和它们的相似性也是有趣的尝试。成都平原早期的陶器主要以泥质陶为主,夹砂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较为常见。石制的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这些石器往往体现出多种制作工艺和工具,主要有锛、斧和凿,它们的体积都异常地细小。 人们在许多遗址中发现了建筑遗迹。许多遗迹证明了当时有着一些建在地面的、有着木骨泥墙的房屋结构,而且当时人们都使用在外形、大小和深度方面都不同的灰坑。没有资料能清楚地证明这些无处不在的灰坑具体功能为何。我们在一些遗址中得知有其他类型的房屋,包括有鹅卵石的地面。墓葬往往是简单的竖穴墓。 为了超越文化描述,研究宝墩文化的政治面貌,我们需要考察等级制度、权力和社会融合有关的方面;也需要讨论这些宝墩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绘制遗址的区域格局网络,找出那些能显示出一些政治互动网络中心节点的证据。 宝墩文化的围墙和公共建筑物最能直接说明权力模式和社会整合机制特征的是位于郫县古城的墙址(图4.5)和大型建筑基址(F5)。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围墙的出现通常被看作社会政治发展复杂化最为关键的指标(Demattè1999;LiuL.1996;任式楠1998;Underhill1994;Underhilletal.1998,2002;许宏2000;严文明1999;YangX.2004)。除了表明有大规模的劳动力动员,围墙也可能证明了社群间的冲突是很普遍的,而这本身也可能是与复杂社会出现有关的现象(Carneiro1970)。此外,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城市所扮演的宇宙中心般的角色,它们作为这种政治力量的典范和象征的潜力不应受到忽视(Wheatley1971)。 但是,对于围墙和其他类似结构建筑的另一种解释却没有对冲突和等级制度做相同程度的强调。围墙很多时候都不是防御性的,而必要的劳动力则可通过全体或集体行动获得(Renfrew1973)。虽然诸如围墙的倾斜度和聚落围护程度这类要素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反映墙体的功能(ArkushandStanish2005),但成都平原聚落围墙的低坡度已被用作说明它们主要是防洪壁垒,而不是防御性堡垒的证据(黄昊德与李蜀蕾2005;XuJ.2001b:23)。不过,虽然这些围墙并不是非常巨大,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也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它们却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去建造和维修,这些围墙所包围的那些相对较大的空间也反映了这些地点的社会吸引力。因此,这些墙是一个标志,表明在宝墩文化时期,社区融合特别显著。 除了上文讨论过的宝墩、芒城、古城和鱼凫的遗址,我们也得知其他几个遗址也有围墙:崇州的紫竹和双河,大邑县的盐店(成都2002;江章华主编2001;王毅2003:129;王毅与蒋成2000;YangX.2004)。此外,保存着宝墩第四期重要遗物的三星堆也有一系列的围墙,但这些围墙似乎比宝墩文化要晚。 对兴建这些围墙所需劳动力数量的初步评估告诉我们(专题4.1),这些围墙可能是由数个以20人为一组的小队在数年,或数百人在一整年修建而成,也有可能(可能性较大)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数倍于此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例如,宝墩遗址的内墙可能是由4000人在一个月内勤奋地工作建成的,或是由较少的人在较长的时间内完成的。虽然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力动员并不具有巨大的里程碑意义,但它确实需要持续的、有组织的、集体的努力。因此,这些墙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综合实践的物化,这种实践在宝墩社群中很常见。此外,近年在宝墩发现的一道外墙可能需要超过1000名劳动力花费数年持续来建造。但在不知道其特有的高度和宽度的情况下,这种工程量所需要的劳动力是很难计算的,而且我们也并不知道它的建造过程是不是连续的。 专题4.1 宝墩文化围墙 在其外墙在近年被发现之前,宝墩已经是中国最大型的有围墙址,但只有东北部长约500米的内墙得到相对妥善的保存。假设这道内墙没有倒塌的话,它的长度将会达到3200米。现存围墙的一部分有3—5米高,其地基则有30米宽,接近墙顶的宽度则为8米。如果我们用一个平均高度为4米的梯形截面的话,我们可以估计墙体总体积为243,200立方米。相比谷歌地球的影像,根据笔者对遗址的调查,我们推算出宝墩外墙的长度约为5850米,但当中有接近550米与内墙共用。我们用墙体横截面尺寸较为适中的芒城围墙(而不是宝墩的实心内墙)来推算建造城墙所需劳动力的最低数量。 就芒城而言,我们根据保存较好的内墙(面积为270米×210米),以及南北长220米(保存较好)、东西宽270米(保存得非常差)的外墙来估计围墙的长度。外墙目前只保留了三边,我们假定四边均有着外墙,但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外墙是封闭的,故使用了这种比较保守的方法来估计长度。保存下来的围墙有1—2.5米高、5—20米宽。在计算时,我们假定城墙有2米高,其底部宽20米,顶部则宽5米。 双河内外围墙的北部和东部都保存较好,但其西边的部分要么是从来没有存在过,要么便是被附近的螃蟹河冲毁了。我们假定是后者,根据现存的部分估计这道墙最小的尺寸为何。我们根据内墙(面积约200米×450米,总长度1300米)和外墙(250米×500米,总长度为1500米)推断其体积。外墙得到保存的部分,宽度在3—10米,高度在0.5—2米,内墙底部宽为15—30米,高为2—5米。我们假定其内墙的底部宽度为20米,顶部宽度为10米,高为5米;外墙底部宽10米,顶部宽5米,高1米。 古城拥有保存得最为完好的围墙,因而在计算长度和体积方面是最为可靠的。长方形的围墙面积为620米×490米。我们根据其平均高度3米(现存部分的高度在1—3.8米之间)、底宽25米、顶宽10米(现存的部分的宽度为8—40米之间)来计算其体积。 最后的鱼凫古城存在一个较大的问题:围墙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残垣保存下来,而且围墙的外形是不规则的。围墙保存的部分有1350米长,包围了30,375平方米的土地,我们据此推测其平均的高度为1.5米,底宽20米,顶宽10米。如果我们假定这道墙如图4.5显示的那样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围墙的长度要再加上650米,我们从而对围墙的长度和遗址的面积做出保守的估计(约27公顷)。 我们可以利用成都平原其他各种围墙的规模来估计这些不同结构围墙的体积(表4.2)。要将这些数字转换成劳动力的使用数量,要求我们根据建筑人员拥有的技术和这些工作在何等程度上是以全职形式完成的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假设。我们推测,为了建造这些围墙而每天花在地面物体移动上所需的能量范围,从近东人们为建造夯土城墙时每人每天搬运0.5—1立方米的大型石块和石质土(Bar-Yosef1986:158;Dorrell1978),到美索不达米亚每人每天搬运1.6—3立方米的物料,后者记录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文献,特别是从乌玛遗址发现的文献中(Waetzoldt1990;与BenjaminStudevent-Hickman在2005年的私人联络)。近年在河南王城岗一个龙山文化时期带有围墙的遗址所进行的实验性研究,考察了利用传统工具和夯土技术来建造围墙的劳动力使用量(BeijingandHenan2007:657—663)。研究人员评估了挖掘、移动和将土壤填进围墙内各自需要不同的时间。他们估计一个人在一天8小时内能挖掘3立方米的土壤,并将13.3立方米的土壤移动20米,或踩平10.1立方米的土壤。如果我们能最有效地为这些任务分配时间的话,那么一个人每天能挖掘、移动和夯实平均1.97立方米的泥土。这种估算其实没有完全考虑到实验员的观察。他们认为,当土坑变得较深时,挖掘和运输的速度将会变慢。人们近年对内蒙古赤峰市三座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防御性石墙和土墙遗迹,也应用了与之类似的评估多个阶段使用劳动力数量的方法(Shelachetal.2011:21)。 宝墩文化围墙的泥土似乎是从周围距离最近的地方获取的(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2001a:97)。考虑到这点,又由于泥土中并非含有特别多的岩石,故在没有证据证明其使用夯土工艺的情况下,每个劳动力每天可以搬动最多3立方米的土壤。在没有强制劳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每人每天搬动2立方米的土壤是一个恰当的估算。我们保守估计,特别是对夯土墙或需要远距离输送土壤而言,每人每天要搬运1立方米的土壤。 此外,弄清居住在这些有围墙社区的人口数量,和这些人是否永久地或只是在某些季节或因特别事件才来到这些地区是很重要的。遗憾的是,学界只进行了很少的能让我们对人口进行评估的研究。我们完全不清楚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为何,也完全不清楚在很多情况下,被围墙包围的地区有多少部分是专门用在农业方面,而不是居住用途。我认为居住在最小的有围墙遗址的人口约为1000人左右,而最大的(宝墩)人口可能还要多好几倍。现在的田野考察将有助于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 这里讨论的围墙明显是有着多个功能的。除了作为抵挡洪水的壁垒和可能是为了保护社区而造的防御工事,围墙亦被用来标记社区之间的界线,并将人口分隔成多个部分。它们的产物就是那些共同建造的历史遗迹(Edmonds1999),而这些遗迹又可能是通过投入集体劳工而创造的中心地带。因此,这些围墙在任何构建当时成都地区的政治和文化格局的尝试中都是重要的交接点。 除了围墙,建筑物亦能说明宝墩遗址权力和统合的关系。迄今为止在宝墩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部分房屋相对来说都是小型的,有着木骨泥墙结构,只有位于芒城的F5(图4.3)内部有着多个房间。很多建筑被解释成居住的场所,尽管它们往往缺乏火炉或其他支持这一分类的遗存。芒城的F5再次充当了一个例外—在其东北角落有着一个灶坑。 古城的F5是一座独特的建筑物(图4.6;成都与郫县2001a:59;王毅2003:126—127)。F5位于遗址的中心,与遗址围墙的方向平行。长方形的地基面积为50米×11米,外围是一个布满鹅卵石的基坑,鹅卵石内埋设木桩,木桩间距为0.7—1.2米。建筑物的围墙由竹框做成,表面涂抹了草拌泥,将涂抹了草拌泥的竹框固定在木架上,用火烘烤变硬。在东边,有一个用鹅卵石铺成的圆形石堆,直径65厘米,这个圆堆可能支撑了一根木柱,这个木柱是用来支撑内部屋顶梁的。建筑物的西侧在古代就被扰乱了。房屋的中心有五个排成一排的长方形鹅卵石堆(图4.6,1—5),这些鹅卵石可能是用来做台基或柱础。石堆周围挖有基槽,槽内埋有密集的圆竹,有些圆竹已经炭化,它们可能是祭坛,或有着其他一些结构上的功能。F5独一无二的特征、巨大的面积和其居于遗址中心的位置都表明这座建筑物在古城社群整合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古城F5很可能是用来举行公共仪式活动的,分散居住在古城周围的人们会参与这种集体活动。 古城遗址的围墙和F5为我们提供了有关集体政治活动的、遗址层面的证据。就区域角度而言,我们需要一个对聚落模式的全面研究,以用来评估政治格局情形。我们仍然不清楚,例如,带有围墙的遗址是一个在稳固统合网络中的地方性中心,还是一个偶尔承接精英活动或公共集体行动的次要中心。近年的调查工作证实,宝墩时期小规模的遗址遍及整个成都平原,故带有围墙的遗址并不代表这段时期唯一的聚落(成都2010)。尽管如此,带有围墙的遗址似乎是这段时期已知聚落中最为重要的(王毅2003;王毅与蒋成2000)。 虽然我们知道成都平原上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在平原的北部,但有围墙的遗址却最先出现在平原的西南部。在第三期,古城和鱼凫展示了平原内部的聚落,而此时西南部较早时期的遗址已经荒废。在下一阶段,只有平原东北部的三星堆拥有密集的聚落 三星堆文化 位于广汉鸭子河和马牧河附近的三星堆最初在1927年被发现,而最早的发掘工作则在1934年进行(Graham1933—1934;有关它的年代的讨论,见Xu2008:11)。1951年之后,人们只会偶尔对三星堆进行研究,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ichuanetal.1987c)的系统发掘与研究活动一直持续至今(有关三星堆研究史全面的描述,见陈显丹2001;肖先进与其他2001;Xu2003,2008)。在三星堆之外,人们还发现了围合面积超过3平方千米的巨大城墙—东亚青铜时代已知最大的城墙聚落之一。 在三星堆的发掘工作出土了新石器时代(即宝墩文化)重要的聚落遗迹。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地层最先是在1963年月亮湾的发掘工作中确认的(马继贤1992)。这些地层被一些人称为“月亮湾下层”,或被其他人称为“三星堆一层”(陈德安1991;陈显丹1989;马继贤1992;四川主编1987c;孙华1992,2000;详细的讨论见XuJ.2003,2008:29—36)。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包括3处房屋基址,其中有两个是圆形的,一个是长方形。其他宝墩文化的遗物包括大量陶器碎片和石器,所有这些遗物整体上似乎都属于宝墩文化。但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该遗址的城墙可以追溯到宝墩文化时期。 相反,围墙的年代似乎属于三星堆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700—公元前1150年)。但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在已出版的著作中,这个文化的绝对年代仍未明确。事实上,个别遗物与三星堆文化的关联程度一直是争论的焦点(XuJ.2003)。例如,一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的晚期青铜时代的地层是属于十二桥文(见后)的,这主要是由于那些地层有尖底盏出土,他们又认为这些地层反映了一个衰落的时期(孙华2000,2013)。但是,其他人却主张这是一种文化延续而不是衰落,反对任何被认为是属于尖底盏带来的转变性暗示,同时认为这种盏在三星堆文化后期已经出现(XuJ.2003)。根据前一种观点,后文(和第8章)将会讨论的祭祀坑可追溯到三星堆文化晚期,但后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祭祀坑的年代为公元前2千纪后期,但不能追溯到任何文化转型时期。根据后一种观点,十二桥地层与三星堆青铜时代最晚期地层(即12和13层)属于同一时代,这反映了当时成都地区开始受到三星堆的影响。 三星堆最为著名者,是那些构成了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的早期青铜时代遗物(即三星堆Ⅱ)。这段时期最为著名的,是1986年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宏伟青铜雕塑,出土这些雕塑的地点后来为整个遗址和与祭祀坑有关的文化提供了名称(四川主编1987a,1987b,1989;四川1999;见随后的讨论)。三星堆文化首先是根据陶器组合来定义的,最具代表性的陶器包括有着三只袋形足的盉、高柄豆、小平底罐和有着钩状嘴的鸟头形勺把(Xu2001b,2008)。本书稍后将会介绍一些其他类型的器物,包括觚、樽和卷口三足器。正如许杰(JayXu,2001b:28)指出的,文化转变似乎表现为在本地的基础上吸收来自长江中游地区和黄河流域中原的新型制陶工艺。大部分有关三星堆的讨论都集中在祭祀坑(Bagley1990;Falkenhausen2003;李伯谦1996;李绍明主编1993;李学勤1997;俞伟超1996;赵殿增1996;邹衡1996。在那些数不清的出版著作中,这里仅举数例)。祭祀坑(K1和K2)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200年。不过人们认为它们的年代稍微有点不同,以K1较早(四川1999;四川主编1987a)。祭祀坑出土了大量有价值的遗物,包括玉石器、青铜器、金器、象牙、陶器和贝壳(Flad2012)。 自从三星堆K1、K2以及仓包包和月亮湾(三星堆的其他地点)其他相似但较小的祭祀坑遗存被发现后,它们便顺理成章地受到关注。这些遗存为三星堆文化时期仪式和经济格局的中心提供了独特的证据。祭祀坑是破坏型仪式所产生的最终结果,这种仪式涉及破坏与特定仪式有关的物品的行为(见第8章;XuJ.2001a)。此外,这些遗物反映了生活在三星堆的人群,至少是从事祭祀活动的个人所获得资源的相对广泛的网络。这些人可能居住在三星堆,至少是参与了这里的仪式活动(Falkenhausen2003,2011;So2008;Flad2012;见第7章)。 尽管这些仪式无疑在该地区较广阔的政治格局中扮演了重要的统合角色,但祭祀坑出土的遗物却没有任何反映政治权威的明确证据。即使是图像元素,包括拟人化的头像和穿着精美服饰、与真人一样大小的青铜人像也不是社群领袖的明确代表,而是超自然的存在。大量青铜头像上不同的头饰和发型或许反映了特定社会角色(孙华2013),但它们在本质上并不必然与政治有关。 然而,这些材料的某些方面确实与建立和维持等级制度的机有关。例如,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玉制武器和青铜兵器,它们显示了战争的象征对于正确的仪式行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这些都不是实用性的武器,这表明参与战争可能既有象征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另外,生产大量玉器和铜器和获得上述资源必须有一个组织良好和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专业工匠系统。 祭祀坑之外,从三星堆不同地点得来的三星堆文化遗物都没有得到完整的出版(虽然预计有一份全面的报告即将出版)。但是,我们确实掌握了一些有关这个遗址建筑物遗存的资料。早期的建筑可能与宝墩文化层有关,有简单的矩形或圆形的柱洞线。后期,在三星堆文化层及之后,是木骨泥墙和火烧墙建筑,以带有木骨架柱洞的基槽为代表(四川主编1987c)。这些围墙长度在3—9米,宽度则为2—9米。有时候两间房间会共有一面墙,但由于这些房间在内部是相连的,故它似乎并不是一座有着多个房间的建筑。此外,人们在青关山遗址(河道北岸,三星堆遗址的对面)的北部发现了高等级的建筑基址,但这些建筑的资料并没有得到详细的公布(孙华2013)。 人们报道了在三星堆发现的墓葬,大部分都是简单的土坑墓,出土有少量随葬品(四川主编1987c)。已经公布的最大型墓群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墙外面的仁胜村(四川2004;宋治民2005a;见第9章)。这些墓葬几乎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社会等级差别。 聚落规模从宝墩文化时期的简单聚落发展到三星堆文化时期有着巨型围墙的大型聚落。这道围墙由三个部分组成:位于墙体中心的土层以及外侧和内侧的倾斜土层(XuJ.2001b:28)。假设各个方向的外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这道墙和遗址内部保存下来的部分围墙的总长度将达到7800米。这长度是很多宝墩文化围墙长度的三倍以上(虽然它的长度比宝墩内墙和外墙合在一起时要短)。因此,修建这堵墙所投入的劳动力,比之前讨论的大多数宝墩文化遗址围墙所投入的劳动力要多几倍。超过1000名劳动力连续数年地投入到兴建这些墙体的工程中,进一步证明三星堆是人口密集的社区网络的中心节点和集体劳动的重点区域。 当然,三星堆并非成都平原在公元前2千纪中后期唯一遗址。人们在三星堆附近的成都平原北部发现了一些同时代的遗址(四川1992b),它们当中有一些已被发掘,包括烟堆子(四川2005)、桂林乡(成都与新都1997)、清江村(成都与郫县2001c)和羊子山、核桃村、金沙巷以及水观音(XuJ.2003:175)。 由于历史原因,位于新都区的水观音遗址是它们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四川1959d)。水观音在1956、1958年进行过两次发掘,是这个地区在“二战”后首批被发掘的遗址之一。人们在遗址中发现了三个文化层,最底层有着我们今天将之联系到三星堆文化的遗物,以及属于三星堆后期的几座墓葬。 成都市内或附近的其他一些地点出土了一些同时代的遗物,三星村(不要误解成三星堆;成都与青白江2006)、精品房(成都2006e)和黄忠村(朱章义与刘骏2001)都拥有三星堆文化的遗物。在东边稍远的地方,十二桥下层可能反映了这个地区从三星堆文化转变成随后的十二桥文化的过渡阶段。毗连十二桥的是方池街,它的第5层包含一些与三星堆文化的器物极为相似的陶器(成都与成都2003)。但在其他方面,它的遗物与沙溪的遗物相似,而方池街据说在文化上与三星堆有别(成都与成都2003:315)。 最后一点引发了一个与三星堆文化有关的有趣问题—这些不同的三星堆文化遗址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由于大部分遗址的结构、建筑特征和陶器之外其他遗物的资料相当缺乏,故我们在这里仅能做出推测。三星堆遗址本身就反映了它们延续了宝墩文化的一些集体策略。墙的建造在三星堆很重要—不仅用一个保护性的壁垒围绕着遗址,而且还将遗址内部分开。但是祭祀坑及其所出遗物却反映了在宝墩文化遗址中没有的活动。 祭祀坑中的遗物反映了一种对相对全面的资源获取网络的控制,并证明了冶金技术的进步。图像学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明显。例如,K1和K2有着一个完整的青铜人像和上文提到的青铜人头雕像。由于有一些木头黏附在一些青铜头像内,又由于其中存在着大量可能是燃烧过的木炭,故这些人头雕像似乎是放在木制身躯上的。这些头像是否代表着某些特定的人物、一般的“祖先”、神灵和其他生物呢?不同的发型是否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身份,或者代表着不同的宗族或民族?孙华(2013)确定了两种发型:将头发束在头后并以饰针维持的髻发和由向后垂的发辫组成的辫发。他认为前者与仪式专家有关,而后者则与行政或军事专家有关,并主张三星堆的领导集团以这两个精英群体的等级关系为特征,进而认为那些负责仪式活动的人在随后的十二桥时期失去了权力。这种解释是有争议的,而我们也很难说这些差异到底是反映了普遍而共有的身份,还是个别而有名字的人物。在任何情况下,在一个明显重要的仪式组合中使用人类肖像至少标志着个人在社会中重要性的相对转变。这说明相对宝墩文化不太明显的政治特点,三星堆社会在政治层面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群体策略(被定义为排他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政治行动,它与较以群体为导向的集体策略相反;Blantonetal.1996)。值得注意的是,特别考虑到青铜头像的木质底座的证据,类似的易腐烂的雕塑可能在青铜制品进入该地区之前就已经制作出来了。但即使这是事实,我们现在仍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它。 十二桥文化 成都平原下一个考古学文化是十二桥文化,人们通常推断其年代为公元前1200—公元前800年。我们仍然需要持续关注这种对成都平原文化史随后阶段所做的断代和年代学的鉴定。正如后文所解释的,现有的理论显示了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有重合的时候。推定从十二桥文化转变到随后的新一村文化发生在约公元前1000年 (Falkenhausen2001b:179),或发生在较接近公元前800年的时间范围一事,正如这里所言,需要对放射性碳测年数据进行更多系统的收集,并且要有稳定的数据采集背景。十二桥文化最初是在成都市中心附近一个遗址被确认的,该文化的其他遗址主要是在这个迅速扩张的城市中被分散地发现的。十二桥本身的地层横跨了三星堆文化过渡到十二桥文化的时期,而它们重要的特征(后文将会讨论到的几个木构建筑)在年代学上可能是仍然属于三星堆文化的(江章华与王毅1998;孙华1996)。具体而言,十二桥第13和12层(在遗址的最底层文化层)中所包含的遗物很多都与三星堆晚期的遗物相同,下文描述的建筑遗存位于这两层之间。人们推断第13层校准后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859±100年(距今3520±80年)和公元前2013±108年(距今3630±80年)。但这些数字相对于地层实际的年代很可能稍早,这很可能是年代较早的木材导致的。从第11层开始,尖底器占有优势一事表明物质遗存的普遍特征有着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的文化(见XuJ.2003中的讨论)。该遗址因而并不是十二桥文化的典型遗址。 第11—9层中的陶器是十二桥文化的典型遗物(图4.7),第9层的放射性碳测年校准后为公元前595±140年(距今2465±105年)。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尖底盏,但我们也发现有其他有尖底或小平底的器型,包括尖底杯和尖底罐(宋治民1998b,2005b)。除此之外,在三星堆文化遗物中很普遍的陶器种类,如鼓肩小平底盆和高柄豆仍然继续出现。我们可在成都和附近的其他遗址,包括在金沙江(诸如黄忠村和人防)、万安药业包装厂、方池街、桂林乡和正因小区这几个地点观察到由十二桥第13和12层所代表的过渡期(成都2001,2005c,2005g;成都与成都2003;成都与新都1997;成都与新都2003,2005;宋治民2005b:25)。 十二桥的典型遗址最为名的是在1985年发现的大型木构建筑(四川1987b)。这座建筑被发现于第12层之下,所占空间从西到东长142米,宽133米。这些桩柱组成了至少两座不同建筑物的地基。 一座大型的建筑物(F1)有一个由一系列地板梁组成的地基(图4.8),基于巨大的面积—约560平方米,F1被解释为一座“宫殿”。另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建筑建立在由木桩组成的框架上。这座较小建筑的墙身是通过将竹篾笆绑扎在木架上建成的。两者的屋顶都是用榫和系在一起的屋顶梁建造而成的。这些遗存为对古代建筑物进行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资料,但对政治或文化强权方面却没有提供多少有用的证据。即使是那个所谓的“宫殿”也不是特别富丽堂皇,而它有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公众集会大堂。无论如何,这些木制的地基要么是早于十二桥文化,要么就只是反映了这种文化极早阶段的某些情况。我们因此必须观察其他地方才能对这段时期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除了十二桥,在成都西部和西南部的南河及其支流沿岸也发现了同时代的聚落遗址。这些遗址有抚琴小区(王毅1991a)、方池街(成都与成都2003)、君平街、指挥街(四川与成都1987)、岷山饭店、岷江小区(李明斌与王方2001;ZhuZ.etal.2003)、高新西区(成都2005b,2005c,2005d,2005e;成都2006b,2006c,2007a,2007b;成都与郫县2005a,2007)和金沙,它们都得到了最深入细致的调查。 金沙位于成都市中心西边5千米远的位置,它是在2001年一次道路兴建工程中被意外发现的(遗址的位置和早期发掘历史全面的概述,见Zhuetal.2003)。这个遗址覆盖了超过5平方千米的土地,包括流经城市中心的摸底河,在这条河的两岸发现了20多处独立遗址点(图4.9)。 在这些地点发现的部分建筑遗迹中,人们于黄忠村三和花园(金沙遗址聚落的北部,它最先于1995年被调查)确认了5座大型建筑基址。这些建筑可能有着行政功能,或作为上层人士居所的一部分(成都2001)。人们在附近发现了大量小规模的建筑基址,大型和小型建筑物同样都是木骨泥墙结构。小型建筑物的面积约为20平方米,大型建筑物占地面积超过430平方米,并拥有对称结构。其他在遗址住宅区发现的建筑附属遗迹包括诸如由鹅卵石铺成的水沟这类集水设施、仓库或灰坑,还发现了16处用来烧制陶器的浅窑窑址。 金沙遗址附近的其他地点也有着类似的遗存,包括灰坑、“井”(一种深坑,坑中埋入一件无底陶罐,坑底及坑壁镶嵌着鹅卵石)、窑址、墓葬和房屋基址。这些遗址包括:黄忠村B线道路工程所在地的灰坑和窑址(成都2004a);毗邻A线的灰坑及遗物(成都2005a);“西城天下”的灰坑(成都2007b);万博的灰坑和墓葬(成都2004d);“春雨花间”所在地的墓葬、窑址和灰坑(成都2006d)和“芙蓉苑”中用作集水的“池塘”与7处十二桥时期的建筑物基址(成都2005h)。这些基址与位于附近三和花园的遗址一同表明,金沙遗址北边有着密集的住宅区和行政区。在后文将会讨论的“献祭区”南侧兰苑所在地也同样有大面积遗迹,包括461个灰坑、17处建筑基址、3处窑址和100多座墓葬(成都2003a)。 从宏观上观察这个遗址,它的很多遗迹都可能是仪式活动的结果:墓葬(见第9章)和所谓的祭祀遗迹(见第8章)。这些遗迹几乎都是小型窖穴,里面埋藏有玉器、象牙、黄金、青铜器,也包括人类俘虏、蛇和虎的石雕。虽然墓葬遍及各处,但祭祀遗迹却集中在行政区对面摸底河南岸的梅苑。这个遗址的建筑物似乎与在三星堆所见的建筑相类,其中住宅区和行政区位于河道北岸,而仪式区则在南岸(孙华2013)。 人们也能在成都之外找到十二桥文化的遗址。诸如沙溪和水观音这些在三星堆部分已经提及过的遗址,说明在这段过渡期内,很多遗址都具有连续性。另一个与十二桥文化有关,重要且神秘的遗址是位于竹瓦街的窖藏。竹瓦街位于彭州东边、三星堆西南10千米处,所出铜器埋藏在遗址的一件陶缸中,可分为两组(冯汉骥1985b;四川与彭县1981;王家祐1961)。一组有21件铜器,其中有13件武器;另一组则包括4件容器和15件武器。虽然我们很难推断这些遗物的具体年代,但这些铜器有可能是在约公元前10世纪生产的,即西周(约公元前1050—公元前771年)早期,与十二桥文化同时(Falkenhausen2001b)。竹瓦街的窖藏可能代表了所谓的“巴蜀青铜器”生产系统的源头(冯汉骥1980:42)。 在成都平原西南边缘,雅安沙溪的早期遗物包括小型的平底、尖底和圈足陶器,以及大量的有肩石器(冯汉骥1989;李明斌1999;四川与雅安2007;四川主编1990)。在其他地方,人们在雅安到乐山的青江沿岸(中国1988),在大渡河沿岸诸如麻家山等遗址(大渡河2003;中国主编2006),甚至在云南范围内做调查时都发现了类似的遗物。在与沙溪和成都方池街相似的遗址中,石器频繁出现的现象延续到了十二桥时期。 十二桥文化与前几个时期存在明显差别。首先,社群之间的冲突似乎变得更为突出,也更加普遍。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出现的武器,其出现频率在整个公元前1千纪日益上升。武器激增的现象可在十二桥文化遗址以及牟托、青羊宫和其他后期遗址中看到(Falkenhausen2003:222—224)。此外,人们在金沙附近和包括方池街在内的其他地点发现了数个石人,石人双膝跪地,手放后背作缚状(图4.10)。我们在三星堆中至少发现过一个与之相似的石人,这件石人现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它的遗存关系。这些武器和石人表明在十二桥文化中,制度化的冲突是政治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讽刺的是,尽管十二桥时期明显强调战争,但围墙在遗址中的角色却似乎淡化了。这可能支持了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围墙的主要功能不是用作防御的观点,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未经过完整发掘。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将来可能会在十二桥遗址,包括金沙,可能还有高新西区,发现防御性城墙。 第二个不同之处在成都平原聚落的分布方面是很明显的。最为重要的政治中心从广汉地区转移到在过去只有较小型聚落的成都地区。唯有在与十二桥第10—11层同时的时代里,权力的中心似乎才转移到成都地区。聚落,包括被较小建筑包围的所谓“宫殿建筑”的一些证据,以及一个独特的仪区—这是与三星堆的另一个明显区别,三星堆是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发现了“祭祀坑”。但在行政和仪式区域的南北分界中,也可能存在着一些延续性。 在三星堆之后,虽然在诸如竹瓦街等遗址中仍然发现了大型青铜器,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纪念性青铜器的铸造痕迹。十二桥文化本身的铜器缺少过去那种复杂而成熟的工艺(Falkenhausen2003:220)。此外,物质遗存的重心亦有转变。三星堆的铜器铸造者将资源、时间、心力和社会资本投放在制作为仪式展示和统合集体行为而设的物品上,但十二桥的铜器铸造者却参与制造了战争武器。冲突和协商对于维持十二桥社会的制度来说变得日益重要。 新一村文化 成都平原从公元前1千纪中期到后期的考古遗存并不如较早时期丰富。不过,零星的研究却使人们确认了这个地区历史中两个额外的时段:新一村文化(约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和青羊宫文化(约公元前500—公元前300年)。这两个时期在文化上与十二桥 文化有多大程度的区别,尚需更多的资料来研究。然而,在我们的概述中,有足够的特征将这些阶段彼此分开,因此我们在这里将它们视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1995年,距离十二桥100米远的新一村遗址得到发掘,由此命名了“新一村文化”(成都2004f)。新一村的陶器有别于十二桥:首先,新一村的陶器缺少了小平底容器以及长颈的豆、瓶、壶和与三星堆文化晚期有关的鸟头形勺把;其次,新一村的陶器只有少数代表十二桥文化的尖底杯。新一村的陶器以与十二桥文化相似的尖底盏为主,但新一村的尖底盏口较大、腹较浅,口沿也直。大型陶瓮与绳纹敞腹罐、鼎和其他个别种类的容器一同构成了新一村文化的典型器物(图4.11)。 其他有着新一村文化遗存的少数遗址包括指挥街和方池街(成都与成都2003;四川与成都1987)、金沙在西城天下所在地(成都2007d)和西南交通大学高新西区新校区(成都与郫县2005b)的遗址。人们在国际花园所在地的金沙遗址找到了与新一村文化有关的墓葬(成都2006f)。 相对于前一期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遗存,以及随后包括商业街船棺葬和羊子山的“金字塔”在内的青羊宫文化,新一村文化在成都平原并不具有代表性。这是说明该地区总体人口减少,还是没有找到新一村人口集中的地方,还是仅仅反映了对新一村文化底蕴认识不足,尚待确定。孙华(2000)认为,这与十二桥文化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普遍的混乱状态和遗址的废弃有关。 青羊宫文化 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最后一个阶段为青羊宫文化(约公元前500—公元前300年),以成都西边一个用来供奉老子的庙宇来命名(四川1956a;四川1959b)。其他与之相关的地点包括上汪家拐(成都与四川1992;它有时被用作这段时期典型的遗址,如Zhuetal.2003)和十二桥遗址群的方池街(成都与成都2003;成都与四川2009;四川1959b;孙华2000:11)。青羊宫文化层的陶器大多是棕色的夹砂陶。比较有特色的器型包括釜形鼎、大口绳纹釜与小口绳纹釜和多种用来盛放食物的豆(图4.1)。但是,也有承续了新一村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尖底盏。其他遗物包括陶制虎形器,它延续了从金沙石虎开始的虎形肖像传统,并从公元前1千纪下半叶开始用来装饰所谓的“巴蜀青铜器”(冯汉骥1961)。 青羊宫本身无法复原青铜时代晚期的聚落是如何组织的,而随后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这段时期的墓葬。在很多出版物中,这些墓葬被确认为“战国墓葬”(见第9章)。独特的青铜器包括有着环形手柄的鍪、一种用来蒸煮食物的甑和所谓的“巴蜀青铜器”。这些巴蜀青铜器包括柳叶形剑和尖叶形矛、圆刃弧肩钺和有着三角形援和方形内的戈,至战国晚期,戈的援变长且弯曲(李学勤1985:207)。许多在中国其他地方已经过时的青铜器种类在四川继续存在了几个世纪,且与它们的中原源头分道扬镳(Falkenhausen2001b:187)。 此外,装饰元素加重了遗物的地域特色。重庆地区出土的青羊宫类型的青铜器经常统一使用一套数量有限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包括风格化的虎、雀鸟、鹿、蝉、蚕、人类手臂、心形或花蕾状的图案,以及盔甲和其他几何、抽象的符号(Sage1992:48—50)。这些符号可以在青铜兵器、钟和印章中找到(Sage1992:74)。此外,后来一些仍保留有这些符号的器物同时也带有一些未被破解的“巴蜀文字”所写成的铭文(Sage1992:73—75;冯汉骥1996;刘志一1989;彭静中1980;钱玉趾1988,1989;魏学峰1989)。尽管这些铭文与周文化圈的铭文有一些基本的相似之处,但它们与中国其他文字系统之间还没有明确的铭文联系,所以现存的少数铭文的内容并不清楚。 青羊宫文化墓葬的几个特征反映了该时期社会阶层的加速分化。一些墓葬,如文庙西街的两个墓葬被装饰得非常华丽(成都2005g);其他墓葬则放置了船棺,即独木舟形的木棺。这些墓穴与没有棺木在内的土坑墓葬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放有船棺的墓葬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成都商业街的墓葬(成都2002;成都2009)。那里出土了17具完整或不完整的船棺,所有棺木都水平排列在一个土坑中,墓坑底部平置有平行的原木(见第9章)。除了两具船棺保存完整,其余棺木均已在古代被盗掠,但发掘过程中仍出土了大量陶器、髹漆的木器、竹制用品及铜器。这些铜器大部分都是武器和工具,但当中亦有几个铜制的印章和带钩。商业街的棺木证实了成都地区在战国时期是上层人士的居住地。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已陆续在整个四川地区发掘了青羊宫时期的墓葬遗址,包括很多置有船形棺木的墓葬(四川1960;见第9章)。当保存状况较好时,青羊宫文化的墓葬倾向于包含有大量遗物。因此,它们不是战国时期普通社会成员墓穴。相反,它们反映了上层人士的墓葬传统,并可能是分散在四川盆地的政治领袖的墓葬。这些墓地中很少有大量的墓葬,这很可能表明绝大多数人的墓地尚未被发现。 已知的墓葬证明了当时人们对军事资源的持续关注。新型武器(剑和匕首)在战国时期的墓穴中变得很普遍,其中很多武器刻有用未被破解的当地文字写成的铭文,或可能是族徽的单一符号。此外,在许多遗址中发现了印章,这些遗址包括商业街、什邡城关(四川与什邡1998;四川主编2006a)、宝轮院(四川1960;四川与广元1998)、荥经附近的遗址(四川1984;荥经1994)。商业街出土的一些印章是几何形的,但其他印章却描绘了可能代表重要仪式活动的场景(图4.12)。这些印章的广泛存在显示了与通信和所有权有关的普遍习俗。虽然印章在战国时期中国很多地区都为人所知(李学勤1985:399—413),但四川的印章由于没有可以识别的战国时期文字而与其他印章有所不同。 青羊宫时期的很多遗物都与远方地区出土的遗物相似。例如,商业街和其他遗址出土的漆器可能是在当地所制的,但它却明显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漆器生产有关。又如新都的铜器与长江中游楚墓的铜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李学勤1985:213)。我们甚至可以确认百花潭的铜壶与其他地方有更深层的联系。这个壶由镶嵌的场景装饰,其中展示了射箭、准备食物、收集桑叶、乐师、上层人士饮酒进食、跳舞、狩猎和处理鹅、狩猎各种珍奇的野兽,以及两个战争场面:攻城与水战。这件容器很有可能是在山西侯马的铸造作坊中生产的,离它埋藏的位置很远(Thote2001:219—220)。 虽然青羊宫文化的墓葬和随葬品较丰富,但我们只有很少的证据来说明遗址的结构。上汪家拐有一些灰坑(成都与四川1992),人们亦在方池街确认了一些“灌溉设施”(成都与成都2003:297)。但是,这些遗迹的规模都很小,无法证明城市规划的重要程度。 一个较能直接地说明集体建造活动的遗迹是羊子山那个所谓的“金字塔”(四川1957)。它曾经是一个10米高的土丘,但却不幸地在发现不久后被破坏了。这个土丘的年代在十二桥文化之后(江章华主编2002:12),是一座战国晚期墓葬(四川1956b)。发掘人员将这座遗迹复原为一座三层的金字塔。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土丘是用于祭祀的(林向1988;孙华2000:213),但到底目的为何,我们无从知晓。孙华相信它的建造和使用与开明部族在成都建立蜀国首都一事有关(孙华2000:212)。 青羊宫文化墓葬和羊子山的位置可能大致与这个地区的政治中心对应,而且明显与第8和第9章所讨论的仪式格局有关。遗憾的是,凭借这些遗迹无法对青羊宫时期人口规模和重要政治节点的分布做全面描述。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回历史文献,我们会对这段时期的政治格局有更多的了解,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要比早些时候可靠些。开明氏族第九代成员在成都建立首都一事可能是在公元前5世纪进行的,而这件事也是这种政治地理的一个例子。此外,墓葬资料表明,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精英阶层内部存在着文化联系。他们的墓葬形式基本相似:均使用船棺和青铜武器、陶器、竹木器(有时髹漆)以及殉牲(有时是放在陶器或竹制的容器之内;成都2007e)。这些墓葬显示了在青羊宫文化时期有着重要而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商业街的墓葬和羊子山的金字塔证实了现今成都地区似乎再次成为一个重要中心的事实。 总 结 出人意料的是,考古资料对于这个地区文化顺序的较早阶段来说是最为坚实的证据,表明宝墩、三星堆和十二桥时期是政治格局的过渡期。我们看到多个面积巨大的早期大型遗址分布在整个成都平原的情况,这些遗址可能代表了对于邻近的村子和农庄来说有着统合作用的公共庇护所。在公元前2千纪早期,这些遗址的其中一个,即三星堆变得重要,并控制了整个地区资源获得的网络。有证据显示以个人为导向的权力结构出现,而不同社群之间的冲突也开始了。冲突在十二桥时期变得更为显著,其时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中心向南转移到成都地区。就我们所知,这种情况一直到这个地区为秦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