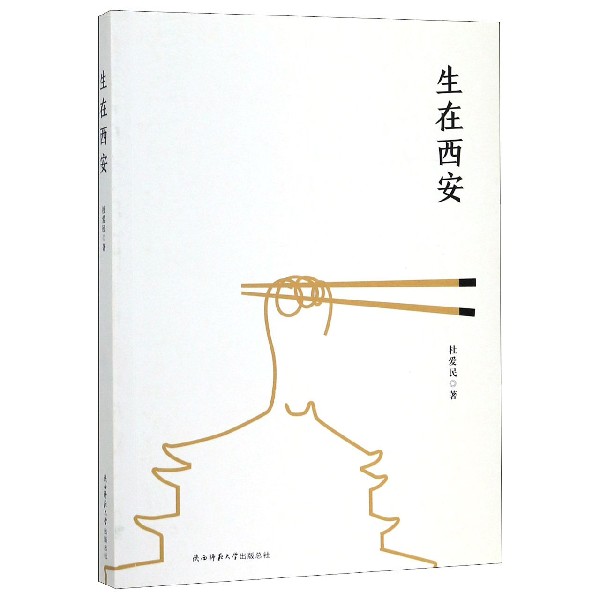
出版社: 陕西师大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0.40
折扣购买: 生在西安
ISBN: 9787569510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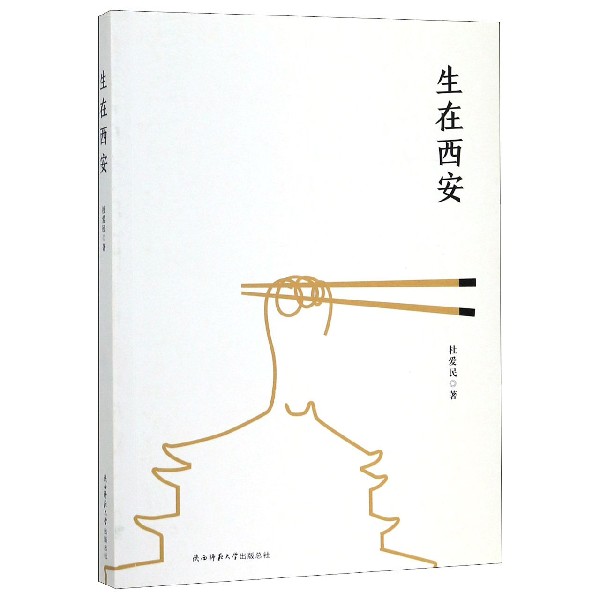
仁义村如今已是灯红酒绿,人群熙攘。 有一阵子,我常去画家赵振川的画室看他作画,途中 要从仁义村经过,每到黄昏时分,街上的花灯初上,仁义 村中的道路两旁,也三三两两亮起烤羊肉串的红灯罩子, 咝咝的烤肉声响起,肉香和青烟缭绕,让我想到炊烟袅袅 环绕的大地,背后暗藏的诗情画意。 从前仁义村只是南门城墙外东南方向附近的一片菜地 ,是出西安南城门外的第一个小村落,村里住的全是菜农 。每到夏天,也是黄昏时,我和王正就要翻过城墙,游过 城河,到仁义村的田塍上玩耍。王正每次先要钻进草丛中 腾空肚子,结束后总要重复对我说:今天的星空真蓝。一 阵凉风吹来,我便会在田塍上打一个尿战。这时候,菜农 们都已收工回家吃饭,菜地尽头,并排立着的几座农舍, 就是仁义村了。农舍屋顶上空,此时也已经升起了白色的 炊烟。不远处,会时时响起狗叫声,运气好的话,还能听 到从陕歌大院传来的圆号声。太阳已经落山,夏日里的夕 阳在天空中留下几道残血。仁义村的菜田摆满了我和王正 享用的盛宴:脆嫩的黄瓜和青豆,黄色的西红柿涩中略带 甘甜。我俩躺在草丛中一边饱食着这些素朴的食物,一边 数着天空的星星。天很低,清澈通透,星星闪亮。黑暗中 ,有人朝我们这边移动,手里好像操持着什么家伙,太远 ,我们也看不清。 王正说,是狗目的老田。 我们即刻从仁义村撤离,游过城河,翻越城墙,回家 睡觉了。 20世纪60年代末,西安看上去还像是一个小城镇。站 在南城墙头望,城圈里尽是大片灰瓦房,只有报话大楼和 钟楼邮局两座高楼,城墙外属郊区,有麦田和菜地。仁义 村那时候也只是城圈附近的一个小菜园子,村里的菜农构 成单一,朴实厚道,经年务农种菜。老田那会儿一大早赶 一驾马车,上面摞满一箩筐一箩筐的新鲜蔬菜,停放在我 们巷口的菜店门前,老田就蹲在马车旁抽旱烟,盯着旁人 卸车。我和王正背着书包经过,喊一声:田伯,你人真特! 老田乐呵着露出一嘴黑牙,咀嚼着黄铜烟杆支吾着:唉, 咱娃特!咱娃特。 我和王正便一路小跑,哈哈大笑。 那会儿在城墙上,你还会感觉到:城乡两立,泾渭分 明。城墙在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并且高高在上。一边是田 园和农舍,还有诗情与画意;一边是勉强能算作城市的老 西安城,住满了小市民和各色闲杂人等。据老人们讲,每 天老皇城里放炮,城门楼子就张灯,城外包括仁义村在内 的农家,才开始生火做饭。这些都是老规老理,跟仁义村 都有关。 到了70年代中期,仁义村的菜田渐稀,我们中学“学 工”去的那间皮件厂就建在仁义村的地头上。那时候,村 中已能见到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出出进进,忙忙碌碌,肩 扛印着日本尿素的蛇皮袋子,鼓鼓囊囊,不知放的什么东 西。逐渐萎缩的菜田旁边,堆满了生活垃圾和建筑废料。 菜农们有的盖起了二层砖楼,底下一层自己住,上面一层 招的是房客。在仁义村租房手续简便,只要说好价钱,就 可以了事。房客想干什么,房主从不过问。自从仁义村从 郊区划归城中的碑林区管辖后,村民的孩子也从城外来到 城里,在我们读书的五中插班上学。他们常常结伙在校园 里出没,剃着瓦青的光头,顶上扣一个草帽,光脚穿草鞋 ,书包里放的凶器是清一色的镰刀。谁要停下来,多瞧上 他们几眼,他们便会一群围上来,把你彻底放翻。 田伯在仁义村口紧靠环城路的地方,摆起了茶摊,兼 卖纸烟和一些小零食,嘴头上叼的已不是旱烟杆子,换成 了带把的纸烟。他很深地吸足一口,烟头就闪亮一下,吸 进肚里的烟气,也不见他朝出吐。我在田伯的茶摊上歇过 脚,买过烟,喝过凉茶。老头已被逐渐滋润的日子弄得有 些糊涂,见我已不认得了,左手的无名指上带着一颗假钻 戒,冲外地打工的人说话的口气像个大款。田伯已无菜可 种,没有马车能让他来赶,生活就这么改变了一切。摆茶 的经历,让他看上去增添了不少江湖的习气。他一边吆喝 着自己的买卖,一双贼眼,在旁边不远处的两个打工妹身 上,来回地打量翻转。 仁义村就像深圳附近的龙岩,上海旁边的青浦,北京 跟前的门头沟,都成了通往大城市的旱码头。被城市的向 心力从远方吸纳而来的人群,又由于城市的排斥和拒绝, 就这样停泊在了这些城乡交会的地带,或城中的村子。仁 义村标志着城乡的分隔。城市在对农村的开放中获益,而 那些涌向城市的人群,在仁义村中又失去了原先生活里的 家族和集体的相互关照。仁义村里的外地人,来来往往, 充满着离乡背井的动荡:温州人开发廊,江苏人卖布料, 河南人收破烂,湖北人打短工,四川人开餐馆,东北人搞 团伙。仁义村的情况,天天都在变,天天都不一样。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