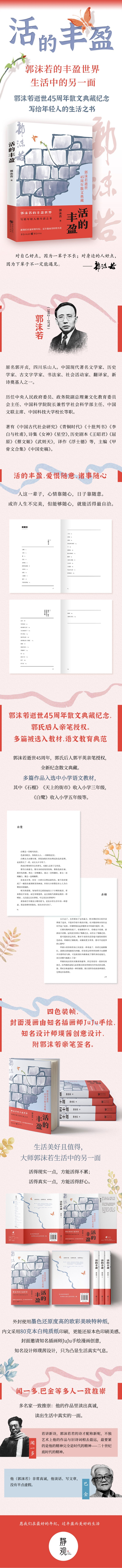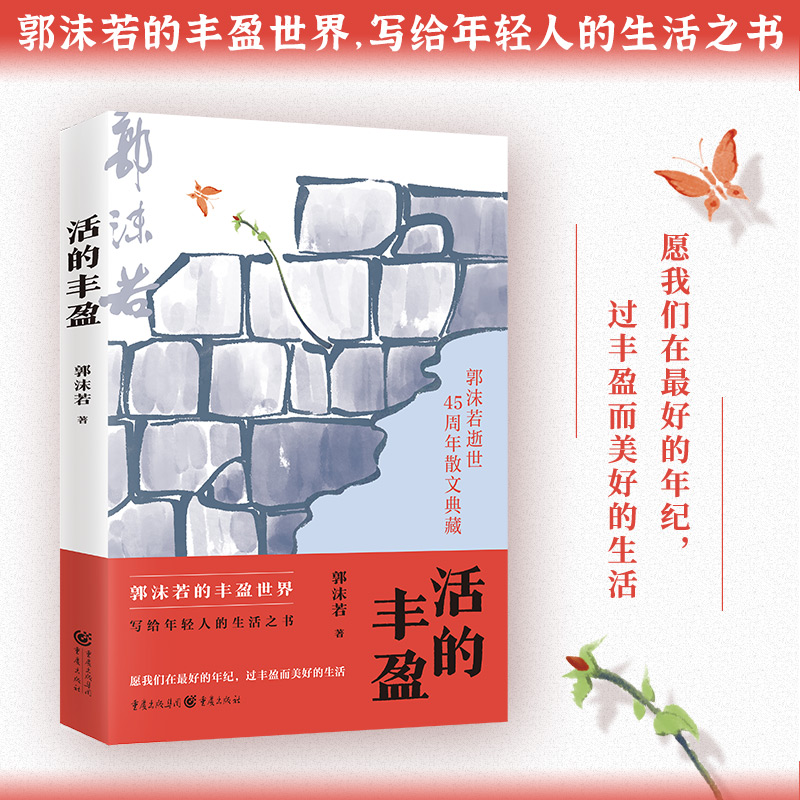
出版社: 重庆
原售价: 46.00
折扣价: 28.60
折扣购买: 活的丰盈
ISBN: 9787229173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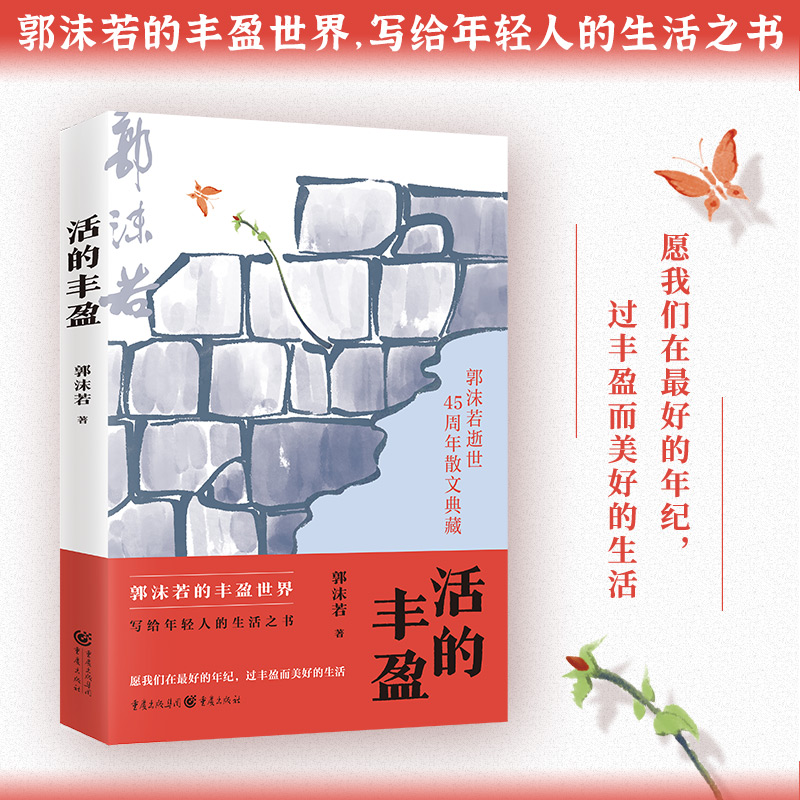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新诗奠基人之一。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等职。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李白与杜甫》,诗集《女神》《星空》,历史剧本《王昭君》《屈原》《蔡文姬》《武则天》,译作《浮士德》等,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
诗歌与音乐 自然界中一切的风声雨声,水声涛声,兽声鸟声,甚至如花开花落的声响,都有一定的顿挫抑扬。人在未有言语时说发出的意思混沌的呼号叫笑,也都是自成天籁。这些都是最早的音乐或音乐的母型。人到发现了自然音乐中的规律,于是便有音阶与律吕的产生,由于音律的合理组成,使音乐更加成长了。 人类的语言发明后,一种兼含着明确意识的音乐出现,它便是诗歌。诗歌对于音乐似乎只是一种分枝或者变种。但言语的音律性有限制,而音律的发展无限制,意识的音乐超越了音律的限制而成长,于是诗与歌便逐渐分离,诗歌与音乐也逐渐分离了。 随着两者的成长与分离,同时更为社会的分化说强迫,诗歌与音乐都错误地走上了权贵奉仕的道路。技巧归诸宫廷。本质留在民间。技巧随着时代的翻新而翻新,本质随着人民的用在而用在。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人民的愿望,始终保持着诗歌与音乐的不断的本流。 三十年来人民在呼唤,要把诗歌和音乐各自的本流充沛起来,要把技巧与本质合而为一,要它们整个地奉仕于人民,反映人民的生活,表达人民的情感,成就人民的愿望。经过三十年的辨证的发展,雅与俗,新与旧,外来与固有者,渐渐到了可以成为新的综合的时候了。人民在要求着新的人们艺术,新的民族形式。 诗歌与音乐要在这新的要求之下平衡地发展,而保持着密切的关联,要以人民的意识为意识,时代的节奏为节奏。没有意识的节奏不能成为音乐,没有节奏的意识不能成为诗歌,这对流动的时间艺术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呼吸,并使其他的姊妹艺术在同一的呼吸之下而发展着新的生命。就这样,我们服从人民的号召,我们要创生新音乐与新诗歌,新音乐与新诗歌的大合抱,和一切艺术的大合抱,奉献于我们至高无上的主——人民。 1946 年 6 月 9 日于上海 忆成都 离开成都竟已经三十年了。民国二年便离开了它,一直到现在都还不曾和它见面。但它留在我的记忆里,觉得比我的故乡乐山还要亲切。 在成都虽然读过四年书,成都的好处我并不十分知道,我也没有什么难忘的回忆留在那儿,但不知怎的总觉得它值得我怀念。 回到四川来也已经五年了,论道理应该去去成都,但一直都还没有去的机会。我实在也是有些踌躇。 三年前我回过乐山,乐山是变了,特别是幼年时认为美丽的地方变得十分丑陋。凌云山的俗化,苏子楼的颓废,高标山的荒芜,简直是不堪设想了。 美的观感在我自己不用说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客观的事物经过了三二十年自然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三二十年前的少女不是都已经成了半老的徐娘了吗? 成都,我想,一定也变了。草堂寺的幽邃,武侯祠的肃穆,浣花溪的潇洒,望江楼的清旷,大率都已经变了,毫不容情地变了。 变是当然的,已经三十年了,即使是金石也不得不变。更何况这三十年是变化最剧烈而无轨道的一世 ! 旧的颓废了,新的正待建设。在民族的新的美感尚未树立的今天,和谐还是观念中的产物。但成都实在是值得我怀念,我正因为怀念它,所以我踌躇着不想去见它,虽然我也很想去看看抚琴台下的古墓,望江楼畔的石牛。 对于新成都的实现我既无涓滴可以寄与,暂时把成都留在怀念里,在我是更加饶于回味的事。 1943 年 2 月 13 日 访沈园 一 绍兴的沈园,是南宋诗人陆游写《钗头凤》的地方。当年著名的林园,其中一部分已经辟为“陆游纪念室”。 《钗头凤》的故事,是陆游生活中的悲剧。他在二十岁时曾经和他的表妹唐琬(蕙仙)结婚,伉俪甚笃。但不幸唐琬为陆母所不喜,二人被迫离析。 十余年后,唐琬已改嫁赵家,陆游也已另娶王氏。一日,陆游往游沈园,无心之间与唐琬及其后夫赵士程相遇。陆既未忘前盟,唐亦心念旧欢。唐劝其后夫遣家童送陆酒肴以致意。陆不胜悲痛,因题《钗头凤》一词于壁。其词云: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这词为唐琬所见,她还有和词,有“病魂常似秋千索”,“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等语。和词韵调不甚谐,或许是好事者所托。但唐终抑郁成病,至于夭折。我想,她的早死,赵士程是不能没有责任的。 四十年后,陆游已经七十五岁了。曾梦游沈园,更深沉地触动了他的隐痛。他又写了两首很哀婉的七绝,题目就叫《沈园》。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这是《钗头凤》故事的全部,是很动人的一幕悲剧。 二 十月二十七日我到了绍兴,留宿了两夜。凡是应该参观的地方,大都去过了。二十九日,我要离开绍兴了。清早,争取时间,去访问了沈园。 在陆游生前已经是“非复旧池台”的沈园,今天更完全改变了面貌。我所看到的沈园是一片田圃。有一家旧了的平常院落,在左侧的门楣上挂着一个两尺多长的牌子,上面写着“陆游纪念室(沈园)”字样。 大门是开着的,我进去看了。里面似乎住着好几家人。只在不大的正中的厅堂上陈列着有关陆游的文物。有陆游浮雕像的拓本,有陆游著作的木版印本,有当年的沈园图,有近年在平江水库工地上发现的陆游第四子陆子坦夫妇的圹记,等等。我跑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又连忙走出来了。 向导的同志告诉我:“在田圃中有一个葫芦形的小池和一个大的方池是当年沈园的故物。” 我走到有些树木掩荫着的葫芦池边去看了一下,一池都是苔藻。池边有些高低不平的土堆,据说是当年的假山。大方池也远远望了一下,水量看来是丰富的,周围是稻田。 待我回转身时,一位中年妇人,看样子好像是中学教师,身材不高,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向我走来。 她把书递给我,说:“我就是沈家的后人,这本书送给你。” 我接过书来看时,是齐治平著的《陆游》,中华书局出版。我连忙向她致谢。 她又自我介绍地说:“老母亲病了,我是从上海赶回来的。” “令堂的病不严重吧?”我问了她。 “幸好,已经平复了。” 正在这样说着,斜对面从菜园地里又走来了一位青年,穿着黄色军装。赠书者为我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从南京赶回来的。” 我上前去和他握了手。想到同志们在招待处等我去吃早饭,吃了早饭便得赶快动身,因此我便匆匆忙忙地告了别。 这是我访问沈园时出乎意外的一段插话。 三 这段插话似乎颇有诗意。但它横在我的心中,老是使我不安。我走得太匆忙了,忘记问清楚那母子两人的姓名和住址。 我接受了别人的礼物,没有东西也没有办法来回答,就好像欠了一笔债的一样。 《陆游》这个小册子,在我的旅行箧里放着,我偶尔取出翻阅。一想到《钗头凤》的故事便使我不能不联想到我所遭遇的那段插话。我依照着《钗头凤》的调子,也酝酿了一首词来: 宫墙柳,今乌有,沈园蜕变怀诗叟。 秋风袅,晨光好, 满畦蔬菜,一池萍藻。 草,草,草。 沈家后,人情厚,《陆游》一册蒙相授。 来归宁,为亲病。 病情何似?医疗有庆。 幸,幸,幸。 的确,“满城春色宫墙柳”的景象是看不见了。但除“满畦蔬菜,一池萍藻”之外,我还看见了一些树木,特别是有两株新栽的杨柳。 陆游和唐琬是和封建社会搏斗过的人。他们的一生是悲剧,但他们是胜利者。封建社会在今天已经被和根推翻了,而他们的优美形象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沈园变成了田圃,在今天看来,不是零落,而是蜕变。世界改造了,昨天的富室林园变成了今天的人民田圃。今天的“陆游纪念室”还只是细胞,明天的“陆游纪念室”会发展成为更美丽的池台——人民的池台。 陆游有知,如果他今天再到沈园来,他决不会伤心落泪,而是会引吭高歌的。他会看到桥下的“惊鸿照影”——那唐琬的影子,真像飞鸿一样,永远在高空中飞翔。 活的丰盈,爱恨随意,诸事随心 ?郭沫若逝世45周年散文典藏。窥见大师郭沫若生活中的另一面。 ?闻一多、巴金等一致推崇。众名家一致推崇认同: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 四色装帧,双封设计。外封使用墨色还原度高的欧彩美映特种纸,内文采用80克本白纯质纸印刷,更能还原本色印刷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