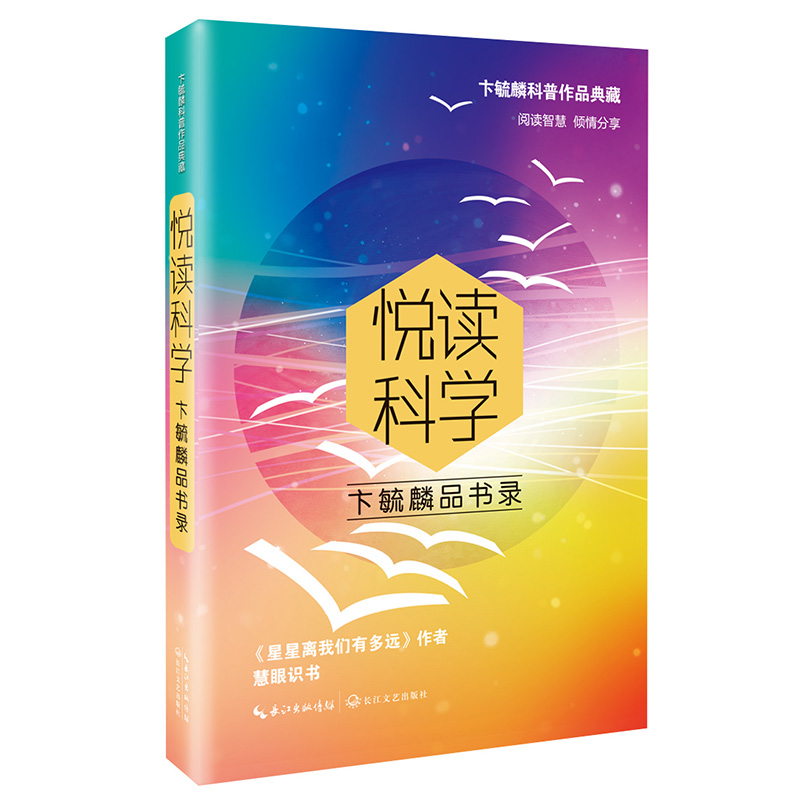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0.30
折扣购买: 悦读科学(卞毓麟品书录)
ISBN: 97875702077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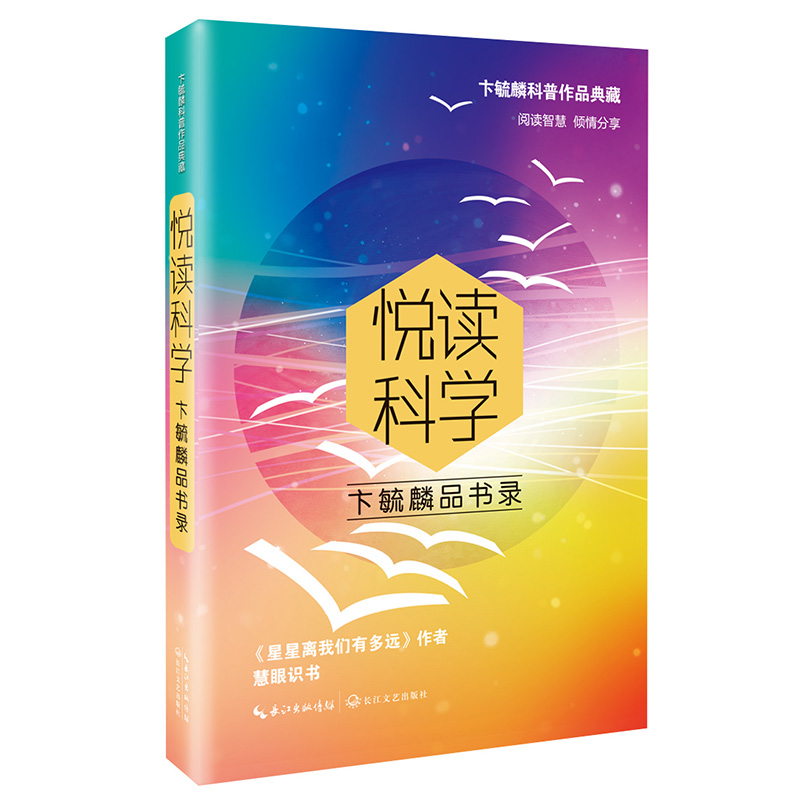
卞毓麟,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顾问,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终身名誉理事长。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天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等。著译科普图书30余种,发表科普和科学文化类文章约700篇。作品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一书获201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入选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配套阅读书目,《拥抱群星:与青少年一同走进天文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7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曾获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贡献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海市大众科学奖、中国天文学会九十周年天文学突出贡献奖等表彰奖励。
永恒的“魔镜” 圣诞夜话埃舍尔 14年前的圣诞节,我在异国的一个小岛上,和一位西方艺术家谈起了埃舍尔。 从大不列颠岛最北端的小城瑟索,再往北越过一片名叫彭特兰湾的水域,便是中国人足迹罕至的奥克尼群岛了。那里住着一对姓斯特鲁特的夫妇,40来岁,无子女,丈夫是作曲家,妻子擅长装帧美术,是一家地道的“个体户”。他们原住在英格兰,因为向往宁静的田园生活,才搬到这人烟稀少的地方。 像现代英国的许多家庭一样,他们乐意邀请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到家里共度圣诞佳节。1989年,我正在英国的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做访问学者,意外收到了斯特鲁特家的邀请。圣诞前夕我到他们家时,送给主人三件小礼物:一块中国真丝头巾,一支中国竹笛和一副中国象棋。同时在他家做客的,还有一位在阿伯丁大学就读的津巴布韦黑人姑娘。 当时的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台长是马尔科姆?朗盖尔教授,他是苏格兰人。听说我要去奥克尼群岛过圣诞,他觉得非常有意义,并告诉我:“奥克尼的文化就像中国一样古老。”史前的文物和遗址,为此提供了无言的证词。另一方面,辞行前夜与主人关于现代科学和艺术的一番海阔天空,也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 其实,斯特鲁特先生对天文之懵懂,与我对作曲之外行堪称伯仲。起初,双方的话锋并未迅速合辙。忽然,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画册,我顿时脱口而出:“埃舍尔!”议题随即就集中到了毛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的身上。我还随手做了一点记录,主人感到奇怪,我说:“留个纪念,以后也许有用。”这条记录注明,他那本《埃舍尔的世界》作者署名是埃舍尔本人和洛赫尔,1971年由纽约的阿布拉姆斯出版公司出版。我们谈得最起劲的作品,是《变形》《昼与夜》《默比乌斯带》以及平面分割习作《骑士》。 图04-2 埃舍尔(右)在逝世前几周告诉《魔镜》的作者布鲁诺?恩斯特:“我的作品是最美的,同时又是最丑的。” 1972年,埃舍尔去世了。不久,一部名为《埃舍尔的魔镜》的新著问世,作者布鲁诺?恩斯特是一名数学教师,此书是他长期拜访和研究埃舍尔的结晶。虽然画家本人未能活到此书付印,世人却对它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它被译成十几种文字,2002年金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以《魔镜——埃舍尔的不可能世界》(以下简称《魔镜》)为题,推出了该书的中译本,译者是田松和王蓓。 从《骑士》开始 “您是怎样知道埃舍尔的?”斯特鲁特先生曾问我。 我告诉他,1963年我上大学时,读了杨振宁教授的名著《基本粒子发现简史》,封面上就印着埃舍尔的《骑士》,它那神奇的对称性令我敬意陡生。 图04-3 埃舍尔速写本上的骑士图 杨振宁这部名著的英文原版,出版于他荣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5年。该书中文版由其胞妹杨振玉和范世藩合译,于1963年9月面世。在前言中,杨先生写道:“骑士图是埃舍尔先生画的,我深深地感谢他允许我采用这幅图。”在正文中,他再次提到:“图39即取自荷兰美术家埃舍尔的一件出色作品。从图中可以看到虽然图画本身和它的镜像并不相同,但是如果我们将镜像的黑白两种颜色互换一下,那么两者又完全相同了。”杨先生借此来阐述物理学中的“缔合转换”引起的对称。 这幅骑士图,画在埃舍尔的空间填充速写本中。恩斯特在《魔镜》中说:“没有任何主题能比周期性图形分割更合埃舍尔的心意……除此之外,埃舍尔只对另一个主题写过文章,那就是探寻无穷——虽然他没有用同样的篇幅。”埃舍尔本人也写道:“这是我挖掘出来的最丰富的灵感之泉,它至今也没有枯竭。” 埃舍尔镶嵌图案的独到之处,特别在于他采用的基本图案总是可以识别的具体图形,如鸟、鱼、人等等。例如,木刻《日与月》中,14只白鸟和14只蓝鸟填满了整个平面。 图04-4 《日与月》,木刻,1948年(见彩色插页1)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白鸟身上,就会被带进黑夜之中:在深蓝色的夜空背景上有14只光明的鸟,还可以看到月亮和其他天体。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蓝鸟身上,就会把它们当作在白日天空背景上的深色剪影,中央的太阳光芒四射。在这幅画中,所有的鸟都互不相同。在埃舍尔的作品中,此类不规则平面分割的实例为数不多。 变形的升华 “变形”是埃舍尔的一绝。在奥克尼的那个圣诞节,我与斯特鲁特先生热烈谈论的《昼与夜》正是“变形”的典范。这幅木刻将人们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图04-5 《昼与夜》,木刻,1938年 画面中央的正下方,有一块近乎菱形的白色田地,它自然地将我们的视线吸引向上;田地变形了,而且变得很快,只用两步就变成了白色的鸟。它向右飞,翱翔在河畔小村上空,陷入黑夜之中。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画面下部中心线两侧,任选一块黑土地。它同样升上天空,变成黑色的鸟,向左飞翔,飞到一片晴朗的田野之上,而这片田野又恰好成为右边夜景的镜像。从左到右,白天逐步过渡到了黑夜;从下到上,田地渐渐升上天空。埃舍尔的视觉使这一切得以实现,使《昼与夜》成了一幅极受赞誉的作品。 后来,埃舍尔以纯技巧令人折服的“变形”作品渐渐减少,“变形”本身也逐渐依附于其他概念的表现。例如,石版画《魔镜》表现的主题乃是“共存的世界”。画中不仅具有镜像对称,而且让镜像获得了生命,生存在另一个世界中。恩斯特对这幅画做了极佳的导读: 图04-6 《魔镜》,石版画,1946年 一切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圆点开始。在最靠近观众的镜子边缘,就在斜栏的下面,我们可以看见一只小翅膀的尖端和它的镜像。让我们沿着镜子向里看,它就变成了整只有翅的猎犬,其镜像也随之而变……当那条真实的狗从镜前向右转身时,它的镜像随之向左;而这个镜像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它竟然从镜子后面走了出来……现在这些有翅犬左右分开,每走一程便使自己的数目增加一倍;然后,它们像两支军队一样开向对方。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面面相对,就从空间跌落到平面,变成了瓷砖地面上的图案……黑狗通过镜面时变成了白狗,恰好填满了黑狗之间的白色空隙。这些白色空隙又逐渐消失,直至最终狗们了无踪迹。它们似乎从未存在过——确实,这些有翅犬怎么可能从镜子中冒出来!然而,还有一个谜“团”在那里——镜子前面还立着一个圆球,沿着某一个角度向镜子后面看去,只能看见这个球的一部分镜像,但是,镜子后面还有一个圆球——一个足够真实的物体,就在左半部分狗的镜中世界里。 “共存的世界”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例如,前文介绍的《日与月》就是以平面分割为手段,实现了两个世界的融合。 透视与无穷 绘画,总是只能把三维的现实表现在二维的平面上。为了使我们在观看一幅画时,与我们观看此画所表现的真实物体时,在我们的视网膜上呈现完全相同的图像,就必须遵循透视法。 埃舍尔对此做过许多探索。例如,他创作《深度》的目的,是要描绘无限伸展的空间。这幅画的技术难度很大,那些鱼要越画越小,缩小的比例要非常准确。而为了加强深度的表现力,鱼离得越远,它们表现出来的反差就要越小。恩斯特评论道:“作一幅石版画可能还容易些,但是木刻就难多了,因为木刻的每一个点都非黑即白,不可能用灰色来形成反差。然而埃舍尔……成功地引入了这种所谓的光透视法,作为增强立体空间表现力的一种手段。这种方法远远超越了几何透视的诸多限制。”诚哉斯言! 埃舍尔对于无限的兴趣使他提出,“比如有这么一个人……突发奇想,要用他的艺术来探索无穷,还要尽可能地精确、逼近”“他将采用什么样的形状呢”? 在考克斯特教授的一本书中,有一个图示使埃舍尔深受触动,觉得它很适合表现无穷。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埃舍尔得出结论:“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法能够……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合乎逻辑的界限之中获得‘无穷’ ……最大的动物图形放到中间,无限多和无限小的极限则在圆周处达到。”他创作了一组《圆极限》,其中最好的一幅是《圆极限Ⅲ》。同一系列的鱼都具有同一种颜色,它们首尾相接,沿着环形路线从这边到那边游个不停,越游近中间就变得越大。 书是明灯,书是清泉,书是宝库,书是利剑。天文学家、科普名家卞毓麟先生读万卷书,写下自己的真知灼见。《悦读科学——卞毓麟品书录》带领你在书海遨游,细细品书论书,为你导航,指点迷津,一卷在手,悦读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