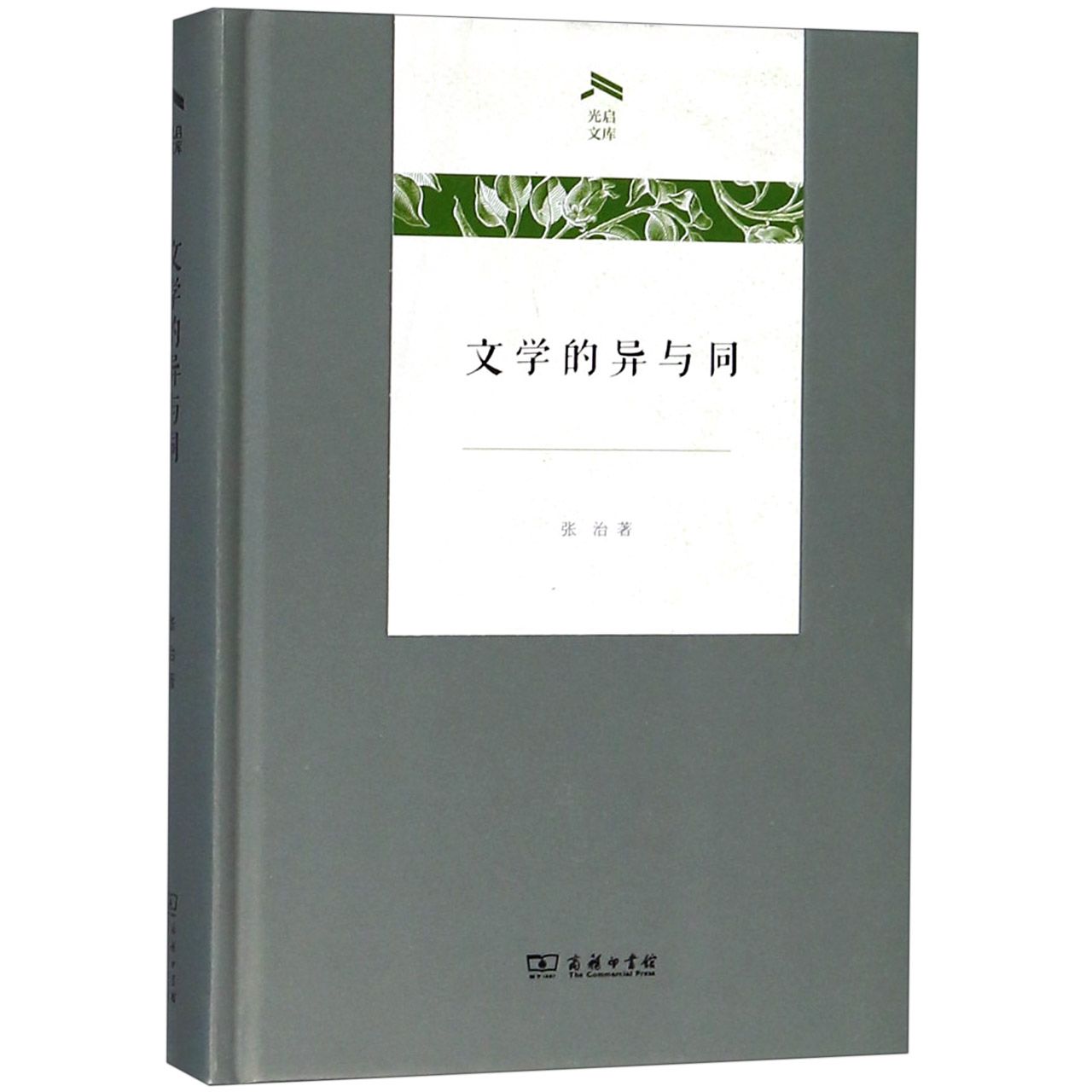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60.00
折扣价: 42.00
折扣购买: 文学的异与同(精)/光启文库
ISBN: 9787100169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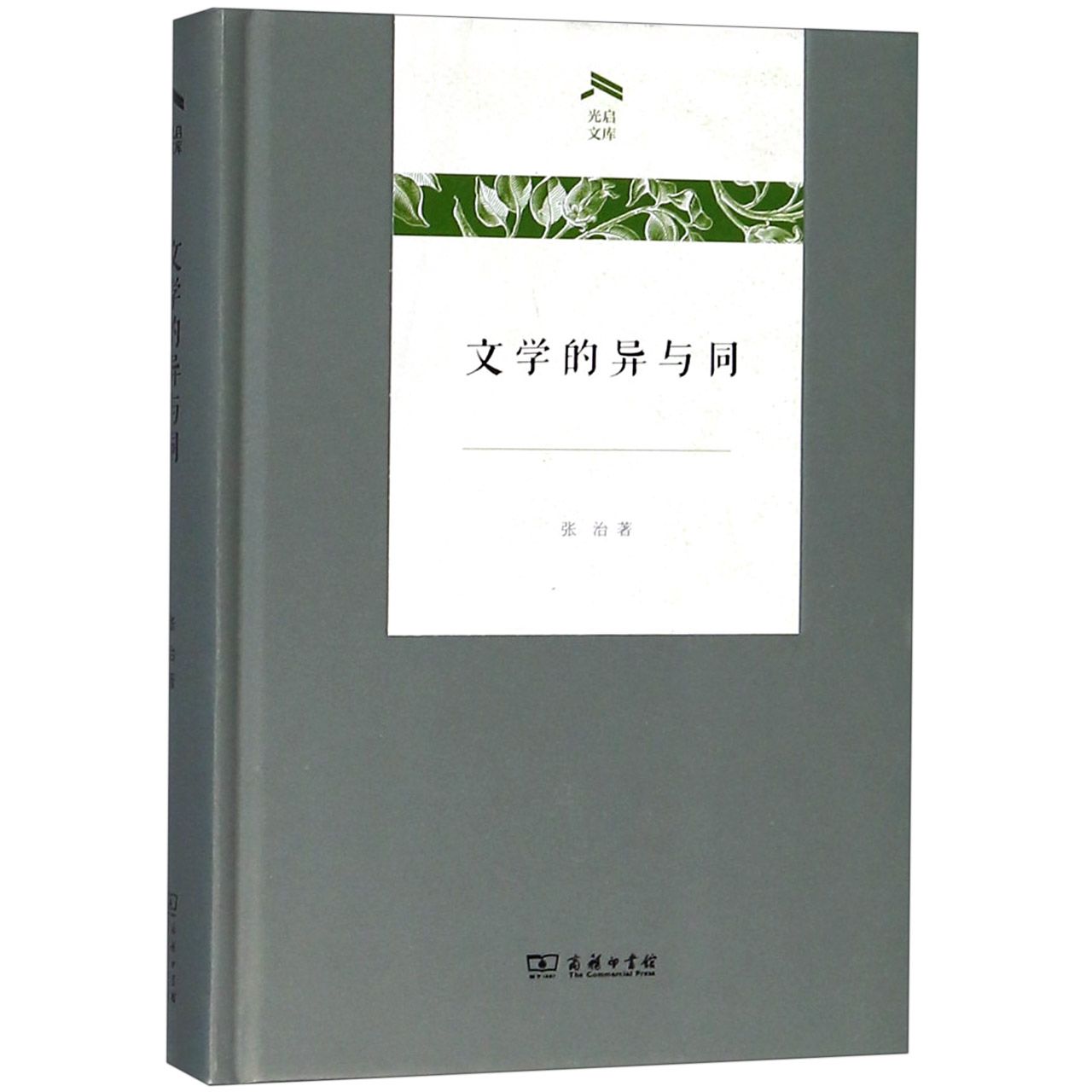
张治,1977年生,山东淄博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译作有《西方古典学术史》等,著作有《蜗耕集》《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异域与新学:晚清海外旅行写作研究》《蚁占集》等。
钱锺书早在20世纪80年代那次中意文化交流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断言,中西文学交流必然早就存在,只是找不到充分可靠的证据。《容安馆札记》第748则载,钱锺书读冯梦祯《快雪堂集》至卷五九日记部分时,注意到后者有和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接触的记载,于是提到多种集部文献、学问笔记乃至“兔园册子”里出现过的与利玛窦交游或评价其思想的资料“皆未见人称引”。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明季人于西教尚稍识,真远胜清季人之妄诞。”2006年年初,我还在北大中文系读博,准备的学位论文研究的就是“清季人”海外游记里五花八门的“新学”之表述,读到《容安馆札记》里这句话时激动不已。正好当时刚刚看到李奭学先生的新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提到晚明时候,来华的都是欧洲的高精尖人才,中国士大夫多能予以认可。可以说《管锥编》前言所标榜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作为源于陆象山心学思想的晚明精神,就是我在“异与同”之间分辨、取舍时最终想要追求的。我想钱锺书拿这个来破20世纪中国文学里过于强烈的国族意识是有效的。正如本书最后的那篇书评所强调的“近四百年”一说,我想我们在今天可以用这个大时段,来破除中国现代文学只是自救自强的一种定位。走向世界,并不是因为闭着眼不看世界会挨打,而是因为交流早就存在。 恰好是70年前,钱锺书的《谈艺录》问世。全书91则,具有首尾相扣的布局,实际上整体是一“圆”象。结尾所论“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即关联开篇引席勒之言:“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Manier)。”我们一方面可感受到钱锺书在行文间情怀涌起、接通中西而产生“同时性”的世界感,另一方面又当理解文学史的演进发展并不应该只是关注新的所谓“时代主题”,之所以存在“异世”,是因为选择“新”未必就一定取消“旧”的存在资格。从钱锺书读书笔记的手稿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文学古典传统在现代文学中的延续问题极为关注。他笔记最为详尽的德语书之一,即库尔提乌斯所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似乎也是《管锥编》有意效法的名著。众所周知的是,与《谈艺录》同年问世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寄寓着作者在“二战”前后对于“岌岌可危的德意志精神”的忧虑。库尔提乌斯在书中指出,一切现代文学的价值都在于将一部分古典传统复活,“过去的文学”并非死去,而是随时可以在当下活跃起来的内容,这揭示着文学的本质特征即“永恒的当下”。就此而论,钱锺书“同时之异世”说法,与之不谋而合。 我不能判断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理解程度是深是浅,甚至也不确定自己妄发的阐述是否有价值,一切都还有待诸位方家的批评指正。 出入经史,文涉中西,锺书遗韵,书心雅趣! 用精审的学术研究将中西文学精髓展现给读者,关于钱锺书的研究尤其深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