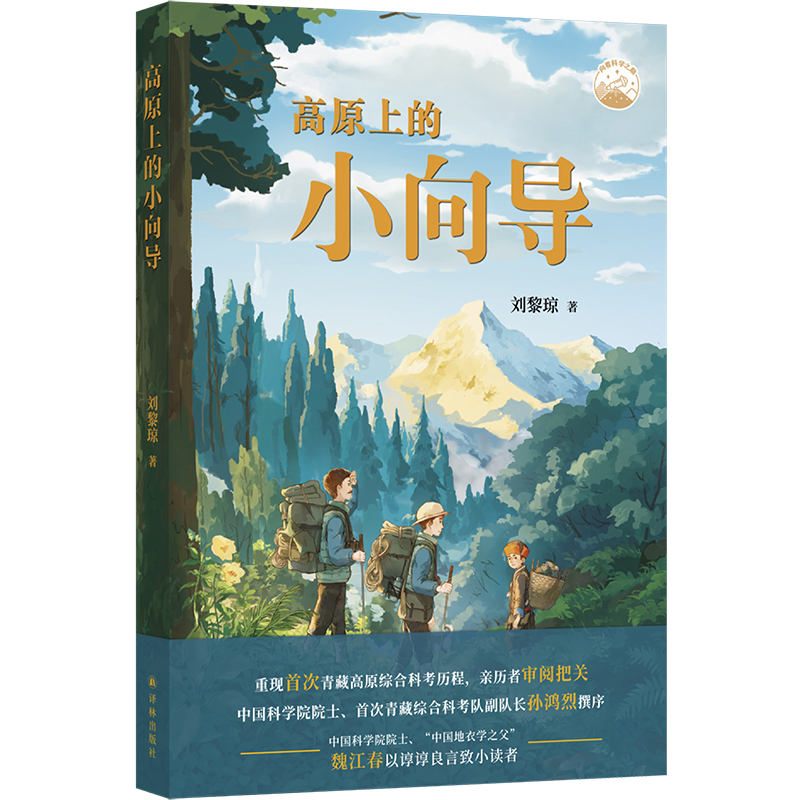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32.00
折扣价: 20.16
折扣购买: 高原上的小向导
ISBN: 9787544798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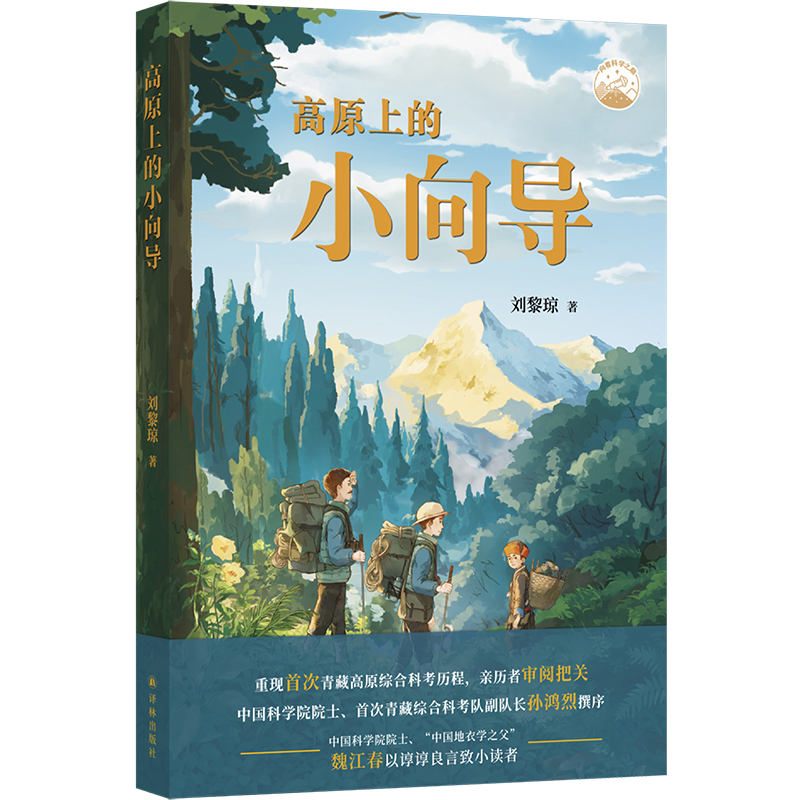
刘黎琼,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科普主管、中国科学院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三联少年”专栏作者,著有《移步红楼》,曾为郑儒永、田波等多位院士撰写传记。
引 子 像往常一样,何千帆迈开两条大长腿,飞快地向前面走去。不一会儿,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半山腰了。 那里有个气象数据的勘测站点,他要在那里下载气象数据。 我从吉普车上下来,伸了个懒腰,等着他完成工作后回来。 这是青藏高原上一个寻常的白天。空气透明,天空的蓝色有深有浅,向天边流去。日光明朗,山川和草木好像都在日光里摊开了身体。近处是个大湖,湖水碧蓝碧蓝的。岸上是大片的草,绿油油的,湿漉漉的。再远处是个山坡,青草像一块毛毯铺在上面,让人想扑在上面打个盹儿。 就在这时,我看到两只体型很大的灰狼出现在山腰上,距离千帆只有几百米。它们时而抬起头来四处望望,时而低下头去闻一闻地面,看上去很悠闲。 千帆显然没有注意到狼的存在,仍然低着头操作手里的设备。 我眯上眼,盯紧那两匹狼,猜测它们的意图。我有点担心它们也许会对千帆发起突然袭击,就加快步子向千帆那边赶去。 就看见千帆他已经向我这边走回来,冲着我挥了挥手。 我停下步子,眼见那两只狼又转悠了一会儿,一前一后离开了。 我放下心,等着千帆过来。 在视线的尽头,是连绵不断的雪山,山顶上放射着明亮的银色光辉。 千帆坐在副驾驶座,我们开车回观测站。 今天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我们两个都松弛下来。千帆靠着椅背,枕着胳膊,吹起小曲儿。 落日的光像一把刷子,有着纤细的毛,从山顶一直刷到山脚下。山脚下的小树林和草丛,在墨蓝的天色里变得温柔了。一切都在彼此诉说着情话,光明、坦荡。遥远的一座山上,隐隐约约有座小小的庙宇,像是一只孤独的鸟儿安静地睡在它的小窝里。 我们的车也像一只鸟儿,在这无边无际里,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但是,这种明媚没持续多久,天边的云忽然间就变成了铅灰色,而且飞快向我们的头顶奔过来。四周变得黑压压的,越来越黑。 何千帆指着那云,惊叫道:“看,要下雨!” 话音刚落,空中就哗哗哗哗下起了大雨,像有人往下奋力泼水一样。 眼前一片白茫茫,雨刷器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我关掉雨刷器,放慢了速度。车子滑过暴雨,就像一条黑鱼在大湖里慢慢地游过去。 这条路我闭着眼都能开。过去的十多年里,每一天,我们都走着相同的路线。只是高原的天气常常在眨眼之间就发生了变化,即使常年行驶在同一条路上,看到的景象也都不同,这也是它有趣的地方。 空气变冷了,千帆缩了缩肩膀,打了个小小的寒噤。 “还真是冷啊!”他从后座上拽过来一条毯子,盖在腿上。 “你才36岁,这点雨怕什么?我这50来岁的老东西,都没把它放在眼里。”我喜欢跟他开玩笑。 “您就在这土生土长的,早就习惯了它的脾气。这点风雨,对您来说肯定不算个啥。我在这里呆了这么些年,还是不很适应。上回我探亲回来,开车回站里的路上不小心着了凉,差点发展成肺炎。那个难受劲儿,我可不想再来一次。我还是小心点好。” 也难怪,谁让他是在长江以南的水乡出生长大的呢?人精瘦精瘦的,平时穿衣服都要比我多套上一两层。我自幼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里长大,风吹红了脸蛋,太阳晒高了个子,雨雪浇硬了骨头。我们族人就像山上的岩石一样结实,像水底的游鱼一样灵活。 前面一拐弯,我们开进了观测站的大门,把车停在院子里。 雨打在车顶上,像狗熊扑过来那么有气势。 观测站的两栋楼在雨雾里是一片灰濛濛的,只看得见轮廓。这楼是二十年前动工修建的,他们说是用来观测青藏高原大气与综合生态环境的。 这些词语听着很伟大,我却感到很迷糊。我刚到这里来时还很好奇,总爱琢磨他们在做什么,做这些有什么用处。到了现在这个岁数,却仍然搞不清楚那些知识。谁让自己早早就离开学校了呢?我大概没有可能把它弄明白了。 后来,我就想通了,也就不为难自己了。他们尽管去做这些大事,我也尽管做好我该做的小事。我把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为他们做大事帮了忙。 何千帆从脚下掏出两件黄雨衣。这个季节,雨衣随时可能要用到,所以一直放在车里准备着。他递给我一件,又把剩下那件往身上一披,特别遮严实了装着存储设备的蓝色布包。他跳下了车,三步并作两步,像只猴子一样跳着跑向主楼的大厅。我也紧跟着他向前冲去,脚底一串一串的水花。 大厅里堆了很多行李,几个陌生人正在低声说话,看到我们进来,纷纷投来探询的目光。夏季是各路科学家队伍密集到我们这里进行科学考察的季节。我们的观测站经常成为他们的临时驻地。等人马来齐了,物资到位了,他们就兵强马壮地出发。这三十多年一路行来,现在的科研条件真是比以前好太多了,我常常这样感慨。当然,我的家乡也比以前好太多了,他们做研究也就方便多了。 千帆认出其中的一位,拍着手欢呼道:“王教授,可盼来你们了!”他扑上去握住了一个人的手。 那人个子不高,跟众人一样穿着墨蓝色的冲锋衣。他头发都花白了,两只眼睛却充满了神采。他笑眯眯地拍了拍千帆的肩膀。 “又见面了,小何!看着比去年胖了些!” 千帆乐呵呵的,跟王教授聊了起来。原来王教授要带着科考队伍,到高原深处去考察冰川。我眯着眼,想起去年确实见过他们。去年来站里集结的队伍特别多,他们这一群人在这里只待了两天就开拔了。 我快速扫了一眼这一群人,注意到里面有一位女士,跟千寻差不多年纪,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结,眼角边堆着许多细小温柔的皱纹。 她的眼神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忍不住又多打量了她几眼,努力在我的记忆里搜寻着。 她也盯住我,皱紧了眉若有所思,然后冲着我笑了一笑。 暴雨停了。雾气在四周飘荡着,观测站像置身在一片雾的森林里。 我照旧坐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吃饭。站里有个大棚,里面种了不少蔬菜。千帆和他的同事们带来白菜、萝卜、辣椒、豆角、西红柿等不少种子,都种在这块地里。这地面积虽然不大,但一直在产出,基本能保障蔬菜日常的供应。此时里面红黄橘绿,非常好看。没事做的时候,千帆也会到里面忙碌一会儿,拔拔草、浇浇水。 那位女士向我走了过来,坐在我的对面,轻轻喊了我一声:“达瓦顿珠大哥!” 我放下了手里吃了一半米饭的木碗,惊异地看着她。 她脸上笑盈盈的,像高原上迎着太阳开放的杜鹃花。看到我脸上的疑惑,她露出了更大一朵笑容。 我们来到了观测站二楼的平台,靠着围栏向远方看去。 越过一重雪山,是另一重雪山。也许在别人眼里,每一座雪山都差不多,但没有谁比我更熟悉她们,更爱她们。她们中每一座都是独一无二的女神,都有自己的容貌和性格,即使在一天之内,也都有不同的模样和风情。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夜晚翻过雪山的背面,向这边轻快地走过来。她身上揣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就像是从一个个故事里走出来一样。 我感到时间就像一场雪崩,从四面八方向我扑过来,那些散开的雪花,是这些年里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等它们终于落下来,安静了,我一眼看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青藏高原,还有眼睫毛上扑满了雪花、还在笑呵呵的一些人。 那年,我十四岁了,已经是我们村子里有名的小猎手,被好几个捕猎高手的叔叔伯伯夸奖过。我从小就跟着阿爸和他们一起,踏遍了周围所有能捕猎的地方。 从春天冰雪融化到大雪再次封山的几个月里,常常会有一些人来到我们村子里,几乎都是来自外面世界的人。他们跟我们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阿爸那时候正值壮年,强壮得像一头熊,敏捷得像一头羚羊。他和叔叔伯伯们会帮那些人背着沉重的行李,引领他们进到大峡谷,穿越雪山,穿过冰雹、暴雪、泥石流、充满旱蚂蟥的森林,到他们要去的地方。 起初桑珠叔叔会跟他们一道。他曾经在外面待过几年,在兵站里帮过工,还开过卡车,当过向导。他特别聪明,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还给他们当过翻译。阿妈去世后,我就决定不再上学了,我似乎对学校里的知识完全不开窍,只粗浅地学了一些汉语。回到阿爸身边后,我常常去找桑珠叔叔,短暂的遛马、放牛之外,很多时间都花在听他讲外面的故事上了。我要感谢那会儿对汉语的迷恋,不管怎么说,如今我在这里的工作,我跟千帆深厚的友谊,多亏会了汉语。 眼前这位女士,有着兰草的芬芳和温暖的笑容。她告诉我,她的父亲给她取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 她故意停顿了一下,笑吟吟地说,她叫苏景峰。是景仰珠峰等一切世间高峰的意思。 是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苏叔叔。他有这样的气魄。他就是这样挺拔。 我告诉景峰:“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我早就见过你了。” 苏景峰惊诧地看着我:“不会吧?我以前没有见过您哪!今天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的,孩子,我第一次见到你,你还是个小婴儿,还不到一岁,眼睛圆圆的,亮晶晶的,小胳膊胖乎乎的,咧开小嘴乐哈哈的,露出两颗小门牙。 我们都被你的小模样逗笑了。但一直在高原上辗转、只能在照片上见到你的苏叔叔,笑着笑着眼睛就红了。再难都难不倒、再疼也不哼一声的苏叔叔,背过身去,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后来,我给许多队伍当过向导,带领他们穿过高原、雪山、峡谷,做这些事已经轻车熟路,但没有哪次的记忆比这次更深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当向导。 给了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以充分的信任来当向导,一起相随着穿梭在峡谷、高原和山峰之间的,就是你的父亲,当时正在高原上开展科学考察的苏岩。 热泉边初遇 灌木丛里发出沙沙的声响,非常细微,像一阵轻风拂过。但在我的耳朵里,这声音很清晰,显然是野兔从洞里探出头在草棵间四处张望。 我轻轻躲在一棵树后,静静地等着兔子出洞。 果然,过了一会儿,两只肥硕的兔子就蹦出来了,灰色的长毛,透着雪样的光,长耳朵支棱着,警觉地倾听着四周的动静。 我端起猎枪瞄准,正要按动扳机,就看见三只小兔子蹦跶到了它们身边,像三个滚圆的绒球。 我犹豫了。 这是一家人。 小兔子在父母的周围快乐地跳来跳去,小鼻子一动一动的,嗅着地面。它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信任。远处雪山慈祥,河水涌流的声音那么寂静。 我不想破坏它。 看看袋子里装着的野鸡和野鸟,差不多了,不需要再更多捕猎了。 我收了枪,背起袋子,沿着野鹿、野山羊踩出来的小路,拨开两边高大的灌木向前走,脚下特别轻松。半天功夫所得,这些猎物不能不说已经很丰厚,足以拿去给多吉爷爷抵偿前阵子阿爸赊欠的药费。上午我步行十几公里,把白玛奶奶亲手制作的8个漂亮的木碗卖掉了,白玛奶奶事先答应给我一份酬劳。 终于能帮阿爸解决很多烦恼,这让我感到说不出的愉快。 夕阳像一团熔化的金子,流了半边天,落到雪山顶,跟白雪一交融,山顶就像戴上一道金色的头冠,显得格外庄严。剩下的一点金光,给了这片林子,穿过浅蓝的雾气后,变得隐隐约约的。 这时我感到口渴,打开行军水壶,看到里面已经空了。这是以前阿爸给人当向导时,别人送给阿爸的,阿爸说特别结实,外出时总带着它。水壶的拴绳都磨出了毛,外面的绿漆也磨掉很多了。最近阿爸受伤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就把它给了我。 我准备到附近的跳跳溪去装一壶水。 跳跳溪是一条小溪流,这样的小溪流我们这儿有很多,看上去没什么区别,也都没有名姓。跳跳溪是我给它取的名,它比别的溪水更加活泼好动,斜着从坡上冲下来,速度很快,水里有许多白石头,总是高高溅起很多浪花。那些浪花雪白雪白的,像鱼的白肚皮。 我正不紧不慢地走着,听到附近隐约有人在说话,声音紧张而急切,好像遇到了什么困难的事情。 我加快了速度,想去探一探究竟。 那些外面来的人,不熟悉我们这里的情况,常会遇到各种麻烦。比如,被马蜂叮咬,被蚂蟥袭击,从山坡上失足滚落,不小心跌到激流里,吃到有毒的蘑菇,碰到有毒的植物,在森林里迷路,甚至遭遇雪崩、泥石流,……我们自己人也常常碰到这些,只是我们祖辈都生活在这里,遇到的不少,见到的更多,有了不少应对的经验。 · 采用门巴族少年仓央的视角,以第一人称讲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的故事,亲历者审阅把关,折射了中国科学家的英雄群像。 · 将人文精神和科普价值融合在一起,为青少年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险、忘我奉献的珍贵品质,传递出昂扬向上、雄健有力的精神力量。 · 门巴族少年和科考人员互相支持、扶助,传达了民族团结共为一体的主旨。 · 故事之外,书中渗透融合科学家野外科考的知识。 · 中国科学院院士、首次青藏综合科考队副队长作序,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衣真菌学家以谆谆良言“致小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