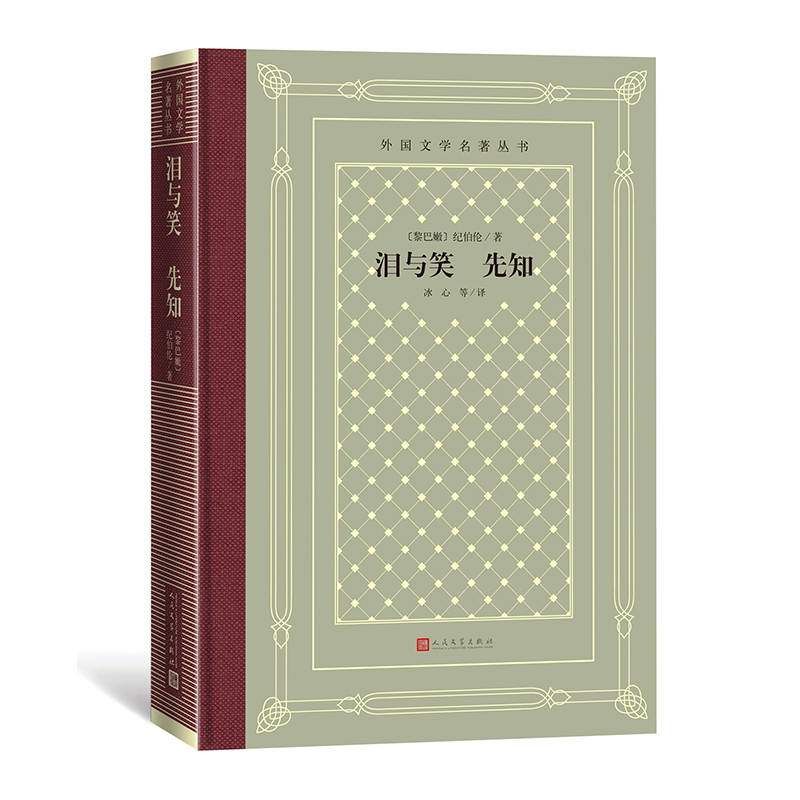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1.90
折扣购买: 泪与笑 先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0201698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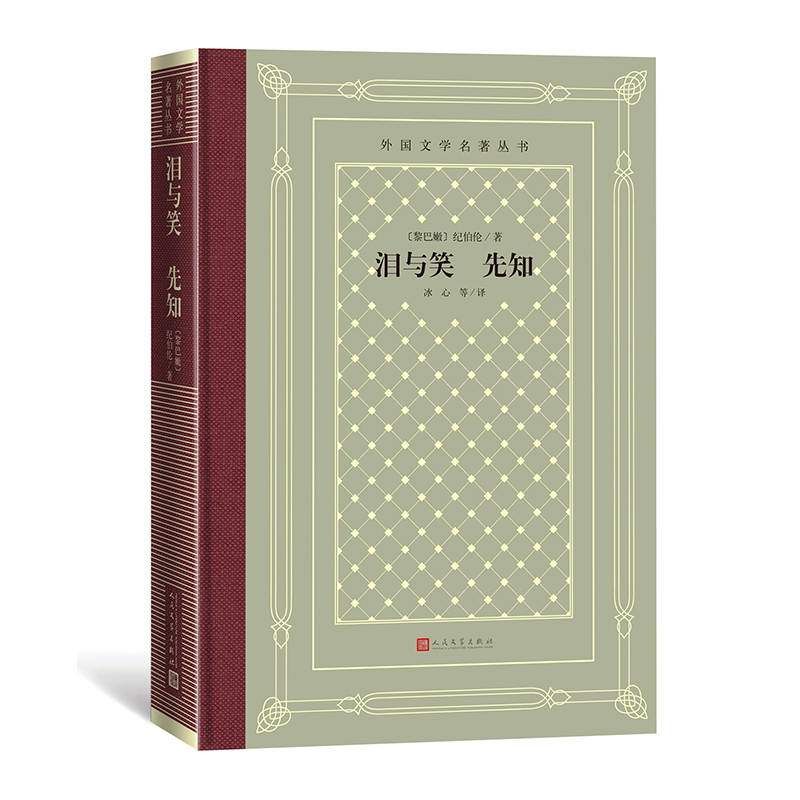
纪伯伦(1883—1931),杰出的黎巴嫩诗人、作家、艺术家,阿拉伯现代小说和艺术散文的奠基人和推动者。早期作品富有浪漫色彩和叛逆精神,同时还展现了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后期作品则探讨人生普遍问题,兼具抒情性和说理性,深受世界各地各个时代读者的喜爱。
译本序 …… 从二十年代开始,纪伯伦逐渐由小说创作转向散文诗创作。纪伯伦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他对阿拉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最大贡献,也体现在散文诗上。 《泪与笑》(1913)是纪伯伦早年写就的散文诗合集,由于这些诗充满了“哀叹、倾诉、哭泣”,当朋友鼓励他发表时,纪伯伦感到“愧怍不安”,认为作品是他“葡萄园中的未熟之果”。其实,这些作品虽然缺乏一些“力度”,但其中洋溢着诗情画意,也不乏智慧与哲理,许多篇什令人爱不释手,充分体现了纪伯伦早期文学创作的理念:爱与美。 散文诗集《暴风集》(1920)和《珍趣篇》(1923)在风格上与《泪与笑》迥异。这是两部极富社会批判性和民族自省意识的作品。作者大声疾呼,想让酣睡的同胞觉醒,打碎那做了千年的空梦。他要人们打碎一切偶像,做自己的“主”,做时代的“巨人”,而不要做“坟墓中的居民”。他讴歌革命,呼唤暴风雨,预言“谁不用自己的风暴吹折自己的枯枝,谁就会厌倦萎靡而死;谁不用自己的革命撕碎自己的败叶,谁就会默默而亡”。纪伯伦愤世嫉俗的宣泄,让我们联想起鲁迅对同处东方的华夏民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一九一八年,纪伯伦还发表了一首长诗《行列歌》。全诗好似两个人的对唱:一个是来自城市、饱经沧桑、深谙世态炎凉的老者,他用低沉、哀伤的声音唱出了人类社会的种种忧患痛苦、邪恶和弊端;另一个则是来自森林与大自然的青年,他纯真、质朴、活泼、乐观,用欢快的声音召唤人们到森林中去返璞归真,寻求一个真善美的理想境界。诗歌体现了纪伯伦对自由、自然和理想境界的向往。 在用阿拉伯文发表上述作品的同时,身处美国的纪伯伦,又用英语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如《狂人》(1918)、《先驱》(1920)、《先知》(1923)、《沙与沫》(1926)、《人子耶稣》(1928)、《大地神》(1931)、《游子》(1932)和《先知园》(1933)。这些作品与前期阿拉伯语作品的主题、风格有了很大不同。如果说前期作品突出的是东方性、民族性,那么后期的英文作品更多地着眼于普遍的人性及人性的升华,其立足点是全人类、全世界。现实的批判锋芒依旧,但针对的是人类的荒诞与卑琐;同时,更有嘹亮的新声在这些作品中回荡,那便是深邃的哲思、形而上的求索、对爱与美的呼唤。这一变化,不仅缘于读者对象的改变,更缘于纪伯伦思想与心智的成熟与转变。 《狂人》《先驱》《游子》主要由一些短小的寓言故事构成,多富有讽刺意味,针对人的虚伪、无知、狂妄和卑微。这些故事娓娓道来,风格简约而朴素,同时又含蓄、隽永,令人回味无穷。此外,这些集子中还收入一些意境深远的抒情短章,体现了作者这一阶段的哲学思想。 《沙与沫》荟萃了纪伯伦道出的隽语、佳句,它是“纪伯伦思想的珍珠串成的一条闪光的珠链”。其中许多论及人生、爱情、友谊、文艺、世界的段落,其立意高远,境界超逸,读者在含英咀华之际,每每有醍醐灌顶之感。 《人子耶稣》被人称为“纪伯伦福音”。作者通过七十七个耶稣同时代人物之口,把一个被神化的耶稣,还原为一个富有人道精神的使命传达者。在纪伯伦眼里,耶稣是人子、人之兄弟,但是,“遗憾的是,他的信徒们却极力要把他尊为一位圣人,尊为神”。 《大地神》是纪伯伦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其形式类似一部诗剧,由三位神祇富有思辨意味的叹喟与对话构成。在长诗的前半部分,甲、乙两位神灵的对话,对生命的意义做了质疑和探寻;随后第三位神灵出场,他对生命存在的神圣性和意义做了层层深入的揭示,最终,他把生命神圣性的最终依托归结为“爱”,这也是贯穿纪伯伦全部作品的核心思想之一。在长诗的尾声,诸神隐退,代表爱的“丙神”为人类的爱情唱起了赞歌:“我们最好明智地寻一块阴凉的所在,/让我们这些大地神入睡,/而让爱情,这人类的柔情,去做来日的主宰……” 在纪伯伦的所有文学作品中,代表其最高成就、堪称其“文学金字塔”的作品,乃是长篇哲理散文诗《先知》。这是一部让纪伯伦呕心沥血的作品,他曾在致梅伊的信中写道:“至于《先知》,那是我已思考了一千年的书……这位先知,在我试图塑造他之前已把我塑造了,在我考虑构写他之前已把我构写了。”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言,《先知》中的“先知”穆斯塔法(亚墨斯达法),可以理解为素有先知情结的纪伯伦本人。《先知》荟萃了作者借穆斯塔法之口向世人传达的大慧之言。 纪伯伦为《先知》安排了一个小说式的故事框架。穆斯塔法这位“被选和被爱的”东方智者,滞留奥法利斯城十二载,一直期盼回到自己出生的岛屿。一日,他登高远眺,看见故乡的船正穿破海雾徐徐驶来。离别的时刻来临,城中的男女都来送行。人们请求他作临别赠言,并告诉他们“关于生和死中间的一切”。他怀着深情,回答了人们一个又一个提问,问题涉及爱情、婚姻、孩子、施与、工作、欢乐与悲哀、理性与热情等众多话题,当他回答完所有的二十六个问题后,又发表了充满祝福和希望的告别词。然后,他登上来船,航船向东方驶去。“溪流汇入大海,伟大的母亲再次将儿子揽入怀中。” 《先知》清新隽永的诗句中,凝结着纪伯伦对人生、社会深刻而睿智的思考,这些思考,是他站在历史的、可以俯瞰世界的高度进行的。他又通过“《圣经》式的”既庄重又温馨、既有启示性又有感染力的语言,加以诗人的奇妙想象和新奇比喻,将这思考的结晶晓谕世人。 《先知》出版后立即在美国引起轰动,并在短短数年内风靡世界,至今发行总量已逾七百万册,被誉为“东方赠送给西方的最好礼物”。黎巴嫩评论家努埃曼把它比作常青树,说它“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的土壤里,只要人类存在,这棵大树就活着”。《先知》之后,纪伯伦又写了《先知园》,这是一部与《先知》风格近似的作品。在书中,穆斯塔法已回到了他诞生的岛屿,他在旧居花园中安静地思考人生,回答人们的问题。《先知园》还比《先知》多了一些抨击政治的内容。 纪伯伦曾有愿望,在《先知园》之后再写一部《先知之死》,作为完整的《先知》三部曲。然而,他的心愿终未能实现,因为他先于笔下的“先知”,去往了她母亲所在的“蓝色天际以外的世界”。一九三一年四月十日,纪伯伦因积劳成疾病故,年仅四十八岁。 背井离乡二十余载的游子,一直盼望重返祖国。现在,他回来了。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纪伯伦的灵柩覆盖着黎巴嫩和美国国旗,乘船回到贝鲁特,又在各界人士的护送下,缓缓向家乡布舍里进发。最终,他安眠在可以俯瞰家乡的玛尔·谢尔基斯修道院的岩室里。在他棺椁的上方,悬垂着一块纪念碑,上面用阿拉伯文书写着:“这里长眠着我们的先知纪伯伦。”或许,“我们的先知”一词在这个宗教气息浓厚的国度里过于敏感,人们后来将“先知”这一单词的上下小点稍做改动,碑文就变成:“这里,纪伯伦长眠在我们中间。” 负有先知使命的纪伯伦,已经走向了永恒的世界。但他留下的那些诗文,还在被一代又一代的世人传诵着。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经由茅盾、冰心等文学大师的译介,纪伯伦的作品也开始走进了中文世界,并征服了无数的中国读者。经过几代阿拉伯文学翻译者、研究者的努力,纪伯伦在当今中国知识界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人物,无可置疑地成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阿拉伯作家,并跻身最受他们欢迎的外国文豪之列。可以预料的是,具有独特魅力的纪伯伦文学,必将在中国一代代读者中赢得更多的知音。 纪伯伦在《先知园》中描绘的先知穆斯塔法曾经感慨:“我的心灵重荷着成熟的果实,谁来采撷,饱尝这硕果?”那么,就让我们伸出准备领受的双手,去承接这位文学大师慷慨施与的硕果吧! 薛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