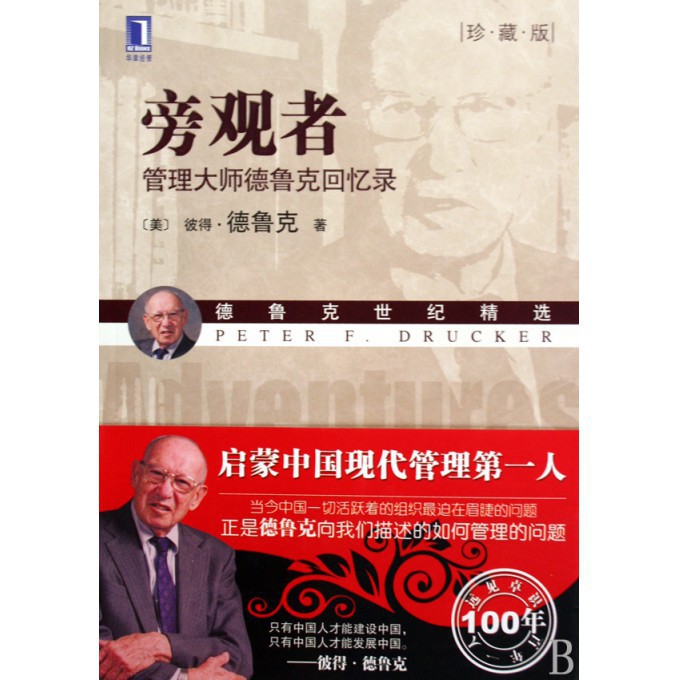
出版社: 机械工业
原售价: 39.00
折扣价: 25.80
折扣购买: 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德鲁克世纪精选)
ISBN: 97871112807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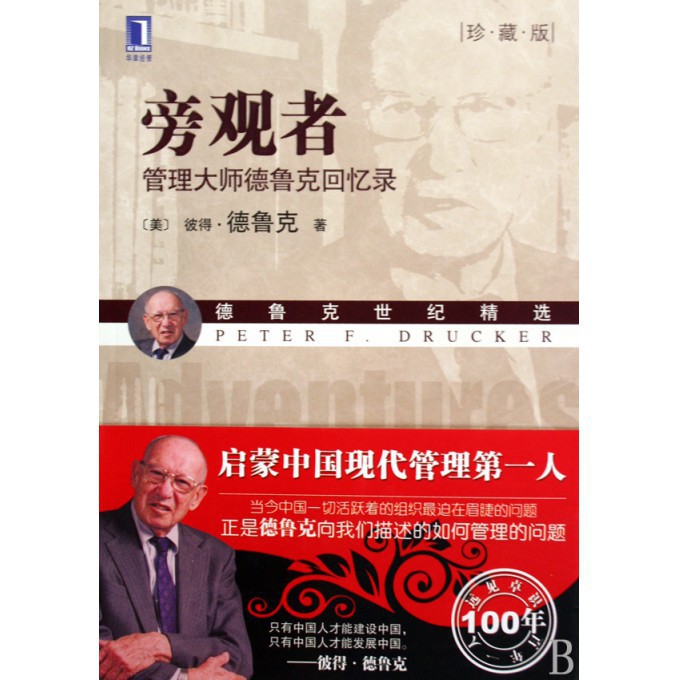
彼得·德鲁克小传,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1909年彼得·德鲁克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37年与他的德国校友多丽丝结婚,并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 在美国他曾担任由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财团的经济学者,以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公司等大企业的管理顾问。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表彰他为非营利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慈善机构“救世军”授予德鲁克救世军最高奖项“伊万婕琳·布斯奖”。 他曾连续20年每月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一生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共发表38篇文章,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他著述颇丰,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旁观者》等几十本著作,以30余种文字出版,总销售量超过600万册。其中《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为全球管理者必读经典。 他曾7次获得“麦肯锡奖”;2002年6月2013,获得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2004年,德鲁克管理学全面进入中国的管理教育。 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在加州克莱蒙特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95岁。
第1章 老奶奶与20世纪 1955年我回维也纳讲学时,已阔别家乡20载。上一次回维也纳做短暂停 留,是在1937年从英国到美国的途中,在这之前,则很少回来。我在1927年 念完大学预科,就离开维也纳了,那时的我还未满18岁,此后返乡,都是为 了同父母过圣诞,而且每每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 因为讲学的缘故,我1955年得以在维也纳小住。我到维也纳的第二天清 晨,在下榻的饭店外散步,途经一家食品店,记得这家店在我小时候已是远 近驰名。来维也纳之前,我答应妻子帮她带瓶奥地利酒,于是就走进去。过 去我并非这家店的老主顾,所以已记不得是否来过。一进门,看到高高坐在 收银机旁的,不是年轻的伙计,而是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太——过去,这是家 常便饭,今天则是难得的景象了。她一眼就认出我来,随即大声地叫我的名 字。 “彼得先生,您能大驾光临,真是太好了!我们从报上得知您来讲学, 还不知是否能见您一面呢。很遗憾,令堂在去年过世了,您那位安娜阿姨也 作古多年。但是,听说令尊还挺健朗的。我们明年是不是真可以在维也纳庆 祝他老人家的80高寿?您的汉斯姨父几年前在这儿得到荣誉博士学位时,那 葛瑞塔阿姨也回来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为贵府服务,凭着这点交情,送 篮水果和一张卡片到您下榻的饭店,该不为过吧?我们刚收到您那葛瑞塔阿 姨的回信呢。这些女士真是通情达理。现在的年轻人啊,”她朝店里销售人 员的方向点了点头,“已分不清轻重厚薄了。哎呀,彼得先生,您听我说, 现在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您的祖母大人。她实在是好得没话说,再也没有第二 个像她那样的人了。而且呢,”她微笑着说,“她这个人实在是太风趣了。 您还记得她给侄女拍的结婚贺电吗?”她咯咯大笑,我也笑了。 虽然这件事是在我出生之前发生的,我还是了如指掌。当时,奶奶因为 无法参加侄女的婚礼,于是就发了一封电报过去,上面写道: 就打电报而言,务求精简,这是最适当而且最好的表达方式,故在此庄 严隆重的一天,祝汝等:幸福快乐! 这件事因此在我们家族中代代相传。听说奶奶一直抱怨,她只不过写了 四个字,电报费却高得离谱。 奶奶年轻的时候十分纤巧,娇小玲珑而且容貌出众。但是,我所看到的 奶奶已是迟暮之年,看不出一点青春美丽的痕迹,不过她还留着一头亮丽的 红棕色卷发,这点让她引以为豪。她不到40岁就做了寡妇,而且百疾缠身。 由于得了一种严重的风湿热,造成心脏永久的损伤,因此好像老是喘不过气 来的样子。关节炎使她成了跛子,所有的骨头,特别是手指,都又肿又痛, 加上年事已高,耳朵也不灵了。 但是,这一切却未能阻挡她到处溜达的雅兴。她风雨无阻地走遍维也纳 的大街小巷,有时搭电车,不过多半步行。她的随身“武器”就是一把可做 拐杖的大黑伞,还拖着一只几乎和自己一样重的黑色购物袋,里面装满了一 大堆包装得好好的神秘小包裹:有准备送给一个生病老太太的一些茶叶,为 一个小男生准备的邮票,从旧衣拆下半打“高级”金属纽扣打算给裁缝…… 奶奶家中有六姊妹,每个至少生了四个女儿,所以侄女就多得数不清了 。这些侄女小时候或多或少都被奶奶带过,因此跟奶奶特别亲,甚至和自己 的妈妈都没这么亲近。在她拜访之列的,还有从前的老仆人、贫困的老太太 、以前跟她一起学音乐的同学、年迈的店主和工匠等,甚至连去世多年的朋 友家的仆人,她都不忘问候。 有一回奶奶想去看住在郊外的“小葆拉”。这个老寡妇是奶奶已过世的 表哥的侄女。她说:“如果我不去看这个老女人,还有谁会去呢?”家族中 的老老少少,包括奶奶自己的女儿还有那一大堆侄女,都一律喊她“奶奶” 。 不管和谁说话,奶奶的声音都愉快而亲切,并且带着老式的礼数。即使 多年不见,她仍然记得人家心中牵挂的事。有一次,奶奶有好几个月没见到 隔壁的女管家奥尔加小姐,再次看到她时,就问她:“你那侄儿近来怎么样 ?通过工程师考试了吗?这孩子可真了不起,不是吗?”她偶尔也会到老木 匠的家里走动,并问他:“科尔比尔先生,市政府不是跟你们多课了些房屋 税吗?后来解决了没有?我们上回见面的时候,你不是还为这件事心烦吗? ”奶奶的妆奁就是这位老木匠的父亲做的。 奶奶公寓旁的街角常有个妓女在那儿拉客。奶奶和这个妓女说话一样是 客客气气的。其他人对这妓女视若无睹,只有奶奶会走向前去跟她寒暄:“ 莉莉小姐,你好。今晚可真冷,找条厚一点的围巾,把身子包紧一点吧。” 有一天晚上,她发现莉莉小姐喉咙沙哑,于是拖着一身老骨头爬上楼,翻箱 倒柜地找咳嗽药,之后再爬下去交给那个妓女。在战后的维也纳几乎没有一 部电梯可以使用,所以奶奶只好这样爬上爬下。 奶奶有个侄女就很不高兴、告诫她说:“奶奶,跟那种女人说话,有失 您的身份。” “谁说的?”奶奶答道,“对人礼貌有失什么‘身份’。我又不是男人 ,她跟我这么个笨老太婆会有什么搞头?” “但是,奶奶您居然还给她送咳嗽药去!” “你啊,总是把性病当做洪水猛兽。对此,我虽无能为力,但是我至少 可以使她的感冒赶快好起来,不至于让那些男人被她传染,得了重感冒。” 奶奶有个侄女咪咪,也许是曾侄女吧,是个小演员,演过几部电影和音 乐剧。在一些比较耸人听闻的星期天报纸上,常可看到她的绯闻。 奶奶说:“希望他们不要再报道咪咪跟某人在她的闺房里打得火热这种 新闻。” 有个孙女说:“奶奶,别假正经了。” “闹绯闻其实是她的手段,她还希望报纸大肆渲染呢,这样她才有戏可 演。不然,像她这样歌声不怎么样,演技又差的,哪有什么发展?希望她在 受访时,别提到那些男人的名字。” “但是,奶奶啊,那些风流男子巴不得自己能因此出名呢。” “这也就是我最看不惯的——煽动那些老色鬼的虚荣心,让他们沾沾自 喜。我觉得这和‘卖淫’简直没什么两样。” 奶奶的婚姻显然十分幸福。直至死前,她一直把爷爷的相片挂在卧房, 每逢爷爷忌日,她一定闭门静坐。不过,听说爷爷却是个“多情种子”。17 岁那年,有一次我在维也纳的大街上行走时,被一辆旧式豪华大轿车拦住了 ,坐在车后的女人摇下车窗,跟我招手。我走向前去一看,前面是司机,后 座有两个女人,一个戴着厚厚的面纱,另一个身穿围裙,应该是女仆。 那个女仆跟我说:“夫人问,你就是斐迪南·邦德的孙子,是不是?” “是啊,他是我爷爷。” “他是我们夫人最后的情人。”说完,车子就扬长而去。 当时,我困窘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是还做不到守口如瓶的地步。这件事 终于传到奶奶的耳朵了。她把我叫进房里,对那戴面纱女人的事提出质询。 “我想,她一定是达格玛·西格菲顿。我相信你爷爷的确是她最后一个 男人。这个女人说来也是挺可怜的,实在算不上漂亮。不过,我敢担保,她 一定不是你爷爷最后的情妇。” “不过,奶奶啊,”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一直都想跟奶奶说的话,终于找 到机会说了,“爷爷这么风流,您难道不伤心?” “当然哕。不过,没有情妇的男人一样令人担心。这样,我就不知道他 究竟跑到哪儿去了?” “不过,您会不会害怕爷爷一去不回?” “一点也不。爷爷一定会回家吃晚饭的。我虽然只是个笨老太婆,不过 倒很清楚——胃也是男人的性器官。” 爷爷去世后,留给奶奶一笔为数庞大的遗产。但是,因为奥地利通货膨 胀得厉害,奶奶还是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她本来有一栋两层楼的公寓房子 ,有许多仆人可以使唤,现在却住在从前家里女仆住的小房间,而且得自理 家务。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却很少听她发牢骚,如果有的话,也只是抱 怨风湿和耳朵不好,因此不能弹琴、听音乐。 奶奶年轻的时候,钢琴弹得极好,是克莱拉·舒曼的学生。她在老师的 要求下,在勃拉姆斯跟前演奏过好几次——这是奶奶一生最光荣的一刻。当 时有教养的女人是不能公开演出的,不过奶奶在爷爷去世后,自己健康尚可 时,倒是常在慈善演奏会中露一手。马勒在1896年职掌维也纳歌剧院不久, 在一次指挥演出中,奶奶也曾共襄盛举,担任钢琴的部分。但是自此以后, 奶奶就不再公开露面了。一般维也纳人总喜欢那种热情澎湃的音乐,奶奶却 嗤之以鼻,认为这种音乐鄙俗,说是给“炒股票”的人听的音乐。 …… 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