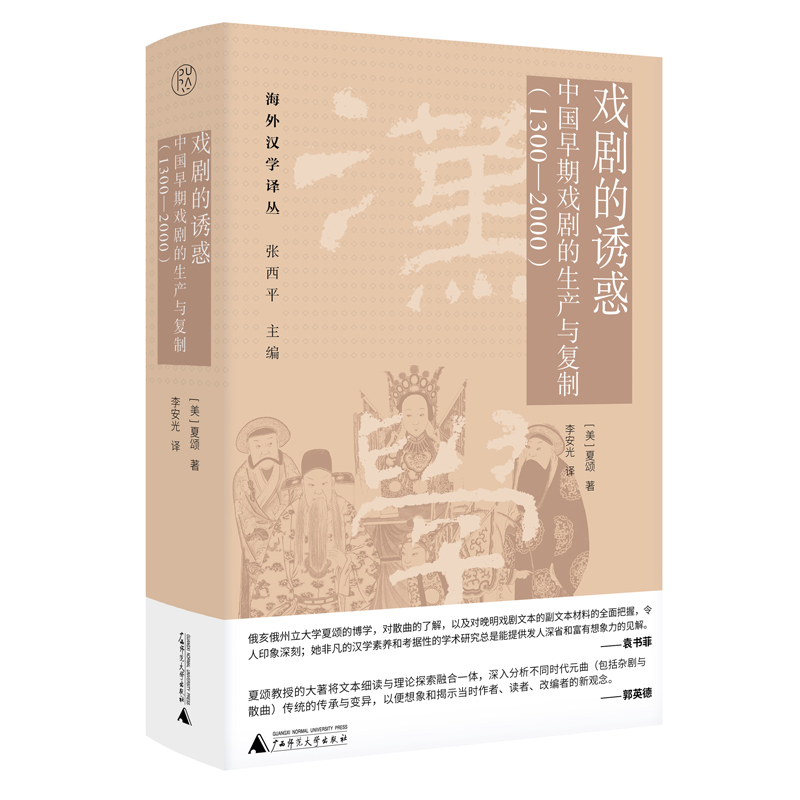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2.80
折扣购买: 海外汉学译丛 戏剧的诱惑:中国早期戏剧的生产与复制(1300—2000)
ISBN: 9787559872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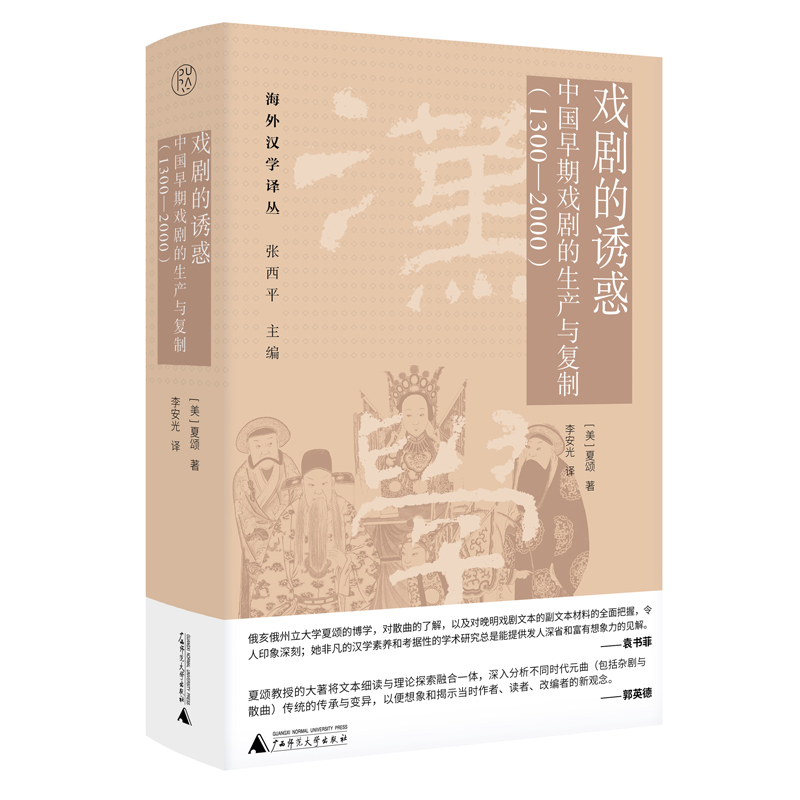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夏颂(Patricia A. Sieber), 生于瑞士,1994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助理教授、东亚研究中心(2005—2013)与中国研究所(2005—2010)主任。其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印刷文化和跨文化研究,素以现代传播学的视域研究自元代以降中国白话文学(特别是戏剧)经典地位的形成而著称,本书为其代表作。 译者简介: 李安光,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河南大学莎士比亚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海外汉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各一项,多次荣获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出版专著《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参编教材《西方文化概论》《比较文学概要》等;在《探索与争鸣》《国际汉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
第一章 散曲选集、编辑归属与情感崇拜:关汉卿与证明性作者身份的转换 ? 引言 在第一部《中国文学史》(1904)中,林传甲不仅指责元代文学粗俗,而且还责难日本著名的中国小说和戏剧的倡导者笹川种郎把“低俗”误认为“高雅”: 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 应新成立的清政府教育部的要求,林传甲对传统的汉语写作教育课程的尖酸刻薄的辩护是在科举制正式废止的前一年发布的。 他似乎暗示,中国文学的衰落在历史上是由元朝引起的,而一个日本局外人的误导性叙述更是过分夸大了这一点。然而,尽管他们在内容、文类等级以及元朝在中国文学演变中的作用上存在分歧,但林传甲和笹川都不愿评论早期的散曲。散曲在文学经典的白话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林传甲对散曲感到厌恶,而笹川珍视散曲。 即使现代学者迟迟不承认这一点,但几乎所有的元代和大量明代的批评著作,以及许多明代的文集,实际上都同时包含了散曲和戏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散曲和杂剧的共同特点。这两种形式都使用了活泼的白话,尽管戏剧比散曲更口语化。通常,同一作家既写剧本又写散曲,即使有些人只因他们的散曲而出名。这两种音乐形式都源于相同的音乐传统,尽管它们之间很少共享单独的旋律。这两种体裁都倾向于直接言说、对话和模仿等戏剧性的表现方式,它们还表现出相似的修辞优势,如数字文字游戏、韵律技巧,以及对曲调和戏剧人物的自指双关语等。然而,尽管文人试图将散曲,有时是戏剧,与较早的抒情传统相提并论,但最初,散曲和戏剧都不符合早期诗歌所具有的社会文学的传统特征。在作者身份问题上尤其如此,因为作者的发展演变轨迹和白话体裁作品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本章将考察散曲和戏剧的早期韵律传统的主要来源——韵(曲)书(谱)、书目文献、文集和选集——它们能告诉我们关于我所说的“证明性作者身份”的演变及其对白话经典形成的影响。证明(attestation)使典范的社会表现成为文学表达道德可行性(moral viability)的试金石,反之亦然。通常,它的表达准则(expressive code)首先要求作品表现出公共效用和个人的缄默。这一章将阐述关汉卿这位当今最著名的元代剧作家的可追溯的作者生涯,是如何拓宽证明的范围的。不同社会地位的元文人批评家、明皇室成员、更广泛的明朝宫廷机构以及晚明的文人编辑,在把社会上默默无闻的关汉卿塑造成“作家”的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对散曲如《不伏老》和戏剧如《西厢记》的错误归属,追溯性地将主题上多才多艺的关汉卿调和成“浪漫文人”。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白话、非正统体裁的公开承认的作家身份,情感和肉欲的广泛表达,以及对精英男性社会地位的肯定,都可以在一个作家的名字下得到调和。 所谓的“作者功能”(author—function)演变的累积影响,使不安的晚明精英们得以在官僚僵化和不受约束的商业主义之外寻找文化替代品,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学实践。围绕早期戏剧的作者形象(authorial figurations)为新剧的创作开了先河,如被精深研究的《牡丹亭》(1598年,约1618年刊刻)。他们还激发了无数早期戏剧的新文本改编,最著名的是《西厢记》。如果汤显祖和金圣叹等中国精英认为这种新的创作尝试是可行的,那么林传甲等其他文人就会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学原则的公然违反。然而,鉴于这种创作实践的变化似乎与元代的文本和人物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早期散曲和戏剧的批评和编辑的社会语境进行考察。因此,令林传甲之流懊恼的是,在有明一朝,证明性作者身份的限制已大大放宽了。 韵律的威望 在一篇周德清有影响力的《中原音韵》的序言中,周德清的密友罗宗信,比较了各种诗体的相对难度。在他的评论中,罗宗信试图建立这些诗体中最新的、最不受重视的元散曲的相对优势: 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学唐诗者,为其中律也;学宋词者,止依其字数而填之耳;学今之乐府,则不然。儒者每薄之,愚谓:迂阔庸腐之资无能也,非薄之也;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14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一系列新编韵书之一,与《切韵》(601)和《广韵》(1011)等早期著作不同,这些新文本大多不是针对科举考试的考生,而是针对有抱负的词曲作者。 与元代以前的韵书相比,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表现出相当大的韵部简化。周氏的《中原音韵》将《广韵》的两百多个韵部减到十九种,力求使音韵与现代北方方言保持一致。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虽然侧重于散曲创作,但也触及了戏剧方面的内容,即从剧本中选取了一些曲词,以说明曲词创作的一些精妙之处。 周氏《中原音韵》在明代的影响清楚地表明,早期戏剧作为文人体裁的经典化,至少离不开其中一个戏剧相对于小说所具有的普遍优势,即早期戏剧与散曲一起,可以被看作一种韵文体裁。 许多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对散曲和戏剧感兴趣的人物都注意到了韵律的必要性和挑战。明皇子朱权在其影响深远的《太和正音谱》(约1398)中,对所有的示例散曲和曲词的音调分布模式,都做了说明。 康海(1475—1541)是他那一代最早从事早期戏曲研究的文人之一,他指出,除了周德清关于如何作曲的技法外,他已从自己编辑的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删除了所有的补充材料;他保留这些技法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韵律基础。 同样,郎瑛(1487—约1566)在其著名的杂记《七修类稿》中转载了周氏作品中的曲谱及其名称,以帮助像他这样有抱负的作曲家学会如何区分它们。 到了16世纪中叶,随着文人对早期散曲和戏剧的兴趣开始增长,韵律成为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李开先所说: 其法备于《中原韵》,其人详于《录鬼簿》,其略载于《正音谱》。至于《务头》《琼林》《燕山》等集,与夫《天机余锦》《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乐府群玉》《群珠》等词,是皆韵之通用,而词之上选者也。 似乎是为了说明曲词的创作只不过是对韵律的巧妙运用,李开先在出版自己的百首简短散曲之前,附上了一张周德清的十九韵部表。 郎瑛和李开先之所以摘录《中原音韵》,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无法接触到周德清的重要作品,而这却是可悲的。 到了16世纪后期,杨一潮觉得有必要扩展《中原音韵》的流传范围。从杨一潮序言到他重印的《中原音韵》可以看出,周德清向上的传记流动性明显反映了曲韵知识日益增长的威望。在1515年的一部地方志中,周德清仅仅被列为“方士”,这一社会分类激怒了杨一潮,他认为周德清与元朝主要士大夫如虞集(1272—1348)和欧阳玄(1274—1358)的交往需要一个不同的社会群体。这样的呼吁最终被清初的一部地方志所重视,将周德清归入文人类别(文苑)。 到了17世纪早期,对早期曲传统的韵律实践的关注加强了,部分原因是新兴的南方散曲和戏剧形式中韵律规则的相对宽松。在最早的主要文人散曲集之一《南北宫词纪》(1604)中,编者陈所闻(1587—1626)称赞周德清的韵律精确,与同时代作者“以其声之相近者任意为韵”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注意到,他的选集排除了那些违反韵律模式的本来很好的曲作,如他所言,“倘可漫为,人人能之矣。” 在著名的杂录《万历野获编》(1606/1619)中,善于观察和八卦的沈德符(1578—1642)赞扬了早期曲作者的用韵实践。他从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中引用了一个与《西厢记》有关的具体例子,他注意到某些形式的内韵,六字三韵并不像其他类型的押韵那么难,但这种韵律技艺对所有元代作家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除《西厢记》外,沈德符还从散曲和三部浪漫杂剧中举出了几个例子,以支持他对前朝韵律成就的评点。 在《元曲选》中,臧懋循充分发挥了韵律的合法潜力,并摘录了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更重要的是,以唐宋科举中押韵片段的先例为依据,臧氏伪造了元代作家将创作戏剧作为元朝科举考试的一部分的说法,但这并非完全不可信。臧氏的假说不仅被广泛引用,而且后来的戏剧爱好者们都是从字面上理解它。在其《西厢记》修订本附录中,沈庞绥(?—1645)将三位元代名家周德清、关汉卿、王实甫列在“词学先贤姓氏”的标题下。在沈氏的名单上,关汉卿和王实甫是仅有的“元进士”身份的作家。 沈庞绥的名单之所以引人注目,有很多原因。首先,它表明了周德清日益上升的地位,以及与他的名字密不可分的韵律事业。其次,如果说周德清的名字最初主要是在散曲的创作背景下使用的,那么这种情况在17世纪开始发生变化;当时沈德符、臧懋循和沈庞绥等文人向他求助,以突出早期戏剧的韵律性。第三,关于周德清稀少的传记知识的各种分类,证明了早期曲传统的一个生产性(如果不是生成性)困境:这些作家有可识别的姓名,但没有牢固地扎根于一个已知的社会实体。创造一个集体的需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沈庞绥声称,这两位元代剧作家是顶尖的宫廷进士,尽管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朝代史《元史》——关于这些杰出人物的传记信息的标准储存库——对他们只字未提。也许没有哪一位元代作家的名字能比沈庞绥谎称关汉卿是两个进士中的一个更能深刻地突显这种阐释困境的丰富性。 传记的重要性 1620年左右,明末剧评家中最有学识的王骥德,也曾不无惊愕地感慨道:“胜国诸贤,盖气数一时之盛。王、关、马、白,皆大都人也,今求其乡,不能措一语矣。” 王骥德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追踪这些剧作家的生活细节。他几十年来多次从家乡绍兴到北京进行元杂剧的实地考察。最终,由于他在研究过程中所获寥寥,他发现自己面临着既不能令人满意地界定个人,也不能令人满意地界定集体的困境,从而遇到了作者身份认证模式的限制。 很少有元、明批评家像王骥德那样坦然承认自己对元作家的无知。元代和明初的批评家们认识到,早期散曲特别是戏剧的创作既不是完全匿名的,也不是名士的创作。他 《戏剧的诱惑》是一部从历史、文化和传播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西方汉学专著。从经典建构和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了元杂剧代表性的剧作在作者、不同时代的读者、历代书商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完善的过程。作者的研究视域新颖,资料翔实,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一种跨文化的视角,对中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