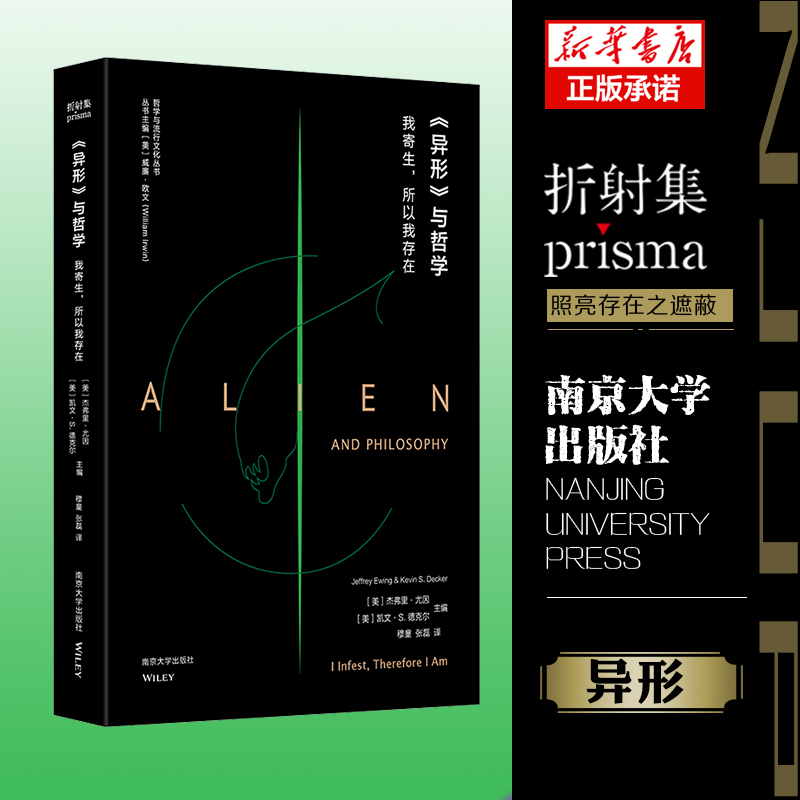
出版社: 南京大学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40.30
折扣购买: 哲学与流行文化丛书:《异形》与哲学
ISBN: 9787305256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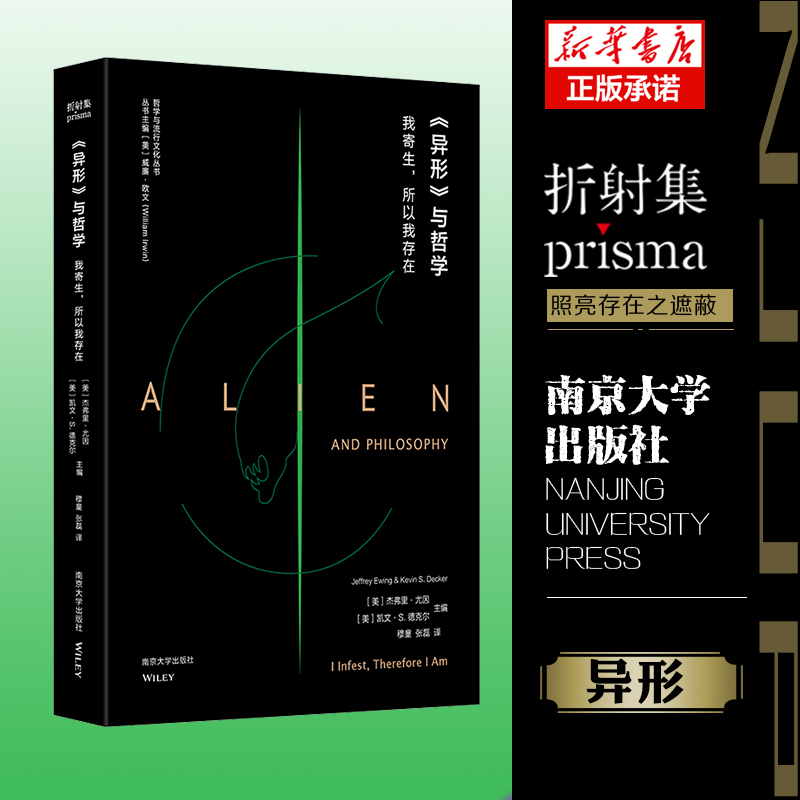
关于编者 杰弗里·尤因 在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他为即将出版的《恶魔学研究的哲学方法》(Philosophical Approaches to Demonology)贡献了一章的内容,有关《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星际迷航》(Star Trek)、魔鬼、《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科学怪人》(Frankenstein)的几卷也有他的参与。 凯文·S. 德克尔 东华盛顿大学(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哲学教授。他曾参与 “哲学与流行文化”系列丛书中多部图书的编辑和撰写工作,包括《终极〈星球大战〉与哲学》(The Ultimate Star Wars and Philosophy)、《终极〈星际迷航〉与哲学》(The Ultimate Star Trek and Philosophy)等。他还在斯波坎公共广播电台(Spokane Public Radio)播出的喜剧小品《负责人》(“Men in Charge”)中担任编剧、演员和制片。 威廉·欧文 宾夕法尼亚州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埃尔弗·A. 勒布朗杰出贡献教授(Herve A. LeBlanc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兼哲学系主任,著作包括《自由市场存在主义者》(The Free Market Existentialist)。1999年,欧文以《〈宋飞正传〉与哲学》(Seinfeld and Philosophy)一书开创了“哲学与流行文化”这一图书门类,近来受他指导出版的该类书籍包括《〈纸牌屋〉与哲学》(House of Cards and Philosophy)、《〈权力的游戏〉与哲学》(Game of Thrones and Philosophy)以及《终极〈星球大战〉与哲学》。 关于译者 穆童 南京师范大学翻译硕士,Python程序员。因为被异形化身的系统步步紧逼而异化,时常怀疑自己是一个仿生人。 张磊 出生于《异形3》上映当天,一定是雷普利转世,以后在星际旅行的时候,DON’T PANIC,相信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选自《“没人一无所求”:〈异形〉与 〈普罗米修斯〉中的仿生人作为洛克式人格的可能性》 克里斯·雷(Chris Lay) “人类”(human being)与哲学家和律师口中的“人格”(person)同一无异,这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或许理所应当。但《异形》系列作品多次质疑这种观点。对于头一回观赏《异形》的人来说,目睹帕克将仿生人阿什的头颈从肩膀处砸断,而阿什的躯体还在奋力还击的场景,其震撼程度不亚于目睹诺斯特罗莫(Nostromo)号飞船的餐厅正中,异形破胸者从凯恩的身体里爆裂而出。为什么?因为直到这一幕来临前,无论从外貌上还是行为上看,阿什都与人类人格(human person)毫无差异(只是有些情感淡漠)。在《异形2》中,合成人(synthetic)毕肖普拒绝被称作仿生人(android),他反驳道:“我偏爱‘人造人格’(artificial person)这个说法。”在《异形3》的片尾,当另一位自称毕肖普的角色出现在费奥里那161星(Fiorina 161)时,雷普利选择纵身坠入熊熊燃烧的熔炉,因为她无法确定这位“毕肖普”是不是维兰德汤谷公司为了捕获孕育在她体内的异形女王而派出的仿生人。对于自己身属某种不及人类之物的事实,来自《异形4》的另一位仿生人考尔(Annalee Call)拒不接受,同时深感厌恶。然而,雷普利的克隆体雷普利8号却似乎暗示过,考尔对他人的同情心压倒了她身为合成人的预定程序,让她得以超越“自动人”(auton)的身份。 上述案例出自异形系列的各部影片,在每个案例中,影片都要求我们自问这样两个问题: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看似是人类但生物学上并非人类的存在物,是否是可能的?“人类”和“人格”的区分从此开始有了意义。毕肖普想要得到同等于人类的对待(尽管他并非生物学上的人)。考尔虽然对自己的合成人本质感到羞耻并震惊,但雷普利8号认为其某些特征——例如她的自省能力——让她比她自认为的更“人类”,这种看法正确吗?如果某物拥有人类的某些重要特性(而又并非生物学上的人类),那么我们也许能将其与人类划入同一类别。就让我们把这种类别称为“人格”范畴吧。在哲学家看来,确定哪些事物属于、哪些事物不属于人格范畴,即所谓的人格性问题(question of personhood)——也就是说,是什么使某物被算作人格,以及非人类人格是否可能存在? 半前传性质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直接触及人格性的问题,程度也许超过了系列中的其他任何一部。对观者而言,仿生人大卫(David)至少看上去属于人格:我们见过他打篮球,见过他对镜梳妆时忧心自己的外表,还见过他表达对《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的喜爱。无疑,这似乎全都是货真价实的人格才会做的行为。然而,这部电影中的许多角色在对待大卫时,却好像认为他绝不可能属于人格。从低温睡眠(hypersleep)中醒来后,普罗米修斯号的船员观看了一段全息影像,其中,大卫的创造者彼得·维兰德(Peter Weyland)这样描述他的造物: 今天坐在各位身边的有一位先生,他的名字是大卫。他是我所能够拥有的最接近儿子的事物。不幸的是,他并非人类。他将永不衰老,永不死亡。然而,他也无法领会这两项非凡天赋的意义所在,因为做到这点所必需的是大卫永远不会有的一样东西:灵魂。 如果我们假设维兰德所言无误,假设大卫确实没有灵魂,那么,为什么灵魂的有无会影响到对大卫能否算作人的判断?如果“拥有灵魂”是成为人格的必要条件,并且,器械设备无论多么复杂,都不拥有灵魂,那么大卫绝对无法算作人格。此外,那些使我们认为大卫形似人格的重要特征,也许不必依附于灵魂的概念。既然如此,我们也许有充分的理由认定,说到底,大卫依然属于人格。 “唔,我猜那是因为我是人,而你是机器人” 要是维兰德对大卫的看法被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听到,恐怕他也会表示赞同。笛卡尔认为,人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实体所构成:肉体(由物理材料构成)和灵魂(由非物理材料构成)。其中,使我们成为人格的那些特性,是由灵魂赋予的。在《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当中,笛卡尔说道: 我确实认识到我存在,同时除了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之外,我又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东西必然属于我的本性或属于我的本质,所以我确实有把握断言我的本质就在于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或者就在于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就是思维。 笛卡尔这段话的意思是,思维是唯一一个他有十足把握的、从属于他的特征。那么,比如说,雷普利可以这样臆测:或许她并没有一副肉体,或者她并没有从水仙号(Narcissus,诺斯特罗莫号的救生舱)中安全获救。如果是这两种情况,那么此刻的她也许只是在做梦,或者做着一场噩梦——如果像《异形2》那样梦到破胸者的话。然而,她不能否认她既存在也在思维着的事实。实际上,她必须既存在又在思维着,才能在脑海中唤出梦境来!对笛卡尔来说,关键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思维特征是灵魂的必要组成,而灵魂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全部本质或本性就是思维的实体”。 当然了,人还有肉体,但肉体仅仅负责人类的生物特性。在笛卡尔看来,我们的物理特征与我们的基本本性(essential nature)——作为一种在思维的东西的本性——无关,因为肉体与思维的概念是完全可分的。思想并非物理的,但肉体是。因而二者在性质上全然不同。对笛卡尔来说,人的基本特征是思维特征,且思维特征是灵魂所独有的,这就意味着判断人格性的标准——其他事物或许可能与人类共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就等同于灵魂的特征。很多东西都有肉体,但只有灵魂(以及引申而言,有灵魂的东西)才能思维。因此,比如说,笛卡尔声称动物是一种“自动机”,其行为——尽管与人类相仿——可完全解释为“来源于动物身体部件的构造”动物没有思维的能力,因为它们没有灵魂。 我想,同样的论证可以延伸到大卫这样的仿生人身上。仿生人行事时仿佛人类人格——他们会语言沟通,表露情感,几乎方方面面都在外在符合人类。然而,他们行为却是严格机械性的。没有灵魂,因此大卫无法思维。没有思想——笛卡尔判断人格性的最基本的标准——因此大卫无法成为人格。他恰好缺少最重要的那些特征。这就是《普罗米修斯》中其他角色对待大卫的方式。在对普罗米修斯号船员讲话时,维兰德直白地指出了大卫缺少灵魂的事实。心情沮丧、半醉半醒的查理·霍洛维(Charlie Holloway)在打台球时,对大卫表现得盛气凌人,而同时又注意到大卫——没有情感的仿生人——无法像真正的人一样感受失落。即使总是乐观友善的伊丽莎白·肖(Elizabeth Shaw),也认为大卫不过是一台精巧的机械。影片末尾,当失去躯干的大卫好奇地询问,为何肖如此急切地想要追踪工程师的下落,并从人类的创造者那里寻找答案的时候,肖就事论事地断言道:“唔,我猜那是因为我是人,而你是机器人。”显然,在否定大卫的人格时,这些角色采纳了笛卡尔对人格的看法。大卫无法感受诸如失落的情感,也不能与渴望答案的人共情,因为他没有灵魂,而灵魂恰恰是这些能力的基础。 试读2 选自《来自群星的恐惧:<异形>作为洛夫克拉夫特式恐怖》 格雷格·利特曼(Greg Littmann) 《异形》是最好的科幻恐怖电影——我个人这样认为。六名太空运输船员与一只变换形态的掠食者,被困于一艘在无尽虚空中航行的小型飞船,没有什么故事比这更惊悚了。 《异形》如此惊悚是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原因之一就在于这部电影证实了洛夫克拉夫特有关优秀科幻恐怖作品由何组成的理论。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1890—1937)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美国恐怖作家,有些读者可能不知道,洛夫克拉夫特是最伟大的科幻恐怖作家,可能也是最伟大的恐怖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的多数故事都设定在同一个幻想宇宙中,同样的角色和异类种族在这些故事中反复出现。 洛夫克拉夫特从未直接提出一种有关科幻恐怖的哲学。但是,在随笔和信件中,他多次论及多种不同的风格,这些风格被他分别称作“星际小说”(interplanetary fiction)、“恐怖”(horror)、“超自然恐怖”(supernatural horror),以及“怪奇小说”(weird fiction)——最后一种风格涵盖甚广,既包括超自然的幻想也包括科幻。综合起来,一种有关科幻恐怖的哲学就浮出水面。 《异形》剧本的原作者丹·奥班农一生都仰慕洛夫克拉夫特,并且在创作《异形》和其他作品时受到其直接影响。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异形》与不计其数的洛夫克拉夫特小说有着相同的基本情节:一个人或者一支小队独自前往广袤无垠的不毛之地,探索奇怪神秘的古代遗迹,结果却与一个或多个异种怪物遭遇,最终常常只剩唯一的幸存者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但更重要的是,《异形》所取得的恐怖效果证实了洛夫克拉夫特的科幻恐怖哲学。这并不是说《异形》的制作团队在拍摄电影时心中一直挂念着洛夫克拉夫特,而是说影片恰好实现了洛氏所推崇的风格,并达到了让人心慌意乱的程度! 如何使人恐惧 洛夫克拉夫特认为最吓人的是神秘的东西。他写道:“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则来源于未知。”神秘之力可以扩展至地点,特别是未知的世界:“未知与危险联系紧密……于是,任何未知的世界便也成为邪恶与危险丛生的场所。” 但仅有神秘是不够的。他写道:“恐惧之物的本质是非自然。”在他看来,最惊悚的恐怖小说依赖于他称为“宇宙恐惧”(cosmic fear)的情感,这种情感来源于神秘而异质的实体对自然规则的破坏:“故事中必须存在着一种无法解释、源自人类理解之外的未知的恐惧,并以此创造出使人屏气凝息的恐怖气氛。而其中也必须具备严肃且充满恶兆的暗示,并以此不断冲击人类思维中最为可怖的构想之底线——对自然规则的违背与破坏。它们之所以能令人感到邪恶异常,全因为这些自然规律是人类面对来自混乱与深不可测之星空中的邪魔的唯一心理防线。” 《异形》中,诺斯特罗莫号到访的小行星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它与那艘外星飞船的残骸没什么两样。异形掠食者是完全神秘且无法预料的威胁。阿什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物种。”它施展各种诡计,让船员们不断地被它的这些能力搞得措手不及——比如从异形卵中直接跳出来攻击,让凯恩(他与异形原本的猎物在生物学上并无关联)瘫痪却不杀死他,用酸性血液保护自己,以爆出凯恩胸口的方式繁衍,还突然从小猫那么大成长为骇人的庞然大物。在营造恐怖氛围过程中制造神秘是很重要的,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设定于《异形》宇宙中的每一部电影都不如前作那么吓人,直到《普罗米修斯》完全没有出现之前常见的异形掠食者,才打破了这个诅咒。 异形的能力如此惊人,因为这些能力超出了我们地球人对动物理应具有的能力的认知。它们似乎是非自然的,因为自然中没有生物可以做到异形能做的事。把一群失控的狮子放在飞船上,也足以让诺斯特罗莫号的船员们处于同样的危险境地,但是影片的吓人程度就会大大降低。狮子确实致命,但它们毕竟不是……异类。 异形来袭也玩真的 洛夫克拉夫特能从同时代的怪奇小说作家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的尝试切合实际。关于太空飞船题材的小说,他写道:“难以置信的事件和状况组成了不同于其他故事元素的单独一类,而且其不能仅仅通过通常的叙事方式就令人信服。它们需要克服不信任感的障碍;这只能通过故事中每个其他阶段细致的真实感来实现。”他无意中重复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在《诗学》(Poetics)中对优秀的、严肃的戏剧提出的建议:“如果诗人编排了不可能发生之事,这固然是个过错;但是,要是这么做能实现诗艺的目的,即能使诗……产生更为惊人的效果,那么,这么做是对的。”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了讲述离奇的故事可以使用离奇的元素,但即使是离奇的故事也应该预设在现实中。就算是故事基于离奇的前提,“事件中不应有不合情理的内容”。 洛夫克拉夫特认为科幻小说中的真实感需要在科学准确性。关于太空飞船故事,他写道:“在表现机械、天文学以及旅行中其他方面的过程中,严格遵循科学事实绝对是有必要的。同样地,外星球也一定要符合科学。 《异形》不是在科学上很写实的电影。甚至连诺斯特罗莫号这样的星际飞船在科学上也很荒谬:诺斯特罗莫号飞得比光还快,这可是件不仅仅需要无限能源的壮举!但是,正如洛夫克拉夫特本应提出,而且被《异形》和他本人作品所证实的那样,有很多方法可以在并不符合科学实际的条件下,营造出必要的、有科学真实感的氛围。《异形》有很丰富的看上去“符合科学”的细节。当诺斯特罗莫号的船员考虑用双脚探索小行星时,阿什对环境做了一番分析:“这里有惰性的氮气、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晶体、甲烷……我正在分析微量元素。”研究过异形之后,他解释道:“它有一层蛋白多糖的外壳。它有一个有趣的习性,可以使细胞脱落,将其替换为极化硅酮,这可以让它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有更持久的抗性。”发明异形追踪器时,他可以说明工作原理。雷普利问“原理是什么?”时,他答道:“空气密度的微小变化。”最优美的是,在我们第一次看到诺斯特罗莫号的电脑被唤醒时,数字和单词一行行滑过绿色和蓝色的屏幕,屏幕发出的炫目光芒反射在一顶无人佩戴的头盔的面窗上这对观众毫不重要,但是可以让我们相信有人考虑到了所有现实情况,准备了繁复的技术报告。 技术因略有瑕疵而更显可信。尽管《异形》中诺斯特罗莫号的超光速航行违反了物理定律,但是影片考虑到太空之广袤、穿行之困难,让船员为了星际旅行而“冷冻”,使生命处于暂停状态,这营造了一种真实的氛围。冻结的过程并不令人愉悦,让兰伯特觉得寒冷,让凯恩觉得好像“死了”一样。操控飞船很辛苦,需要小心计算,就连在小行星着陆这样的事情都危险到足以导致飞船严重受损。工作场所狭小凌乱,有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显示器、信号灯、控制器以及奇怪的管道和线路。照明不足,口粮乏味。“回去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点好的。”凯恩一边用勺子舀起太空面条,一边笑着说道。甚至有船员在墙上紧挨着从杂志中间撕下来的色情插页的地方,贴了一张煎蛋的照片。 打造“异类” 《异形》中的异形掠食者就像诺斯特罗莫号本身一样,在科学上很荒诞。就算无视其以酸为血的荒诞特性,这个家伙有能力在不吃东西的情况下增加质量,还长到了一个大个头的人那么高。或许最让人难忘的是,它能够让人处于将死未死的瘫痪状态,并利用人类进行繁殖,尽管人类在生物学上与它本来的猎物毫无关联。从贴近现实的角度来看,抱脸虫应该松开凯恩,就像你会把适合蜘蛛、螃蟹或植物的食物吐出去一样,而这些生物与人类的关系比异形要近得多。然而,洛夫克拉夫特鼓励用异类生物打破我们人类愚蠢地认为是自然法则的东西。毕竟这才是“宇宙恐惧”的根源! 他的异类访客很乐于吞噬人类,比如《异星之彩》中有意识的彩色之物,它进入加德纳(Gardner)农场的水井之后,耗尽了加德纳一家的生命;再如《畏避之屋》中埋于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郊区一栋房屋地下的可以变形的巨物,它坑害了好几代人。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洛夫克拉夫特的异类生物要穿越空间时,它们会打破物理定律,其方式类似于让诺斯特罗莫号显得真实的方法。它们通常会拍打翅膀飞过“以太”(aether)。此外,它们还可以用意念致动(telekinesis)的方式行进,可以遥控人的身体,也可以用行走、掘地或游泳的方式跨越维度。 尽管如此,洛夫克拉夫特认为很有必要让异类生物的特异之处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它们一定要是真正的异类,而不是本质上与人类相似。他写道,异类生物“在外形、心智、情感和命名法等方面一定要明确地与人相异……一定要记住,异人生物要完全不同于人类的动机和思考方式。 诺斯特罗莫号的船员们发现的失事外星飞船正是如此,它一点都不像我们预期中太空飞船应有的样子。它有着奇怪的非对称的外形,没有明显的火箭推进装置。穿过幽暗狭长的入口后,探索小队发现他们进入了一个像是巨大有机体的内部空间,通道黝黑发亮,排列着肋状物。外星领航员的尸体不像是地球生物,看上去半生物半机械,身体好像与它倚靠的椅子连在一起。从其枯骨来看,它不仅不能离开座位,甚至连它的头部都不能转动,只能固定向前望向巨型的望远镜。根据《普罗米修斯》,我们看到的这具“尸体”实际上是一套包裹着一个人形生物的服装。尽管如此,仅从《异形》出发,影片让我们认为这位驾驶员很可能不是人类,因为它第一眼看上去就不像人类——这为我们提供了更具洛夫克拉夫特风格,也更令人恐慌的可能性。这具尸体暗示着,它们不仅在生理上与我们不同,在心理上也是不同的。在我们看来,这位一动不动的领航员过着一种特殊的悲惨生活。但它自己也许还觉得相当惬意。 至于异形掠食者,它有不止一个而是三个完全陌生的形态,用于其怪异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它外形的灵感来自瑞士艺术家H.R.吉格尔的《死灵之书》(Necronomicon)。吉格尔非常仰慕洛夫克拉夫特,“死灵之书”这一名字就取自洛夫克拉夫特的著作。在洛夫克拉夫特的虚构中,《死灵之书》是一本魔法手册,也是一座满载有关宇宙真正本质的可怕秘密的仓库。 在太空中,没人能听到你的尖叫 洛夫克拉夫特将人类躯体的渺小、寿命的短暂与宇宙的辽阔永恒做对比,从而突出了我们的脆弱。他为此所采用的最简单的技巧就是把人物放在广阔的背景之中。他写道:“世上最糟糕的处境,也许就是荒凉广阔空间中的孤独。”他的这一原则在《异形》中得到了证实:例如孤单地身处毫无生机的小行星上的探险小队;不得不在空旷的宇宙中对付异形的船员;特别是船员同伴逐个丧生,只剩自己一人与异形作战的雷普利。尽管诺斯特罗莫号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飞行,但在观众看来,它只是缓慢地在屏幕上漂浮,电影用这种方式体现出距离的遥远。 正如与宇宙相比我们很渺小一样,与时间相比,我们生命和文明也显得微不足道。洛夫克拉夫特写道:“时间在我的很多故事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这一元素总是作为宇宙中最宏大壮观且最可怖可惧的东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与时间抗争对我来说是所有人类的表达中最有力和最多产的主题。” 在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中,人类不可避免的灭亡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他的创作体系中,时间将会在我们的文明被外星人摧毁之际终结——而假如《异形》中公司保存活体异形样本的计划成功,那么我们也将迎来这样的结局。但是,洛夫克拉夫特不满足于让我们只被一种外星人摧毁。相反,当群星排列成正确的图案时,很多不同种类的外星人将会毫无限制地同时发动袭击,造成一场毁灭的狂欢。 洛夫克拉夫特同样描写过文明的外星物种被其他外星物种消灭的故事,这样的事件过后通常只会留下遗迹,就像《异形》中那艘废弃的星际飞船一样。地球曾经被植物一样的远古者所统治,但是他们被修格斯(shoggoths)所灭绝,而修格斯是他们创造出来充当奴隶的生物。同样,圆锥形的伊斯人(Yithians)也曾经统治地球,但是被来自更边远太空的水螅(polyps)所推翻,而长鼻的亚狄斯人(Yaddithians)——住得很远不会打扰到我们——注定要被体型巨大的巨噬蠕虫(dholes)所毁灭。 《异形》中威胁人类的掠食者,在两个主要的方面类似于洛夫克拉夫特笔下摧毁文明的外星人。一是,它不停变换形态,让船员们不断猜测接下来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恐怖。修格斯和水螅完全没有固定的形态,其习性近似阿米巴虫,可以变成它们想要变成的任何外形。而在地下人类文明昆扬的下方,生活着一种有意识的黑色黏液,它们总有一天会向上渗出,将昆扬文明抹除——这种生物同样也没有形态可言。毁灭性种族的无形性体现了生物演化混沌而漫无方向的特点。 二是,没有迹象表明《异形》中的异形掠食者具有同等于其猎物——无论是生化机器人还是人类——的智慧,并且它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也更低。它像动物一样狩猎、伏击,把牙齿当作武器。同样的,《北极星》(“Polaris”, 1918)中攻陷古老人类城市奥拉索尔(Olatho)的近似猿猴的生物,就是一群使用基本工具的野蛮物种;而巨噬蠕虫则没有意识;至于修格斯和水螅,它们没有掌握任何已知科技,智力上远逊于被它们抹除的那些物种。没有意识或者智力有限的物种的力量能够摧毁更高级的社会,这体现出演化的无意识以及这样一种认知:智力上的优越只是赢得物种竞赛的方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有效的。